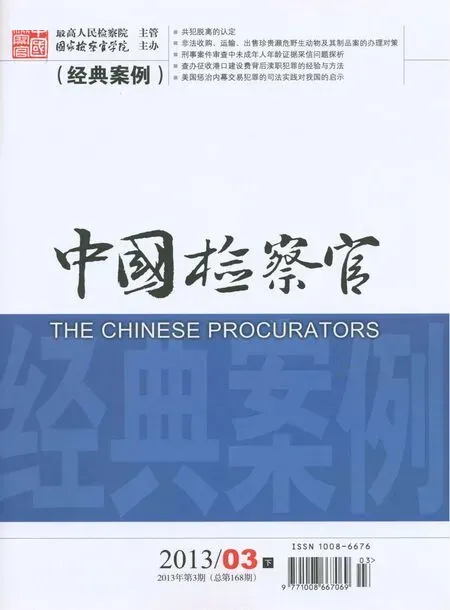共犯脱离的认定
文◎陈丽玲 诸葛旸
共犯脱离的认定
文◎陈丽玲*诸葛旸**
本文案例启示: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应按共犯脱离理论对其以犯罪中止论处。在共同犯罪既遂前的任何阶段都应允许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只要其表示并从心理、物理上隔断、撤回共同犯罪关联的加功行为,即使未能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不必承担共同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541002]
[基本案情]2011年9月,张某、李某、付某等人预谋对某金店进行抢劫。为避免被监控系统摄录,张某委托其女友刘某网购了CS蒙面头套三个,并告知其抢劫计划。刘某明知头套系抢劫所用,但仍用支付宝网购头套三个,并交给张某。期间,张某、李某、付某多次采点查看地形、制订研究抢劫计划和逃跑路线,刘某一直未予参与相关活动。2011年12月的一天,刘某在观看相关新闻报道后,对抢劫金店可能被判死刑的严重后果极其惧怕,遂向张某力陈利害关系,请求张某不再参与抢劫活动。张某未予听从,反而威胁刘某不要告发否则将伤害其家人。刘某即趁随父母外出经商之机,通过更换手机号、QQ号等方式中断与张某联系。2012年6月14日晚,张某、李某、付某戴上头套并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玩具仿真手枪、铁锤、电警棍等作案工具,闯入某金店内实施抢劫,在打死一名保安后共抢走金店内首饰价值约20万元。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审查起诉中,对刘某犯抢劫罪并无争议,但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明知张某等人预谋实施抢劫,但仍为其提供抢劫所用作案工具,虽然刘某因惧怕而退出犯罪并规劝张某不要参与,但张某等人仍最终实施了抢劫。根据我国刑法“一人着手,全体着手;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共同犯罪罚则,刘某的行为应构成抢劫既遂,但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可从轻、减轻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李某、付某共谋实施抢劫犯罪,刘某为犯罪提供作案工具,由于此阶段未着手实施犯罪,应属于犯罪预备。此时刘某主动放弃犯罪,应单独认定其为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故刘某的行为应构成抢劫中止。
二、共同犯罪的法理释义
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是否恪守通说追求刑罚形式正义,还是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共犯脱离理论强调刑罚实质正义的价值合理性之争。按照前一种观点,对刘某以抢劫共犯既遂论处,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主流观点,但从情理而言,刘某仅在犯罪预备阶段提供了头套,其本人未参与任何其它犯罪活动,且在着手实施前自动放弃犯罪,并试图规劝他人放弃犯罪,因受胁迫未能阻止犯罪的发生。在本案造成一人死亡和价值20万元金饰被抢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第263条之规定,刘某被认定为从犯仍可能被判十年左右的有期徒刑,这一刑罚结果明显与其行为不存在合理比例性,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而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在促使刑罚节俭的同时突出了刑罚功利的价值取向,符合刑法的实质正义观。有学者指出“在具体案件适用时,认定是否应该成立共犯,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根据实质的解释,进行出罪,其根据则是实质的危害性之大小”。[1]与此相对应的,起源于日本的共犯脱离理论对此案正确认定提供了一种新的注解,对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共犯脱离,也称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共同犯罪人从共同犯罪关系中退出,但其他共同犯罪人仍继续实施犯罪,并达到既遂的情形。[2]这一理论最早由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提出,主要是弥补日本刑法对于“犯罪中止失败行为”的刑事责任处遇空白,解决了“虽为中止做出了努力,但没能有效防止结果发生的共犯者的刑事责任问题”。[3]但他将认定共犯脱离的时空节点仅限于共同犯罪着手实施以后而备受争议,其后日本西田典之教授、大谷实教授对该理论提出了不同见解,使之更为完善,其它国家也相继对共犯脱离予以不同程度的立法界定,如英国刑法的“共犯退出”规定。
相较于传统的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共担原则,共犯脱离在主动放弃犯罪的部分共同犯罪人与其他执意完成犯罪的共同犯罪人之间实现了有效切离,有效地减轻犯罪对法益的侵害。[4]其主要价值体现为,一是完善了犯罪中止理论,避免因中止犯条件过于严格而带来的实践困境。传统犯罪中止的构成必须满足时空性、自动性、彻底性和有效性四个要件,而部分共同犯罪人中止犯罪往往只符合前三个特征,难以实现有效阻止犯罪的有效性,并由此承担共同犯罪既遂的责任,不免过于苛责严峻,也有失罪刑均衡。
二是符合刑罚人道化要求和刑罚比例性原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正,就是合比例;不公正,就是破坏比例”,[5]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匹配,在均衡法益中体现法律的理性与公平。共犯脱离理论恰恰关注了个别犯罪人主动放弃共同犯罪的真诚努力,从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综合考虑其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从而更为客观、正当,避免了法律沦为教条。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刑法理论,符合法治进步的时代要求。社会转型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国刑罚目的由过于注重惩罚犯罪向惩防相结合的功能转变,民主法治的要旨不仅通过法律控制国家,更重要是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成为所有人行为的最高规范。共犯脱离理论有利于鼓励其他更多的共同犯罪人由“恶”向“善”,既努力实现了刑罚个别化,又在共犯既遂与共犯中止之间填补真空,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难题,也推动我国刑法体系更加充实完善。
关于何种条件下方能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共犯脱离,主要应考究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时空条件
共犯脱离成立于共同犯罪实行行为之前,或是限于实行行为着手以后,亦存在于共同犯罪既遂前的任何阶段,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对于犯罪预备行为原则上视为是非实行行为而不予处罚,这也是共犯脱离理论最初之所以主张只存在于着手实施之后阶段的主要法律背景。而我国刑法对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尚未着手实行的犯罪预备行为也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因此将共犯脱离的时空阶段限于着手实施之后,既与我国刑法规定不相对应,也对犯罪预备阶段的共犯脱离行为认定形成新的法律空档。但如将共犯脱离止于着手实施之前,又显得过于狭窄,且混淆了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关系的解除的区别。简言之,如以着手实施犯罪后共犯关系不可脱离为论点,那么必然导致着手实施犯罪前是否有共犯关系的逻辑疑惑。因为既然着手实施后才有共犯关系,那么理应着手前就不存在共犯关系,则共犯关系的脱离无疑成为伪命题,且共犯脱离理论的关键点不是评价其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是对其刑事责任作出客观恰当的评价。精准地说,共犯关系的脱离不可能存在于共同犯罪结果发生以后,但可能出现在犯罪既遂以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毕竟犯罪既遂并不当然意味着出现犯罪结果,如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因此,笔者认为,以犯罪既遂为标志点,只要既遂之前主动脱离共同犯罪的行为都应视为共犯脱离,反之既遂之后则当然不予成立。至于部分犯罪人在犯罪既遂后主动减少法益侵害的情形,如绑架案中的部分共同犯罪人将被害人释放等,只能作为量刑的情节考虑,其犯罪形态仍定位在既遂状态。本案中,刘某只是在张某、李某、付某预谋抢劫的预备阶段提供了作案用头套的帮助行为,并未参与张某等人着手实施抢劫的犯罪活动,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共犯脱离。
(二)主观条件
我国刑法对犯罪中止的认定强调必须具备自动性,即中止行为是犯罪人在客观上可以继续犯罪和实现犯罪目的的情况下,自动作出不继续实施犯罪或不追求犯罪结果的决意,且这种选择是完全、彻底和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至于决意产生的动机,是出于对法律的恐惧还是由于生理的不适或心理的激烈斗争致幡然悔悟抑或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在所不问。共犯脱离实际上是犯罪中止的特殊形态,因此构成共犯脱离也必须在主观要件上具备“自动性”,即必须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主动放弃犯罪,而非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对于何为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犯罪,学界有不同主张,但笔者认为,犯罪中止制度的旨趣在于对中止犯罪的迷途知返者予以减轻处罚的奖赏,鼓励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前放弃犯罪,从而为部分主动放弃犯罪的共同犯罪人搭设了一座理性回归社会的“黄金桥”。在此语境下,只要行为人“能达而不欲”继而主动、自动地放弃犯罪,即可认为是自愿放弃犯罪,至于其丧失犯意的主观动机如何,既难以查究也并无实意,与是否成立共犯脱离毫无关联。本案中,刘某出于法律威严的震慑而主动退出共同犯罪,在主观性上具备了放弃犯罪的自愿性。
(三)客观条件
是否成立共犯的脱离,必须对刑法意义上“脱离行为”进行界定,即客观上行为人的脱离行为要满足“彻底性”。基于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人在主观上有共同故意的关联性,客观上共同实施了犯罪加功的行为,因此构成共犯的脱离就当然应向其他共同犯罪人明示其退出犯罪以切断主观故意的关联依托,同时应通过努力撤回或削减自己的犯罪加功行为,从而尽可能消除或降低脱离前其行为对共同犯罪继续实施或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因果性。如果说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是心理的脱离,那么其客观上的脱离即是物理的脱离。对于脱离的标准,学者分为绝对意义上的脱离和相对意义上的脱离以及积极的脱离与消极的脱离。笔者认为,按照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对其脱离认定采取不同的评断标准更为理性,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实事求是的刑罚理念,如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教唆犯与胁从犯、从犯的脱离标准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对于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组织、支配地位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由于其犯罪加功行为和主观犯意对共同犯罪的实施起到强化领导作用,因此他不仅要明确向其他共犯表示自己放弃犯罪的意思,而且应通过积极的努力切断自己先前加功行为与犯罪发生的因果关系。对于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胁迫或仅提供铺助作用的从犯而言,相对于正犯的主观恶性和犯罪加功强度,其只要消极地以言语或举动传达或表达自己放弃犯罪的意思表示或单方面撤回或消除、降低自己的加功行为,也同样成立共犯脱离。同时,共同犯罪着手实施以后的脱离相对于犯罪预备阶段的脱离在条件上应更为严格,即均应以明示的方式表明。关于何为积极地真挚的努力,笔者认为这事实上涉及到对法律行为的道德评价问题,依据社会公众的一般评判标准即可,但必须是有积极的作为,如向司法当局预警、规劝其他犯罪人、通知被害人等,形式不一而论。至于行为人主动放弃犯罪的脱离行为是否应被其他共同犯罪人认可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必苛求。毕竟犯罪是一种反社会行为,面临着刑罚的严厉处罚以致有失去生命的风险,共同犯罪人正是在相互心理支撑、补强和信托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关联,并通过相互的分工协作配合完成整个犯罪活动。一旦其中有人退出,对于共同犯罪的其他行为人而言将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冲击,也影响了共同犯罪行为的延续,因此征得其他共同犯罪人认可理解其脱离行为不太现实,也未免强人所难。事实上,只要这种脱离行为为其余共同犯罪行为人“认识”到或者“察觉”即可。本案中,刘某因惧怕而规劝男友张某不再参与抢劫活动,在受到威胁后即中断与张某联系的行为,既有积极地表达放弃犯罪的意思,也有试图阻止共同犯罪的认真努力,依其帮助犯的身份这种脱离表示和行为应予认定成立共犯脱离。
三、本案解析
综上所述,刘某主观上主动放弃犯罪,至案发时间已达六个月之久,在其中断与其他共犯人联系后,甚至不知道抢劫是否发生、后果如何,也未参与分赃或获得其他利益。且其在共同犯罪中处于帮助犯的地位,在受法律震慑后还规劝其他犯罪人放弃犯罪,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只应对脱离之前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从客观行为上看,刘某通过网购为共同犯罪提供了头套的犯罪工具,与持械抢劫的严重暴力性和危害性相比,其帮助行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对犯罪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较弱,且其系在犯罪预备阶段即抢劫犯罪着手实施之前主动放弃犯罪,故认定为抢劫中止。至于作为公民有义务向司法当局告发犯罪并尽力阻止犯罪,对于刘某一个弱女子且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这样的期望值不免过高。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在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与告发和阻止犯罪的两难之间,刘某选择断离与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联系,并采取规劝的方式试图影响犯罪进程已足,符合刑罚的目的。
注释:
[1]刘艳红:《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2]刘雪梅:《英日刑法理论中共犯关系脱离的要件之比较》,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2期。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4]冯卫亚:《共犯关系脱离之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5期。
[5][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周汉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