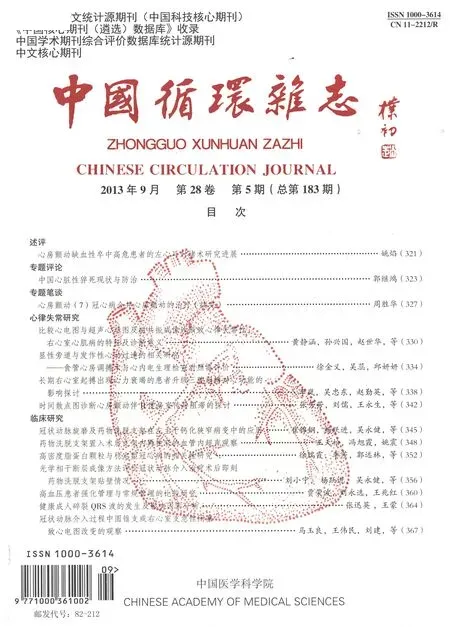谈医学生涯中部分难忘的病例(二十五)
陈在嘉
谈医学生涯中部分难忘的病例(二十五)
陈在嘉
病例61 多动脉炎中西医结合治疗
患者男性,21岁,农民。发现高血压4年,气短浮肿1年余。患者1963年查体发现高血压180/100 mmHg(1 mmHg=0.133 kPa),伴有头痛,眼花,未经特殊诊治,仍参加挖河重体力劳动,一年多来上述症状加重,并出现尿少、色红,全身浮肿,心悸,气短,慢步行走也有症状。在当地医院予用洋地黄制剂和降压药两月余,血压不降,症状依旧,且出现左足第4、5趾尖发红疼痛,皮肤紫红色花纹,继以上两趾发黑,疼痛加重,彻夜难眠,遂于1967-01-13转来我院。
患者以往健康,无经常咽痛史,家族中无类似疾病。
入院查体:发育正常,营养中等,自由体位,表情痛苦,全身皮肤有散在紫红色花纹,无出血点,表浅淋巴结无明显肿大,咽无充血,两侧颈静脉充盈,两肺清晰。心浊音界向左扩大,心律齐,心率80次/分,心尖有2级吹风性收缩期杂音,A2>P2,血压左上肢180/120 mmHg,右上肢200/120 mmHg,腹平软,肝在右肋下4.5 cm,剑突下10 cm,质中等硬度,有压痛,脾未及。脊柱无畸形。两下肢有明显可陷性水肿。两足背动脉搏动尚正常,两桡动脉搏动良好,膝反射正常,无病理反射。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126 g/L,红细胞3.64×1012/L,白细胞10.56×109/L,中性粒细胞86%,淋巴细胞11%,单核细胞3%。血沉5 mm/h,住院过程曾上升至41 mm/h。尿常规,蛋白(++~+++),镜检白细胞0~2、红细胞0~2、颗粒管型0~2 /HP。便常规(-),潜血(+)。丙酮酸转氨酶573 IU/L,凝血酶原时间17.6 s,活动度42.7%。血非蛋白氮28.1 mmol/L,二氧化碳结合力36.5 mmol/L,酚红排泄试验第一小时18%,第二小时16%,红斑狼疮细胞(-),血胆固醇4.52 mmol/L,24 h尿中3-甲氧基-4-羟基扁桃酸(VMA)1.5 μg/mg肌酐。眼底:高血压视网膜动脉狭窄。心电图:左心室肥厚劳累。
入院时体温正常,以后偶有低热,心、肝、肾功能不正常,血压高,多脏器和两足末梢动脉受累。住院中发现嘴角发歪,说话不利落,左手握力较差,神经系统亦受影响,皮肤上有紫红色花纹,考虑多动脉类可能性较大。应用利血平,双氢克尿噻及洋地黄制剂,青、链霉素抗感染,1月16日开始用去氢考地松20 mg/日,后加量至30 mg/日,并加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和烟草酸静脉滴注。患者最突出症状是左足趾剧痛难忍,大汗淋漓,肢端厥冷,不得不用杜冷丁、安侬痛等强镇痛剂,2月3日右足趾也出现疼痛。外科会诊左足节4、5趾干性坏死,侵入趾间第二趾节,跖面有小点状坏死,做腰交感神经封闭,对疼痛不见效。请院外骨科会诊认为左足疼痛剧烈,足趾功能已丧失,如不切除可能继发感染,病变蔓延越广,自左裸关节以下截肢有适应证,但术后可能出现幻肢痛,右足趾疼痛加重,伤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对截肢正犹豫不决,3~4日后发现左足趾已化脓,2月14日将左足第4趾近趾骨远端切开排出较多坏死组织及稠脓液。细菌培养有大肠杆菌生长,换用合霉素及链霉素抗感染。次日请广安门医院朱仁康老中医会诊,予用补气、活血通络清热解毒的方剂(当归、参三七、炙乳没、香附、黄芪、赤芍、桃仁、红花、干地龙、银花、淮牛夕、外加醒消丸),三日后足趾疼痛已明显减轻,除换药时已不需用杜冷丁等镇痛药。2月21日即排脓及服中药1周后两足变红润,循环改善,已完全不需用杜冷丁等镇痛药,血压下降至140/60 mmHg。中药再加服西黄丸。3月3日患者已能用足跟着地上厕所,同时肝肾功能尿常规亦恢复正常,说明除两足外其他脏器动脉炎亦好转,患者精神食欲好,无不适症状。2月20日将去氢考地松30 mg/d减至20 mg/d,1周后减至7.5 mg/d,缓慢减量至3月18日全停。同日低分子右旋糖酐及烟草酸亦停用,中药继续服用。3月底左足第4、5趾已脱落。随后创口完全愈合。心率减低至60次/分,血压160~170/60~70 mmHg,特别是舒张压明显降低。皮肤上花纹仅隐约可见,嘴歪,说话不利落均恢复。肝在右肋下已触不到。剑突下8~9 cm已无压痛,下肢不肿。血沉38 mm/h,尚未正常,与1967-05-13带降压药及中药方出院,患者未因复发再来院。
患者病变涉及多脏器,神经系统及双足,足趾剧痛,使患者最难忍受,几乎要考虑截肢,足趾疼痛最明显减轻是切开排脓清除坏死组织并开始服用中药,两足皮肤循环好转,但同时其他脏器功能亦好转,就不好单用局部手术切开解释。患者已用去氢考地松,低分子右旋糖酐、烟草酸数周,多处血管等改善可能与中药,外科共同治疗综合所起的作用有关。看来治疗血管炎是根本,截肢不可取。
多动脉炎过去亦称为结节性多动脉类或结节性周围动脉炎,是累及中、小动脉为主的坏死性炎症,症状根据累及范围而异,是一种少见病。大多数中年发病,但也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病因尚不完全明瞭,一些报道认为是抗体、抗原相互作用的结果。病毒可能是主要致病因素,乙型肝类病毒常与本病并存。后又发现人类免疫缺陷与本病一种亚型有关,此外巨细胞病毒、甲型肝类病毒也可能有一定关系。现今治疗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活动期加用免疫抑制剂如环磷酰胺等。本例是许多年前治疗的病例,回想起来中西医结合治疗仍可借鉴。
100037 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心血管病研究所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冠心病诊治中心
陈在嘉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冠心病临床研究 Email:chenzaijia120@126.com
R541.4
C
1000-3614(2013)05-0388-02
10.3969/j.issn.1000-3614.2013.05.019
2013-02-27)
(编辑:常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