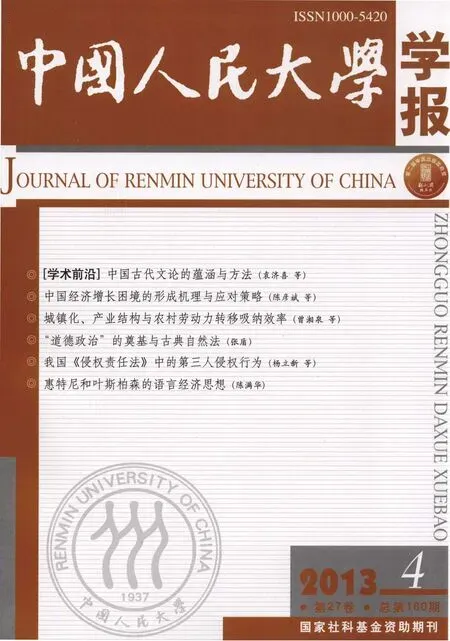如何知人,怎样逆志——对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再
张海明
由孟子提出的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作为一种传统解读诗歌或文学批评方法,其意蕴本不难理解,但在历经汉儒、宋儒、清儒乃至近人、今人的注解发挥后,反倒分歧迭出、不易求得共识了。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论者对孟子关键词的理解各执一端,不如说是文学自身发展所导致的鉴赏、批评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关西方文学理论的介入,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前视野,使得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先见加诸孟子,背离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提出的具体语境。因此,无论是肯定还是质疑该方法,其所针对者已不全是孟子之言,而是或多或少地渗入了后人的理解。
一
《孟子·万章上》记: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1](P637-638)
对于孟子这段文字中几个关键术语——文、辞、志之具体含义及相互关系,周裕锴先生有很好的解释。他以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为据并结合钱钟书 《管锥编》所论,认为: “‘文’就是‘文字’,也就是 ‘词’(word);‘辞’就是 ‘篇章’(text),而 ‘志’就是诗人的志向,即创作意图(intention)。由于 ‘词’ (即 ‘文’)是‘意内而言外’,因此 ‘文’有其意义,同理,由‘文’积成的 ‘辞’也有其意义。这样,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应是,由文字之义组成篇章之义,由篇章之义显示作者之志。”至于 “以意逆志”之 “意”,则从赵岐所注为说诗者的 “己意”。据此,孟子 “故说诗者”一段文字当做如下解:“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片段的意义而妨害对篇章整体的意义的理解,不要因为篇章整体的言词义而妨害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理解;应该采用设身处地的测度方法来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才能获得 《诗》的本义。”[2]
这的确是一个合乎 “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基本规则”的解释,尤其是以词释 “文”,以篇章释“辞”,以创作意图释 “志”,用心颇为细密。不过,仍有可斟酌者。如以篇章释 “辞”不误,但篇章或文本本兼指作品之全文或部分,若如周文所言,“辞”谓 “篇章整体的意义”亦即整首诗的意义,那么岂不是与孟子所举 《云汉》一例相抵触?(孟子明言:“如以辞而已矣”)同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咸丘蒙之失究竟是 “以文害辞”还是 “以辞害志”?再如称 “由篇章之义显示作者之志”不误,但如果 “辞”本身即篇章 (整体)之义, “志”即诗人之创作意图,又怎会有 “以辞害志”之虞?显然,依周裕锴先生之见,诗人之创作意图与篇章之义二者并不完全对应,甚至可能存在某种 “错位”,而这正是导致 “以辞害志”的原因所在。但事实上,在孟子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所谓诗作之题旨与诗人之创作意图只是存在形态不同,其内涵并无二致,如后来 《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孟子所言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乃是对《北山》一诗题旨亦即诗人之志的说明,“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两句亦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错位”或“脱节”问题。①《诗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其对 《北山》诗旨的解释综合了孟子之说。
所以,对于周裕锴先生以 “篇章”释 “辞”,似还有必要加以限定,即篇章非谓全文,而实指“章节”,以至于 “段落”,始与孟子所言相符。周文所引焦循 《孟子正义》正作此理解: “辞则孟子已明指 ‘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为辞,即‘普天之下’四句为辞,此是诗人所歌咏之辞已成篇章者也。”相应地,“不以辞害志”之 “志”,固然可以解释为诗人之创作意图,同时也可以说就是诗作之题旨。
由此再来看 “以意逆志”,也就不易再生歧义。既然诗人之创作意图与诗作之题旨原属一事,则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的说法便不能成立,所谓 “以意逆志”之 “意”,当然只可能是说诗者之心意。至于 “逆志”之 “逆”,论者多从 《说文》训之为 “迎”,其实逆字在此更宜解作“反向”、“倒向”,或者是 “回溯”。若以诗人赋诗言志之过程为正向,则读者由诗求志之过程就为反向,如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 “沿波讨源”之喻,正可为 “逆”字作一注脚。值得注意的还有刘勰接下来的一段话: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诸笔端,理将焉匿?”刘勰显然相信,作品之底蕴、作者之用心绝非不可体察,关键在于读者自身的 “识照”如何;而孟子同样认为,只要说诗者能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在此前提下 “以意逆志”,诗作之题旨便不难领会。
可见,当孟子就咸丘蒙的问题提出正确的说诗方法时,其含义本不难索解,也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但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迁,一方面是表现技巧渐趋丰富而导致了作品构成的复杂化,另一方面则是读者与作者的时间距离越来越远,客观上增大了说诗者 “以意逆志”的难度,同时也对 “沿波讨源”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大概唐宋以降,古典诗歌的解读渐入难言之域,故司空图有 “辨味”之说,严羽称诗之佳处如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至明人谢榛乃谓 “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镜花水月,勿泥其迹可也”;清人王夫之更主张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在此情势之下,“以意逆志”中的 “意”、 “逆”二字自然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我们从朱熹以 “迎”释“逆”,一再强调 “以意逆志”并非 “以意捉志”的话语中②《朱子语类》卷五十八云:“‘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又曰:‘谓如等人来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须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将意去捉志也。’”参见黎清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1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不难看出他对仅凭己意解诗倾向的警觉和不满;而清人吴淇以 “意”属古人,谓“以意逆志”乃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①参见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 《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36~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同样是有见于以一己之意解诗易犯主观臆测之病。
也正因为如此,孟子本用以论述 “尚友”之道的“知人论世”说便被整合到 “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之中。清人顾镇认为:“以意逆志”当以“知人论世”为前提,“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预忧后世将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说以防之。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也。”[3](P639-640)近人王国维也说:“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4](P169)显然,在吴淇、王国维二人看来,将“知人论世”作为 “以意逆志”的必要补充,的确有助于正确理解诗作的意蕴,能够有效地避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弊端。
通过以上简要辨析可知,孟子之 “以意逆志”说实为一据于文本以解读诗歌的方法,其大要则在于通观全篇以求得诗之本义。这里有必要澄清两点:一是孟子提出 “以意逆志”是否出于反对 “断章取义”的目的。不错,就方法而言,“断章取义”与孟子批评的 “以文害辞”、 “以辞害志”类同,但孟子针对的只是 “说诗”中的断章取义,并不包括 “引诗”中的断章取义,那种认为孟子引诗仍不免于断章取义而咎其未能身体力行的观点恐难成立。二是孟子所说 “以意逆志”是否有意突出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肯定 “以意逆志”之 “意”属读者,但并不认为孟子主张对诗之本义的领会须着意 “钩考”或用心“测度”②“以意逆志”句中 “逆”既为动词,则 “意”只可能是名词,且 “以意”本为介宾结构,故强解为 “测度”、“钩考”,虽有据可依,但是置其特定语境于不顾也。,无论是将 “逆”解作 “迎取”还是“回溯”,读者(说诗者)要做的只是不拘泥于文辞,着眼全篇,则诗之题旨自然呈现于前。他甚至不必 “知人论世”,更不必证以史实,诗歌文本自身就提供了现成的答案。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也。”赵岐所注简单明了,而最近孟子原意。
二
当然,孟子所言仍留有若干空白或未定点。比如说关于“意”之归属。有论者认为:“从孟子原话的文气看,‘说诗者’一气贯下,‘以意逆志’的主语承前省,当然是 ‘说诗者’了。 ‘以意逆志’是‘说诗者’的‘以意逆志’,亦即读者以自己的意思、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认识去探求作者的旨趣。”[5]谓“以意逆志”四字主语承前省,当为“说诗者”不误,但若云此句意谓说诗者以作品之意探求作者之志,于语法亦无不通。以今人的理解,作品之意与作者之志不得混同为一,而作品之意与作者之志既为二事,则说诗者凭借作品之意推求作者之志又有何不可。再比如说,“志”在心抑或在文的问题。孟子并未明言说诗者所逆之志究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还是其在诗作中的呈现,虽然我们认定二者在先秦实为同一事物之不同存在方式,但后人对之做出两种解释却并非全凭己意。如吴淇所言: “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将意与志的关系理解为车舆与所载之物,这确实有违孟子本意,却不能说与孟子表述过于笼统毫无关联。还可一提的是对“逆”字的训释。 “逆”作“迎”解在先秦是通行的用法,然原地等候是迎,上前亦是迎,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孟子本意究竟为何呢?若依朱熹之说,“逆者,等待之谓也”[6](P180),是主张读者勿受己见之干扰;而今人释 “逆”为 “推测”、 “推求”③《孟子译注》将 “以意逆志”译作 “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参见杨伯峻编著、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修订:《孟子译注》,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丁秀菊认为:“就接受者对作者、作品的了解、把握而言,他绝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主动地探求”,故 “逆”字 “可用现代语词 ‘推求’对应之”。参见丁秀菊:《孟子 “以意逆志”的语义学阐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载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4)。,则是强调读者对诗作题旨的认知有主动性且必然受制于己见的一面。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理解无疑都可以由孟子原文导出,我们又该根据什么来判定孰短孰长呢?
如果说这些空白或未定点的存在已经给后人对孟子之说做出不同解释预留了空间,那么后人,尤其是今人所据之立场及视域更使得孟子之说难有定解,而且所作评判也更趋多样。
朱自清 《诗言志辨》所论即为一例。一方面,朱自清沿袭汉儒旧说,认为孟子所言 “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孟子虽然还不免用断章的方法说诗,但所重却在全篇的说解,却在就诗说诗,看他论 《北山》、 《小弁》、《凯风》诸篇可见。他用的便是 ‘以意逆志’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于后人牵合 “知人论世”与 “以意逆志”的做法,朱自清则不以为然:“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 ‘读书’与 ‘知认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 ‘尚友’的道理。后世误将 ‘知人论世’与 ‘颂诗读书’牵合,将 ‘以意逆志’看作 ‘以诗合意’,于是乎穿凿傅会,以诗证史。 《诗序》就是如此写成的。”[7](P24)虽然前人对汉儒解诗也多有辩驳,但朱自清的批评却是建立在现代文学观念之上的,恰如朱自清自己所说: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 ‘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 ‘文学’的意念。”[8](P3)而新文学观念最突出之点,就在于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强调诗史有别,朱自清之所以反对以诗释史,以史证诗,根源即在于此。还有来自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影响。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理论风头正劲,而其重要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相继来华讲学,遂对当时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自清在 《诗多义举例》一文中便称赞燕卜荪的《多义七式》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9](P181)。所以,朱自清虽批评汉儒“以诗合意”,却并不否认诗歌可有多解;而且他认同瑞恰兹的语义学理论,将语义分析视为理解诗歌的有效手段。①参见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载 《文学遗产》,1991 (1),该文后用作 《朱自清说诗》一书代序。朱自清 《诗言志辨》论 “比兴”一节道:“如何以己之意 ‘钩考’诗人之志呢?赵氏举出 ‘人情不远’之说,是很好的。但还得加一句,逆志必得靠文辞。文辞就是字句。 ‘以文害辞’ ‘以辞害志’,固然不成,但离开字句而猜测全篇的意义也是不成的。”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77页,上海,开明书店,1947。这里强调依凭文辞以逆志的观点,与新批评派重视文本的主张正相吻合。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的传入,学界对于孟子 “以意逆志”说的解读较之先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伽达默尔对传统阐释学以探求作者原意为旨归做法的彻底否定,以及他所提出的 “视域融合”的理解途径,无疑将诠释主体的重要性摆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而姚斯等人区分 “第一文本”、“第二文本”,主张文无定解,更是突出了阅读过程中读者参与的不可或缺。受此影响,再加上此前新批评理论提出的 “意图谬误”说,当人们再重新审视孟子的说诗方法时,关注的重心便不再是怎样避免 “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弊病,而是作者之 “志”究竟是否可 “逆”,以及读者又该怎样以己意去解读作品。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在论及 “以意逆志”时就特别指出:孟子所说之 “意”,“指的是读者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包括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的统一,而且在不同的读者那里是各各不同的”。“所谓 ‘以意逆志’,就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以意逆志)是不能离开欣赏者主观方面的想象、体验、理解等活动的,不能不受欣赏者的 ‘意’的制约”[10](P194)。虽然他们并未提到阐释学或接受美学理论,但其反复申说的正与阐释学、接受美学的主张相符。又如顾易生、蒋凡1988 年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释 “以意逆志”之 “意”,一方面承认,以 “意”属读者和以 “意”属作者作品两种解释 “各有所见,未容轩轾”,另一方面又表示:“评说诗歌,自应首先探索作家作品的志意,也总受到评说者本人立场观点方法的制约,因而往往是作家作品之意与评者自己之意的结合。”[11](P117)显然,认为孟子所说“以意逆志”之 “意”既包含了 “作家作品之意”,同时又包含了 “评者自己之意”,并非孟子原意,而毋宁说是在阐释学、接受美学影响语境下的一种现代解读。值得注意的还有该书对赵岐《孟子题辞》中一段文字的理解。赵岐之言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出 《孟子》一书的特点在于 “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二是认为孟子 “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孟子》一书的解读:“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这实际上是说,欲解孟子之文,必先通孟子之意,通其意然后始得解其文,恰与钱钟书说 “阐释之循环”之 “探本以穷末”相合。①钱钟书 《管锥编》道:“乾嘉 ‘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须复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 (“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 (“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 (“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 ‘阐释之循环’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如果说孟子之据文辞 “以意逆志”为 “推末以至本”,则赵岐 《孟子题辞》所言便是 “探本以穷末”。顾易生、蒋凡二位失察,误以此 “意”释 “以意逆志”之 “意”,而不晓此“意”乃 “全书之指”亦即作者之志。若究其原因,恐亦与今人某种 “先见”的影响不无关系。
总之,在现代西方文论影响的大视野下,学界对 “意”的解释渐趋一致,基本上倾向于将其解释为说诗者或读者之心智活动,即便是以“意”为作品之意者,也不忘说明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前提,今人对于孟子“以意逆志”说的评价也就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从积极一面而言, “以意逆志”说肯定了作者的主体地位,肯定了把握作者之志,得其用心的可能,肯定了作者及其志的客观性、社会性因素,为文本阐释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途径 (“知人论世”);而从消极一面来看, “以意逆志”说部分否认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受者阐释文学文本之能力形成阻遏和遮蔽,且忽视了不同接受个体存在的 “先结构”差异,忽视了作为阐释对象的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开放性和审美特性。[12]
三
那么,在文论重心已由作者中心论转向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当下,“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作为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是否还具备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首先,虽然 “以意逆志”说的诠释指向是作者之志,但它并不否定读者参与的作用,甚至可以对之作出重视读者 “推测”、 “钩考”的解读。前引周裕锴文章就指出:“孟子的 ‘以意逆志’说含有极丰富的互相对立的阐释学因子,一方面,他肯定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提倡一种所谓 ‘意图论的阐释学’;而另一方面,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就意味着承认不同读者的推测都具有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 ‘多元论的阐释学’。”事实上,由于孟子对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把握只是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同时也因为孟子表述所留下的 “空白”,于是客观上不期然而然地具有了较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不但可以整合同样出自孟子的 “知人论世”说及后世学人的理解发挥,而且能够吸纳外来的或古典、或现代的诠释之学。其次,西方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对阅读、诠释过程中接受者 “先见”及建构意义的强调自有其合理性,对我们理解孟子“以意逆志”说也多有启示,但它同样存在某种与生俱来的缺憾,即由于强调诠释的历史性、差异性而消解了诠释的客观性,从而可能走向相对主义。正是有见于此,美国当代文论家赫施在《解释的有效性》一书中重新肯定了探求作者意图的合法性,对伽达默尔过分强调诠释之历史性的偏颇作了批评。在赫施看来,文本的含义(Sinn)与文本的意义 (Bedeutung)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 “一件文本具有着特定的含义,这特定的含义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阅读或诠释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文本的含义亦即作者之意图,而是文本之意义。赫施进而指出:“迄今为止,解释学理论中所出现的巨大混乱,其根源之一就是没有作出这个简单的然而是重要的区分。”[13](P16-17)尽管我们不能将赫施所论简单等同于孟子的 “以意逆志”说,但由此反观读者中心论者的责难,不能不说确有简单盲从之嫌。再次,从文学批评实践来看,将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结合的方法不仅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且往往较单一的文本分析或仅凭感受、印象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也更能切中肯綮。上文曾提到朱自清不满汉儒以史证诗及认同瑞恰兹的语义分析学,其实朱自清在其文学研究中并不排斥 “知人论世”,比如他曾对陶渊明、李贺年谱做过专门的研究,其见解多为后来学者所取。而他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又多与考据相结合,所以朱自清的诗歌语义分析便不尽同于瑞恰兹等人的做法,用朱自清自己的话说: “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 ‘断章取义’的毛病。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只就一章、一句甚至一字推想开去,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 ‘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数。”[14](P181)可见,对于外来方法,朱自清只是取其所长,并非照单全收;而对于传统方法,朱自清同样择善而从,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持读者中心论的人每每爱举李商隐 《锦瑟》诗为例,证明像 《锦瑟》这类朦胧含混之作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愉悦,这固然不失为一说;然而,诸如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 《锦瑟》解人难” (王士祯)这类诗句所传达的,不正是后人欲逆其志而不得的遗憾吗?唐人朱庆余有一首 《闺意》(一作 《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将新婚女子拜见公婆前的忐忑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就算读者不知朱庆余写作此诗的真实用意,也一样是脍炙人口之作。可如果读者知晓此诗写作的来龙去脉,包括张籍的回赠之作 《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那么他对朱庆余诗的理解无疑会更进一层。张籍的名篇 《节妇吟》亦然。孤立地看,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已堪称名句,但只有在知道此诗本事乃张籍婉拒权贵李师道之后,读者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佳处,从而折服于作者的巧思妙喻。
如果说阅读欣赏还多少可以置作者于不顾,那么对于评论、研究来说,知人论世无疑是其能否切中肯綮、客观公允的先决条件。以古小说《燕丹子》的研究为例,如果我们不能确认小说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则诸如《燕丹子》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荆轲刺秦事孰先孰后?《燕丹子》为何在题旨、人物性格、对话、细节等方面与《史记》多有不同?以及如何评判其文体属性及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难以对之做出合乎史实的科学评价。既然我们将孟子之说视为文学批评方法,相关讨论就不该止于欣赏层面。
在 《解释的有效性》一书中,赫施除了区分文本的 “含义”与 “意义”之外,还对 “解释”和 “批评”的差异作了辨析,认为 “文本含义和意义分别是解释和批评的各自对象,解释是为了揭示含义,批评是为了阐发意义”。①参见赫施:《解释的有效性》,前言及第四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有意思的是,顾镇也对 “以意逆志”作为读书穷理之法与说诗之法加以区分,认为前者不妨断章取义,而后者则须顾及全篇,兼用 “知人论世”之法。“诗则当知其事实,而后志可见,志见而后得失可判也”。[15](P639)这表明对文本义理的解释和文学批评本应有所不同,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二者很难截然分清。批评者固然是据于己见评判作品,解释者又何尝能做到完全超越自身视域的制约;自另一角度看,读书也罢,说诗也罢,同样都是以文本为依凭,而文本既为传达作者之志的符号系统,则无论何种理解,其实都与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存在关联,差别只在于距离之远近而已。
当孟子为咸丘蒙讲解如何正确说诗,提出“以意逆志”之法时,他大概不会想到,“以意逆志”四字竟然会成为后人一再以意逆之的对象;他也不会想到,本来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在后世竟然会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议;他更不会想到,原先用于说诗的方法,竟然被拓展到整个文艺批评领域,甚至成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重要构成。可以这样说,对 “以意逆志”解读、研究的历史,正是不同时代学人据于己意 “以意逆志”的历史,也是其意义、蕴涵不断沉积、叠加的历史。从东汉赵岐将 “以意逆志”解作以说诗者之意逆诗人之志,到南宋朱熹谓 “逆志”乃 “等待”、“迎取”诗人之志,再到清人吴淇以 “意”属古人,顾镇提出论世而后知人,知人而后逆志,由孟子开启的 “以意逆志”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学批评方法体系,并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今人来说,一方面可以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对孟子 “以意逆志”说之 “含义”进行考辨;另一方面也不妨望文生义、郢书燕解,发掘其 “意义”以建构新的方法和理论。我们如何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灵活应用以证实其有效性,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1][3][15]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载 《文艺理论研究》,2002 (6)。
[4]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载周锡山编校: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5][12] 尚永亮、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载《文艺研究》,2004 (6)。
[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7][8]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
[9][14]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1] 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先秦两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3]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