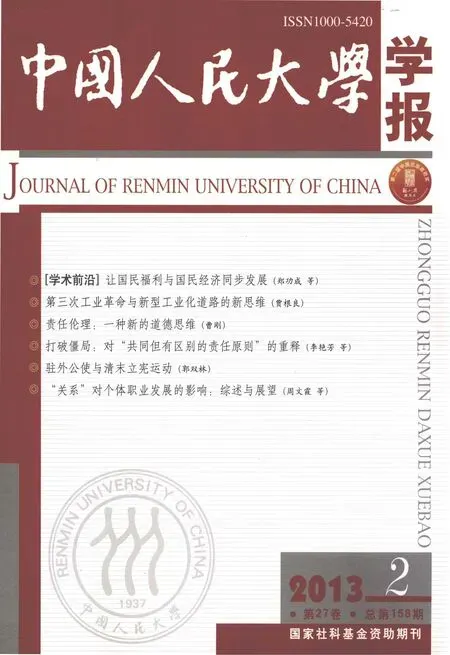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法律的 “法俗”特质
杜文忠
民国时期及当今学者多有对 “中华法系”特质的概括,然而却没有对其风俗性意义进行专门探讨。在 “法俗”与 “法律传统”的关系中,“法俗”是构成 “法律传统”这一概念的基础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法律传统”是一个历史剧场,那么以权力为后盾的主权者的法律就是演员,而 “法俗”则是这个剧场下的大众,他们共同构成所谓 “法律传统”。芝加哥大学的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提出的 “大传统”和 “小传统”概念[1](P352-353),对我们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法律具有启发意义。所谓 “大传统”和 “小传统”,即认为在比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由于阶级分化、权力管理、神职人员的专职化、国家权力与统治阶级的形成、通过用文字记述历史以及专职人员而分离出大传统和小传统。前者指社会精英们建构的观念系统——科学、哲学、伦理学、艺术等等;后者指在平民大众间流行的宗教、道德、传说、民间艺术等。雷德菲尔德认为大传统决定了文明的传统特色,而作为民俗生活代表的小传统则使人们对文明的了解具体化。大传统的发生是从小传统中分离出来,后于小传统而形成的,大传统是由知识阶层的创造性活动形成的,因而成为塑造文明传统结构的主要动力。大传统为整个文化提供了 “规范性”要素,成为有规约力的取向,同时不断从小传统中吸收新的养分或根据小传统基础的变化发展出一些新的方向。
从史料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不过是政治史与民俗史的区别,具体到法律史研究,是官法记载与法俗记载的关系。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人们强调法律史研究应当重在史,此说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的问题在于这个 “史”是什么样的“史”?是官家制定之刑典,还是包括了政教风俗的法俗史?实际情况是,法学界至今不习惯把 “法俗”作为“法”来研究,而是仅仅视之为 “国学”或 “风俗”。
一、中国古代早期法律与风俗
法律往往起源于风俗,由风俗进而为法俗,由法俗又进而为所谓之法律。因此,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
中国古代法律本有风俗之形,正如顾炎武所言:“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以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 《立政》之书曰: ‘文王罔攸兼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 ‘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与兹。’”[2](P488)这是说中国古代政治自古有重风俗轻法制之教,或者说有以俗为法之传统。如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此同为褒扬 “正人心、厚风俗”于治国平天下的意义。中国又有 “国将亡,必多制”之说,此为叔向与子产之书所云,这同样是强调风俗本有法律之用,又何须多立制度。而能够 “正人心、厚风俗”者,又赖于人,故有杜元凯之解 《左氏》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3](P489)俗重于法,以俗为法,这是中国古代人治的基本理由,也体现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
“法俗”的概念应当是涉法风俗的意思。不是所有的风俗都是 “法俗”,具有规范意义的风俗方为法俗,比如民间禁忌、神判等。历史上的中国,亦是先俗而后法。《路史·前纪》卷八载祝诵氏:“刑罚未施而民化”,《路史·后纪》卷五记载神农氏: “刑罚不施于人而俗善”,《商君书·画策》中有:“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说明法律产生之前,当是 “以俗而治”,“三皇五帝”以俗而治,故常为后世推崇,道家 “无为而治”理论的历史渊源亦本于此。在中国,若以神农之世算起, “以俗而治”经历了很长的时期,法俗的形成同样也是逐渐而复杂的过程。中国有史以来,民族众多,民俗纷呈,“北族辫发,中原冠带,其俗执之甚固,度非一朝一夕之故”[4](P28)。华夏法律之起源,既缘于本族之风俗,又伴随着它与诸族风俗的融合,同时兼取他族风俗。兹举数例:
中国古代法律以 “刑”相称,这个 “刑”是刑罚,且是肉刑。最初的 “五刑”包括黥 (刺面额)、劓 (割鼻)、膑 (去膝)、宫 (去势或幽闭)、大辟 (处死),除宫刑中幽闭女子之法外, “五刑”皆是惩罚人的肉刑。《慎子》云:“斩然肢体,凿人肌肤,谓之刑”。刑者,罚也,因此 《玉篇》曰:“刑,罚之总名也”。与今天讲的刑不同,当时肉刑才称为刑,属于中国古代刑法最初的形式。“五刑”本是俗而非法,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以俗称之,云:“膑者膑之俗,去其膝头骨也。”这些处罚方式往往具有耻辱刑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刑罚之初本是不施于本族的,《周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此为刑罚之初不施于本族的证明[5](P39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刑最初是针对异族的处罚形式。刑罚最早起源于 “象刑”,象刑又多是肉刑,肉刑与象刑应当是相随而生。从象刑的特点看,象刑多为耻辱刑罚,有异族风俗之元素,应当是对异族战败者的羞辱,也是异族战败者的身份符号,因而象刑的表现形式多取于异族之装束风俗。
首先如 “五刑”。“五刑”从苗民至周穆王时而未改,苗民在江、淮、荆州,“五刑”当与越蛮之风俗有关,且《吕刑》中已经说明它是来自苗民的旧俗,“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尚书·吕刑》)。黥者,原是越人文身之俗。后来的黥面文身本非华夏民族的风俗,而是当时异族的习惯,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 “五刑”之一的黥(墨)刑,就是起源于异族的雕题 (在额上雕刻花纹,并涂上颜色)。而刵者,原是越人儋 (穿)耳之习 (《后汉书·南蛮传》)。中国古代五刑虽不全是来自四方异族的风俗,但至少部分源于此,战争中以这些异族为奴隶,后来由此发展,本族人亦以有罪者为奴隶,故而黥其额以为耻,且以此为识别异类之标志,由此异族的风俗而演化为本族之法俗。此为中国 “法俗”与异族装束关系之一例。
又比如,古籍中常以这些异族的装束作为 “髡刑”的代称,一定程度上具有 “法俗”的性质。 《论衡·四讳》载:“古者肉刑,形毁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钳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 (弛)刑,采衣系躬,冠都与俗人殊何为不可?”(王充:《论衡·四讳》)。在古籍记载中, “四方”民族的装束是被发、断发、髡头。《后汉书·东夷传》:“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6]《集韵》载: “髡,刑名,髡去其发也。”商周皆 “束发冠带”,而其他诸族皆被发、断发或髡头。比如 “髡头”亦有考古文物为证,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东周时期北方东胡族的遗存。所发现的青铜短剑,剑柄顶端的人物形象,其头光而无发。南山根编号为M102的墓中出土刻纹骨板,上刻狩猎者形象头部亦皆无发;赤峰红后山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面形铜牌,上层人物形象也是髡头者。[7]髠即是东夷、东胡断发之俗,《秦律》中有髡耐刑,即剃光头发、鬓须的附加耻辱刑罚;《汉律》中有“予者髡为城旦”之说。[8]这说明了 “东方”民族 “髡头”之俗与作为中国古代 “象刑”之一的髡刑之间的联系,髡刑极有可能来自于 “四方”民族 “髡头”之俗。此又为中国 “法俗”与异族装束关系之一例。
再比如服饰。服饰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的一部分,服饰风俗对于中国古代治国礼教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颖达 《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古云垂衣裳也。”所谓 “垂衣裳者”,是生产进步的结果,区别于其他落后者,在当时是文明的标志。曾为李白之师的唐朝隐士赵蕤,其所题黄帝之妻 《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故而古代才有 “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说。《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又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礼记·缁衣》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此处所说 “衣服不贰”,楚竹简作 “衣服不改”①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有 《缁衣》一篇,见 《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衣服不贰”的目的是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②《礼记·缁衣》,此处 “章好以示民俗”在楚简中为 “章好以示民欲”,“欲”字与 “俗”字,二者古音同部。,强调服饰对于社会引导和约束作用,以做到 “民不惑”。
据 《荀子·哀公》载: “曾有鲁哀公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易鲜乎!’哀公曰: ‘善!’”[9](P537-538)意思是着古人服饰,自然会从古人之道,倘若穿古人服饰而为非作歹是难以想象的。同样,荀子也认为 “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觸陷生疾”(《荀子·修身篇》)。在 《墨子》中,曾有儒者公孟子与子墨子的对话,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公孟》)礼服饰与 “仁”联系在一起,是礼的重要内容。而所谓礼,亦是俗、法也。因此,在儒者的治国观念中,服饰不仅具有日常生活的基本功能,还具有一定的社会礼法功能。儒者的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雅致的一面,呈现出类似西方 “罗可可”式的文化气息。对衣饰的限制和规范是雅与俗的标志,按照孔子的说法,着雅致的服饰应当对人的为非行为在心理上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华夏文明虽然承认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但是对于自己的服饰文化十分重视,在法律上把着异服等同于淫声、奇技、奇器,对于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进行严厉的惩罚。《礼记·王制》有 “四诛者”之说,其中 “异服”属 “四诛者”之列,谓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以居州里,而民耻之。注:纯,缘也。犯刑者,单易之衣服,自为大耻。屦,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饰。”[10](P3)又如 《白虎通》: “五帝画像者,其衣服像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处而画之,犯宫者履杂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11](P4)再如 《管子·侈靡篇》:“俈尧之时,其狱一踦腓,一踦屦,而当死”,房玄龄注:“诸侯犯罪者,令著一双屦以耻之,可以当死刑。”[12](P206)服饰对于政教法律如此之重要,服饰与法律的关系如此之密切,可见一斑。
除服饰装束之外,许多刑罚也兼采异族风俗。比如《秦律》以酷刑而别于当时诸国,这些酷刑极可能来自异族。《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 ‘相坐’之法,造 ‘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 ‘鑿 (zao)颠’、 ‘抽脅’、 ‘镬 (huo)亨’之刑。”法家本只有重刑的思想,申不害、《管子》、《韩非子》、 《商君书》的理论都是如此,并无造酷刑的理论,而车裂、鑿颠、抽脅、镬亨、夷三族、腰斩、具五刑这些秦国使用的刑罚,已经不同于当时传统的 “五刑”(墨、劓、宫、剕、大辟)。这些刑罚来自何处?今并无证据说是商鞅发明的。秦国本是开化较晚之地,处戎翟之所,其先祖成分之一为犬戎[13](P49),当时极可能用“戎翟之俗”。故太史公云: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史记·魏世家》卷四四),“始秦戎翟之教” (《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八)。因此,这些酷刑中可能有自创的,不过大多也可能采用了 “戎翟之俗”,如 《史记》载:“(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史记·秦本纪》卷五)日本泷川资言著 《史记会注考证》云:“余有丁曰,秦法自来惨刻,尽夷狄之故俗也”[14],又有 “黄淳耀曰,三族之罪始于秦文公,而商鞅因之”[15],此等刑罚对后世影响极大,汉名为除秦苛政,然秦之此刑,终汉世不变。此为“法”与 “俗”关系之又一例。
中国上古观念中,本有刑而无法, “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16](P390)。《尚书·吕刑》载:“墨法之属千。劓罚之属千。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所谓三千者,并非三千条法律;有人认为是 “五刑属的三千解,仍是礼”[17](P391),多疑为原始习惯法的汇编。前者有其道理,“三千”是指当时的各种礼俗,犹言其多,而后者多为概念化的臆断。“三千”之谓,正说明法俗形成时期,刑礼相随的样态。也就是说原始风俗进而为法俗,而非形式化和法典化的法律,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夏、商、周时期没有成文法律。此又为中国古代 “法”与 “俗”关系之一例。
汉代重视法俗,故于之多深入研究且率范践行,“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于成康盛也”[18](P489)。一般认为是班固在 《汉书·地理志》中首议 “风俗”,曰:“凡民函五柴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主上之欲,故谓之俗。”[19]
由此可知,风俗的形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本土及外来风俗的影响,有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格的影响,还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可能影响风俗的内容。中国古代自身礼俗的趋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汉书·地理志》中对先秦及汉代中国风俗之迥异就有一番概括和描写。[20]
总之,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内,其民俗之纷呈,其民性之迥异,有优有劣,有善有恶,有礼有俗,此为所谓的 “小传统”。面对如此复杂的风俗,而欲求文化的统一,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介入,更需要知识阶层在文化上的创造性活动方能够做到。就其历史发展过程而言,法家和儒家之显著于政治法律,这意味着是由此二者来完成这一 “创制”使命的。
二、儒者的创制与中国古代法的风俗性
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其统一的方式,除主张 “以法化俗”之外,还需要 “以礼化俗”。“以法化俗”和 “以礼化俗”构成了中国古代 “制法”和 “制礼”的出发点。
中国古代法律的 “风俗性”最早来自两类法俗:一类是上述的 “四方”民俗;另一类就是自身的礼俗。礼是中国古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中国古代之礼本起源于风俗,它本身就来自 “俗”,是知识阶层 “化俗”的结果。早期的儒者就是以 “方术”为业的 “方术之士”,儒者既知 “方术”,也深知 “方俗”之善恶,有 “问俗”传统。“子曰:众善焉,必察之;众恶焉,必察之。”(《论语·卫灵公》)《风俗通义》云:“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翫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事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21]显然,这里所谓 “通儒”,是指 “入仕”的儒者,他们以“纲纪国体”、“原本要化”为使命;而没有 “入仕”的儒者,则是 “讲诵而已”的 “俗儒”, “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22]。儒者本来自司徒,做个 “通儒”自然是他们希望的。司徒本有教化之责,属于 “教书匠”,不能当 “通儒”,能够做个 “俗儒”也是其本分。
总之,儒者是当时的传统知识阶层,他们对礼法的形成进行了许多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是儒者以古代圣哲之教、典籍之道为标准,通过对 “方俗”的解释而进行的。汉代应劭在 《风俗通义》中所说的 “原本要化”,就是在方俗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的义理性的解释、判别。
儒者的这种义理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创制活动,在此之前的夏、商的民间法俗,除了一些占卜活动之外,我们无从知晓更多。在西周之前,儒者的义理创制对民间风俗的制度化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们同样难以明了。正如孔子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意思是我能说出夏之礼,但夏的后人杞不能作为例证;我能说出殷之礼,但殷之后人宋不能作为例证。孔子不知夏礼、殷礼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它们是否符合他的义理标准,因此孔子崇尚的是周礼。不过,华夏文明的继承性很强,所谓 “义理”的形成是古已有之,从三皇五帝即已经开始。《周易·系辞下》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尚书大传》(卷三)云:“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与事创业”;又有:“颛者,专也;顼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质,使天下蒙化,皆贵贞操悫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如此这般,圣人之教不绝,“义理”之学不断,遂成为中国复杂之风俗文化逐渐趋同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的儒者追求 “一民同俗”,因为在他们看来,“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23]。他们认为民众是冥然罔知的,因此才有 “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政,圣人废,则还其本俗”[24],此一义理是圣人的义理,而圣人的义理也是圣人在风俗经验知识上的积累和创制,后世朝代在此基础上义法并用,在不断 “以法化俗”的同时,也贯彻了作为经义表现形式的 “礼”。因此,中国哲学、政治学同其法学一样,皆来自圣人之教,是 “圣人哲学”、“圣人政治”,也是 “圣人法学”,三者皆是圣人义理之学。圣人义理是圣人对风俗的提炼,圣人义理由此而表现为 “礼”,因此 “礼”被解释为圣人“化俗”的结果。
孔子在分析了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 “礼”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当以 “五教”之礼来教化民间风俗,所谓 “五教”,就是丧祭之礼、贵贱之礼、朝聘之礼、乡饮酒之礼、婚聘之礼。此 “五教”应对了现实生活中五类社会问题和风俗,孔子倡导 “五教”之礼,是要通过祛除 “淫俗”,实现 “一民同俗”,同时防止 “不教而诛”现象的出现,在制度上最终实现 “无陷刑之民”的目的,此亦是孔子出于仁爱之心而做的制度设计。子曰:“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能教仁爱,则丧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斗变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长幼必序,民怀敬让。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婚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明,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
这段话中,孔子的逻辑是通过 “五教”之礼教化风俗,努力做到 “无陷刑之民”,进而从 “出礼入刑”的原则出发①《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汉书·郭陈列传》卷四第三十六载:“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 《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构建 “俗—礼—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孔子认为:“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则饬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狱者,则饬丧祭之礼;有犯杀上之狱者,则饬朝觐之礼;有犯斗变之狱者,则饬乡饮酒之礼;有犯淫乱之狱者,则饬婚聘之礼。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由此,在国家 (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进而创制 “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关系的社会制度模型。
西方历史上也有其 “方俗”,而且这些 “方俗”也对其法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比如英国早期地方习惯法就是其判例法的主要内容,但是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同样也是王室法院巡回法官与当地陪审员共同 “制礼”的结果。在西方法律中,如果说大陆法确立了国家制定法在国家法律形式中的唯一性,那么普通法则是在对 “方俗”整理的基础上对之 “制礼”的结果。所谓英国普通法的“发现主义”,诚如 “周公制礼”那样,都是 “官”对“俗”作用的过程。
从西周开始,“礼”开始成为社会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 “礼”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德”使得后世法典所主张的 “德主刑辅”和 “礼法合一”成为同义语。“礼”在其中的主导性不仅突现了 “方俗”的意义,而且使得原始形式的礼乐文化始终赋予法律对天、地、人(祖先)敬畏的宗教意识,而这一宗教意识同样是建立在“方俗”基础上,这使得中国古代法律在世俗化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些宗教色彩。在后来的历史中,对天地的膜拜和对先人祖训的遵从,演化为 “敬天”和 “遵循古制”的法律原则。敬畏天地和遵从祖训的法律原则,也成了后来中国古代法律以理性方式独立发展的一种制约因素。此外,“周公制礼”的意义还在于它强化了古代中国法的阴性特征及其运行的基本方式。中国古代法律运行的基本方式是:依靠司法 “问俗”来弥补国家律典之不足,这就是为什么除了 “律”之外,历代要依靠大量的 “例”来进行司法判决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明清)。“例”可以理解为是 “情”与 “理”结合的产物,“情”与 “理”的基本根据则是 “礼俗”,而 “官”的作用则更多是通过规范 “俗”和 “问俗”的形式来发展法律,在司法中长期存在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礼记·曲礼》),由此使 “方俗”具有类似于法的统一规范样式。
三、刑名与鬼神:兼谈法墨两家对法俗之影响
中国古代有 “八刑”之说,“八刑”见之于 《周礼》。大司徒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吕思勉先生认为 “这当是社会习俗”[25](P132), 他 还 认 为 这 种 刑 “也 和 礼 无 甚 分别”[26](P132)。
“刑名之学”产生于春秋末世之 “三晋”。与齐学不同,齐之治,乃是管仲之学。司马迁曰: “管仲既任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卷六十二)。管仲治国,“令顺民心”,要 “令顺民心”,亦是太史公所云 “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至管仲卒,齐行其道,百余年后,晏子相齐,节俭力行,二者同道,且通儒道,皆不重刑名,此齐学之实。
“刑名之学”当起于 “三晋”,三晋的风格是多论术而少论政,往往以术论政。 《淮南要略》曰: “申子者,韩昭侯之佐。韩,晋之别国也。地激民险,而介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莫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这是说 “刑名之书”的产生,是因为新法旧令、韩法晋礼之矛盾,产生于 “三家分晋”后的韩国,“刑名之书”生于斯,刑名之学自然起于 “三晋”。关于此说,还可以见之于韩非子 《定法篇》:“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
刑教者,如 《周礼》所云 “八刑”,古已有之,否则不会有刑教。“刑”本是惩罚人的技术,属于 “技术”范畴,故刑者,术也,此人皆知之,不再赘言。春秋时晋学之兴起,“刑”不再属 “技术”范畴,而 “刑名之学”又使 “刑”上升为治国的义理之学。刑名之学的内容,曰 “术”、曰 “法”。在法家看来,“术”与 “法”如同衣服之于隆冬、饮食之于人。衣服和饮食皆 “养生之具”(《韩非子·定法篇》),如同术与法皆 “急于国”,“皆帝王之具”,“令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以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篇》),二者不可以无一。在 《定法篇》中讲到申不害辅佐韩昭侯之所以使韩国 “七十年而不至于霸五者”的原因,就是因为韩国重 “术”而没有重“法”。“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讬万乘之劲韩国,七十年而不至于霸五者”(《韩非子·定法篇》),因此才有重 “刑”之议,刑名之学由是而生。
因此,法家刑名之学以 “法”和 “术”为基本内容,在刑名之学产生之前的所谓刑教,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风俗性,也没有使 “刑”得以理性化的学说和实践。唯秦兼用法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此前刑教的风俗性质,这对后来中国古代法律的逐渐理性化、概念化和法典化也产生了影响。尽管如此,至汉朝,上志承古义,下昌明经学,“六艺”(六经)化俗,“德主刑辅”,刑教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终得以保持它的谦抑性。春秋决狱,礼法结合,刑教在立法和司法上于后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它的风俗性。刑教、礼教、书教、乐教、诗教、义教,此六者为王者综合运用,共同形成一套可以相互解释的知识文化系统和社会控制系统,从而实现 《礼记·王制》所说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的目的。
中国先秦子学之发展有这样一个规律:凡入官学者,昌盛;凡不入官学者,泯没。与墨者行走于民间不同,儒法皆是上层社会的学问,儒法弟子亦皆行走于权贵之间。孔子死后,其学成弟子大都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传》)汉之儒家公孙弘等都是如此。此同法家申不害之于韩昭侯,商鞅、李斯之于秦。中国的大一统,首先是官学之一统,官学之一统是自上而下之一统,故其风俗教化亦是自上而下,如此法俗有可望为之一矣,此是儒法不同于墨学之处。
说到墨者,虽然有 “墨家独盛于宋”之说[27](P68),但韩非子 《显学篇》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说儒墨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儒墨之义本同气相求,但墨学在后来往往无人问津。相反,儒家则如傅斯年说:“虽有些自造的礼法制度,但信仰无主,不吸收下层民众,故只能随人君为抑扬,不有希世取荣之公孙弘,儒者安得那样快当的成正统啊!”[28](P28)
由于墨学曾是显学,战国时期墨者弟子也往往行走于民间,可以想象其教化自然且特立独行,它对于中国民间风俗、思想的影响自然也不简单,尤其对后来中国民间鬼神风俗的形成和流传少不了会产生影响,而民间鬼神之信仰,影响深刻而持久,必也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实践活动。墨子 《明鬼》中讲了许多古代鬼神的故事,其目的是说明当时天下祸乱之由,认为是 “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29],所谓 《明鬼》,是 “明鬼之实”的意思。在 《明鬼》中言鬼神故事甚多,且多分析 “先王”旧事,认为三代圣王皆祭鬼,“古者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还列举了许多故事说明有鬼神的存在,如:“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30],三年后,杜伯变鬼于圃田诛宣王,此事 “著在周之春秋”;又列举郑穆公、燕简公、宋文君等诸侯的鬼神故事,且言皆得之于所在各国春秋。
四、“除其恶俗”与法家的律令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影响的不仅限于秦国,也包括类似制订了 《法经》的魏等国,然而真正彻底贯彻法家思想的,乃是战国时之秦国和后来的秦帝国。
法家思想的基本概念是 “术”和 “法”,如前说 “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讬万乘之劲韩国,七十年而不至于霸五者”(《韩非子·定法篇》);商鞅则于秦曰法、重法,故秦律被今人冠以理性主义和法治主义之名,尤其秦朝奉行之以 “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商君书·开塞》)的重刑主义,强化了国家权力,由此开创了中国强有力的国家形态的历史。而此前的 “国家”,不过是依血缘而分封之 “家”,仅仅依问俗而治理之 “国”, “国”只是地域意义上的封国,是城邑,而非一以贯之的文化和权力。
秦朝要实现商鞅所说的官员 “一岁受法令以禁令”(《商君书·定分》)以及司马迁所说的 “法令由一统”[31](P161)的统一大业,必然面临如何对待如此复杂的风俗局面问题,在行政上实行 “海内为郡县”,破除了原来封邑制度的松散性,在法律上实行 “皆有法式”、“一断于法”,以此约束各异之风俗。
秦律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世俗理性主义法文化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古代律典中少有风俗性的元素,同时也表明了它为风俗文化在 “大传统”意义上的趋同提供了制度平台,这正是秦朝立法的一大贡献。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秦朝武力统一后,不仅需要统一原来各国的法律,而且还需要使各地不同的风俗与它的法律相宜。
秦在统一中国后,要实现法家所谓的 “一断于法”的制度理想,必然要 “去其邪僻,除其恶俗”[32],但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基层的社会习俗给秦法的推行带来的障碍一定也很大。
在法家的思想中也没有绝对排斥法俗。商鞅认为:“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商君书·算地》)在这里,商鞅强调的是 “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所谓的 “此臣之所谓过也”,其 “过”不是指 “刑用于将过”的 “过”,而是相对于民间法俗而说的立法之 “过”,“过”在这里是指立法的界线,掌握这个界线,需要察国本,观时俗。如果不能处理好法律与社会风俗的关系,则会 “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社会就会出现混乱。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十一号秦墓中秦代竹简,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提供了可考的材料,也为我们研究秦朝法律与风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依据。竹简 《语书》中云:“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多有间令下者。”[33]对这段话,我们可以分解为:一是承认 “民各有乡俗”;二是乡俗有时 “不便于民,害于邦”;三是应当 “去其邪僻,除其恶俗”。由此可见, 《语书》对当时民间风俗的态度,它不仅阐明了强势的国家之法 “去其邪僻,除其恶俗”的意义,而且隐含了 “俗”已被分为 “恶俗”和 “良俗”。
“恶俗”和 “良俗”的标准,正是以强势的理性政治文化为标准的,最关键的一句是: “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多有间令下者”,说明当时相对于各类 “恶俗”,强调的是 “民多诈巧”,由此其对于当时法制状况的判断是归于 “法律未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秦朝法律 “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重要理由之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推行国家法律时十分困难,遇到类似涉及风俗的案件应当不少。秦简 《语书》中,南郡郡守腾于秦王政二十年发布的一道文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夫:……凡灋 (法)律令者,以教道 (导)民,去其淫避 (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灋 (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 (泆)之民不止。甚害于邦,不便于民”,这是说当时国家律令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不仅民不用,而且吏也不用,原因是 “乡俗、淫佚之民不止”,“恶俗”与国家律令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面对这样的局面,南郡郡守腾又当如何对待这些不服从秦律的南郡楚人呢?作为秦法律改革先驱的商鞅本有 “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这种 “因俗而治”的思想,秦的官员可能对此并不陌生,且从现实需要出发,也可能采取 “因俗立法”的做法。
此外,腾在修灋 (法)律令、田令时,很可能依据当地风俗,在立法上做了一些让步。“故腾为是而修灋(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 (知)之,毋巨 (歫)于罪”,腾通过文书告诉县、道、啬夫各级官吏,需要修改法、律、令、田令,予以颁布,让当地吏民知晓,不再犯法,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灋 (法)(也),而养匿邪避 (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胜任、不智 (知)(也);智 (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 (也)。此皆大罪 (也)。”这说明民间私好、乡俗之心仍然不变,这里的所谓 “私好、乡俗之心”,是指地方法俗,人们仍然拒绝适用官方律令,这充分说明楚地涉法风俗的顽固。楚地如此,想必在其他地方亦然。
再从 《秦纪会稽山刻石》看秦法的风俗性。秦始皇在位时共刻石有六,其中亦多有涉及民间风俗者。顾炎武认为此六块石刻 “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34](P751)而具有法令性质。如山东泰山刻石是针对有孔孟风气的鲁地,因此不过是强调 “男女礼顺,慎遵戠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这些针对风俗的文辞都比较一般化,只是泛泛而云罢了。但在风俗隔异、素有 “淫泆”之风的越地则不然,其石刻内容大不同于其他,《会稽山刻石》文中对当地风俗有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其词曰: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 ,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①“寄豭”,司马贞索隐:“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猪也。”豭,音加。这实是针对当时越地淫俗的一项重要法令,“防隔内外,禁止淫泆”,进而化正风俗是其主旨。
从整个法律史的发展来看,秦的法治主义伴随着秦统一中国,为中国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提供了经验。尽管汉代以后法律沿着儒家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国法中 “律”始终体现了这一特质。“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 “问俗”,还要 “化俗”,要 “去其淫避 (僻),除其恶俗”。这对中国古代法律 “以法化俗”样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今法学研究也有深刻启示。
[1]Robert Redfield.“Vincenzo Petrullo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New Series,1957,59 (2).
[2][3][18][3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全校本,黄汝成集释,乐保群、吕宗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5][16][17]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7]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载 《考古学报》,1987(2)。
[8]《居延新简》EPS4.T1:100。
[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11][1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13]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4][15]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
[19][20]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22]应劭:《风俗通义校注·序》(上),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24]应劭:《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26]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7]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载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杨佩昌、朱云风整理,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
[28]傅斯年:《诸子、史记与诗经文稿》,杨佩昌、朱云风整理,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
[29][30]吴毓江:《墨子校注·明鬼下》,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3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2][3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家乡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