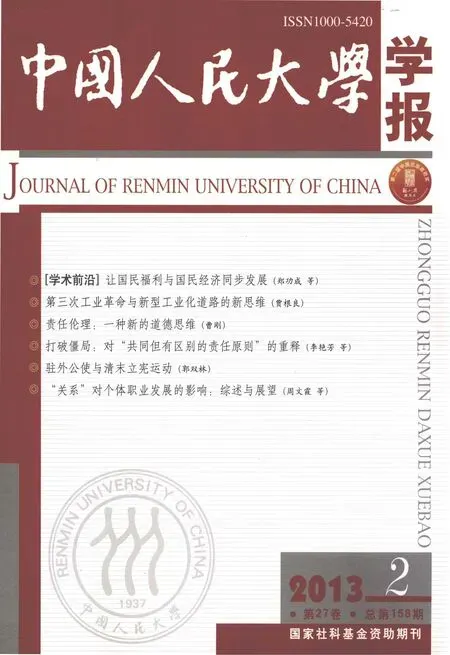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
金炳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统的机构照料方式在国外被普遍认为不够人性化,即使得福利服务对象缺乏隐私保护,并且与社会严重隔离。为解决机构保护存在的问题,提高机构居住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大型福利机构不够人性化的环境,发达国家着力推进由社区提供保护和服务。如此一来,社会福利机构的规模和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减少,机构内原有的被保护对象通过与机构外的个人、家属或其他公益组织建立有机的关系网来维持生活的存续或发展。这就是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去机构化趋势进行考察。首先,分析这一概念的内涵、产生的背景及优缺点;其次,讨论去机构化带来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最后,探讨因去机构化引导的社区福利的作用,探索今后社区福利的新实践方向。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发展过程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概念
所谓去机构化,是指从20世纪初开始,欧美国家针对大型福利机构中暴露出的非人性化问题,不断地进行讨论、批判并积极寻找应对措施或者解决方法的实践活动。在此之前的社会福利大多是机构化的,即人们通过住院或者入住福利机构的方式享受福利服务,如残疾人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进行集中或分散治疗。机构化的社会福利服务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也使得机构居住者的生活与家庭和社区分离,对接受福利服务者造成了新的生活困扰。而社会福利去机构化则是与传统机构服务相对立的概念,彰显了让福利服务对象从机构重返家庭和社区的意义,是一种强调保护对象的社区生活的新保护模式。去机构化强调解决社会福利机构的隔离收容方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允许在社区里为福利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使其能在社区中维持生活。也就是说,与社会福利机构相比,社区更能提供有效保护。根据美国审计署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的报告书,去机构化是指:(1)防止不必要的机构服务;(2)在社区中为那些不必入住福利机构的人提供治疗、训练、教育以及康复的方案或过程;(3)改善需要机构保护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治疗过程。
去机构化运动的兴起是基于保障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制约最少、使人们尽可能保持独立生存权利这一正常化或者常态化原理[1](P71-115),弱化了传统性保护和机构隔离服务方式,允许被保护对象在社区里生活。此外,去机构化还力图通过改善机构的环境,以提高残疾人等福利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因此,去机构化不是全面否定机构服务,而是弱化机构服务,将其与社区服务相结合以改善相关福利服务。
从这个角度看,去机构化并非是要去掉机构保护或使机构解体,而是去大型机构化。它不仅着重于关闭机构,还要聚焦于机构服务的灵活性和多元化;不仅要着重于治疗病症,还要聚焦于积极的个人成长;不仅要着重于使人获得自由,还要聚焦于在自由中提升生活质量;不仅要着重于专业化的服务,还要聚焦于开放的、具有弹性和非结构式的全人全程照顾。[2]根据去机构化的代表性研究者希尔恩伯格 (R.C.Scheerenberger)的观点,机构保护对象应该拥有最少的生活制约,为此需要进行以下六项改变:从制约多的生活到制约少的生活、从大型机构到小型机构、从大生活单位到小生活单位、从集体生活到个人生活、从隔离生活到社会融合、从依存的生活到自立的生活。[3]由上可知,去机构化的过程伴随着正常化的概念。
在支持去机构化的人看来,福利机构的生活被描述为,被保护对象接受机构所提供的一致性的服务并且无法回归社会,个人需求被剥夺或被无视。去机构化提倡发展社区福利,将机构中的被保护对象逐渐送回社区。这与被保护对象的自由和独立生活的权利息息相关,其核心理念就是把制约最少的生活环境诉求和社区统合起来。
(二)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背景
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运动并不仅仅是由某一个重要因素引发的,而是急剧变化的各种经济、社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影响去机构化产生的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对保护机构的社会关注增加。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普遍关注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特别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福利保护机构的恶劣状况被揭露,以及1972年纽约福利保护机构非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曝光,大型保护机构存在的负面问题成为社会话题,福利机构受到批评,相关政策制定者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被保护对象开始被送返到社区中接受治疗和服务,对保护机构实际状况的社会关注度日益增强。
(2)对保护机构的批判。19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出现的大型保护机构对照顾对象的控制、虐待和标签化等非人性化的现象,使被照顾对象受到了严重伤害,妨碍其人格的完整,而且机构的建设费用、管理费用和运行成本昂贵。此外,随着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中尽可能过正常生活的“正常化”思想的兴起,人们希望消除机构保护对被保护对象的生活方式的 “扭曲”和 “变态化”等负面影响。[4]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保护机构非人性的生活实态和教育缺失的现象引起了大家对保护机构的关心,引发了反对大型保护机构的社会运动。虽然保护机构的设立和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了解决机构服务存在的各种问题,人们开始提倡去机构化的概念。
(3)政府财政投入的削减。在以保护机构为主的福利事业中,设施费用的提供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去机构化政策实行以后,政府对患者的保护提供及相关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特别是精神障碍者医疗费用的节减是去机构化进程加速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美国州政府预算的5%~10%用于精神病院。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和控制持续增加的精神健康费用,保守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减少保护机构数量来减轻财政的负担。相反,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去机构化会提供更有人性、有效的以社区为主的福利服务。[5]虽然去机构化政策中节省费用的效果使政府受到了推卸责任、弱化政府福利功能的批评,但去机构化与大型保护机构相比,则更人性化且更有效。
(三)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
在美国,去机构化运动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成为国家政策发展的一个趋势。在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推动下,通过对机构侵犯人权现象的大规模揭露和批评,形成了去机构化的政治社会协议。此外,1957年制定的 《社区精神保健法》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正式拉开了美国去机构化政策的帷幕。无论障碍的种类和程度如何,把以前在医院及大型机构中接受不适当服务的保护对象转移到社区,以社区为中心,提供各种精神、社会康复服务的社区精神保健成为普遍方式。
约翰·肯尼迪的妹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因此,1960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热衷于修改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国家政策。1961年,美国政府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主导全国的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目标是提供现代精神医疗服务,以使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在社区中维持正常的生活。19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者转移至社区,使他们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并由联邦政府拨款,推动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re Construction Act)的实施。该法案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病患者在六个月之内可以被治疗的,应将其放回社区之中。《康复法》(Rehabilitation Act,1973)和《残疾儿童教育法》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s Act,1975)等相关法律的制定保障了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及其权利。这些措施使得在社区中按照社会整合的理念为残疾人提供居住环境,保证残疾人生活在制约最少的环境和整合的社区中。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各州政府开始关闭大型残疾人机构,出现了在许多州和社区隔离性的保护机构都消失的情况,隔离、集体保护的传统形式的残疾人机构逐渐被小型机构所代替。在这些小机构中,一般会有在社区中居住的1~6名残疾人。[6]20世纪90年代末,去机构化运动余音未了,美国政府提出 “以社区为中心的服务”的口号。1999年美国最高法院以ADA法案(American Disability Act)裁定各州应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尽量避免机构安置与非必要的隔离。该法案指出,精神病患者应该和社会中其他人一样,享有权利和尊严,不应该因为精神上的障碍而受到排斥。
20世纪50年代,英国也开始了社会福利服务 “从机构到社区”的运动,以社区为主的精神障碍患者和老人保护项目日渐增多。随着治疗方法的发展,还主张早期患者出院和关闭精神病医院。这种变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体现。例如,《格里菲斯报告书》(Griffiths Report)的发表引导地方政府坚持首要提供社区保护的责任,为了让残疾人、老人等社区保护对象享受适宜的生活,政府应对保护对象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并发挥计划、调整、购买社会服务的作用。在英国,去机构化政策具体是指实施和扩大为残疾人和老人提供的社区基本娱乐项目。
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去机构化政策一样,都坚持社区服务比机构保护更有效果的基本宗旨。但两国的政策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在英国所重视的是社区福利,而不是去机构化。
二、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影响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积极效果
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最大优点是相较于大型的福利机构设施,能提供更人性化、更有效的以社区为主的保护。具体来讲,去机构化体现的积极意义包括:
(1)保护机构的减少带来小型机构增加。已有的研究发现,去机构化的直接效果是居住设施的减少。例如,在美国,1977年重度障碍服务受惠者约有84%在大型机构里居住,但2004年服务受惠者中有84%在社区里居住。[7]在英国,机构病床从1976年的518 000个以上减少到2002年的48 000个以下。[8]澳大利亚也出现类似的情况。[9]同时,随着大型机构里居住人数的减少,以社区为主的小型设施逐渐增加。[10]居住设施的小规模化并不是单纯减少机构的物理规模,而是从以控制和接受为主的传统方式转到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支援体系。
(2)整体生活质量提高。对去机构化后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追踪调查显示,居住在大型机构中的残疾人转到小型机构和社区居住生活以后,其生活的正常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提高。[11]尤其是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社区治疗比医院治疗更有效,对出院后的功能恢复、社会适应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实际效果。[12]另外,对精神障碍患者短期治疗和长期治疗效果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以普通医院和社区精神保健为主的治疗比精神病医院的长期住院治疗更有效果。随着去机构化运动的开展,很多设施条件和服务质量比较差的大型精神病医院被关闭,大量精神病患者被转移到社区或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1955年,美国每10万人口拥有339张精神病床;到了1994年,已经降到了每10万人口只有29张精神病床。同时,大量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转入社区后,获得了全面康复。[13]
(3)多种服务项目登场。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不仅带来居住地点的变化,而且带来开发多种类型居住设施的效果。和自然的家庭环境最相近的 “寄托家庭”,以及可容纳4~6名居住者的普通住宅或公寓居住者的 “集体之家”等新型居住设施出现了。社区里出现了很多可以利用的设施,福利享受者和家人申请后就可以接受相关服务。另外,短期住院治疗和日托医院等住院形式及新疗法出现,在家庭中生活并接受服务的形式也出现了。而且,为了使残疾人能在社区独立生活,政府提供单纯居住支持之外的多种形态的社会综合支援服务,这种支援体系的构筑带来了积极效果。
(4)政府公共财政负担减轻。研究结果表明,以社区为主的保护比传统方式的保护机构所需的费用更少。例如,沃尔什 (K.K.Walsh)对残疾人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费用的比较分析显示,大型机构服务比社区服务的花费要高约2.5倍。[14]随着住院患者数量逐渐减少,政府的公共财政负担将会减轻。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与机构保护比较,社区服务因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15]
社区服务可以满足照顾对象的基本生活、康复护理、精神情感娱乐等多方面需求,获取资源的渠道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功能的全方位性、资源的多元性以及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弥补了单一机构服务的不足,受到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欢迎,为社区福利提供了社会基础。[16]
(二)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争议依然存在
去机构化的最大意义在于跳出以大型机构为主的福利框架,提供以社区为主的更具人性化、整合性的生活环境。[17]根据国外经验,有许多残疾人通过去机构化运动实现了离开机构、回归社会、独立生活的目标,去机构化不仅有利于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而且对提供具有整合性的社会环境也做出了贡献。但是,对去机构化的批评和反论也存在,并且去机构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虽然改善了机构环境,但不能克服根本性的局限。去机构化所主张的内容是整合还是隔离,都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已,从机构保护到社区保护并不是保证残疾人正常化和社会整合的唯一手段。[18]通过机构环境的改善、小规模化、社会化等方式来保证残疾人的平等权,残疾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团结也能够得到实现。对于这种支持机构服务的言论,支持去机构化的人们主张无论再怎么改善机构设施环境,机构服务的根本性局限仍是无法克服的。在机构中居住的残疾人的自主权依然受到侵害,社会经验被限制,残疾人的生活也被控制。
(2)机构设施的需求依然存在。根据琼斯(P.A.Jones)的研究,虽然人们强烈主张正常化和去机构化,但机构设施的存在也说明原有的机构服务的必要性,因此,今后机构服务并不会消失。[19]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作为替代家庭保护功能的机构保护设施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如果连保护机构都没有的话,家庭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增加,对于受到家人虐待或与家人之间存在矛盾的残疾人来说,选择摆脱家人的生活方式会更好。支持去机构化的人们主张,对保护机构的需求依然存在的原因是残疾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残疾人生活的地区可以提供适当的居住设施和支援服务,保护机构的需求将逐步消失。
(3)需要构筑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行去机构化可能给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积极促进去机构化的实践中也遇到过。在不具备充分的财政和其他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推行去机构化产生了负面结果,包括第二次机构化、迁移机构化、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社区居民对类似于集体之家的残疾人居住地的集体抗议等问题。
另外,在 “去机构化”的热潮中,一些资质好、人性化的机构也未能幸免。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出院走向社会,他们需要社区的服务与支持,但是很多社区并不具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设备,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如住房、庇护、食物、衣物、收入、医疗照顾以及康复措施等。社区也没有做好接纳精神障碍患者的准备,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区后,由于被社区或家人排斥而增加病耻感。一些无家可归的病人,或露宿街头,或藏身于避难所,他们反复住院,过度使用急诊医疗。因触犯刑律而进入矫治系统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数也急剧增加。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死率也在不断增加。[20]
三、去机构化实践中社区福利的作用
“去机构化”奉行尊重人权的理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去机构化运动提倡治疗及康复服务,着重于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增强他们的生活能力,以使他们无障碍地获得生活资源,尽可能使其在接近正常生活的空间和环境里,过着接近正常的生活,同时,使其有机会根据自身的能力贡献于社会和他人。去机构化帮助被保护对象增强在社区中的生活能力,增强自立意识,在社区中享受各种福利,满足不同需求,因此,社区福利将是 “去机构化”的一个坚实落脚点。[21]
(一)社区福利的优势
对于社区福利的优势的分析,除了因为现实需求和服务的社会化要求之外,也是由于政府开始倾向于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在工业化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转变。之前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许多功能正逐渐被新型的现代化社区所代替,社区福利在我国当代社会服务中的地位凸显,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社区福利研究不断拓展,开始进入系统化的发展阶段。首先,它符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福利思想,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家庭与宗族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基本需求,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相适应。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借鉴西方发展成果,将国与家的福利概念融入社区之中。由此可见,它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几经磨合的必然结果。其次,社区福利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使得社区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通过社区福利,社区内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支持。再次,促进了我国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等新现象、新形势。最后,社区福利价值和理念能够推动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因为社区福利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互动机会,对于安抚他们的心灵,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22]
(二)社区福利的具体措施
起初,去机构化主要以精神病医院为主展开。但随着去机构化进程的推进,去机构化现象除了在精神病医院之外,在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的福利机构中也能找到。无论是对于老人、儿童还是残疾人,社区福利之所以受到他们的青睐,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区中生活最能满足服务对象的多元化需求,能在最大程度上让服务对象生活的像一个 “正常人”,尽可能让服务对象按照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正常地过日子。[23]接下来将通过与残疾人康复有关的 “以社区为主的康复事业”来说明去机构化当中社区福利的作用。
以社区为主的康复事业是指为了利用残疾人本人和他的家人及社区居民等社区资源采取的所有社区服务项目。这个概念简要概括如下:加强社区居民对残疾人康复的理解和树立责任意识,提高残疾人的自助、自立意志。通过治疗、教育、职业培训和相关技术方法提升康复效果,增加主动解决问题的机会。将社区拥有的资源 (包括残疾人及其家人、社区里的其他人力资源等)和各种机关、团体的下级体系 (医院、教育、社会、心理、职业等相关的部门)所开展的项目在实际服务中加以利用,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
以社区为主的残疾人康复事业更重要的在于社区融合,强调资源融合与心理融合。首先要考虑社区各项服务资源的建构,即替代机构的各项社区服务资源是否足够、是否完整、质量是否达到要求。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完备的社区服务资源,服务对象所能接受的服务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其次,社区要接纳残疾人成为社区的一员,而不是仅仅将其转移到社区中去生活。为了让残疾人被家庭与社区接纳并稳定下来,较为谨慎的做法是通过赋权与长期介入,累积社区资本,进而培养当地居民充分的接纳心态。再次,主动思考全控式机构与社区服务之间如何进行衔接的问题,比如创设中途之家、庇护工场、日间留院、居家照顾等,以填补机构与社区之间可能出现的断层。[24]
总之,残疾人的康复,采取以残疾人的生活起点——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服务形式是最有效的。为此,残疾人本人及其家属以及邻居和社区居民应该相互理解,多方合作,共同解决残疾人康复问题。
四、结论
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兴起是由于机构福利服务中出现了人道主义问题。这些国家的经验引导被保护对象从与家庭和社区隔离的医院或现有的保护机构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得福利服务回归家庭和社区,积极展开了以预防、治疗、康复及社会融合为主的日托服务,出现了集体之家、社区精神保健中心等社区服务机构。发达国家实施并扩大了以儿童、残疾人和老人等为中心的基于社区政策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运动。
去机构化运动也对东亚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影响,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方向已经从以机构福利为中心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去机构化的发展引导了具有多种形态的社区服务体系的出现。特别是,使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建立的以社区为主的服务传达体系是社区精神保健中心最典型的去机构化结果。社区精神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短期住院、门诊治疗、日间医院、日间保护、应急服务、临时居住设施、集团之家等,而且进行咨询和提供教育课程。另外,以社区福利馆为主的社区福利事业也是去机构化的做法。居家福利事业不是仅服务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以及儿童的福利,而是社区里所有家庭均能享受的服务。
去机构化的影响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果。但这些负面结果不是去机构化的本质性问题,而是推行过程中伴生的问题。这是在对不具有成熟条件就进行去机构化可能引起危险的一种警告。[25]因此,为了给被保护对象提供成功的社区生活迁移和更加有利的生活环境,人们应该努力对去机构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出预防对策。最重要的不是将国外去机构化政策直接引进,而是按照各国实际情况推行去机构化政策。去机构化不仅是社会福利设施的结构性变化,还具有整合社区有机联系的功能,让福利服务对象从社会上接受服务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如果能够整合分散且复杂的服务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被保护对象及其家属的过度责任和费用负担,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区福利将逐渐得以发展。
[1]Wolfensberger,W.“The Definition of Normalization”,In R.J.Flynn & K.E.Nitsch (Eds.).Normal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Baltimore:University Park Press,1980.
[2][13][20][21][23][24]赵环:《从 “关闭医院”到 “社区康复”——美国精神卫生领域 “去机构化运动”的反思及启示》,载 《社会福利》,2009(7)。
[3]Scheerenberger,R.C.“D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Perspective”.In Paul,James L.Paul et al.(ed.).Deinstitutionalization,Program and Policy Development.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7.
[4]刘继同:《从 “个人不幸”到 “社区照顾”——中国残疾人福利典范的战略转变》,载 《唯实·社会纵横》,2007 (1)。
[5]Halpern,Joseph,et al.The Myths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Policies for The Mentally Disabl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80.
[6]Braddock,D.L.&Parish,S.L.“An Institutional Closure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ictoria's Institutional Redevelopment?”.In G.L.Albrecht,K.D.Seelman & M.Bury(eds.).Handbook of Disability Studies.Thousand Oak:Sage,1995.
[7]Baez,B.Deinstitutionalization at the Front Lines: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
[8]Emerson,E.“D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ngland”.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2004,29 (1).
[9]Young,L.,Ashman,A.,Sigafoos,J.,& Grevell,P.“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losure of the Challinor Centre”.Journal of I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2000,25 (2).
[10]Prouty,R.,Lakin,K.C.,&Coucouvanis.“In 2006,fewer than 30%of Persons Receiving Out-of-family Residential Supports Lived in Homes of more than Six Residents”.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2007,45 (4).
[11]Emerson,E.,& Hatton,C.“D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UK and Ireland:Outcomes for Service Users”.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1996,21 (1);Emerson,E.“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Live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ople”.American Journal of Mental Deficiency,1985,90:277-288.
[12][17]Segal,S.Deinstitutionalization,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9thed.).Silver Spring,MD:NASW,1995.
[14]Walsh,K.K.,Kastner,T.A.& Green,R.G.“Cost Comparison of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idential Settings:Historical Review of Selected Research”.Mental Retardation,2003,41 (2).
[15]Halton,C.,Emerson,E.,Robertson,J.,Henderson,D.,&Cooper,J.“The Quality and Costs of Residential Services for Adul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A Comparative Evaluation”.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1995,16 (6):439-460.
[16][22]张甜甜、王增武:《我国大陆地区社区照顾研究综述》,载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1(3)。
[18]Nirje,B.“The Normalization Principle”.In R.J.Flynn & K.E.Nitsch(eds.).Normal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Baltimore:University Park Press,1980.31-49;Bank-Mikkelson,N.“The Normalization Principle”.In R.J.Flynn & K.E.Nitsch (eds.).Normal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Baltimore:University Park Press,1980.51-70.
[19]Jones,P.A.,Conroy,J.W.,Feinstein,C.S.,& Lemanowicz,J.A. “A Matched Comparison Study of Cost-effectiveness:Institutionalized and Deinstitutionalized People”.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1984,9 (4).
[25]Talbott,J.A.“Deinstitutionalization:Avoiding the Disaster of the Past”.Psychiatric Services,2004,55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