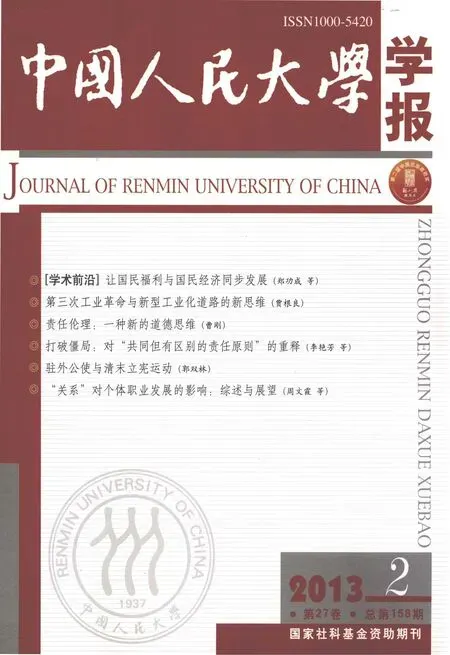打破僵局:对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释
李艳芳 曹 炜
一直以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的核心议题都是责任的分配问题,而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所有争论又都指向了责任分配的标准和准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UNFCCC)缔约方以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Principle,以下简称CBDR)。围绕 《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有关缔约方责任承担的历次会议均表明,CBDR事实上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①通常情况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理解为一项国际环境法原则,但本文并不仅仅在国际环境法原则的范畴内界定它,而是将其看做法律原则、伦理准则和谈判策略的集合体,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都会使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术语。各缔约方在有关强制减排责任的分配、履行机制、信息交流以及经济和技术援助等问题上,主要是围绕着CBDR展开的。有人甚至认为:“UNFCCC谈判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尝试贯彻和实施 CBDR 的过程。”[1](P1)然而,无论是在减排 责任分担的谈判过程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质疑CBDR的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甚至要求废除这一原则。[2]不管这种要求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都在事实上影响了CBDR的贯彻与落实。因此,我们需要正视CBDR所面临的困局及对它的质疑,并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CBDR进行修正。唯有如此,才能最终打破谈判僵局,解开气候变化谈判的死结,并最终构建起双赢模式。
一、冲突与平衡:“共同责任”还是“有区别责任”?
综观CBDR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发展史就是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的战争史。在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之前,京都模式所确定的绝对的区别责任占主导。而在 《巴厘行动计划》之后,整个谈判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共同责任,有区别责任正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确定了将缔约方划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由附件一国家率先承担起减排义务的基本方案,这一方案最终促成了1998年 《京都议定书》“全有全无”的责任分配模式的建立。[3](P498-499)但是,由于“全有全无”的方案过于极端,因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反对,这导致2005年开始的就 《京都议定书》之后的责任分配问题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4](P13-14)为了打破僵局,2007年的缔约方大会最终形成了 《巴厘行动计划》。根据 《巴厘行动计划》,除了在原有的 “《京都议定书》之下 《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AWG-KP)外,又设置了 “《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AWGLCA),负责就所有国家旨在履行公约的具体义务进行谈判。[5](P14)这表明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向脱离 《京都议定书》模式的方向发展,即发达国家逐渐推动原有的不对等的 “全有全无”模式向对等的减排义务分配模式发展。[6](P502-503)此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在 《巴厘行动计划》中,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 “国家的适当的缓解行动(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的要求,但是仍然将这一要求与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联系在一起。[7]到2009年, 《哥本哈根协定》却将这两个部分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并且努力切断两者间的联系,从而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独立减排。[8]2010年缔约方大会通过的 《坎昆协定》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趋势,该协定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相对减排义务,到2020年实现相对于“正常排放” (business as usual)的偏离。并且,为了实现全球到2050年大幅度整体减排,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应尽快封顶,即尽快开始绝对减排。[9]
通过考察各国对CBDR从强调 “区别责任”到强调 “共同责任”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前期的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而后期则开始逐渐向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这样一种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反应。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一个美好的时代已逐渐逝去,如果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话,也要尽量推迟强制减排义务时代的到来。由于发展中国家认为,这将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目标的实现[10],因此,“区别责任”成了发展中国家对CBDR关注的重心所在,所有的理论研究都围绕 “区别责任”合理性的论证展开。而发达国家往往强调 “共同责任”,认为 “区别责任”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以及印度等排放大国可以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11](P600)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认为 CBDR 是无效率的,甚至成了谈判的最大障碍,让谈判步履蹒跚。[12](P51)尽管谈判在不断深入,但这种观点和立场的对立并没有随着气候变化谈判的发展而趋于缓和,反而愈演愈烈。
从CBDR所引起的对立与冲突来看,CBDR并没有实现 “共同”与 “有区别”的均衡,相关的制度安排总是在 “共同”与 “有区别”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种局面的出现表明,CBDR还远远没有实现其调和两大阵营的目的。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协议对于义务与责任的安排都是有差别的,而差别对于法律正义之实现必不可少,否则,法律对于利益分配制度的设计就很容易陷入绝对平等的泥潭。但差别分配同样危险,一旦 “有区别”的义务分配由于缺乏稳固和确定的理论基础,使得义务与责任的承担者在直觉上感觉到 “不合理”,区别就会导致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制度的失败。
二、僵局与困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复杂性
为什么本来用以解决分歧与争议的CBDR却会导致这种谈判僵局的出现呢?从表面上看,CBDR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行动计划》以及 《哥本哈根协定》的文本中都得到了清楚的表述,其内涵是确定和明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CBDR的内涵一直在不断变化。有学者认为,剥离CBDR所处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其理论基础、内涵、适用范围以及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无法真正获得对CBDR的正确认识的。[13](P500)从 CBDR 的内在属性、使用者对它的法律解释以及更深层次的气候变化谈判格局来看,这是因为CBDR在内涵上没有实现内部结构的均衡,在实践中无法获得统一的解释,在发展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干扰。
(一)CBDR内容的不均衡性
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词序结构中,“共同”在前,表明 “共同”应当是CBDR主导性的意涵,理应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无论是将 “共同责任”原则看做底线、第一性要素还是主导性要素,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都应始终坚持 “共同责任”优先的立场,“共同责任”的适用应当是无条件的。与此相反,“区别责任”并不是 “普遍的”,而是 “特殊”的,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适用的标准,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其适用何种国家和何种情况。国外有学者认为,“区别责任”的适用必须遵守下列要求:一是 “区别责任”不能背离条约的目的,即使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2℃以内;二是当 “区别责任”所针对的情况不存在时,“区别责任”就应当停止适用。[14](P213)因此,从理论上来说,CBDR的两个要素应当是以“共同”为原则,以 “有区别”为例外,二者间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并不均衡,“共同责任”(Common Responsibility)所指的是两个或者更多国家具有共同保护某种具有特定自然资源的义务,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适用于那些不属于某个特定国家或者不在某个特定国家完全管辖范围内的自然资源。[15](P286)“共同责任”暗含着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国际社会在面对环境保护议题时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UNFCCC缔结阶段,尽管 “区别责任”也发挥了一定的吸纳 (buy—in)作用,但公约的签订主要是基于 “共同责任”获得了各国的认同。但是,“共同责任”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过于宏观和抽象,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共同”不是 “相同”,也不是 “协同”,无法为责任分配的细节问题提供指导。因此,在满足了 “共同参与”的前提之后,“共同责任”就逐渐淡出了谈判视野,UNFCCC缔约方的争论、甚至各国学者都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贯彻 “区别责任”的问题上。
CBDR内在结构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连贯的、统一的、清晰的准则。具体来说,尽管CBDR包含了 “共同”与 “有区别”两个责任分配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标准并没有产生互动,而是相互抵消,从而无法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统一的指导。对CBDR的不同理解导致分歧的出现和扩大,甚至使CBDR成为整个谈判继续深入的最大障碍。CBDR的发展不自觉地滋养了一股在权利的意义上不断增强的反对它自身的力量,CBDR最初所具有的那些优点现在却成了其致命的缺点。[16](P66)因此,尽管从理论上看将 “共同”和 “有区别”糅合到一起是一项令人叫绝的创举,但在面对其所需要真正发挥调整作用的国际气候变化立法时,却是一个无法转化为实践的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达国家才一直要置CBDR于死地,要求彻底废除这一原则。
(二)CBDR内涵的不确定性
当利益各方和持有不同取向的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 “区别责任”上时,就产生了对 “区别责任”如何加以解释的问题。相较于 “共同责任”,“区别责任”就显得非常复杂了,从不同立场和视角出发,可以作出许多截然不同的解释。《里约宣言》原则6、7以及UNFCCC第三款都对CBDR进行了规定[17],但这些规定都非常抽象,无法直接用于调整和解决各国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适用CBDR,就必须对 《里约宣言》和UNFCCC的规定进行具体的解释。可是,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具体标准又是各不相同的,在条文中提到的标准——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needs)”、“发展中国家环境易受损害性”、“历史责任”以及 “能力差异”等都是比较模糊的,从而导致了在如何适用这些标准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18](P653-654)比如,国外学者一般对于 “历史责任”采取否定的态度[19](P292、Footnote86),而突出强调效率标准的重要性。[20](P36-38)国内学者则较少关注能力以及效率标准,而对其他几项标准有着较浓厚的兴趣。显然,这些可以说称不上标准的标准本身就是可以进行多重解释的,即便认为这些标准具有确定的内涵,也会出现这些标准适用的先后次序的问题,而 《里约宣言》和UNFCCC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标准在适用时的次序,更没有明确规定是需要达到几项标准还是一项标准就可以适用 “区别责任原则”。由于各国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在研究某一缔约方是否应当根据 “区别责任”原则给予其较为优惠的区别对待时,经常会遇到上述标准相互冲突的问题。例如,某些富裕的小国(例如文莱、新加坡)由于在海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些国家却并不能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能力标准。这种标准的重叠与冲突为各缔约方按照自身的需要 (例如道义诉求、经济地位或者政治立场)进行解释提供了多种选择。
最重要的是,在UNFCCC框架内缺乏权威和统一的裁决机构,这就为各国各自进行解释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CBDR的解释权被抛入云谲波诡的政治谈判之中,无法求得自身的确定性。从理论上来说,参与UNFCCC的缔约方均可以通过不断博弈来最终决定如何理解和适用CBDR。但在实践中,由于缔约方之间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差异,使得缔约过程更像是各缔约方和利益集团力量的角斗场,而不是一个平坦竞技场。这种角斗的结果使得如何对CBDR进行解释和论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 “有权力”解释,谁的解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解释上的多种可能性和解释权力的角逐是各方无法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突然抛出 “丹麦文本”,正是因为缔约方大会对于解释权缺乏实质性的程序限制和约束。
(三)CBDR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各国为什么会选择对CBDR作出多样化的解释而不是努力谋求一个统一的解释?要回答这一问题,在原则内部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已经远远不够,必须突破法理论证的范畴,将这一问题放在更广阔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历史之中进行考量。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对CBDR作出多种解释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国的经济地位不同。经济力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一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而,一些国家及其学者们要求突破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而去深入地考量各国经济地位的差异,认为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国在经济上已经不能完全归属为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收入仍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中、印等国已经具有较大的经济总量和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从这一点来看,中、印等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多过相同点。因此,在中、印等国仍然坚持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 “全有全无”的区别责任模式时,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已经悄然转向,开始强调共同责任,要求中、印等国承担强制减排责任。例如,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一名教授认为,后京都模式必须将所有国家纳入减排行动之中,在确定总量的基础上将缔约方分成三种类型:历史上排放较少并且未来潜在排放量也较少的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获得最大的排放量;历史上排放较少但是未来潜在排放量较大的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获得中等排放量;而历史上排放较大并且未来排放量仍然较大的国家(发达国家)获得最少的排放量。[21](P620、640)
二是各国的政治立场不同。从谈判的实际过程来看,UNFCCC缔约方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在利益需要以及政治传统等方面的影响下结为同盟。主要的同盟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欧洲各国组成的欧盟集团,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众多小岛国组成的小岛国联盟。[22]尽管这些同盟在力量和紧密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对外时都能够采取较为一致的政治立场。因此,仅仅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博弈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到各国所处的政治阵营对于CBDR解释的影响。
三是各国的道义诉求不同。由于UNFCCC规定了历史排放责任这样一个标准,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立法上的支持,从而不断地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谴责;又由于发展中国家占据了伦理上的制高点而将发达国家置于道义上被谴责的位置,从而实现了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责任的合理性证明。应当承认,对发达国家作出这种道义上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将历史排放因素纳入责任分担机制的同时,也明显地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并加剧了各国间的对立情绪。
四是 “阴谋论”的影响。所谓 “阴谋论”,是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上的经验而对发达国家的一种先天的排斥情绪,其核心观点就是,气候变化与碳排放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还是一个无法得到确切证实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炮制出来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要通过限制排放的方式来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保证发达国家在未来全球经济新格局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3](P372-374)阴谋论与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以及道义立场所产生的观点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由于CBDR的解释受制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其复杂化的程度也相对增加了。本用来解决分歧的CBDR完全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不仅无法在谈判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反而使分歧变得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CBDR开辟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制造新分歧的领域。总体来说,CBDR自身固有的“共同”与 “有区别”的不均衡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解释时遭遇各国不同的利益需求、政治立场以及道义主张,并伴随着各种阴谋论、流言以及争吵,也就远离了形成CBDR的原初动机,甚至完全走向了其反面。
三、重释与区分:一种多形态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由于CBDR结构上的不均衡性以及对它作出解释的不确定性、影响因子的多元性等,致使各缔约方以及学者们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使用被赋予不同意义的CBDR。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注意。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斯通教授指出,CBDR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 “合理讨价还价的CBDR” (Rational Bargaining CBDR)。这种类型的CBDR的内涵是把 “有区别的责任”理解为参与多边条约谈判的各方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谈判去获得某种结果。通过自由讨价还价获得帕累托改进,好过没有谈判。第二种类型是 “平等的CBDR” (Equitable CBDR)。这种类型的CBDR比前者更进了一步,对自由的讨价还价增加了公平的限制,各方被限制在从若干可以产生帕累托改进的利益分配方式中作出选择,这有利于特定的谈判方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第三种类型是 “无效率的CBDR” (inefficient CBDR)。这种类型的CBDR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以纠正现实的不平等的名义将合作的收益全部分给发展中国家,以至于发达国家的境遇比合作之前变得更坏。[24](P283-284)
斯通教授的分类方法表明,在谈判中存在不同类型的CBDR。但是,这一分类方法无非是要说明不同类型的CBDR所导致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果是不同的,显然没有更加细致地从本体上描述不同结果背后的CBDR的性质、表现及其在国际气候变化责任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这是一种出于解释需要的分类,而不是出于解决问题需要的分类。但是,就斯通教授试图对CBDR进行分类而言,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类型化的研究视角。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不同类型的CBDR的话,笔者认为,CBDR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中表现出以下几种不同形态:作为 “法律原则”(Legal Principle)的CBDR、作为 “伦理准则”(Ethical guideline)的CBDR和作为 “谈判策略”(Negotiating Strategy)的CBDR。
(一)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
将CBDR作为法律原则来加以认识,就可以看到它的元规范功能,从而使它与缺乏可预见性的政治谈判相分离。这样一来,其作为一种通过法律推理而发生作用的法律原则的本质特征就可以得到显现。这时,CBDR就是一种没有现实背景 (non-contextual)的元规范,从而为通过形而上的理论推导对其加以解释提供了确定性的空间。[25](P411)
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价值普适性。CBDR必须在整体上服从作为普适价值的公平、正义、秩序、自由以及效率等法的价值理念,并求得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这种CBDR不能偏向于某一种特定的价值,否则便有成为 “恶法”之虞。“与其他法律的结构成分只负载法律的一两项价值不同,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法律的所有价值的负载体。”[26](P355)二是权威性。尽管CBDR承认乃至于侧重于区别责任,但其作为法律原则 (而非政治导则或者道德规范)应当成为各种各样的平等约束所有主体的具体规范得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也就是说,CBDR不考虑主体在具体经济地位、政治同盟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所有主体都必须服从CBDR的安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三是规范性。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处在 “原则—规范”的框架之内,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为规范的制定提供指导与限制,并为规范提供漏洞填补与解释的功能。其目标是促进稳定缜密的规范体系的建立,避免规范体系受到过多的法外因素的影响。四是权利义务的综合性。由于必须受到法的基本原理的制约,所以,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在生产规范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并重,避免权利与义务不均衡的情况出现。
法律的原则只有在与法律的理念以及法律的规范发生联系时才能发挥作用。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具有主体间性的、共同的、稳定的和具有普适性的规范体系,并为这套规范体系提供指导和解释依据。此外,为了保证规范能够具有合法的程序基础,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还应有调整气候变化责任分配程序性规定,以保证这种责任分配的过程的公平与公正。
一旦我们注意到CBDR作为法律原则的地位,就会发现它对于UNFCCC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机制的价值。当我们从法律原则与规范链接的角度来观察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时,目前所进行的UNFCCC谈判作为一种政治程序而非法律制度程序的特征就会显现出来。既然是一种具有政治活动性质的谈判,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博弈各方讨价还价的市场。如果认识到了CBDR作为法律原则的属性,其实也就确定了谈判的方向和过程,就会尽可能地避免把谈判变成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然而,在减排责任分担的谈判中,各国都没有意识到CBDR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被建立起来的,因此,各国也就不会自觉地去探寻一种能够获得主体间性的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CBDR,更不会以CBDR为基础去协商建立进一步的规范体系,而是不停地试图为CBDR开 “后门”,努力让自身的价值判断从后门走进厅堂并成为CBDR的核心价值。就此而言,在缔约各方中都存在着对CBDR的误读,因而导致了CBDR与具体规范体系建立之间的脱节。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把CBDR作为法律原则来认识,其就无法通过与规范的互动求得自身的发展,反而只能依赖于UNFCCC谈判中的力量角逐。可见,CBDR是被谈判过程所决定的,而不是决定谈判的因素,无法成为具有稳定性的文本。因此,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事实上比较低,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基础性作用。
(二)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
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要比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更进一步,或者说,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当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而失灵的时候,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就开始在讨论历史责任时发挥作用,其核心内涵就是鉴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而认为发达国家有伦理上的责任,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承担更多乃至全部责任。
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在价值上偏向公平与正义,而比较忽视效率。与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不同,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更多地服务于公平和正义价值,而不考虑具有潜在冲突的价值之间的调和。二是其所调整的主体不平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大量的排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使得发达国家单方面处于伦理上的低地,而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制高点上。三是在规范的设计上,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过分重视规范的伦理性,因而并不遵循法律原理对于规范的要求,而要求规范设计偏向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一面,体现出对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要求,可见,这种规范从法律的原理上来说属于第二性的规范。四是在权利义务的设置上,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不要求权利义务分配的均衡,而要求发展中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利。
自CBDR被提出以来,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乃至国际环境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1992年《里约宣言》原则七的制定过程中,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就曾经被要求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当时,77国集团提出了自己草拟的原则七的条文:“全球环境持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鉴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退化所负有的历史和当下的责任以及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退化的能力,发达国家应当在优先和优惠的条款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新的以及额外的经济援助和环境友好技术,以保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27](P36)与最后的条款相比,77国集团拟定的条款显然更加直接地要求对过去和现在的责任加以追究。[28](P37-38)发展中国家认为,77国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应当将资金和技术转移看做是弥补环境退化的补偿 (compensation)。事实上,这样一种观点一直扎根于发展中国家的观念中,并一直延续到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
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的影响非常显著。一方面,这种CBDR支持了 《京都议定书》所采用的 “全有全无”的责任分配方式,当区别责任被理解为一种对历史和现在的责任追究时,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责任承担就具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这种责任承担被理解成弥补过去和现在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此相对的另一面则是,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意识。由于责任被理解成一种补偿,就会将谈判进程引向放手让发达国家去作决定的方向,即发达国家因承担责任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就会被排除在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和法律规范制定的过程之外,因而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利。例如,资金和技术转让制度通常被理解为最能体现CBDR要求的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主导权一直在发达国家手中。伦理准则的CBDR主张与其所带来的后果出现了一种自反性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度增强了,制造了一种新的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才会有人就援助的问题提出抗议:“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援助是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环境协议下展开的,而不是慈善事业。因此,发达国家不应当主导相应的国际法律框架的构建,而应当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进行平等的协商。当使用 ‘相应的能力 (respective capability)’作为国际环境法上区别责任的一种有效的论据时,发达国家并不应当将其用来否定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程序的权利。”[29](P51-52)
(三)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策略的CBDR
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策略的CBDR处在一种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当做战场的语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策略的CBDR使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体现出一种“丛林法则”,让各国各自以服务于其国家利益为谈判的主要目的,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CBDR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一种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策略的CBDR,致使各国都极力要在气候变化谈判可能形成的法律框架中确保自身的利益要求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一来,CBDR就失去了作为协调各方利益的标准的意义。
作为策略的CBDR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在价值上,CBDR并不服务于任何固定的普适价值,只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利益。但是,为了保证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CBDR又是必须以某种普世价值作为其基础的,因此,其具有一定的伪装性。二是其所调整的主体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利己主义个人,如果说在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下,各国将平等地去为创设规范体系而共同努力,在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下,各国之间划分成明确的阵营而进行责任分担的争论,那么,在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下,各国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之间一样的面目,各国都只为在 “具有险恶用心的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求得生存和利益最大化。三是这种CBDR不具有规范性。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和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虽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它们分别形成了两种对权利义务的安排要求,而且所安排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固定的。与之不同,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是动态的,往往根据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变化而随时变化,始终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美国一直要求将排放总量作为责任区分的标准,将自己的减排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挂钩,根据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行动采取行动。又如,大量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都采取一种抱团的态度,将发达国家视为对手。然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又开始显示出另一种明显的策略性选择,即要求中国等大国承担强制减排责任。[30](P135)
由此可见,虽然CBDR只有一个文本,但在事实上却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CBDR,尤其是策略性的CBDR,几乎无处不在。这种情况让缔约国以及学者们烦愁不已:对于缔约方来说,谈判策略的存在使得建立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体系更加艰难,甚至没有任何形成法律框架的可能性,可谓前途渺茫;对于学者来说,在解释和评判CBDR时,只能按照传统理论解释框架来选择正义的立场或效率的立场,而对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尽管这种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实际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不加以正视的话,CBDR就不可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四、出路与结论:中国的选择与减排义务
客观存在的三种不同意义与形态的CBDR决定了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无法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合理的行动路线。目前,我国在UNFCCC谈判中已经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需要同时承受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挤压。继续维持以往的立场、态度和策略已经无法保证我国的国家利益,更不利于我国塑造大国正面形象。要在UNFCCC谈判中重新获取主动权,我国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性的调整。概括来说,我国的对策选择应当是:尊重和捍卫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创新性地使用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重视作为谈判策略的CBDR。
(一)尊重与捍卫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
明确的目标是人类行动最重要的前提。在应然的意义上,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目标既不是一部分国家和另一部分国家之间的 “清账”(如战争赔款等),也不是一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的掠夺 (如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而是要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与规范框架,以调整国家间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协同关系。因此,我国在后京都谈判中首要的对策选择是坚持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
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通过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去争取在后京都谈判中的主动地位。作为世界上发展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中国一直无法在UNFCCC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这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31](P88)如果期望在未来的后京都谈判中取得有利的位置,我国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强调建立谈判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调整机制上。比如,我国可以通过提议将程序议题纳入到谈判过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中,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打破现有谈判的僵局,另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主动权。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实体性议题还是在程序性议题中,我国应始终坚持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坚持各方共同服从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我们这样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和响应,也能够得到具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尊重。
(二)创新性地使用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需要得到伦理的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规范的建立也不例外。应当承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人们一直持有伦理的立场和视角,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对CBDR的伦理解读,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发达国家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在能力弱势的情况下求助于道义支持的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重新陷入发达国家隐性的侵略、压迫和掠夺。这种伦理考量是具有合理性的,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而处在道义弱势地位上也是值得这些国家反思的。基于道义的考量,发达国家应当较多地承担起减排责任,而且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通过掠夺所积累起来的能力也决定了它们能够承担起这种责任。但是,发达国家也会存在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因为其道义上的弱势地位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没完没了的追究。因此,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也有较大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还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使得各方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责任分担上,而无法使各方面对未来就集体行动达成协议;其二,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偏向于区别责任,并且推动区别责任的设定脱离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使得CBDR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权威性。
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中国一直扮演着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角色,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中国对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的支持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中国在对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的支持中使自己在后京都谈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受到了削弱。一方面,由于支持伦理准则的CBDR,我国无形中首当其冲地成为发达国家压制发展中国家的首要对象,总是首先和直接地承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大部分压力,并且无法平等地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商谈。另一方面,由于坚持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我国所提出的有关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的相关理论无法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也就无法充分影响到谈判的规则设计与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体系的构建。由于形势的变化,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的排放量提出非议,这就使中国处于两头受夹击的地位。
由此,我国需要对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进行重新解释。其基本思路是:我们应当要求把承认历史与面向未来统一起来,一方面要求必须承认因历史原因而获得的责任;另一方面则需要面向未来采取行动。具体地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不会改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着共同的或相近的历史遭遇,中国必须代表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中国又需要面向未来去拓展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的内涵,要求注入包容和合作的内容,并且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道义的要求分配责任,在包容与合作的道德中采取行动。这样的话,我国就可以通过对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的创新性解释来获取优势地位。
(三)灵活和有弹性地使用策略意义上的CBDR
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中,中国亟须发展出一整套灵活和有弹性的谈判策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我们需要把坚持作为法律原则的CBDR和创新性的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主张与灵活的和有弹性的谈判策略统一起来。
在是否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的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这是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是其首当其冲要求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的国家;对于大量没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在我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方面有着强烈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味地拒绝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就会在全局意义上陷入被动局面。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如果我们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也就无法享受到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享有的权利,更不用说我们坚持拒绝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会在各个方面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不仅会使得我国背上阻挠气候变化谈判的恶名,而且在其他国际事务中都有可能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遭遇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许多观察家表示,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关键议题上阻挠了一致的决定,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迫切地希望谈判能够向前推进。”[32](P103)这里的所谓 “一小部分国家”其实指的就是中国。
从长远来看,我国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与其使用CBDR进行拖延,还不如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例如,虽然我国已经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由于是强度目标而非总量目标,是自愿性减排而非强制性减排,因此,依然受到一些国家的非难。其实,我国可以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加以化解,如尝试提出更长远的强制性减排目标。这样,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也可以倒逼国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化不利于有利,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辩证法的具体运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应当明确承诺是有条件的,即应当以发达国家作出相应的承诺为条件,甚至我们可以基于历史、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原则而提出责任分配的比较原则,从而增强其可操作性。
作为伦理准则的CBDR事实上已经使应对气候问题的谈判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不同的阵营中作出选择,处在哪个阵营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策略的选择。在许多国际问题的谈判以及行动中,各国都在不断地根据需要变更自身的策略。
必须承认,美国在策略的选择和变更方面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例如,综观美国21世纪以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策略,有着许多独到之处:2001年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搞亚太清洁发展伙伴关系,抓中、美、日、印、澳和韩六个大国;后来进一步扩大搞20国集团,然后不断地强化G8+5;2006年开始明确提出G2;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又建议,由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来控制气候谈判过程,所谓排放大国即美国加 “基础四国”。[33](P12)
与之相比,我国的策略则比较单一和缺乏灵活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运用的是团结77国集团的策略,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巩固南方阵营。但近些年来,许多迹象已经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集团,已经站在了与中国对立的立场上,而我们的策略却一直没有改变。目前,要求将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单独划分为一种国家类别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我国在这方面却一直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笔者认为,我国应顺应这种趋势,积极地设计团结新兴经济体的方案,根据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利益需求,提出这一集团有关CBDR的策略性选择,尤其是重点团结基础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
总之,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世界也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关系的任何一个新的变化都会使中国的地位发生改变,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会引发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拥有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在法律原则和伦理准则方面建立起能够行之一贯的观念、原则和规范体系框架,而在策略选择上,我们则需要随时根据我国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而作出调整。这一点需要贯穿于对CBDR的理解和解释之中。
[1]Douglas Bushey,Sikina Jinnah.“Evolving Responsibility?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in the UNFCCC”.Available at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public6&div=3&g_sent=1&collection=journals(last visit February 28,2013).
[2][3]Chee Yoke Ling.“‘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under Threat”.Available at http://www.twnside.org.sg/title2/sdc2012/sdc2012.120606.htm (last visit July 22,2012).
[4][5]谷德近:《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载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6]Lavanya Rajamani.“The Cancun Agreement:Reading the Text,Subtext and Tea Leaves”.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11,60(2).
[7]《Bali Action Plan》,Para1 (b)(ⅱ).
[8]《Copenhagen Accord》,Paras 4and 5.
[9]LCA Outcome Decision (1/CP.16),Para48.
[10]Jairam Ramesh (Indian Minister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and Forests).“Letters from Jairam Ramesh on the Cancun Agreement”.Available at http://www.sanctuaryasia.com/index.php?view =article&catid=122%3Aclimate-change&id=3929%3Aletter-from-jairam-ramesh-on-the-cancun-agreement&option=com_content&Itemid=289(last visit Oct 20,2012).
[11]John Copeland Nagle.“How Much should China Pollute?”.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2011,12(Spring).
[12]Mary J.Brotscheller.“Equitable but Ineffective:How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Hobbles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 Policy,2010,10(2).
[13]Philip M.Kannan.“Mitiga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Designing a Dynamic Convention to Combat a Dynamic Risk”.William and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2012,36(Winter).
[14]Kerry Tetzlaff.“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7,56(1).
[15]Philippe Sands.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6]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7]《里约宣言》原则六、原则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
[18]Veerle Heyvaert.“Levelling down,Levelling up,and Governing Across:Three Responses to Hybrid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20(3).
[19][24]Christopher D.Stone.“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98(April).
[20]Paul G.Harris.“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the Kyoto Protocol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1999 (7).
[21]Albert Mumma,David Hodas.“Designing a Global Post-Kyoto Climate Change Protocol That Advances Human Development”.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8,20(Summer).
[22]李艳芳:《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23]Rumu Sarkar.“Critical Essa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Development Law:a Reconciliation of Opposites”.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2005,33(Summer).
[25]陈卫东:《论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载 《中外法学》,2004(4)。
[26]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的局限性之克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7][28][29]Duncan French.“Developing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0,49(1).
[30]谷德近:《巴厘岛路线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演进》,载 《法学》,2008(2)。
[31]王小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 〈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载 《社会科学》,2010 (7)。
[32]Jutta Brunnee.“From Bali to Copenhagen:towards a Shared Vision for a Post—2012Climate Regime?”.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0 (25).
[33]潘家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争议焦点与反思》,载 《红旗文稿》,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