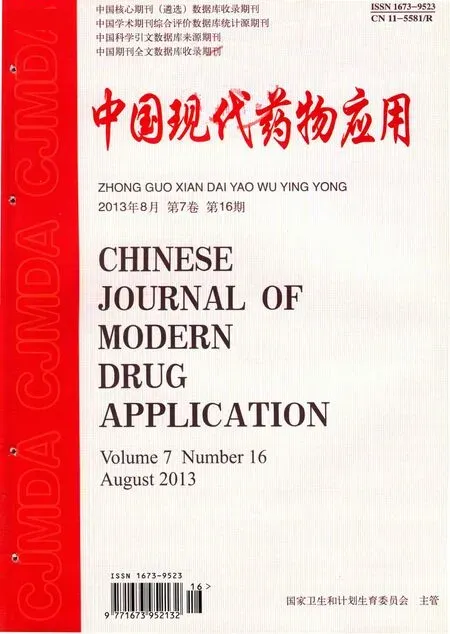牛蒡子的临床应用
靳瑞英
牛蒡子辛苦寒, 入肺、肝、胃经, 其疏散风热, 解毒透疹, 利咽消肿之功, 尽为人知, 但其作用远不止此, 通过近年来临床体会发现, 牛蒡子别有妙用, 略述如下。
1 散瘀滞 壮腰膝
《用药法象》云:“利凝滞腰膝之气是也”, 甄权亦云:“利腰脚”, 由此可见, 《外科正宗》立“阳和解凝膏”温经行阳,行气活血, 祛风散寒, 化痰通络以治疮疡阴症、乳癖, 以牛蒡子根茎叶(鲜者)1.5公斤入药, 确属高明之举。盖牛蒡子味辛质润, 是辛香通络, 辛柔和血, 宣痹散结之妙品, 其苦寒之性入血分而属肝象, 兼之质润味辛, 当属通络散结之润剂, 用于阴疽漫肿, 乳癖不消, 骨质增生, 糖尿病足, 坐骨神经痛以及硬皮病, 多有显效。如曾治一糖尿病足的患者,患者患糖尿病已7年余, 近二年来脚部疼痛难忍, 活动后减轻, 以致夜不能寐(一夜只能睡1~2 h), 近期足大指出现如大豆黑斑, 处方:熟附子30 g、丹参30 g、细辛45 g、牛蒡子40 g、豨蔹草60 g、炙麻黄20 g、白芥子30 g、紫草30 g、制马钱子8 g、山慈菇24 g、毛冬青30 g、制乳没各20 g、刘寄奴24 g、皂角刺30 g、生甘草30 g, 煎汤外洗, 目前已能睡6~8 h, 大指黑斑已除。有骨质增生患者无论是腰部颈部还是膝部, 用下方醋拌酒蒸外熨皆效(蔓荆子60 g、大青叶60 g、白芷60 g、川断60 g、牛蒡子60 g、独活60 g、透骨草60 g、羌活60 g、刘寄奴60 g、红花90 g、芙蓉叶90 g、血竭40 g、粉甘草40 g), 见效者多人。
2 通利二便
《本草正义》“凡肺郁之邪, 宜于透达, 而不宜于抑降者,如麻疹初起犹未发泄着, 早投清降, 则有遏抑气机, 反致内陷之虞, 惟牛蒡子则清泻之中自能透发, 且温热之病大便自通, 故牛蒡子最为麻疹专药”。又《食疗本草》云:“通利小便”。由此可见, 牛蒡子具有通利二便之功。盖牛蒡子辛香入络,开启肺窍, 而高原水治, 水道通调;子质富含油脂, 润肠通便, 多用于上焦气滞而引起的二便不通, 加之苦寒入血, 清血分之毒热, 兼有散瘀通络之功, 则多用于急慢性肾炎, 尤其是慢性肾炎因罹患感冒而引起的浮肿, 小便不利, 大便不爽之证。并可配伍其他药物, 用于老年虚性便秘。曾治一例慢性肾炎因罹患感冒而急性发作者, 患现咽红肿痛, 面部及下肢浮肿, 大便不爽, 小便时带血而短涩, 脉细数, 舌苔黄质红。处方:夏枯草20 g、土茯苓30 g、牛蒡子24 g、紫草15 g、泽兰叶20 g、小蓟30 g、白茅根30 g、益母草30 g、车前子15 g、丹参30 g、玉米须30 g、生地30 g、当归24 g、生甘草15 g, 服药十剂后, 诸证消失, 之后服用健脾益肾, 活血通络之剂调理, 而使病情稳定。
3 祛风止痒
《用药法象》云:“治风湿隐疹”,《珍珠囊》言“去皮肤风”, 由此可见, 牛蒡子是一味祛风除湿止痒良药。《古今录验》载其“用牛蒡子(炒)浮萍各等分, 入薄荷煎汤服二钱,日二次”治疗风湿隐疹。《外科正宗》载消风散用于治疗湿疹,接触性皮炎, 牛皮癣等, 可见二贤皆誯善用牛蒡子者。盖牛蒡子辛寒入气分, 疏风散热, 清气分之热邪, 透热达表;苦寒入血分, 清血分之热毒, 化气分之湿滞, 兼之活血通络, 则血和风熄, 牛蒡子通利二便, 则湿热毒邪从二便而消, 不失为活血祛风除湿止痒之佳品, 临床常宗《外科正宗》消风散加减治疗皮肤病属风热或湿热者, 每获佳效。
4 凉血散结
牛蒡子具有清热之功, 故多用于疮疡初期如《东垣十书》中曾载普济消毒饮方中曾用牛蒡子, 尤多用于乳痈初中期。如《医宗金鉴》载瓜蒌牛蒡汤, 宜用于牛蒡子;清代“三张”之一—张锡纯氏可谓善用牛蒡子者, 其用牛蒡子不但用于外伤咳嗽, 亦用于内伤久嗽, 其中“牛蒡子与山药并用”, 并且载“燮理汤”用于治痢, 可谓高见, 用于下痢赤白, 腹痛, 里急后重, 数日不已, 方中牛蒡子“取其能通大便, 自大便以泻寒火之凝结。”由此不难看出, 历代医家对牛蒡子有一种误解, 认为其为疏风散热之剂, 清热解毒之品, 实则不然, 牛蒡子用于疮疡初起, 乳痈初中期, 痢疾久而不愈, 实赖于其清热解毒, 凉血散结之功。《灵枢·痈疽篇第八十一》云:“寒邪客于经络之中, 则血泣, 血泣则不通, 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返, 故痈肿, 寒气化为热, 热胜则腐肉, 肉腐则为脓。”由此可见, 血瘀、热毒乃是疮疡形成的两大要素, 因此清热解毒, 凉血散结, 便是治疗疮疡的两大重要法门, 牛蒡子除具有以上两种特性外, 更兼通利二便, 因此不失为疡科要药,广泛用于疮疖疔毒、痈疽漫肿, 乳痈、肠痈、急慢性痢疾,而随手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