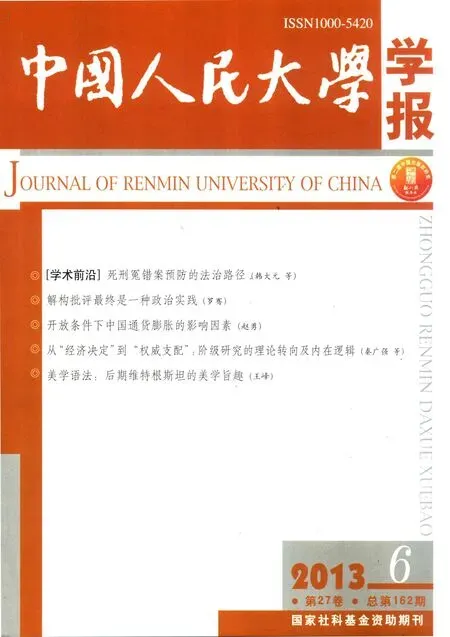朝向他在性:公共行政的演进逻辑
张乾友
公共行政需要重建,这已经是一种共识。那么,公共行政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进行重建?是像“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主张的那样把一切交给市场,或是像 “黑堡学派”所坚持的那样求助于宪法,还是像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突出关怀的价值?这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诉诸公共行政的历史。只有理清公共行政发展本身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及趋势,才能找准重建公共行政的正确方向。而从历史入手,我们将发现,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了一条不断朝向 “他在性”的逻辑线索,包含一个从拒绝他者到承认他者的存在、从面向他者进行建构到向他者开放的现实过程。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他在性”概念和视角的引入是法默尔的贡献。法默尔在其代表作 《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1]中,将他在性视为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不同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基本维度之一,进而提出了依据他在性而开展行政建构的方向。法默尔关于他在性的阐述引发了许多回应,催生了一批体现他在性视角的理论著作。但无论法默尔还是他的追随者,都未从他在性的角度来思考公共行政的历史发展,相反,在与 《公共行政的语言》齐名的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2]中,麦克斯怀特把公共行政的发展视为一个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合法性就是认同,而认同就是自我。所以,从合法性出发,麦克斯怀特看到了公共行政在演进过程中不断丧失自我的事实,这是一个体现了他在性的发现;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证明公共行政重寻自我这种努力本身的合法性,而这又体现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所以,麦克斯怀特从他在性出发开展的历史反思是不彻底的,他发现了公共行政背离自我的事实,却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所蕴含的朝向他在性的逻辑。他在性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指向,将公共行政的发展视为一个朝向他在性的过程,体现了对公共行政的一种开放性的理解,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理解中,公共行政的重建才是可能的。
公共行政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从基于自在性进行建构向基于他在性进行建构的转型过程,它所蕴含的是公共行政从一个封闭的自为系统向一种具有为他性质的开放系统的演进趋势。由此可以推断,未来的公共行政必然是一种具有他在性维度的行政模式。因此,从他在性出发将是公共行政重建的正确方向。
一、从拒绝他者到承认他者的存在
自我是现代哲学的核心,也是理解所有现代现象的出发点。如米歇尔·苏盖和马丁·维拉汝斯所说:“从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 ‘我存在’, ‘自我意识’和 ‘我’的体验在西方被认为是最高体验。”[3](P78)作为一种现代建制,公共行政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自我哲学的影响,因而,当人们试图将公共行政确立为一个独立的治理部门和领域时,所采取的途径就是拒绝他者,通过将所有被视为他者的东西从这一部门和领域中排除出去来确证自我的合法存在。比如,在被公认为公共行政学起点的《行政之研究》一文中,威尔逊对公共行政做了如下界定:“行政领域是一个事务领域 (a field of business)。它被从政治的混乱与争吵中解脱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甚至置身在宪法研究的辩论场外。” “行政处于 ‘政治’的特有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设定了行政的任务,却不应自寻烦恼地去操控行政机构。”[4]由此,通过对政治这一他者的拒绝,公共行政找到了它的独立的自我,进而开启了它在“自在性”的原则下进行建构的历史。
在浅层的意义上,对政治的拒绝意味着对所有具有政治属性的国家机构的拒绝,它划定了公共行政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范围与活动空间。这就是:“尽管并非无视司法的或军事的职能,但我们所理解的公共行政主要是指文职机构在法定授权下执行分派给它们的公共事务的工作。”“在约定俗成的用法中,‘公共行政’的概念主要被用来表示对于政府行政部门有效地完成其被授予的民事职能至关重要的组织、人事、实践和程序问题。”[5](P6)在深层的意义上,对政治的拒绝意味着对政治过程所蕴含的各种价值的拒绝,它确定了公共行政作为一个价值主体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在行政——不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科学中,基本的 ‘善’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标是花费最少的人力和物力完成手上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价值量表中的头号原则。”[6](P192-193)由此,通过对政治的拒绝,公共行政逐渐确立起了一种以效率为基本追求的技术性实践的自我形象。
沃尔多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认为行政是一个事务领域,一个 ‘政治’应当被严格排除在外的领域的观点得到了几乎所有文官制度改革者与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普遍认同。”[7](P42-43)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 “市政经理制”(city manager plan)这种独特的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流行,随着一大批 “把自己描绘成温和的、无血气的、非政治化的和办事的公仆”[8](P51)的市政经理的出现,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也更加接近于一种具体可见的客观事实。在自在性的原则之下,公共行政被建构成一个自足的、封闭的技术性的领域,它的基本特征被莫里森归纳为:“‘好政府’就是 ‘好行政’,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9]或者如法默尔所说: “行政就是行政就是行政 (administration is administration is administration)。”[10](P60)
不过,尽管早期学者们对政治这一他者做出了集体性的拒绝,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拒绝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学者们如何坚称“行政处于政治的特有范围之外”,在现实中,行政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如果说早前人们关于行政与政治可以分离的观点有着文官制度改革的现实依据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 “新政”中行政部门的崛起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全面介入,随着现实世界本身的变化,“行政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成了这一时期学者们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政治这一他者究竟在行政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成了这一时期理论探讨的核心主题。
1937年,在威尔逊 《行政之研究》发表50周年之际,迪莫克发表了一篇同名文章,明确反对威尔逊关于 “行政是一个脱离了政治之混乱与冲突的事务领域”的观点。迪莫克指出:“官员们经常希望这是真的,但它不是。政治 (在法律与政策的意义上)贯穿于行政的始终。集团压力直接而不间断地作用于公共行政的每一个部门与分支。”[11]也就是说,在集团政治的大背景下,行政不能独立于政治,这是一项基本事实。而如果行政不能独立于政治,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将是,行政本身就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根据阿普尔比的看法,“不仅政治在它的非党派方面对行政机构有着持续而彻底的影响,而且政策与行政在执行部门的运行过程中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因此,行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词最好的含义上”[12]。
米德在分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时指出:“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明确关系中才能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之间不可能划出严格的界线,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时,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能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13](P145)在哲学史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它否定了笛卡尔以来的存在论命题,取消了“我思”作为 “我在”之证据的合法性,而将他人的存在作为自我存在的前提。显然,这是关于存在问题的一种认识进步,它标志着人们获得了关于存在问题的更为科学的认识。在公共行政学史上,对 “行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发现就是这样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人们获得了关于公共行政存在本质的更为科学的认识。这就是:公共行政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它的存在是以政治这一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不仅不能独立于政治,而且只有在政治过程中才能证明它的存在,也只有在政治过程中才能获得它的完整性。因而,行政官员不可能仅仅是技术性的,不可能仅仅追求效率,相反,“公共行政官员是政治性的,当他在开始阶段帮助形成立法的时候,而今天的多数全国性立法都是这样形成的;他是政治性的,当他与总是试图影响他——既在起草立法的过程,也在执行它的过程之中——的压力集团打交道的时候;他也是政治性的,当他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与其他公共机构发生关系时”[14](P4)。而由于行政官员的政治属性,“就其对于民主政府的重要性而言,行政责任并不亚于行政效率;从长远来看,它甚至是行政效率的一个促进者”[15](P13)。由此,政治这一他者得到了承认,责任这一从他在性的角度衍生出的价值也得以被增添到公共行政的价值量表之中。
如果说威尔逊是通过拒绝政治这一他者来确认公共行政的自我的话,到20世纪中期,当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公共行政是处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时,他们发现,政治并不是公共行政面对的唯一他者,除了政治,社会这一他者也在公共行政的自我塑造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马克斯看到,“与对行政过程的公共参与紧密相关的是政府活动在公共关系领域中的扩张。甚至相对独立自主的部门也已变得对公众相当敏感”[16]。显然,政府部门公共关系的发展意味着政府意识到行政过程并不是自足的,也不是完全由政治过程所决定的,而需要进行社会评价,接受社会这一他者的检验。进而,公共行政研究也需要承担起发掘社会这一他者对公共行政的自我有何影响的功能,在高斯看来,就是要开创一种关于公共行政的生态学路径。高斯认为,“仅仅将政府看做分肥——无论是某一经济阶级、政党或派系——的工具是不够的,尽管它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服务于这一目的。还可能存在一些如此广泛的环境变化,它们要求并维持一种公共而非私人的回应……因此,公共行政研究必须包括它的生态”[17](P5-6)。事实上,行政生态学在20世纪中期成为公共行政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随着这一路径的产生与发展,学者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公共行政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众多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也无时无刻不接受着这些他者对自己的塑造和建构。至此,他者的在场已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而在这一前提下,公共行政应当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继续或者说重新建构自己,就成了学者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面向他者的行政建构
在人类文明史上,“他者”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汇。从中国古代的 “蛮夷”到古希腊的 “异邦”,对于他者的称谓总是充满了鄙夷之情。直到今天,当庙堂学者们煞有介事地谈论 “文明冲突”时,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仍然暗含了某种不祥之意。不过,与古代相比,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可能对他者抱有某种敌意,却不可能继续无视乃至拒绝承认他者的存在,而只要我们承认他者的存在,就将不得不与他者开展交往,进而在交往中接受他者对我们的建构。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在19世纪后期的文官制度改革运动中,当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学者们试图为公共行政确立起独立的自我形象时,作为他者的政治像瘟疫一般遭到拒绝。而到20世纪中期,随着他者在行政过程中的存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公共行政不仅重新向他者敞开了怀抱,而且逐渐把他者及其存在作为自身建构的方向和依据。
关于公共行政建构初期对他者的态度,斯蒂福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它不是行政对政治的拒绝,而是男性对女性的排斥。斯蒂福斯认为,尽管女性参与了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她们的努力在当时是不被承认的,甚至,那些致力于建构公共行政的男人们还把进步主义运动变成了一场通过对女性工作的政府接收而实现公共行政的 “去女性化”的运动。结果,“女性只能在被视为小事情的话题上发言,而不能参与探讨男性视为公共领域的普遍话题——我们公共行政现在称之为公共利益的对话”[18](P33)。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公共行政中价值观 (善意、民主、公众)和技巧 (效率、管理)之间的核心冲突到处都有性别的影响:正如在改革中女性牺牲了她们从事慈善工作时独特的女性方法,以便达到公事化实践的标准,因此,公共行政为了效率至上也牺牲了民主”[19](P148)。根据这一解释,在公共行政中,男性是自我,女性则是他者,因而,对他者的拒绝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的拒绝,反过来,他者的获得承认也就是女性的获得承认。前者的结果是为了效率而牺牲民主,那么,随着后一种情况的发生,民主也将重新成为指导公共行政的一种重要价值。由此,随着他者的回归,民主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一种重要的建构方案。
基于 “新政”以来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发展,列维坦呼吁民主行政,将民主这一政治的或者说他者的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之中。他说:“行政程序体制远不止是执行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行政程序体制是每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行政程序体制的本质被认为与政府的哲学原则的本质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民主政府意味着在行政中也要有民主,正如在最初的立法中一样。为了人的尊严,出于执行法律而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与意识形态。”[20]这一呼吁得到了实践的响应。根据海纳曼的归纳,当时美国的行政实践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第一,公民投票与民意测验的发展,比如美国公共舆论机构 (AIPO)的成立,其职能是专门负责向行政部门传达民意;第二,农业部设置了用来讨论农村问题和改善公共政策与农村公共需要之间关系的委员会制度,建立起了一条直接面对行政部门的正式表达渠道;第三,利益集团在行政组织中代表渠道的增加;第四,听证等调查方法的应用,以及行政官员对调查结果的回应。[21]总之,行政机构的代表性与回应性显著增强,标志着公共行政树立起了民主的价值取向。
民主是一项政治原则,民主的实质内容则是要求保障社会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因而,民主实际上是公共行政所面对的两大他者——政治与社会——的共同要求。但从这两大他者出发,民主的具体要求是不一样的。在政治层面上,民主意味着民选机构之于非民选机构的优先性,意味着非民选机构需要对民选机构负责,具体来说,就是公共行政需要对政治负责。而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民主意味着所有政府机构都需要对社会负责,至于民选机构与非民选机构之间则没有必然的责任关系。如果政治部门与社会公众要求公共行政承担的责任是一致的,那么,对公共行政来说,对他者负责是没有什么歧义与冲突的。但如果政治部门与社会公众要求公共行政承担的责任不一致,那么,对他者负责就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价值选择。事实上,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公共行政面向他者的建构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以 “新公共行政运动”为代表,它要求公共行政直接对社会负责,因而强调社会公众对行政过程的直接参与。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新公共行政对回应性和社会公平的承诺蕴含着参与……强调的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22](P8)尽管通常并不被归入新公共行政运动之中,但奥斯特罗姆对民主行政的阐述则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民主制行政的基础,一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平等至上主义的假设,二是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给所有社群成员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代表考虑,三是把命令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最小的范围,四是把行政机关的地位从主子的行政机关变成公仆的行政机关”[23](P87)。简言之,就是要让行政机构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公民参与的机制和渠道。
第二个方向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行政改革中,它要求公共行政对政治部门负责。在60年代的 “伟大社会”时期,美国政府曾推行过一些以 “社区行动”和 “示范城市”为代表的公民参与项目[24],部分践行了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等关于民主行政的构想。但在70年代以后,由于 “伟大社会”的失败,这些项目迅速被取缔,而让位于尼克松所提出的 “新联邦主义”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项目与行政责任都被转移到了更低的政府层级,通常是州上。这不是第一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那种分权。权威被转移到了州和地方的民选官员,而不是分散化的公民团体与新公共行政官员手上……因此,它限制了新公共行政运动最初所支持的公民参与和灵活性。更重要的是,参与到这些新活动中的公民不是新公共行政运动所强调的受剥夺者,而更像是传统的利益集团”[25]。也就是说,民主行政受到了集团政治的污染,因而重新沦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另一方面,在1978年的文官制度改革中,以高级文官的设立为标志,政治部门对行政体系的控制得到了加强,行政官员对于政治官员的回应性也得到了显著增强。但这种回应性却与新公共行政运动所主张的对普通公民的回应性背道而驰,所以,“许多过去自称非常开明与进步的人——新公共行政人物——却最为抵制这些变化”[26],因为它们同样标志着行政官员沦为政治官员的工具与附庸。
总之,在意识到并不得不承认他者的存在之后,公共行政开始面向他者的建构,并在两个方向上付诸实际的行动。可以看到,朝向对社会负责的建构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它体现了学者们的一种价值诉求,而朝向对政治部门负责的建构则得到了实践的采纳,它反映了政治部门对公共行政控制的加强。这样,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脱节:一方面,理论逐渐失去了对于微观现实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理论也对现实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追根溯源,理论与实践冲突的原因在于对公共行政所应对其负责的他者的认识不同。因而,要让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良性的共同发展,促进对公共行政的积极建构,就必须清楚界定公共行政的他者,澄清公共行政建构中的他在性维度。
三、向他者开放
有学者指出:“在整个20世纪,政治与行政二分,不仅是行政学理论的一种叙事原则,而且也是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处于主流状态的行政学理论,无论是持辩护还是批评态度,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践方案的设计,都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维框架下展开的。可以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是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不仅是理论上的起点,同时也是实践的起点。”[27]而如果把政治替换为他者,行政替换为自我,那么,可以认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公共行政演进的基本线索。只是,公共行政所面对的他者并不仅仅是政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面对着社会这一更具普遍性的他者。如果说20世纪中前期的公共行政理论主要是围绕着公共行政与政治这一他者的关系而展开的话,那么,20世纪后期以来,公共行政与社会的关系则成了理论家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思考中,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才是时刻存在于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之中的他者,因而,社会的存在与要求应当取代政治的存在与要求而成为公共行政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公共行政不应按照自身的要求而进行行政建构,或是根据政治的要求而进行政治建构,应当根据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社会建构。
在公共行政领域,社会建构的主张是由全钟燮明确提出来的。作为最初参与拉莫斯在20世纪60年代南加州大学掀起的现象学运动的成员之一[28],全钟燮关于行政世界的认识受到了欧洲现象学哲学的深刻影响,后者帮助他在学术生涯的开端就形成了一种他在性的观察视角。这一视角促使他在70年代投身于比较行政研究,并惊喜地发现现象学的方法极其适用于对比较行政中比较对象——也就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分析。[29]而当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将学者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时,这一视角也帮助全钟燮提出了对公共行政进行社会建构的设想。
全钟燮认为,“公共行政存在于社会世界(也就是公共的)的背景中:它不是社会中一个孤立的实体。一个社会环境能改变行政管理者思维和计划的方向,同时,行政管理者根据他们的知觉、知识和体验解释着社会环境。通过与环境和公民的互动,行政管理者建构了社会环境的意义。因此,公共行政是一个正在进行中并存在于社会、制度、行政知识和个体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30](P51)。或者说,公共行政存在于与社会世界中诸多他者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过程之中,而无论作为关系还是作为过程,公共行政与他者之间都是交互影响的,都在互相建构着彼此。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公共行政建构着社会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会在社会世界中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而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建构则长期受到公共行政自身的排斥,这种建构被认为是与公共行政对效率和专业精神的追求相忤逆的。然而,在全钟燮看来,“我们经历的许多重大变革不仅仅是由于政府积极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尽管政府的积极干预具有多方面的效果,同时,社会变革也是民众在社会建构中经由集体选择与共同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政府官员是无法完成这些项目的”[31](P18)。因此, “21世纪公共行政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公民在提升公共价值中的积极参与能力。如果我们继续依赖政府和官僚的权力来强制地改变社会和世界,那么,我们将无法开启人类力图创造美好治理制度的潜能,在这一制度中,参与者能够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公共事务的各种挑战,诸如平等、社会公正、正义、包容、多元文化、参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等”[32](P24)。也就是说,21世纪的公共行政需要张开怀抱迎接社会对它的建构,这是一种向他者开放的立场。
不过,在法默尔看来,张开怀抱迎接社会的建构与真正向他者开放还是有距离的。“让公民介入决策过程对于真正的向他者开放而言还不够。后者还意味着不仅要让共同体介入自上而下的计划实施,而且要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当他的愿望与 ‘来自上面的计划’或行政者的专业判断相冲突时……若仅仅就量的大小来说,就需要一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是反行政的逻辑必然。”[33](P364)具体来说,“一种朝向反行政的转向包含一种朝向完全不顺从的政治的进步,这种政治不是在国家—公民关系,而是在公民—公民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心理能量的”[34](P281)。也就是说,真正向他者开放意味着公共行政及其官员要抛弃自己不同于甚至高于社会与普通公民的观念,放低姿态,首先把自己作为一个他者,进而从他者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与其他他者开展交往。在斯派塞看来,这就要求公共行政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种具有他在性的公民联合 (civil association),而不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目的性联合 (purposive association)。“通过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公民联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经几个世纪而传承给我们的有限治理体系中的政治权力的分散而有限的性质,并能够与之相协调,而不是相冲突。我们也将能够通过有利于减少压制与减轻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后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加的文化多样性。”[35](P107-108)也就是说,公民联合的观念与政治层面中的分权、法治、民主等价值很好地契合在一起,同时也符合后现代状况中的差异化语境,因而,以公民联合为建构的方向,公共行政既可以实现与政治这一他者的共在,也可以实现与后现代语境中高度差异化的多元他者之间的和谐。显然,公民联合的观念是对法默尔所说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具体阐释,它打破了政治与行政、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将公共行政变成与其他公民联合平等的一个他者,从而实现了公共行政对他者的开放。
当公共行政作为一个自在自为的行动主体而存在时,它的存在与政治、社会等他者的存在是并立的、对立的,甚至是冲突的。而当公共行政接受了他者化,变成了与其他他者平等的一个他者时,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公共行政与其他行动主体都作为他者而存在的结果,是消除了单纯作为对象的他者,进而,行动主体间的所有不平等关系也都不复存在了——行政不再只是政治的工具,社会也不再只是行政的控制对象。如果说自在性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他在性则绝不意味着以他者为中心,相反,它预示着一种彻底的 “去中心化”,当所有行动主体都把自己视为一个与他者一样的他者时,任何中心都已无处立足了,所有行动主体都处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都作为平等的行动主体而相互建构着。他在性的本质并不是以他者为宗旨,而是对他者的开放。以他者为宗旨意味着自我需要迁就他者,甚至为他者而牺牲,它导向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逆向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他者开放则为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创造了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主体之间可以付诸合作的行动,并通过合作来谋求共赢的结果,而不必继续挣扎于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之中。通过对他者的开放,公共行政不仅接受了社会的建构,而且也反过来实现了对社会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社会主体一道,共同参与了对它们所共同面对的行政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合作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向他者开放将导向合作的行动,在一个普遍向他者开放的世界中,公共行政将与其他行动主体一道合作开展公共行动。“因此,直面后工业化社会动荡、不断演进的社会环境是每一个组织不可逃避的任务。环境、组织、信息技术和民众价值观的复杂性迫切需要行政管理者通过与民众的互动、对话和信息分享,促成新的理解和思维方式,促成与民众的广泛合作。”[36](P2-3)
可见,公共行政的建构史呈现出一条从拒绝他者到承认他者、从面向他者进行建构到向他者开放的清晰线索,而这种演变的结果则是日益突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他在性维度。从他在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需要不断地向他者开放,并通过这种开放来谋求与他者的合作。公共行政不断朝向他在性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朝向与他者合作治理的过程。
[1][33]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米歇尔·苏盖、马丁·维拉汝斯:《他者的智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7,2 (2).
[5]John A.Vieg.“The Growt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Fritz Morstein Marx(ed.).Elemen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 Inc.,1946.
[6]Luther Gulick.“Science,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Luther Gulick,L.Urwick(eds.).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3.
[7]Dwight Waldo.The Administrative Stat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2007.
[8]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八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Donald Morrison.“Review: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Art of Governa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5,5 (1).
[10]David John Farmer.The Langu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ureaucracy,Modernity,and Postmodernity.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5.
[11]Marshall E.Dimock.“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7,31 (1).
[12]Paul H.Appleby.“A Reappraisal of Federal Employment as a Care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8,8 (2).
[13]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14]Marshall Edward Dimock,Gladys Ogden Dimock,and Louis W.Koenig.Public Administration.Revised E-dition,New York:Rinehart &Company,Inc.,1958.
[15]赫尔曼·芬纳:《民主政府的行政责任》,载颜昌武、马骏编译:《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Fritz Morstein Marx.“The Lawyer's Rol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Yale Law Journal,1946,55 (3).
[17]John Merriman Gaus.Reflection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47.
[18][19]斯蒂福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0]David M.Levitan.“Political Ends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3,3 (4).
[21]Charles S.Hyneman.“Review:Executive-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Democracy”.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2,2 (4).
[22]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3]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4]Robert A.Aleshire.“Power to the People:An Assessment of the Community Action and Model Cities Exper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2,32.
[25]Patricia Wallace Ingraham,David H.Rosenbloom,Carol Edlund.“The New Public Personnel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9,49 (2).
[26]Gregory D.Foster.“The 1978Civil Service Reform Act:Post-Mortem or Rebirt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9,39 (1).
[27]张康之、刘柏志:《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 〈行政学研究〉120周年》,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8]Michael Harmon.“PAT-Net Turns Twenty-Five:A Short Histor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Network”.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2003,25 (2).
[29]Jong S.Jun.“Renewing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ossibilitie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6,36 (6).
[30][31][32][36]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4]David John Farmer.“The Discourse of Anti-Administration”.In Jong S.Jun(ed.).Rethinking Administrative Theory: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Century.Westport:Praeger,2002.
[35]Michael W.Spicer.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te:A Postmodern Perspective.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