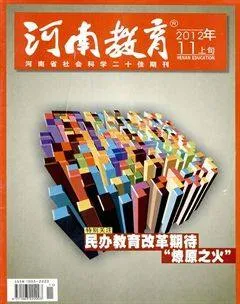让撤并学校回归对村民权益的尊重
教育部今年7月23日公布的《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意见》)提出,将通过县级政府专项规划和省级政府专项督察,解决农村学校由撤并引发的几个突出问题。其中包括: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应保证学生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不超过40分钟,明确农村小学低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明确盲目撤并的学校如有必要可以恢复,明确村小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可按100人核定,明确班额超标学校不得再接收其他学校并入的学生等。
盲目撤并农村学校的后遗症显现已久。2008年,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对甘肃等8省、自治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部分地区由于布局调整失当,辍学率出现反弹。例如甘肃山丹县7个乡镇的初中生被集中到一所育才中学后,九年级有的班级辍学率达20%。再如内蒙古赤峰市,6000多名初中生被从苏木(乡)集中到旗(县)的一所学校,产生了母亲租房陪读使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是政府的法定责任,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努力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良好义务教育的要求。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规范意见》征求意见后的最终确认,被舆论认为是对撤并学校政策执行不当的迟来的纠错。
《规范意见》还不够规范
始于本世纪初的全国范围大规模撤并农村学校是由当地政府主导进行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于减少教育投入、方便管理学校考虑,甚至撤并了不少生源充足的学校。在强制推进撤并的过程中,村民们反映的不愿意的理由合情合理,却都没有被政府部门采纳。撤并的结果是,当初村民所担忧的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严重、上学成本增加、低龄孩子不适合寄宿等问题全都发生了。一些变成了“巨无霸”的中心校,在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方面,给学校管理带来巨大的难题;被撤并学校遗留了大量尚可使用的校舍和教师,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相比既往对各地撤并学校所云“不要一刀切、不要一哄而上”笼统的原则性要求,此次《规范意见》提出的要求比较具体和量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要求明确规范农村撤并学校的呼声。可是,由于相关的描述仍然尚欠明确,《规范意见》仍有可能遭遇弹性执行乃至变相不执行,因此,《规范意见》能否改变盲目撤并的局面,还难免让人心中没底。
《规范意见》的不够规范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撤并农村学校的量化要求不甚明确。比如“应保证学生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不超过40分钟”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测算的?其主体是六七岁的小学生还是十二三岁的初中生? 路况条件有无崎岖、起伏?设置步行上课时间的标准,需要明确应因学生年龄以及当地路况不同而异。
其次是有些条文之间还不够协调。比如“原则上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1所初中”,和“各地要根据实际条件合理确定学校覆盖范围”是什么关系?学校的布局究竟是遵循前一条规定,还是后一条规定?相互不协调的意见会使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再次是关键措辞疲软。比如多处以“一般”“原则性”的字眼替代“必须”,看似尊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会给“必须”执行留下回旋余地,一些地方很可能以此作为搞特殊的理由。
过去10年间,农村小学数量在被撤并中已从2000年的55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6万所。地方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撤并学校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十分严重,而且十分复杂。《规范意见》出台的目的无疑是为防止诸多问题进一步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意见》对撤并学校的条件应再明确些,措辞再硬性些,各项规范之间再协调些,这是全社会的期待。
在农村学校锐减一半的现实下,此次《规范意见》已属“亡羊补牢”。至于《规范意见》提出的“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由于许多农村的教育生态已经因此被破坏得支离破碎,农村学校普遍的不景气并非想扭转就能扭转得了,或许真的如一首歌中所唱的“永远不会再重来”。
现实中的“死结”有待解开
我国中小学现行的编制标准,农村小学的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为1∶23。也就是说,如果一所学校有40名学生,最多只能配备2名教职工。显然,这样的学校连开展正常的教学也将相当困难。此次《规范意见》直面这一问题,力求在农村学校的编制问题上先行一步,提出“提高村小和教学点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这为化解现实中因生源少、教师编制不足使学校难以为继的问题,传递出了积极的信息。
然而,落实这条意见的前提在于需要解开现实中的“死结”:其一,核定的公用经费由谁来支付?当地政府不可能有这个积极性。其二,如果缺乏监督机制,这笔公用经费很可能出现“合法”的虚报冒领。其三,“有编不补”在农村学校长期普遍存在,《规范意见》能否促使当地政府为农村学校配齐教师?因此,除了强调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以及改革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办法,还应加强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建设,严格督促各级政府不折不扣执行,否则,《规范意见》很可能仅仅停留在纸面。
另一个有待解开的“死结”就是校车安全。据中国扶贫基金会2011年3月对老少边区贫困县168所完全小学的调查,撤点并校整合了农村教育资源,却为偏远山区徒步翻山越岭求学的孩子们埋下了安全隐患。比如贵州省榕江县高扒小学的孩子,每天需要往返3个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冬天上学在冰雪上行走还要靠手电照路,一些父母接送孩子上学的情况又不可能持久,于是配置安全校车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2011年造成群死群伤的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导致现实中出现了因没有达标车辆以及害怕发生校车事故,使农村学生出现无车可乘的局面。如果学生上学必须乘车,要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提供达标车辆,可问题在于,没有达标车辆,怎样做到既要有车又保障安全呢?可行的办法就是自定达标标准,如此一来,万一出了校车事故,由谁来承担责任?“既要保证安全,又让学生有车可乘”,这的确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规范意见》强调了校车安全,表示“坚决制止采用低速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以及拼装车、报废车等车辆接送学生”。实现校车达标,必须解决校车的经费来源。然而,在财政部门迄今没有拿出各级财政分担办法的背景下,达标车辆不到位、满足不了孩子们上学用车的刚性需求,就会有拼装车、报废车取而代之。针对不达标车辆出没于“江湖”,教育部门每到新学期开学,都会要求各地对校车进行专项治理。“不达标车辆接送孩子上学→发生安全事故→每学期一度专项治理”,如此形成的“周而复始”依然在今天延续,治理前景不容乐观。
纠错从完善决策机制入手
通常,一项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纠错是正常的,而纠错能不能收到好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政策制定时是否尽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其次在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是否采取有力措施及时遏制。遗憾的是,撤并农村学校的政策在这两个环节上做得都不够,以至于使整合教育资源和师资优势的初衷大打了折扣。
比如一些农村学校被撤并时,政府部门向当地反对的村民解释,撤并是为娃娃们上好学考虑,可以有更好的老师,有更好的教室云云,可村民并不认同。孩子到那么远的学校上课,每天来回几个小时,路上的安全怎么保证?集中到一个地方上学,一个班并进了七八十人,是为孩子上好学考虑吗?如果制定政策时多一些站在孩子们求学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不当撤并”的后遗症大多是可以预防的。
再比如对执行撤并学校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是有察觉的。2009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对农村“撤点并校”,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只可惜这番话没有对地方政府起到约束作用。难怪有评论说,此次《规范意见》早在撤并学校之初就该公布。
撤并农村学校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村民表达的意见不被尊重。此次《规范意见》中明确的一些“硬性要求”,比如学生步行上学单程不得超过40分钟,仍是政府主导的思维。如果有村民代表参与制定政策,那么,围绕撤并学校的学生上学路程、校车接送、寄宿管理、撤并后学校的班额、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在充分讨论中形成解决方案。这样的决策机制得到的结果,远比政府出台《规范意见》更符合当地实际。
作为一项影响面极广的民生政策,撤并农村学校由于严重缺乏当事村民的参与,导致政策一出台就疏漏百出、“带病运行”,必然是折腾了村民,又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实,解决撤并农村学校相关问题的根本指导精神,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有明确表达: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
社会在发展,科学地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利益相关的全体村民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规划布局调整的标准和过程就不会拥有广泛的认同感和公平感。而要回归“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和保障村民权益的法治轨道,则应是此次《规范意见》的本意。
(责编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