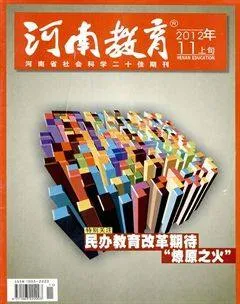且听吟唱
前段看到很多报纸上都在评说着10年来社会的风云变幻、个人生活中流逝的似水年华,也许是这些文字触动了我心灵上的弦,从来不喜欢总结回顾的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登上讲台竟然已经有好些年头。为人师的这十余年对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脑海里努力地寻找着答案。
一
我是在1997年考入的师范,在那里度过了3年的懵懂时光。3年里,老师们经常向我述说教师的伟大和光荣,但我没有丝毫的感觉。直到师范毕业前的实习,我才真正意识到做一名教师的真正意义。
学校为了方便管理,我们的实习被安排到了学校附近的几所小学,一人作课,老师和其他同学在下面听,回去后点评交流。当时我给四年级讲了节课,思路模模糊糊,效果自然糟糕至极,当时我窘极了。下课铃一响,我匆匆忙忙就走出了教室。
课后的点评和交流,老师和同学们把我的课批评得一无是处。我在旁边默不作声,静静地听着他们议论。
第二天,我独自一个人去了那所学校。在离学校不远的路口,我正失魂落魄地走着,耳边传来了一声清脆的童音:“老师好!”我抬起头一看,是个满脸稚气的小学生,戴着红领巾,大而亮的眼睛正看着我。
“你是和我说话吗?”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是啊!老师好!”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也好。”我慌乱地回应道。
他笑着跑远了,我呆立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跑进校门,融入了千百学生中,再也找寻不到。“老师好”,这是多么庄严而圣洁的字眼啊,竟然送给了仅仅教过一节课,并且一度对教师这个职业并无多少好感的我。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识才逐渐有了深刻的体悟,知道了它的内涵,体会了它的意义,开始真正渴望早一天毕业,登上讲台。
2000年8月,我被分到了母校任教。这是一所地处偏远的农村中学,校园很小,连个正儿八经的操场都没有,每天早上上早操,400多名师生就绕着坑坑洼洼的篮球场跑,学生摔倒是常有的事。
条件很艰苦,但我干得很卖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当时我教七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我无论备课、改作业,还是管理班级,一样都没落在人后。我也无法说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好像那讲台、那黑板、那课本,一样样都与我是如此之亲切,不能不为它们付出全部的热情和汗水。在这年的教学质量抽检中,我毫无悬念地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有次校长对我说:“新老师一定要在5年之内创出成绩,树立起自己的好名声,否则过了5年,再想去做就晚了。”
现在回想起这句话,虽然他说的有些偏激,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初登讲台的5年时间是最充裕的,没有家庭的牵累,也没有诸多琐事的纠缠,可以心无旁骛地干事业,出成绩自然是容易的了;5年已过,要结婚生子,种种琐事纷至沓来,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事业。
我拥有了所谓的资本;其实,让我更感动的还是学生。
我记得初秋的一天放学后,大大的太阳悬挂在天空,有风吹过,带来浓甜的收获气息。我和几个刚刚值完日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口的空地上闲聊,他们睁大好奇的眼睛倾听我讲述自己求学时候的历史,也把自己的感受和经历讲给我听。我们的心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成为我内心永恒的定格。
我也记得有个学生的父亲那年去世,有学生向我提议给该生捐款,我当即同意了。我率先把自己刚领的工资拿出一半投到了捐款箱中,学生们受到了感染,纷纷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零花钱,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捐了几百元。当我和班干部一张张清点的时候,觉得捧着的不是钞票,而是孩子们一颗颗纯洁无瑕的心。
我还记得那年中秋节过后,班上的一个学生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小心翼翼地把捧着的纸袋子放到了我的桌子上,纯洁的眸子里闪动着亮光:“老师,这个给您!”我尚未问是什么东西,他转身就跑了出去。我打开一看,是一颗颗涨红了脸的大枣,捏起一颗放到嘴里,是那种从心里生发出来的甜蜜。
二
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就这样持续了3年,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难道我一辈子只能待在这所农村中学,一辈子就这么简单而庸常地工作?
2004年3月,校长送给我一张听课证,让我去听上海大学李白坚教授的报告。我是第一次听到李老师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外出听这样的报告。当时我是第一个赶到报告地点的,旁边一位负责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了,他不停地感叹说:“不错不错,坐到前排好好听,回去好好咀嚼消化应用。”
门一开,我走进会场,坐到了第一排。听了李老师的报告,我了解到他与众不同的经历,也终于知道了一个教师除教学之外也可以大有作为,关键是要敢于梦想,勇于去做。回去以后,我利用几天的时间整理了李老师的报告,大约写了有2万字,不但有李老师的报告实录,还有我的感受,我还给这个报告配上了精心设计的封面。
有收获,也有困惑。我着手给李老师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写的书和指点。这封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的信发出去不久,我就收到了李老师寄来的书和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告诉我,只要好好去做一件事,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的。
上海大学的教授能这么对待一位来自农村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老师,让我大为感动。我反复阅读着李老师的专著,把里面的实例经过改编运用到了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许是我的水平太低,也许是我处理不当,收效甚微。虽是如此,但我毕竟迈出了研究的第一步。至今想来,自己能在当时毫无研究气息的氛围中踽踽独行,也算是一种勇气。
在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语文课堂,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写下了一大摞教学笔记。
后来有次听了特级教师陈钟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一线教师其实手中掌握着最鲜活的教学案例,这是最最宝贵的资源,只是很多老师没有去用的意识,没有把它们扩展成为文章,如果一线老师有意识朝这方面努力,很快就会有收获。
陈老师的这番话顿时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为什么不去写呢?
三
对于写作,我除冲动和热爱外几乎一无所有。一位同事告诫我说:“穷乡僻壤的小地方的老师,就是写也难写出啥名堂!”他失落的话语让我不免担忧,可年轻的心里升腾起来的勇气促使我硬起头皮去闯一闯,我不相信,甚至狠狠地想,我就坚持10年,如果不成功,我就放弃!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漫漫征程。
没有人指点,我就默默冲向书海。学校那间许久没有人开启的书柜成了我最神往的地方,一本本泛黄的教育书籍转到了我的案头。学校订的教育报刊也让我留恋不已,平日里它们总也无人问津,堆放在校长的档案柜里,他都觉得碍事,现在看我看得津津有味,很大度地全部“下放”给了我。我很细心地拂去它们上面的尘土,一页页地翻看着,一点点地勾画着,一行行地摘录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翻看它们上面。
我知道,写东西要先过文字关,做到这一点还要靠文学书籍。为了迅速过关,我没少在灯下翻阅,一本岳麓版的《红楼梦》,我至少看了10遍。记得有次给学生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有个学生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当我把满满一本摘录下来的《红楼梦》诗词赋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惊愕了,继而眼睛里流露出钦佩和敬仰。
每天的早自习,当把背诵任务布置给学生以后,我也没有闲着,坐在讲桌前开始背诵诗词曲赋,从《唐诗三百首》到《宋词鉴赏辞典》,从《龙文鞭影》到《韵律启蒙》,从《御选唐宋文醇》到《古文观止》,我一点点地啃噬着,一篇篇地背诵着。曾经有次学生嫌课文长,不想背诵,我说道:“这样吧,老师给你们背一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你们听听如何?”当我把这首长篇七言古诗流畅地背诵下来后,教室里啧啧声一片。我没有多说,学生的抱怨没有了,响起的是一片清亮的诵读声。事后我告诉学生“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其实真实的意图是为了圆心中的文字梦。
我断断续续也写了好多篇稿子,可发出去的几乎都是石沉大海,得到回复的也是退稿和不用。我没有灰心,我知道被认可除了努力,还需要时间,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
2006年12月,我的第一篇作品《一生珍藏的礼物》终于在《教育时报》上发表了。虽然这只是一篇散文,但对我的鼓励很大,因为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终于获得了肯定。
进入2007年,我又有多篇作品见诸报端,其中教学论文占了很大一部分。有次我尝试着把学生的作品发给了《中学生阅读》的编辑李梅斌老师,没想到她竟然给我回了信,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希望我经常把学生的作品发给她。在李梅斌老师的支持帮助下,我辅导的学生已有多篇文章发在了这本全国知名的中学教辅刊物上。通过此,更是让一大批学生爱上了语文,爱上了写作。有个经我辅导发表过作品的学生来拜访时,说上学时候让他收获最大的就是曾经发表过作品。现在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在书中游弋特别爽快,而且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当别人为写个总结计划搜肠刮肚时,他几乎不用准备就可一挥而就。“老师,真的谢谢你!”听完他诚挚的谢语,我的心里盛满了甜蜜的喜悦。也许,为师者能存留在学生心中如此之记忆,此生足矣。
2008年,我的《〈梨一样的苹果〉阅读》刊发在了《中学生阅读》第4期上,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年的河南省中招语文试卷竟然选用了这篇文章,并且有3道题目与我的命题几乎完全一致。当接到李梅斌老师发来的信息时,我喜极而泣:这么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让我能够骄傲地站在了教学的制高点,我并不比那些占有优势资源的老师们差!
2012年秋天,我坐在电脑前翻看自己6年来发表的文章,发现竟然有200篇之多,其中有不少刊登在《中国教育报》《中学生阅读》《教育时报》等颇具影响力的报刊上。
四
我写下这段自述的时候,脑海里忽然想起了宋代文人柳永从皇帝那里获得的批语:“何要浮名?且去填词。”我不禁感叹连连:自己的这段自述何尝不就是一番浅吟低唱呢?述说着自己的经历,历数着自己的收获,用一行行文字展示着自己为人师后的每一个脚步,每一点成长与进步——这也算是对自己从教以来的一次总结吧。
(责 编 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