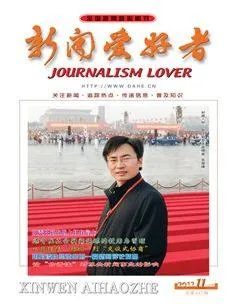电视法制节目“乱象”探析
【摘要】电视法制节目是以电视为传播媒介,以传播法律知识为内容,以普法、释法和指导用法避免或减少犯罪为宗旨,关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电视节目,为我国实现法治化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法制节目的繁荣,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除目前法制节目娱乐化、同质化现象备受关注之外,法制节目本身存在的“乱象”也愈渐明显,这与法制节目倡导的法治精神是相违背的。本文从“乱象”入手,探讨法制节目“乱象”的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
【关键词】法制节目;乱象;探析
1985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法律与道德》栏目的创办,标志着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产生。在这一年,中宣部、司法部制定的“一五普法规划”要求:“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都要由专人负责,办好法制宣传栏目。”随之各级电视台纷纷开办了名目众多的法制栏目。法制节目的“繁荣”对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有些由于制作者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律素养,媒体缺乏自律机制、审核把关不严等原因,在选题、表现方式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违法治精神、违法甚至犯法的“乱象”,给社会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我国法制节目中存在的“乱象”
第一,报道内容过实与失实。
报道内容过实。新闻的价值在于真实性。但在媒体的报道中,对某些题材的真实报道就可能不被许可,甚至可能违法,报道过实可能产生“悖法”现象。“有的法制节目为争夺收视率,过细展现犯罪分子的作案方法,全面再现犯罪过程,详细披露司法机关的侦破思路、侦破方向和侦破手段,对未成年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有的出现凶杀场面、有被害人家属悲痛欲绝的表情、有犯罪嫌疑人被擒拿后的垂死挣扎……这些报道的内容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让人看后感觉很不舒服。”[2]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2000年1月金华未成年人徐力一案,有关媒体的报道严重违反了现行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在某些媒体的首次报道和追踪深入报道中,徐力的真实姓名、所在学校等关于嫌疑人的个人资料全都公之于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有些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鉴别能力较弱,如果媒体提供了大量的涉黑、色情、凶杀等犯罪类的法制节目,会使他们对犯罪行为产生一种内在的倾慕,甚至去模仿。比如××电视台《××说法》有一期节目中,曾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2003年11月28日,湖南衡阳连续发生青少年抢劫案件,受害人报案以后,抢劫者的同伙主动到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经过警方调查,最后认定其所提供的破案线索都是假的。破案后,公安机关才弄清楚,原来他们为了保护同伙,故意提供虚假线索,转移警方视线,逃避警方追捕,而这些反侦查方法都是他们从电视法制类报道中或电影警匪片中学到的。
故事化和娱乐化导致新闻失实。法制节目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关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设法制栏目,竞争渐趋激烈。竞争一方面给法制类节目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利于节目本身发展的“乱象”。法制节目的故事化和娱乐化消解了法制节目本来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某些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和轰动效应,不惜在涉及伤害、抢劫、强奸、色情、诈骗等恶性刑事案件的报道中过分夸大渲染,甚至胡编乱造,节目中出现不当的画面表达和语言描述,严重损害了节目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造成了新闻侵权。如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尹东桂案件:尹东桂因贪污受贿被起诉,在案件审理期间,媒体对她进行了很多报道,夸大渲染,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被称为女张二江(张二江号称五毒书记,吹、卖、赌、贪、嫖五毒俱全,曾经与107名女性有染)。为此,尹东桂提出了侵害名誉权诉讼,经法院审理查明,媒体构成侵权,一审判决赔偿尹东桂经济损失2.8万元,同时给她2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指出:有些制作者有急功近利的倾向,疲于应付播出节目的数量而导致一部分节目粗制滥造。“许多案件的事实、证据、相关背景、条件、司法机关裁判的理由甚至一些基本的法律程序和根据都没有搞清就急于制作,只得大量省略或删改细节,容易造成事实不清和评论者的片面评论。”[3]作为电视节目,合理运用各种手段追求收视率以提高节目的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但是法制节目的宗旨是护法、普法、释法和指导用法。
第二,采编方式失范。
偷拍偷录、身份冒充——采访误区。偷拍偷录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但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代言人”的新闻媒体有一定的监督权力,新闻界偷拍偷录在一定条件下是被允许的,如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不得不使用之。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采访既受法律保护,又受法律制约。然而,目前没有一部专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力,人们对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有的权力理解模糊,甚至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自己应有的权力也无法明确,这就使得一部分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采访过程中难以把握尺度,不知不觉地做出一些违法行为,造成侵权。有些记者使用法律禁止的偷拍偷录器材,在采访过程中假冒嫖客、假充人贩子等进行卧底暗访。如果记者没有参与到事件当中,只是客观地观察和记录,没有推波助澜,也不构成侵权。可是在一些暗访和偷拍中,记者主动扮演一些角色,还使事件有了质的发展,这样记者就违反了《刑法》,可能犯“引诱别人犯罪”罪。有些新闻从业人员越位成为“警察”、充当“执法者”的现象在法制报道中也屡见不鲜,这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我国《刑法》第279条之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从重处罚。”只要是行为人冒充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来谋取非法利益就构成了此罪的要件,就可能触犯法律。
“真实再现”——引发负面效果。目前,在法制类节目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表演”成分过大,甚至为了引发观众兴趣,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不惜对一些恶性情节详细地加以描述或再现,让人倍感惊险刺激。有些节目甚至演绎如何偷盗、如何杀人等。某法制栏目有一期节目讲一个男子和两名女性发生了关系,然后把她们捂死,再后来碎尸、吃肉的报道,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宁夏发生的为了抢枪而袭击110的案件,被某栏目“真实搬演”上了荧屏,当一个罪犯对警察描述引埋在路上的炸药炸毁警车的情景时,脸上洋溢着得意、满足的神情,真是令人费解。“真实再现”是法制节目常用的报道手段,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旦节目的报道尺度把握不好,就会引发严重后果,甚至会犯传授犯罪方法罪。《刑法》第295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法制节目的制作人员更要牢记法制节目的宗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降低媒介暴力的消极影响。
第三,影像声音处理不当。
报道过程中影像声音处理不到位,引发侵权。某法制节目记者在跟拍“三陪小姐”时,镜头里摄入了与“三陪小姐”在同一餐厅用餐的一名年轻女子,竟未加处理一同播出,使得这名年轻女子的名誉无辜受损。法制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技术处理不到位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在查阅有关法制节目的视频资料时,发现很多法制节目在播放时对报道主体的肖像没有做仔细处理,特别是在做有关未成年人受害的节目时,经常只是简单地蒙盖上受害人的眼睛,其他肖像识别系统都没有处理;有的虽然在受害人脸部打上马赛克或进行虚化,但是对其家人和家庭环境都不处理,这样仍然能通过各种信息推测出受害人的相关资料。
错用法律术语,导致媒体审判。法制节目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犯罪嫌疑人被五花大绑示众,新闻报道者动辄以“罪犯、犯人”称呼之,在法院未判刑之前,就给犯罪嫌疑人话语定罪,形成“媒体审判”,违反了未经审判、不得定罪的原则,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一个人有罪有错,媒体不能随便给其乱加恶名。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容践踏,即使是腐败分子,也不可以随便打、随便骂,法律对他的人格尊严给予同样的保护。法院判决只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但作为人的权利还存在。法治时代,已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媒体更有责任引导人们走出误区,更好地理解法律意义。
法制节目产生“乱象”的原因
第一,新闻自律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尚没有出台《新闻法》,这对规范新闻监督过程中的“乱象”来说是严重的缺失。此外,我国新闻自律机制不够完善。发达国家限制媒体或规范媒体行为的法律也并不多,但是其媒体自律机制却非常完善,在涉及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上,都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机制。在新闻职业道德和电视的节目标准中,媒体自己制定行为准则,遵守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和投诉。新闻自律机制不完善,对媒体报道就不能很好地规范,特别对法制节目中的暗访偷拍现象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比如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行暗访偷拍、何种偷拍工具可以使用等。
第二,节目制作人员。法制节目“乱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制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不高造成的。节目繁多,制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素养缺乏、责任心不强等。还有人照搬书本知识,观众看后不知所云,往往只看到了案件本身,却并不理解案件里包含的法律内容。有些制作人错用法律术语,滥用“十恶不赦”、“恶魔”等污蔑性术语,间接干涉司法审判,形成“媒体审判”。再加上有些制作人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大肆夸张渲染案件本身,使案件故事化、娱乐化,对案件的侦查过程和手段也不加选择地报道,更有一些制作人员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妄加评论。还有些节目制作人在节目制作时粗心大意、把关不严,图像技术处理不到位,也同样会产生新闻侵权等违法行为。
第三,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矛盾。《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据此,新闻媒体承担了部分舆论监督的功能。同样,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权是依法独立行使的,除了对产生它的人大负责之外,不受任何非法干预。由此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就存在一些矛盾。观众常常会对媒体报道的监督功能产生误解,往往把媒体作为“包青天”,有事找媒体而不诉诸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如此司法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的破坏。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遵循“无罪推定原则”,许多媒体对相关案例的报道却有违这一原则。有些法制报道为追求时效性,甚至在法院介入前或未作出判决前就针对一些热点法律问题、案件进行品头论足,形成“媒体审判”,干扰司法审判,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如“张金柱案”、“夹江打假案”等。此外,法制节目中经常涉及司法腐败,也会造成降低司法权威、影响司法系统声誉的不良后果。法制节目中有庭审直播,司法部门对入堂记者带的采访工具和采访方式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有些记者违反规定,私藏禁止带入的采访工具。
法制节目“乱象”治理对策
第一,电视媒体本身要进一步改进。
报道内容要层层把关,报道方式要掌握好分寸。法制节目的报道内容要层层把关,报道要客观公正,避免涉及国家明令禁止的范围,避免涉及新闻侵权,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在作有关未成年人的报道时一定要慎重选择,不能仅仅考虑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漠视新闻客观存在的对受众包括未成年人的涵养作用。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细节和手段要淡化。过分地细化报道无疑有“指导”别人犯罪的嫌疑,也容易使一些不辨是非的未成年人模仿作案,甚至学会反侦查。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罪犯和未成年受害人应全部采用“马赛克”或虚化处理,避免暴露其他识别标志。慎用“真实再现”的报道方式,坚决杜绝大肆地“再现”血腥杀人等作案过程,回避尸体、凶杀血腥等场面,避免观众产生不适反应;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要做倾向性的报道,避免由“媒体审判”造成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地少使用暗访和偷拍手段,避免误导观众。
提高节目制作团队的法律素养。节目制作团队的法律素养高低关系到节目本身的质量。一个好的法制节目制作团队不仅应该具备优秀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我们并不强调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必须确保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本行业涉及的法律知识和行业规则了如指掌。只有了解什么内容应该报道、怎样报道,才能减少媒体对公民或法人权利的侵害和对司法公正的妨碍,才能在报道中不会出现法律常识错误,不会误导观众,媒体也不会因此经常被推上被告席,因此加强法制节目制作队伍的法律素养刻不容缓。
加强人文关怀,规范使用法律术语。河南电视台李玉洁认为:“应该把法律事件从案件转向人本身,法制节目必须关注人、帮助人、教育人。”节目制作人特别是主持人应该有较强的人文关怀意识,从节目的选题到节目的拍摄录制,以及最后节目的播出都要深深浸透着人文内涵,不能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违背道德伦理。有的法制节目的“真实再现”可能会伤及很多人,比如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节目邀请专业人士对节目中涉及法律的阐释,也应当浅显易懂,避免照本宣科,使受众能真正理解法律条文的内涵。法制新闻报道要求法制节目制作人运用法律术语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否则会使人对新闻报道的事件和内容产生歧义,影响宣传效果。报道用语一定要认真辨别、运用准确,否则就会在内容上产生歧义,避免使用“杀人恶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场毙命”等词语。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案例的报道在涉及案件定性、量刑及未成年当事人名誉等诸多方面的时候,应尽量体现理性、公正和法治精神。
第二,端正观众看待法制节目的态度。
作为法制节目的观众,不能一味追求节目带来的感官刺激,而应积极思考节目中案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学习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规范自身的日常行为。如果和未成年人一起观看,应积极引导他们,必要时向他们解释相关法律的内容,消除未成年人的好奇心和模仿心理。观众在思考节目的借鉴作用和教育意义时,也可以站在一个高度理性的角度对节目进行评价,帮助法制节目真正实现规范化。可能有些观众看节目的目的是从中“推敲”作案手段和反侦查手段,当然这类观众动机不良,一旦犯罪,迟早会被法律制裁。
第三,正确处理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法制节目大多在司法机关已下结论(如判决后、提起公诉等)之后再发表意见。对于已决案件,即使发表不同意见,也应尽量避免片面极端的评论,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对于未决案件,记者有权利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跟踪报道,但只能作转播或庭审实录,不能发表倾向性意见,更不能在报道中擅自下结论,或者自称代表群众的意见给审判人员施加压力。媒体与司法都是社会中平等而相互独立的系统,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只应限于贪赃枉法、违反程序、吃拿卡要等工作作风与办案程序方面,对于法律的运用则无权进行干涉。司法机关有时会为了增强司法透明度,而采取公开审判、庭审直播等方式,这时就依赖媒体报道来增加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所以司法机关在特定的时候需要寻求媒体的帮助。当然司法部门应杜绝腐败行为,呈现给媒体公正严肃的正面形象,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是说避免和媒体合作,必要时司法机关确实应该和媒体交流沟通,以期在媒体监督的压力下,真正提高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第四,完善法律自律机制。
法制节目自律机制不健全,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新闻媒体主管机构的国家广电总局近年来在规范媒体报道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为规范电视法制类报道,国家广电总局规定了11种禁止或限制类行为,要严格控制绑架、纵火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和恶性刑事案件的报道;不得过细披露执法机关的办案细节、侦破手段等;不得对犯罪行为、作案手段、犯罪心理做过细描写与分析;不得渲染凶杀、暴力、色情、恐怖等情节和场景;不得报道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种内容等。对于法制类新闻报道,国家广电总局重拳出击遏制追求猎奇刺激和娱乐化的倾向,对法制类节目片面追求收视率超过必要限度的谬误做法予以必要的行政处分等,这些规定对治理法制节目“乱象”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呼吁出台《新闻法》。
我国社会各种法规日臻完善,唯独新闻法滞后。新闻媒体行业仍依靠散布于《宪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广告法》的一些法律法规规范报道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缺乏对新闻这一特殊行业的针对性,而且在实际运作中漏洞颇多,这是法制节目记者常常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媒体如何履行新闻监督的责任?媒体如何确保在报道的同时不会同司法独立相冲突?媒体如何在保障当事人对案情知情权的同时不侵犯其隐私权?偷拍偷录到底应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是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解决的。总之希望我国的《新闻法》早日出台,使我国的媒体运作走上规范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张晓禾﹒国家广电总局要对法制节目“消毒” 称其危害年轻人[N].华商报,2006-11-18.
[2]诸葛红梅﹒办法制节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魅力中国,2010(10).
[3]范愉﹒电视法制节目评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7).
(张如成为中国矿业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世存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党教学科主任,讲师)
编校: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