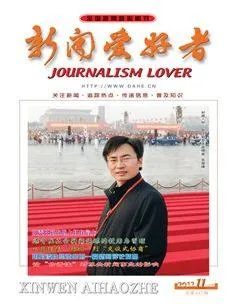我们应当怎样做记者
上午通知我演讲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做父亲,做父亲对他来讲是将来的事,可他写了这么一篇著名的文章。而许多做了父亲的人士却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来。
现在要说怎样做记者,而做记者是你们将来的事,你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良好的基础知识和文字功底,现在又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对将来一定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有的同学恐怕还有自己的计划和设想。如果要做“将来怎样做记者”的文章,一定会比我做得好。
至于我,虽然已经做了30多年的新闻工作,却反倒感到无话可说。实际上,我自己的工作也好、经历也好,的确也没有多少可讲的。但我既然是《新闻爱好者》杂志的主编,那么,自然对新闻界一些知名记者的经历、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等多少有一些了解,那就不妨和同学们聊聊这方面的情况。
同学们要我演讲“我们将来怎样做记者”,首先,我也要提一个问题:“你们将来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坊间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叫“一等记者拉广告,二等记者拎红包,三等记者搞报道”。你是想做一等记者、二等记者,还是要做三等记者呢?能做“一等记者”“二等记者”,当然很好,可惜我对此没有研究,没法跟同学们交流。
我想,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立志将来做“一等记者”“二等记者”,或者谋取更高的职位,那都是你们自己的权利。但是,第一步,从“三等记者”做起,积累一些经验,肯定也会大有好处。如果有兴趣,也不妨在此听我絮叨一番。
那么,我现在要演讲的内容,严格地说,其实是说我们将来怎样做个“三等记者”的问题。
“三等记者搞报道”,既然要搞报道,那就要解决报道什么或不报道什么的问题。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根据彼时彼地的情况,会提出具体的要求,又会有许多具体的限制。这是真正到了记者岗位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也没必要说。能说的还只是一个要负起“社会瞭望者”责任的问题,是要按照“社会瞭望者”的职责来抉择你的行动,来决定你自己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你作为记者的职业、记者的身份,你的社会责任感,决定你一定要忧国忧民,一定要和普通的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你若是仅仅拿记者的身份当作“敲门砖”“通天路”,当作晋升阶梯,那你可以去“傍大官”“傍大款”,你可能平步青云,也可能升官发财,但你肯定不会是一个好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新华社老社长、著名新闻记者穆青同志和他的老搭档冯健、周原,继60年代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又采写了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读了之后,浮想联翩,激动不已,提笔撰写了“本报评论员”文章《不信东风唤不回》。据范敬宜先生说,当时仍然“心潮难平,中夜转侧,忽成一律,以尽评论之所未言”。这首律诗是这样写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新篇续就意难平。
豪情满纸见肝胆,卓识如炬明古今。
论议常含贾傅泪,怀民总带杜陵心。
拳拳心曲谁评说,读与穷乡父老听。
这几句诗是说,穆青同志年事越高文章就越老辣,从《人民呼唤焦裕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豪情”“肝胆”和“卓识如炬”。他的忧国忧民,就像汉朝的贾谊、唐朝的杜甫。“论议常含贾傅泪,怀民总带杜陵心”,这应当是我们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必须说真话,至少是不说假话或少说假话。自古以来,说真话有不少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说假话行不行?有的时候也不行。我年轻的时候,经常遇到政治运动,每个人都得做政治表态。那时候,“阶级斗争为纲”,事事得有个“态度”,否则就是“划不清界限”,就是“跟党不一条心”。你想不表态吗?有人就会以组织名义对你说,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所以,那个时候违心地说一些什么话,违心地举手通过什么,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我这里提出这么几个层次:一、要说真话;二、不说假话;三、少说假话。特别是关系人民生死的问题、某些非常急迫的问题,冒死也要说真话,冒死也要以可能的形式反映出去。鲁迅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要当个好记者,要尽到“社会瞭望者”的责任,就应当以此来自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某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一点或几点上,专业之外,漠不关心,不感兴趣的事不屑一顾。有的地方极注意,有的地方极不注意。注意的地方,心细如发,纤尘可见;不注意的地方,熟视无睹,菽麦不辨。因此,他不大会看人眼色行事,往往见微知著,“危言”耸听。像老舍先生说的那样,“在别人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你们说,这样的人会受到权势者的欢迎吗?你们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想做这样的记者,那么,我再讲讲做记者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我想起著名记者艾丰同志的一句话。他说:“名记者手里没有‘魔杖’。”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不可能他教你几句口诀,你背下来照着做,也就可以当个名记者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对我说,他和通讯员一起去采访,提什么问题,人家怎么回答,都是公开的,不保密啊。可写出的东西很不同。这是为什么?
你可以说是水平有不同。不错,水平有高低。可水平是怎样形成的,不同的表现在哪里?艾丰同志说:“面对采访得来的一大堆材料,我考虑些什么问题,考虑问题的角度、深度与同去采访的通讯员不同,这个他不知道。”这就有区别了。区别在什么地方?
一、我考虑:记者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他看问题的着眼点与常人不同。记者的眼光,他看什么问题,都有一个标准、都用一杆秤来衡量,这杆秤就是新闻价值标准。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挑出来,突出地去表现它;没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可以视而不见,舍弃它。记者写的新闻和一般工作人员写的总结材料、领导的讲话稿有很大不同。我曾经在一个大机关工作,和做组织人事工作、做文秘工作的同志混得比较熟,他们戏称我们做记者工作的叫“本报讯”。什么叫“本报讯”?它是报纸上常用的显示是由该报纸获得的消息的一种标志。“本报讯”一般都是一事一报,比较简短,记者经常采用这种形式在报纸上发消息。称记者为“本报讯”,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记者工作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做记者工作的同志回敬他们一句什么话呢?我们戏称他们是“一、二、三、四”。因为他们写的总结材料和讲话稿往往是面面俱到,讲了一个方面接着讲另一个方面,讲了第一个问题以后再讲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一直罗列下去。“一、二、三、四”也概括了文秘人员写材料的特点。两种特点反映了两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着眼点不同,行为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中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让北京市委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是在一次会议中做出的,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是对整个会议的报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淹没在整个会议的报道中,很不起眼,很多人没有注意。而新华社却把它挑出来,用了百十个字,单独摘要报道了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称“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让全国人民振奋。因为1976年4月5日,人们借清明节之际,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究竟是革命活动,还是“反革命暴乱”,一直是人们争论、关注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急切地盼望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现在果然平反了,自然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人民日报》瞅准了,把它单挑出来进行突出报道,自然取得了轰动效应。《北京日报》虽然不可能不对那次会议作比较全面的报道,但把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大的事情淹没在一般的会议报道当中,没有单独成篇地予以突出报道,可能有他们的不便之处,有一些我们现在体会不到的难以言表的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历史地看,总是一个败笔。
记者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地方,是他们更注意事物的变化。一般来说,事物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影响力的大小与新闻价值的大小成正比。俗话说,“变动出新闻”嘛!因此,记者比较注意不正常的现象和反常的现象。当然,这种“不正常”和“反常”现象与我们通常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概念不是一个意思,不是指好或坏、正面或负面两种情况。新闻学上所说的变动是指对于某种常态的打破。而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或向坏的方面发展超出了通常的情况,都可以说是对一种常态的打破。《人民日报》老记者商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开始做新闻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青年。有一天,编辑部派他去采访一位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他到了剧场,发现剧场布告牌上写着这位女演员因故停演的通知。这时候他想:戏不演了,也就不用报道什么了。于是,打道回府,休息去了。到了半夜,当编辑部得知纽约的所有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那位女演员自杀的消息而唯独不见泰勒写的报道时,便把他从睡梦中叫醒,问他为什么没有把稿子送交编辑部。他此时还天真地回答说:戏都停演了,还报道什么!根本没想到要问问那位女演员为什么停演了。编辑气恼地批评他说:“像这样一位著名的女演员的首场演出突然被取消,本身不就是新闻吗?何况它背后还可能有更大的新闻!”这位年轻的泰勒先生之所以漏报著名女演员自杀的重要消息,原因就在于他的思维方式还不是记者的思维方式,没有意识到计划内的演出突然中止,其实就是对按时演出这种“常态”的打破,就有新闻可以挖掘。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记者的思维方式应当有自己的特点,除了正常的顺向思维以外,还应当有逆向思维、发散性思维、不规则思维、跳跃性思维,等等。有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在一条轮船上,一位记者给一个小学生出了一道数学题。记者问道:“什么情况下3+2不等于5?”小学生回答不上来,去问他的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想了好半天也回答不上来。于是,小学生又去问记者。这位记者哈哈一笑说:“做错了的情况下,3+2不等于5嘛!”这里记者的思维方式是发散式的,而小学生和他的数学老师则是按正常的逻辑思维进行推理,所以,3+2怎么也推不出5以外的得数来。①
记者不能老按常规考虑问题、按常例和常识来进行推理,那样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列宁早就说过,常识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才具有真理性。超出一定的范围,再按常识说事,就会出现谬误。据《羊城晚报》报道,1994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3月10日晚6时左右,在大连站西旅社,服务员在整理205房间时发现一对男女躺在床上,地上有6个空安眠药瓶子。后据大连站派出所干警调查得知,两人是夫妻,因丈夫嗜赌双双觅死,便买了6瓶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制药厂生产的“佳静”牌安定片服下,谁知欲死未成。这件事被一名干警迅速地写成稿件送到了新闻单位。3月12日辽宁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播出,并且称是“假药救了性命”云云。接着,3月15日,即“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当地发行量很大的《辽沈晚报》又以《夫妻轻生假药救命》为题,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进一步引申说他们服下的是“掺有大量淀粉的假药”。之后,该消息由上海《新民晚报》再次刊发,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时舆论大哗,给驻马店地区制药厂的销售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以当年的春季全国药品交易会为例,往年该厂的交易额总在1000万元以上,而当年不足100万元。驻马店地区制药厂以自己的名誉、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把辽宁两家媒体告上法庭。据说,经大连药品检验所按卫生部药品标准检验,该药含量完全合格。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有关药学专家的介绍揭开了其中的原委。原来,“佳静”安定片属于甲基三唑类药物,药效以镇静、安神为主,具有服用剂量小、治疗作用强、毒副作用小等优点,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安眠药(超剂量服用会因呼吸麻痹导致死亡)不同。一般来说,一次服用20瓶以下不会导致死亡。实事上,它不仅不是假药,而且还是“佳药”。据报道,经过多次法庭调解,最后原、被告达成协议,由辽宁电视台向驻马店地区制药厂赔偿30万元人民币了事。这件事情对于撰稿人和媒体的教训都是深刻的。诸如假农药使农妇寻死未成的奇闻传得多了,就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一种“常识”:凡未在一定剂量下致人死命的药物都可能是所谓“假药”。尤其是河南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往有过制造假药、假酒、假电线的“前科”,人们很容易产生联想,想当然地把他们还没有接触过的一种产品视为“假货”。以上事例说明,新闻记者如果不能从一般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不仅不能发现新的问题、新的事物,还会造成被动、造成失误,被谬误牵着鼻子走。可以想见,如果那篇稿件不说“假药救命”的话,它就不会引起官司;如果经过调查,而说明是“佳药”救命,则肯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外,新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还要注意研究著名的新闻记者具体的采写实例,从经典的新闻采写实例中得到启示。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是在校的大学生,没有那么多新闻采访机会,而且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因此,我主张多揣摩名记者的成名之作。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最终要在作品上见分晓。可是现在的新闻教学有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从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的来稿看,他们对新闻业务实践较少关注,对新闻写作、新闻作品的分析也不够。2002年第8期《新闻爱好者》发表的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的文章《“我是‘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子!”——李希光实说媒体教育脱离媒体实际》,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李教授说:现在一些新闻教育界的学者写些文章大多是起到一种哗众取宠的作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新闻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现在研究生取得学位、老师评定职称,都需要写论文,这对理论研究有推动,但不能忽视新闻采访和写作的锻炼。我这样说,绝不是轻视理论。理论一定要学习,要提高。但我们必须想明白:读四年大学新闻系所为何来?是为了将来留校搞科研、当教授,还是当记者、做编辑,从事具体的新闻工作?我看大多数同学恐怕是从事具体的新闻工作。新闻学是“事学”:学习新闻知识,要从解剖具体的事例入手。要研究一些媒体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研究一些著名记者的重要的采访经历和他们的得意之作、成名之作,建立对一些新闻作品的评论分析机制。我们今年专门组织了文汇报驻杭州记者万润龙写的《我这样与大师对话——采访霍金、丘成桐等科学家的问题设计》一文,从中可见一个记者面临重要采访任务的时候,应当怎样设计问题、提出问题,才能取得采访的成功。平时,我们还开设了《耐人寻味的采访》的栏目,专门介绍一些著名的采访事例,供读者学习研究。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不要这样写》,另一本是《应当这样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新闻写作上的得得失失的。结合自己的经历、体会,仔细揣摩他人的经验,我相信会在认识上产生一个飞跃。
注 释:
①现在叫“脑筋急转弯”,有了赵本山、范伟的小品来普及,已瞒不住大众了,但之前还是可以让老实人一时语塞的。
(本文为作者2002年记者节的时候对郑州大学新闻系2002级学生的演讲)
编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