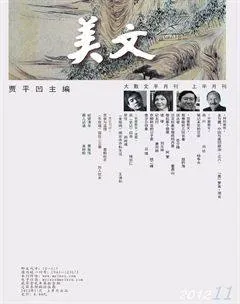鲁沙尔印象
吕锋
陕西眉县人,现居汉中,公务员,文学爱好者。
鲁沙尔风貌·民俗
我们的汽车穿行在海东湟水谷地的公路上,晨风中透出一股寒意,想来是雪域高原的落山之风吧。八月的青海高原,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这里海拔三千余米,内地秋苗正壮难耐秋热的时候,这里的麦田却是一片墨绿,油菜花才泛金黄,蚕豆又肥又厚的叶子在风中微微摆动,雾气浓重,似乎是一派早春气息。
在一百多年前的清代道、同年间这里曾发生过震惊西北、动摇清朝统治的甘青河湟回民大起义,西北乃至全国的回民积极响应,声势浩大,是清代末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最终被陕甘总督左宗棠所镇压,是西北地区回族反抗清王朝统治最为灿烂惨烈的一页。走进这块曾经名载史册的土地,山河依旧,群雕般的英雄已去,让人心情激动不已。
西宁南行二十余公里,穿过农业发达的湟水谷地,就到了藏胞视为圣地的湟中县城所在地——鲁沙尔镇,这里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之地,也是藏胞心目中的圣地。
下了汽车,须搭乘一种马拉的小篷车,这种交通工具,一次能载客四人,车厢四周各支起一根竹竿,用鲜艳的丝绸绷在上面做成一种类似花轿那样的伞盖,或方或圆,花色热烈,再饰以金黄色的穗子,马跑起来,系在伞盖四角的铃铛有规律地摇了起来,丁当作响,车子一颠一颠地往前跑,人坐在上面很是惬意,正好能消除旅途的疲乏。
根据大街上行人的服饰可以判断,这里聚居的主要是汉、藏、回、撒拉、土等几个民族的百姓。藏胞和回族从其服饰即可分辨。穿大襟黑色长袍,下摆镶有红、兰、墨绿等几色寸边,腰束丝带,灰色毡帽扣在自然卷起的头发上,脚踩皮马靴的为男藏胞,个别的腰间还挂一柄金光闪闪的藏刀;姑娘则服式不改,而色彩较多,尤以兰、绿、白、红相间者为主,最大的特点则是头发梳成好多个小辫子,或披在肩背上,或分成两股,分别辫在左右臂的外套衣服里,戴的帽子自然漂亮多了。回族的男性,无论老幼均戴着白帽,而女性则根据不同年龄,头顶墨绿、黑、白三色丝织盖头。撒拉、土族同胞,慈眉善目,无论男女,一般都是阔脸盘,大眼睛,且多为双眼皮,这种相貌的人在内地也许很多,但是在特定的地方,一眼就能感觉出来这是什么民族的人。
这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可能与地域开阔有关吧,这里一般的房子都比较低,很少看见高层的楼房。挂着的各种幌子,尤以挂蓝底白字布幌的穆斯林兄弟开的牛羊肉馆子为多,空气中充满着羊肉的腥膻和牛粪的混合气味儿,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它时刻提醒你,这里曾是西域的边缘地带,你的内心自然升腾起一种身处边地的情怀。
我觉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在这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我正沉浸于这种气氛之中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喊了我一声:“塔尔寺到了”。
宗喀巴·活佛·灵童
远望去,在一圈莲花形的小丘陵环绕的中心,有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群,气势雄伟,绵延成片,笼罩在一种吉祥、静穆的晨雾之中,若隐若现,恍若羽化之境。
塔尔寺因宗喀巴而知名,也因其而传名海内外。
宗喀巴,藏族、青海湟中地方人,俗名罗桑智华,因其创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善规派),俗称黄教而被奉为圣人,所以僧俗共尊他为“宗喀巴”,意为“湟水之滨的智者”。从这里,我们仿佛能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身影。我们知道,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土发展中逐步形成三大系列,即藏传、北传、南传,藏传佛教内部又形成诸多理论派别,在格鲁派诞生以前,在西藏地区把持佛教论坛的当属藏传噶举派,又称白教,因元世祖曾赠送黑边金帽给该派领袖,又称黑边金帕派。在公元1360年(元顺帝至正20年)的时候,白教一高僧噶玛巴·饶贝多吉由西藏经青海去北京,在途中见到三岁的罗桑智华,即称赞说:“此童子后当入藏,主持正法,犹如第二能仁也”。他就给年幼的宗喀巴受戒。从此,大师一心向佛,七岁削发,十六入藏,游学藏地各名寺,研习佛学,尤精于显密经论,取得很深的佛学造诣。他每读完一部经书,就参加一次大型辩论会,此即为以后的“辩经大法会”的雏形,果然在三十岁起,即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著《菩提道次论》《密宗道次论》两书,形成格鲁派理论基础。大师看到当时佛教徒戒律不严,有些僧人生活放荡,即推行宗教改革。为区分自己教派与其他的不同,把帽子翻过来,黄色的里子露在外边,从形制上予以区别,这就是黄教俗称的来历。
格鲁派历来受到政府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想与它的发展有极大关系。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即由黄教而产生。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嘉操杰和克珠杰分别是达赖与班禅两系的首任实际承受人,由此延续下来,就成了目前的格局,可见该派的势力与影响之广之远。它事关藏区的稳定与发展,也事关边疆的安全,这也是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政府十分重视藏传佛教的政治根源。
关于藏传佛教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活佛及其转世灵童的寻找这两件事情了。
活佛,按宗教含义即“乘愿来世之人”,说明活佛本身就是人,不过是死后能按自己意愿再生的人。根据教义,达赖(蒙语意为“大海”)是释迦牟尼的化身,而释迦牟尼是现世佛,即掌管人们现在世界的最高佛。而班禅(藏语意为“大学士”“圣人”)则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无量光佛则是佛教的理想王国——香巴拉国的国王,信佛行善的人死后能进入这个国度,在这里人能长寿,地上到处长满水果和青稞,潺潺的河水长年流淌,空气中弥漫香味,没有痛苦,只有快乐,想什么有什么。一句话,物质极大丰富的一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无怨无争。国王勇敢善良,像牧人对待羊群一样对待自己的臣民。而要想去这个国度,不但要自己终生行善,而且必须有班禅亲签的路引子,谁持了这个路条,上面画有通往香巴拉的路线图,据说,国址就在现在中印交界的某个地方。而想出发,必须从班禅的驻锡地西藏扎什伦布寺的一道影墙处起步,这样才能经过八十一劫难而到达香巴拉。
活佛的死,叫圆寂,他还要来世再生,所以在他死以前,还要留下偈语,言明自己将重生在什么地方,死后人们按活佛圆寂时头所面对的方向,去寻找他们的转世灵童,这是一项极其艰难而旷日持久的工作。按照政府的法令和宗教仪轨,分派几路人马,根据活佛死前的暗示及各种瑞兆,要找到活佛死时诞生在同一时间的儿童,有时一下子就找出几十个,但是必须在中间找出最聪明的一个。有一个鉴定方法,就是等这些幼童到一定年龄时集中起来,让每个人从一大堆真伪法器中挑出活佛使用过的法器十件,如能准确挑出,即被确认为活佛的真正灵童。然后指派专门的高阶级经师教其读经学习,到适当的时候,报经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始行座床仪式,类似于皇帝登基那样,从此正式被确认为新的活佛。
我想,活佛的转世,目的主要在于使宗教贵族阶层不因活佛圆寂换了新活佛而失去了既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但同时不可忽视活佛及其转世体系在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现实影响力。
塔尔寺
在塔尔寺大门外,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三大景观,一为方底圆身尖顶的八座活佛功德砖塔,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毫光,极显庄重;二为络绎不绝的游人,西北人、内地人及高鼻蓝眼金发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三为一步一扑地膜拜的从草原深处远道而来拜佛的藏胞男女信徒,他们简直是用身体做尺子把寺前几百米的地方量完的,站起时双手合十高举,然后落在胸前,接着扑趴在地上,双手伸前贴地,额头着地,然后依次再做,那种真诚和严肃,令人起敬。
塔尔寺最有名的当属大金瓦殿,这里就是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地方,也是塔尔寺建筑群——这座宗教城的中心所在。从外至内,溢彩流金,金瓦、金脊、金檐、金柱、金身、金烛台、金法器,一切都是豪华、尊贵的象征。大师端坐在那里,法相庄严,目光如炬,头顶光环,左肩扛经书,右肩扛宝剑,意味智勇双全。据说这座金瓦殿,内外共使用黄金1.2吨、白银1.7万两,各种宝石及象牙等不计其数。殿内大柱上包的有历代蒙古和硕特部宗王赠送的挂毯,座像两边专辟地方安放有历朝皇帝敕赠给塔尔寺的法器及题辞。案前点的是酥油灯,明亮无烟,柱间垂下丝制的幛幔,白发喇嘛正在做功课,端坐如松,呢喃有声,仿佛游人的进来与他无关,我想他的思想早已进入佛国了吧。墙壁上有壁画,大多以宗教故事或民间故事为内容,有飞天图等。那壁上的佛国女儿,一个个仪态万方,雍容华贵,身轻似燕,或弄琴,或沉思,或抚卷,或轻寐,或飞升,或戏水河边,图案及造型显然极具印藏艺术特色。那种酥油的味道,使殿堂中空气肃穆凝重。小金瓦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院中的两丛菩提树,据传菩提树下释迦成佛,悟道得真,从此广授门徒,遂使佛教播布天下。所以,当人们看到这种丛生的枝桠蜿蜒的传奇之树时,升腾于心间的往往是崇敬和庄重之感。当我愚蠢地突发奇想,竟想采一两片类似于榆叶的菩提树叶以做纪念时,一看护的武警战士和小喇嘛同时走过来,告诉我说菩提本无树,只要心中有佛,走遍天涯,佛会随你在一起。我自愧学问太浅、悟道不深啊!在小金瓦寺东边的高台上是时轮坛城。我看到主殿上没有供佛,却是一个半径为三四米的圆形木制的平面凸缘螺状转轮。我起始不解其意,仔细观察,发现上边有用木头雕刻的太阳、星宿等图案,且每一种图案均用动物形象代替,我认真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型设备是塔尔寺僧人用来推算天文及天象的浑天模具,通过转动,各种星体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对其中奥妙我看不懂,但藏胞确实是通过这个巨大的仪器来确定藏历的,据说,塔尔寺还设有专门研习藏族天文及历法的博士学位呢。
让人最感兴趣的当属花院和大经院了。花院里边有塔尔寺最为有名的酥油花。酥油本身就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白色凝脂状食油,晶莹透明。每年冬天,塔尔寺艺僧就开始做酥油花了,看说明上写的英文“mutter sculpture”,意为“黄油雕刻的艺术品”。在陈列室的全封闭大玻璃背后,就是形态内容各异的色彩斑斓的酥油花了,立体感很强,内容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有大小上百个人物、有花轿、有旗幡、有军队、有水、有河、有草、有牛马、有云彩,人有三寸来高,形态丰满、生机盎然,仿佛呼之欲出、唤之欲应,可以想象当年文成公主和亲进藏的庞大气势。酥油花上所有颜料是当地产的一种矿石,经磨细互调,即成各种颜色,涂在用酥油捏制好的形象上,经久不变。我了解了制作的方法,每一个艺僧独处一室,在严冬的天气中,屋内不生火,在零下15℃以下,自己选题材,自己领油去做,先用酥油捏成各种形象,再涂上颜料,在做的过程中,身边还要放一块青石或一盆冰水,做的时候,由于手上有温度,怕融化了酥油,不时地把手伸进冰水中或放在青石上,降温后才能继续工作。做成后,到正月十五大法会时,各位艺僧才展示出自己的作品,让僧俗群众评看,往往引来参观者的啧啧称奇。我们在这里时,玻璃闭护后边全部用冷气机在制冷,才使它保存到了夏秋季而不融化。
sqRoE5fAUlrJ0iCRIV4O+Q== 大经院中最引人的就是堆绣,它也是塔尔寺一种特有的工艺,用丝或毛线编成各种形状的毯,或条或块,然后根据立意选题,在巨大的廊柱间挂起来,以什么东西做底色就先挂什么,然后把代表别的什么意图的东西或条或块再挂到它的上面,互相重叠,形成各种意境,当然以宗教为主要内容,是一种立体的堆层布画,很形象也很生动,引得游人不住回头,流连忘返。
至于那些一间间的群殿,相互联结,翘檐飞脊,红砖绿瓦,豪华极致。回廊宽阔,几乎在每个殿的四周走廊都安装有转经筒,小如水桶,大如巨缸,直径有半米,高有两三米,人手一拨,它即旋转,按藏传佛教说法,对没时间读佛经的人来说,转完塔尔寺近千只经筒,就算通读了所有佛经。难怪每个经桶上都被游人和信徒摸成了油亮的颜色。在阿嘉活佛院,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转经筒,衣衫褴褛,头发很乱,好像脸都没洗,但眼睛很有神。我问他们是当地人吗,他们说他们是从四川阿坝来的,先到拉萨,再到这儿,走了三个多月。我说这么远来干什么,他们只说两个字:“拜佛。”但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一处展室中,既有解放前藏区农奴的苦难生活图片,也有用农奴人骨做成的法器、骨笛、用人皮蒙成的鼓面,还有贵族、官员、高层僧侣享用的奢侈品,包括清末英国王室赠送的一辆豪华轿车。这些冰冷的物件折射了过往的现实,清森冷冽,充满残酷和无情。我看到这些,心中一阵一阵地发凉。
时间紧迫,不容多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塔尔寺。这里的一切让人觉得神秘,那虔诚的脸庞,那代表骏马的哈达,那如宝座的莲花山,那金顶,那时轮,那酥油,那壁画,还有来自远方的客人赠送的法器,加上高原的风景等等,说不清,道不明,只能让人感觉到塔尔寺是一座宗教的城市、精神世界的王国。它虽处高原,但它慑服的是人的心灵,由此而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此膜拜和了解它。据讲,塔尔寺仅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这里只是宗喀巴诞生之地,他少时离开青海再未回家。而他的驻锡地西藏扎什伦布寺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拉扑楞寺更具有特色。要揭开宗教之谜,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它的发展轨迹,必先了解和研究它的精神世界,而宗教就是它的文化缩影。惟其如此,才能尊重它、团结它、发展它,实现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国家。因为我觉得,能够长久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潜在作用的是思想,而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