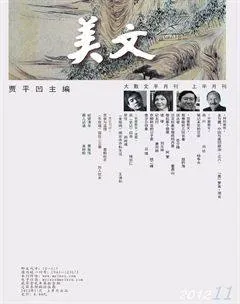记太行
唐兴顺
1957年出生于河南省林州市。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兼任安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出版散文集《心地集》《大道在水》。曾任乡镇党委书记、教育局长多年,现为林州市民政局长。
风 林
认识风林,是我在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他是学校一位化学老师的爱人。这位老师身材小,面容却姣好,肤色白,眼睛很神气,住在学校操场南边的一间平房里。不知道风林是什么职业,人们只看到他经常在学校操场上当篮球裁判,穿一身白蓝相间的运动衣,脖颈系着一个哨子,跟着运动员在场上跑,经常的形象是,弯着腰,半蹲身子,两手放在膝盖上,脖子前伸,一双小眼睛瞪得很亮,一有情况就迅速发出哨音,并且跨步上前,打出手势,表情认真而严厉,好像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似的。边场上有人就笑他,觉得本来是业余时间的娱乐玩耍,又都是同事和熟人。风林连看也不看,继续夸张而认真地跑着。时间长了,人们觉得他说不上什么不好吧,却终归有些特殊和怪异。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是冬天的一个中午,有人照例在操场上传球、投球,半玩不玩地活动,突然风林的爱人从南屋里跑出来惊叫。人们赶过去把急病了的风林放在平板车上拉着往医院跑。出了校门走到麦田间的横路上,他却在车上猛然坐了起来,一时像个好人似的。人们调转方向,又把他拉了回来。一种说法是中了煤毒,更多说法是新婚不久夫妻俩中午云雨过度,风林一时虚脱。这件事成了风林在我记忆中的底色印象。
后来,人物东西,风流云散,时代的风,时代的雨,刮了一阵又一阵,下了一场又一场。社会完全变了样,可是风林却像一个特殊的精灵,一直闪亮地存在,可是又一直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说不准从什么人的嘴里,在什么庄严神圣罢了的场合,偶尔就会有人提到风林,他便常常从堂皇世界的缝隙中毫无逻辑关系地跳出来。他做的事不入正流,似乎好笑,可是有时候又能挂在主流事物的边上,叫人想否定又不好说什么。比如,他曾经找县长说本县地下有热源,可以开发利用。县长说,你的热情很好,我们有机会勘察论证一下。他说,好。就走了。领导多少事啊,早把这忘到了脑后。过了一个月他却又找到了县长办公室。领导挠挠后脑勺,等等,说这得有个过程呀。他说,是,可过程总得有个时间吧。县长和他握了握手,又说了些感谢的话。过了一段,他又来传达室登记,要求见县长。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嘀咕一阵,说领导出差去了。他又从身上掏出一份材料放在了传达室。再比如,此地山中有条河流,两山夹一峡,风林带着过去体育上的几个朋友,到山里看地形,绘地图,提出搞太行漂流的设想。其中有个人按照风林的设计搞了这个项目。风林呢,他穿上红色的救生衣,坐在圆形的橡皮筏内顺着河槽漂了一趟,至中心水面时,丢开桨板,仰望两岸高崖巨壁,用手拍打流水,连声高喊“快活”。然后就再没到过现场。他脑子里很少钱的概念。差不多尽是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新鲜事。县城西边的林泉庄,前几年有一对弟兄挣了钱,想标新立异,不知从什么渠道买了一架小飞机。很简单的那一种,前边一个玻璃罩子,后边像个电风扇。预备搞低空飞行旅游。在村边承包几十亩地,修成长长一溜跑道。标语和广告打了出去,县电视台、省级报纸作了报道。两弟兄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可是飞机停在那里快一个月了,还没人乘坐上天。成群结队的人只是去看热闹,围着飞机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为了招揽顾客,有时候飞行员就坐在飞机上把飞机发动了,机翼转动起来,周围树木摇晃,尘土四起。飞行员一再向人们招手,可就是没一个人有胆量上去。风林说要乘坐。人们看着他轻松随便的样子,以为听错了,再三问过,风林也不正脸回答,而是直接进入上机程序。他今天下边穿了条短裤,上身只穿个背心,一件破旧了的衬衣斜搭在肩上,脚下呢,哈呀,就汲拉着双拖鞋。弟兄两个见此情况喜出望外。这可是登机第一人呀,不能简单对待。赶快把风林请到了路边的业务室,一边上烟上水,一边打电话请记者。还迅速设计了一套方案:用汽车把两名漂亮的女业务员送到三十里外的旅游区,让她们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等飞机过来,搞天地呼应的宣传效果。老板本来还准备付给风林些报酬呢,看到他无心无意的样子,就只是表面热情,其他凑合着不提。风林就这样上了飞机。伴随着拖拉机一样的轰鸣声,固定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腾空而起,离开了村庄和大地。他没坐过正规的大飞机,空中的感觉让他真的激动了起来。此时正是麦子快要成熟的时节,田野里青黄相间,波涛翻卷,房舍逐步变小,道路,池塘点缀,人和各种车辆都成了儿童玩具一般。飞机越过了太行山顶,峰峦、沟壑,像幻灯图片一样向后闪去,碧绿的山前树林如无限大的地毯平铺向前。按照安排,飞到旅游区上空以后,他把一条红绸布垂了下去,地上的那两个姑娘一个撑一把大红伞,另一个撑一把大黄伞,像走剪刀股一样的转动摇伞。旅游区里的其他人都仰着脸向天上望,人们看到飞机垂下的来标语是三个字:“我爱你”,便更加欢腾起来。好几家媒体的记者拍摄下了这些镜头。风林在天上只能望到大致的场面,根本也不知道红绸布上写了什么内容的字。对于这些轰动的效应,他有点出乎意料。他迈步登上飞机的镜头登在了市一级的报纸上,在旅游区里的欢庆场面也被印成广告。人们拿给风林看,在他面前摇晃着说一些庆贺之类的话,他呢,真正是看都不看,也无话语,也无表情,完全的与己无关。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个副县长去登山消遣,地点选在相邻的另一个行政辖区内,荒僻偏远。几十年前是徒步翻越太行山的一条大路,现在坍塌毁坏,荆棘掩隐,但路的轮廓,还有从峡谷向山顶盘旋的石台阶还一段一段地残留着。我们攀登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越往上人的痕迹越少,自然风光越好。高耸入云的山崖和逶迤下来的陡坡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像夜空星辰般耀眼。我们坐在一个拐弯的地方,侧身遥望,议论感叹,这时候突然听到旁边的灌木丛里好像有人在活动,这么高的地方,不可能有人的呀!难道是什么动物。立刻有些警觉起来,仔细听,窸窸窣窣,愈来愈近,似乎还有极其轻微的哼哼唱曲儿的声音。是人不假,会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不说话,瞪眼望着发出声音的地方。不一会儿,从浓绿丛中现出一个人来,正是我们的主人公风林先生。他扇披着布衫,手中取了一根木棍儿,横斜着来到我们面前。县长和我吃惊异常,他却笑哈哈的,很自然地在石台阶上坐下来,仰起头来和我们说话。我还在朝着他来的地方张望,心想一定还有其他人,风林会和什么样的人到这种地方来呢?哈呀,难道他也会从歌厅带一位小姐来浪漫吗?看了半天,没有任何人,确确实实就这位仁兄一人在行动。这叫什么?“闲云野鹤”中的“鹤”应该就是他吧,不取鹤的高贵,也不取鹤的圣洁,在这里我们只取他的独立和特异就够了。虽然路途不是太远,毕竟也算他乡吧,又是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县长表现出十分随意和友好,说了些平民式的家长里短的话。谁知风林却不接着说,他截断话题,大谈了一通法律和民主。完全不是社会上常见的那种发牢骚式的,他声调轻轻,语速缓慢,一层意思一层意思地讲。讲法律对民主的保障作用;讲民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上不同的内容和责任,甚至讲到在特定社会形态下,权力可以大于法律和民主等等。他这样讲的时候,除了使用方言有些土气之外,完全是很洋气的讲坛式风范。县长很吃惊,不时从上边伸过手来拍拍他的肩膀,风林却一次一次把他的手推开去,继续认真望着他的脸说话。让我感觉到,这个表面上衣冠不整的人,内心里装着的是一团思想,一团精神,一团形而上学的思维元素。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又是一个不被普通人理解的普通人。由于内心里经常电闪雷鸣,所以躯壳和表面总是苍白着。
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正规的岗位和职业,也不知道他靠什么收入维持生活。在家里他有一个独立的房间,里面挂着乱七八糟的纸张图画,还摆放着他从民间收集来的瓦头、瓷片等。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一些破烂的东西回家去。他妻子肯定会埋怨他,但一定也是默许和认同的。她对人说起丈夫时,好像是生气的样子,却总是有些掩饰不住的笑,至多也总是这么一句:“俺家这个人就是与人不一样,俺也弄不清他整天想着啥。”在他所住的小区,不知谁什么时候在墙角上放置了一个破旧面包车,风吹日晒,越来越不成样子,差不多就是一架废铁皮了。却被风林派上了用场。他上去把座椅平伏,把窗户用报纸糊上,用铁丝把四周封住,只留下一个偏门。然后把他喜好的东西全部移到了这台破车上。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也住到了车上。小区的人们都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私下里说他和拾破烂的没什么两样。可是何必又都要人理解呢?风林有风林的处事逻辑。一些世俗礼节的事他也做,只不过是特立独行罢了。邻居家一位老人在故乡过世,小区许多人共同乘车去吊唁。本来想叫风林的,可是考虑他平时的行为,怕惹难堪,就没叫。谁知车到了路上,却远远望见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已经先行了。在灵堂内大家都上礼金,鞠躬致意,风林却没掏一分钱,也不鞠躬,而是跪下来磕头行大礼。你说,对亡人而言,哪种礼节更隆重呢?风林就是这样,常常依着事物本vZU5XXZ9RTgS0rfJGZxQdQ==身思想,常常在世俗的混沌中亮出一道光来。他也关心时事政治,但又不是都关心,很难界定他关心的是哪一类。孟学农在北京和山西任职,两度被免职,复出任职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诗在民间流传,题目是《我的心在何处安放》,很个性化的,所用词语包括“妻子温柔的胸膛”之类句子,抓住了官民两界所有人感情深处的软肋。可是你知道这首诗我最先是从哪得到的?对了,是从风林手里。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下班回来,风林突然从传达室跳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小纸片。他专门从一份好像是科技类的地方小报上,把这首诗剪下来。应该也是专门在此等我吧。还用笔在一些语句下画了圈儿。我拿在手上看时,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半张着嘴,长时间看着我。这个情景让我记忆深刻,也是风林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
按说这样一个人,完全应该久存于世的。他处在最平凡的人群中,与谁都没有竞争。他思考这个世界,又不给这个世界添乱。他是有些怪异,但那不过是他伪装太浅,暴露了人的一些本质而已。走就走吧,走的方式也很异常。他和一个朋友共乘摩托车到一座山上去。山名叫“柏尖山”,太行群峰如浪,此山独举一臂。北京大学的一位地理学教授,刚刚为这里题写了“神州初庙”的匾额,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山上本来很少有车辆的,恰恰就让他给碰上了。他们向下走,汽车向上走,在一个拐弯处出了事。一下子坠入深渊,就什么都没有了。
春 明
春明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夏天穿军绿色衬衫,束在裤腰内;冬季喜欢穿列宁式大衣,两手斜插在衣兜里。面色微黑,双目有神,走起路来迈着大步,耸着肩膀。作为男性,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是那时的农村,这种形象的人常常被误读,特别是他同时又能说会道,什么事经他嘴一说都清清楚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书记或主任大多翻开笔记本,一句一句照着传达,念错了再返回去念。春明却不,经常是把开会精神搅和了,结合现实工作,重新排列顺序,重新组织句子,变成自己的语言在会上说。讨论一件事情,别人有的说不清,有的装糊涂,他一掺进来,三句两句,谁也就无话可说了。本来准备用半天时间的,一下子没了话,缺乏思想准备,大家都搓着手,说说天气,说说笑话,难堪的散摊收场。时间久了,人们都觉得春明“精”,后来又上升成“小聪明”,再后来就把一顶脱离群众的帽子扣到了他头上。这些称号没有任何人在正式场合宣布过,但私下里说得多了,大家越来越形成了印象。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别人给他提意见就提了这一条。当然话说得很婉转,比方就说“要注意走群众路线”等。春明心里想,我是最不脱离群众的呀!心里有抵触,嘴上还得客气,要不然又得落下“不接受同志批评”的评价。这样次数多了,连他自己也将信将疑,可能自己真是有脱离群众的表现呀!
那一年运动来了,是运动就要整人,整人就要有对象,有成果。群众会,座谈会,检举揭发会,拉出去打进来,几个回合过去,仍然没有锁定目标。上边来的工作组有点着急,拿出了另一套方案:“背靠背”办学习班。把大队革委会成员和部分群众代表集中在一个院子里。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再亮态度表决心。大家情绪很激动,温度升高后,一个人一个人“过堂”,依次到工作组的密室里揭发他人,人与人互不见面,不说出点什么不许离开。学习班结束时,工作组长的脸松弛下来。几天后召开群众大会,揭开了此次运动的“盖子”,宣布春明两条罪状:一是有脱离群众思想,二是有贪污行为。会场上还有人领着高喊了几声打倒他的口号。开大会前工作组已经找春明谈了话,脱离群众的话没细说,所说的贪污,是有人揭发他几年前去新疆给大队买马,本来付了五匹马的钱,交到大队的却是三匹马,另二头是骡子。说中间所差的钱春明和当地人合伙贪污了。春明回忆,真不是这回事,在边塞之外人生地不熟,白天看了马,晚上上的车,马和骡子本身差别就不大,没有仔细看。到宝鸡换车时才发现了失误。春明让把当时同去的另一个人找来核对,那个人低着头,红着脸,支支吾吾说记不清楚了。他又给工作组提出,请组织上到新疆搞外调。工作组有一个人就沉下脸来呵斥:“谁给你向组织提要求的权利了!”组长在旁边又声音低低地给他谈心说:“群众运动就是给干部洗澡,泡一泡,出身汗,再上来嘛。”这句话对他触动很大,好多年后进澡堂就想起组长的面孔来。当时组长还说:“揭发你,是治病救人,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比内容更重要。”然后春明就说:“我肯定也有错误呀。”组长又说:“这就对了嘛,春明同志认识了就好。然后让他回了家。”也没人再说什么,不想突然就开了这么大的会,自己成了这次运动的“把子”和成果。
既然贪污了就得退赔呀,可是也没人再追究这个,只是免了他的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工作组长最后找他时态度很和蔼,面容慈祥,细声细语:“组织上不会一棍子打死人,你先回去,组织上会考验你的。”从大队部出来,正是月色朦胧时分,不知怎么,他的心情反而有一点说不出的愉悦。工作组长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不是因为搞运动,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对象,这么大领导,怎么会与自己这样友好和亲密?何况从领导的表情上看,对他还有些感谢的意思呢。到家后他对妻子说,“毛主席语录上不是说嘛,好事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咱不泄气,好好干,让组织考验咱。”妻子说:“好好干?不是大队干部了,干,干什么呢?”春明说:“我想好了,就在小队干。”
大队总辖十三个小队。春明家所在是第四队。他从此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社员在小队上干活。内心里却以大队干部要求自己,就当是在小队蹲点呢。重活脏活抢在前。队里布置积绿肥,他除了白天与社员一起上工外,夜里悄悄地到西山边割青蒿,铲草皮。没用几天,在自家门前沤了两堆小山一样高的粪堆。数量和质量超过四队所有人。有个社员承包了村北一个土堆开地,结果打开一看发现里边全部是石头,用工多报酬少,嫌吃亏,发懒不干了,给队长出了个大难题。春明迎上去,说按原来发包时的工分自己干。他累得弯腰弓膝,心里却想群众的眼睛在看着自己,不能软,大队干部就要有大队干部的觉悟。非要争来这一口气。五月天到地里割麦子,咬着牙冲在前边当“第一镰”,看看咱是不是脱离了群众。不是在蹲点吗?要通过自己表率作用把这个小队各项工作都搞到前边去。他给队长出主意,让小队发展了养猪,种药材,开油坊几个副业项目,到第二年底,生产队的每个工有原来的一毛五上升到了七毛八。这个标准在全公社都是很靠前的。春明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很满意,总觉得应该引起组织上的注意了。可是始终没有任何动静。后来他装着路过办事从大队部门口走过几次,向里望望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变化。看看墙上黑板报,还是写着那几条标语,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回到家就想,组织?组织?组织在哪里呢。组织早把自己忘了呀。后来经过打听,说那个副书记早就调到外公社当革委会主任去了。他此时才感到真的失落了,几天几夜地睡不着,人瘦力乏,在家躺了好几天。
春天的时候,相邻大队的一个好伙计被抽到公社的水泥预制厂当了厂长。这个人对春明的本事很了解。有一天找到家请他出山。仅是这种态度就让他很感动。当即带着铺盖,骑自行车和厂长来到了离家二十里外的预制厂。厂里有上百号的工人,按不同的产品分成“电杆”、“楼板”、“水磨石”等几个车间。厂长指定他负责全厂生产管理,他却一头扎进“水磨石”车间亲自操作了一台机器,脚蹬水靴,身披皮护襟,和工人们一样握着机器长柄,推过来摇过去,横磨竖磨,切割,喷水,上油,每道工序按图纸上的标准操作。只在业余时间召开车间主任会议,听汇报,做督查。这样的抓法,反倒收到极好的效果。水磨石车间自不用说,其余两个车间互相赶超。到年终全厂利润增加了一倍还多。按照预先的规定,春明可以拿到三百多元的额外补贴,并且被评上了县里的“多种经营模范”。补助款他坚决不要,却十分珍惜模范称号。
表彰大会在县剧院举行,春明和各方面评选出来的模范坐在前三排,上台接奖状。主席台正中坐着一溜县里的主要领导。舞台两侧是一层一层的彩色帷幔,绿色、粉红色、黄色、红色从外向里,越往里越伸出来,错落得层次分明,县招待所漂亮的女服务员身着天蓝色的制服,手上端着镶着奖状的玻璃镜框,一队一队从帷幕里出来,先把镜框放到每个领导面前,接着才是模范们上台亮相。舞台上方早就安置好的射光灯,依次照向他们。把每个人照得精神欢喜而紧张。春明这一轮上场时,他恰好站到了县委书记的面前,书记狠劲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春明激动的有点结巴,加上响亮的音乐和台下嘈杂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回答清楚了没有,朦朦胧胧中,他只是用劲的看着书记的脸。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事情,包括过去当大队干部也没有过如此机会。散会后,他先回了厂里,然后又坐着单位的客货两用汽车回到村上。一到村口就跳下车来,很多人围住他看奖状、说话。本来可以近路回家的,他却心意难平,仰着脸在大街小巷里转了半个村。
这件事完全将他的精神支撑了起来。副厂长的职务,虽然只是厂长个人指定,但厂里的工人很认可。公社领导,鉴于过去的事悬而未决,不便正式表态,但场面上,礼节上也都默然允诺。春明自己呢?有了县里表彰会的认可,差不多已经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态了。可是,我们这位不幸的人儿啊,他哪里知道在世代更替的波飞浪卷中,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正从幽冥中向这个小人物走来。一九七七年夏季,他代表厂里到省城销货,住在一家名叫“南河道”的旅社。晚上无事,心情又好,拿起配发给房间的一本杂志翻阅起来。翻阅了一会儿,看到杂志底面上是空白的,就按在桌子上,拿圆珠笔在上面画“一笔宝葫芦”。这是厂里一个青年工人刚教他的,一笔下去,拐来拐去,密密匝匝,不抬笔,不断线,最后恰好与落笔处吻合。他刚学,画着画着就错了位,只好毁掉重来。这般多次,竟把杂志底面全画满了,又接着翻过正面来画。差不多画成了,却突然发现封面上是毛主席像。一下子吓得站了起来。在毛主席身上乱画,当时是天大的事情。这可怎么办?好在是夜里,房间又无其他客人,他赶快把这个封面撕下来,撕成碎片,扔到垃圾篓里。心想应该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被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发现后报了案。春明开始并不知情,正准备去食堂打饭吃,警察来了半院子。以“现行反革命”把他带走了。通过公安系统的内部联系,春明很快被押回了县里。一个最看重组织的人成了反革命。春明像在做梦,变成了个傻子。他被五花大绑的押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牌子,在县城游街示众。后来形势变化,他在监狱里住的时间不是很长,就被放回了村上,也不说话,也无表情,整天在家院子北墙根的椅子上坐着。后来,面部神经麻痹,肌肉萎缩,那个衣着干净,说话透彻的人跑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