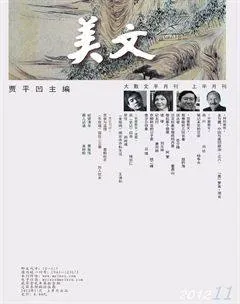坡嗲
刘元林
1966年出生,陕西省周至县“坡嗲”人。1984年入京,从学校到报社。从事新闻编采工作。作品曾获全国散文大赛、《羊城晚报》杂文大赛、博联社“十大博客”等各种奖项。
秦 腔
是一碟油泼的辣子
是一袋新烤的旱烟
是一壶陈年的西凤
是一座祖传的家园
《五典坡》长满千年的怨
《六月雪》诉说世代的冤
《生死牌》写满人间的情
《铡美案》长着好人的胆
老汉们谈论着忠和奸
娘儿们领量着孝与贤
姑娘娃见识了负心汉
小伙子嘛,惦上了女狐仙
有多少恨就有多少爱
有多少缺就有多少盼
黄土地是鼓黄河是弦
戏里戏外无非是生丑和净旦
——摘自旧作《陕西六唱·秦腔谣》
五一节,法定假连着年休假,我在坡嗲老家待了整整十天。除了陪父母亲说说话,出门转转,一有空,我就在家里看秦腔,看的是DVD。在西安下了火车,我就直奔音像商店,买了一堆秦腔碟子,任哲中的《周仁回府》,刘茹慧的《辕门斩子》,郭明霞的《五典坡》,马友仙的《白蛇传》……凡是早年我看过的戏,都买了。每天听着秦腔,吃着母亲亲手做的油泼辣子浆水面,间或喝几杯浓烈的西凤酒,我像一条在河沟里干涸太久的鱼,终于回到早年的湖泊里。
在陕西关中,周秦汉唐的盛世辉煌,都埋在了土里;唯一活在地面上的秦风古韵,大概就只有秦腔了。一种流传了数千年的艺术,像贯穿秦川东西奔腾不已的渭河,灌溉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如果关中的草木会唱歌,唱的也一定是秦腔。一个在田野上扶犁的老汉,于吆牛喝马的间歇,吼的是“为王的打坐在长安地面,盼的是天心顺国泰民安”;一个坐在家门口拐线(理线)的妇人,面对绕膝的儿女,吟的是“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关中三面环山,一面向东敞开,宛若中国的一座大戏台。千百年来,先人和乡亲在这座戏台上,观看、传说也上演着一幕幕或豪迈悲壮、或哀婉凄凉的人间悲喜剧。土生土长的我,秦腔就成为早年别无选择的精神浇铸。
那天,看完一折戏,我对母亲说:“我想去看看我二姨夫。”母亲说:“是该去,你姨夫总念叨你呢。你姨夫七十多了,如今没人叫唱戏了,还闲不下,整天给儿在地里刨呢。”
姨夫住在离我家十里地儿的集贤堡子。集贤是紧挨公路的一个大村子,曾有一个秦腔剧团,姨夫是这个剧团管场合的,文雅点说就是剧务。剧务是我后来知道的名词,当时我只看到,戏一开场,他就台前幕后地跑,一会儿把大幕拉合,一会儿把二幕拉开,一会儿放烟火,一会儿摆布景,整个戏台上就数他最忙。他不拉大幕,戏就不开演,我觉得他权力很大,对他充满尊敬。
那时,无论哪个村子唱大戏,都是十里八乡共同的节日。家家落锁,十村九空,都去赶赴这难得一遇的精神大餐。仅有几个大村子有现成的戏楼,其他村子唱大戏,都是在田野上临时搭建戏台。再开阔的地方,也盛装不下四面拥来的观众。那些青壮劳力喜欢在人堆里撒欢儿,每次开演前,台下都要上演一出拥挤大戏。剧场转眼间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充满刺激也充满凶险。每到这时,不及大人肩膀的我,就一步步向戏台口游走。看到戏台上的姨夫,我就像看到了灯塔,高喊着“姨夫!姨夫”。姨夫转过身,蹲下来,从戏台边上伸下两只长长的胳膊,像一个救生圈。他把我抱上戏台,放在锣鼓乐队的一角。坐在台上,台下一览无余,我神气十足。
姨夫家在集贤堡子东头,普通的三间瓦房。正是午后,我推门进来,偌大的烧炕沿上侧躺着一个老汉,身体嶙峋如山,我想就是姨夫。姨夫掀开黑兮兮的被子,缓缓起身,定睛看我半天,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我说我是元林。姨夫揉揉眼睛,就张开了两臂抱住我:“我娃回来了!”两行泪水从黏着眼屎的眼角流了下来。
我不再是那个他一下就能抱上戏台的毛头小子,姨夫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浓眉大眼、英俊干练的剧务。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沟壑纵横,像他常年侍弄的土地;两只青筋暴涨的手,在抓住我手的那一刻,感觉像柿树皮一般粗糙。
我没有看过姨夫演戏,父亲说他看过,在现代戏《朝阳沟》演个苦大仇深的翻身农民。一场病后,嗓子打(哑)了,才开始管场合。管场合事无巨细,都得用心,那时舞台没有那么丰富的灯光,全靠幕布维持场面,三四道幕,什么时候拉那一道,都要紧随剧情,拉错了就出笑话。演《智取威虎山》,演员开枪时,他在后台甩炮仗。前台的杨子荣抬手举枪叩动了扳机,他的炮仗却没有甩响。演员随机应变,临时改了台词:“怎么,子弹受潮了吗?”演员刚把枪口拉回眼前欲看个究竟,他的炮仗响了。台上台下爆笑不已。他却因工作失误差点被开除了。
说起当年唱戏,姨夫有说不完的故事。我问他这些年还唱么?他说剧团十多年前就解散了,只维持着一个江湖班子,给乡邻红白喜事应个景。他说秦腔就像辣子,爱它的人爱得要死,怕它的人怕得要命。听说在西安市坐公交车逃票,不罚款,售票员把你拉到终点站,集中在一个屋里,放秦腔作为惩罚。就是在农村,这些年唱大戏的也越来越少了,戏台下坐的多是老汉、老婆,年轻人都唱歌跳舞、上网去了。我知道,江湖班子只能唱小戏,小戏是不需要剧务的。一生钟爱舞台,晚年无事可做,姨夫一定很落寞。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问:“那秋棠现在呢?”姨夫眼角掠过一丝笑意:“你还记得秋棠?”
怎么不记得。秋棠曾是集贤剧团的当家红旦。这家剧团当年很红火,经常到外县外省演出,很难说是剧团火了秋棠,还是秋棠火了剧团。我那时想,《天仙配》一定是真的,秋棠就是天女下凡吧。她每到一地演出,只要一落脚,身边就围一大群人。一些媳妇挺着大肚子,盯着秋棠看个不够,说这样生的娃就能像秋棠一样漂亮。秋棠上个厕所,后面都能跟上一串人。村民们看戏,先打听是不是秋棠的戏。秋棠的戏,台下的观众就分外多;她出场前,台下也挤得分外凶。但她一出场,全场一下就鸦雀无声了。她不只扮相好,唱腔、演技都很出色。她最擅长苦音戏,一出《三娘教子》,一出《生死牌》,她唱得风云变色,满场抽泣,心软的妇女不忍卒看,堂堂须眉也会泪落满襟。那时流行一个说法,看秋棠的戏,得提前带上毛巾。
秋棠是大众偶像,年轻小伙的梦中情人。她有没有婆家,许给了谁,是村民讨论不休的话题,有说她许给了县长的公子,有说她的未婚夫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又说秋棠坐公交车不用买票,连她的亲戚都跟着沾光。有人去粮站交公粮,收购员说你这麦没晒干,只能验二级。交麦的说,干着呢,你再摸一下——我是秋棠她大舅。收购员却不再摸,说你既然是秋棠她舅,那就一级吧。
我那时虽然未尽谙人事,但大约已懂得了爱慕,爱看秋棠演戏,爱跑到后台看她涂唇描眉,喜欢听人们谈论她。或许还向姨夫打听过她,只是记不清了。
秋棠后来呢?姨夫说,剧团散了,秋棠去甘肃一个剧团唱了两年戏。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再结婚,前后拉扯了三个娃,就不再唱戏了。
姨夫佝偻着身子,坚持要送我走到街口。街口有一条尺许宽的水渠,水还清亮,哗哗地流着。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垂落的头帘遮挡了她的半边脸。女人蹲在河边,用棒槌一下一下地砸着衣服,水星四溅。棒槌起落之间,背后一片肥硕的腰身忽隐忽现。
走过后,姨夫对我说:“那洗衣服的,就是秋棠。”
啊?但我没有再回头。
浆水菜
中国正在经历亘古未有的历史变革。从经济形态上讲,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从文化形态上讲,是从集权专制的子民社会向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过渡。这就是所谓世界潮流,任谁也拦不住的。这个过渡期不是三五代人的事。按著名旅美学者唐德刚的观点,自夏以来有记录可查的中国历史,凡四千余年,基本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封建时代、帝制时代和民治时代。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依唐先生的看法,“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见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换句话说,最快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才能真正步入民治时代。
若按唐先生的这个分析,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是中国第二个过渡期的“冲刺阶段”。这个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发和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恐怕不为过分。坡嗲也不例外,随着一条高等级环山旅游路的开通,东去西安的距离由原来的两三个小时缩短为一个小时,开发、发展的步子也进入了快车道。目前,村里有了美国人援建的全国一流的乡村小学,有了村村相连、街街相通的水泥公路,有了为全村统一供水的自来水厂,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耕作,八成家庭都住上了两层楼房。现在的坡嗲,养猪的人家少了,养“机”(农业机械和机动车)的人家多了;烧柴禾的人家少了,烧煤、烧沼气的人家多了;拉土起圈施农家肥的人家少了,使用化肥农药的人家多了;种地的人家少了,外出打工做买卖的人家多了。
坡嗲是工商业资源匮乏的地区,首先是缺水。水不但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工商业的命门。虎峪里流出来的水,过去勉强供坡嗲的几个村子人吃马饮,这些年水量越来越小,几近干涸。国家先后打了几眼饮水井,吃水已不成问题,但农业灌溉用水,目前还没有保障。坡嗲曾是一片狼虫出没的荒野,传说隶属汉武帝当年终南山狩猎的上林苑。经过数百年开垦,虽然大部分变成可耕地,但基础差底子薄,半尺薄土下面,硌硌尽是沙石。客观地讲,坡嗲这些年的发展变化,面子不小,里子不大,自给有余,接近小康,要说富裕文明,还很遥远。
县乡政府不甘落后,积极探讨发展的路子。一度,县里提出发展种植农业的思路,在沿山地带兴建万亩杂果林。那些年,几乎家家的责任田都改栽果树,以苹果为多,间见猕猴桃、梨、李子、杏、桃等。一度风靡全国的“中华猕猴桃”,就有从这儿出产的。但市场就像天气一样风云不定,没有几年,果多而贱,果贱伤农,种植业就丧失了优势。这些年,特别是与西安的高等级公路通车以后,发展旅游,又成为一个新的导向。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旅游方面,坡嗲还是有相当优势的。没有工矿企业,环境纯净天然。背负终南山,山高林深,四季自有风光。坡嗲之上的鹰嘴峰、观音山,都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近年来,有关部门又在坡嗲上下发掘出两处名胜,一处是汉武帝当年狩猎的行宫五柞宫遗址,一处是商末周初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的首阳山。前者的故址小有争论,但差之不远;围绕首阳山的争论就大了。史学界一说在河北迁安,一说在山西永济,一说在陕西周至,莫衷一是。家乡文史学家拿出各种史料,认定就是在坡嗲之上的首阳山。
伯夷、叔齐是商代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两人都不愿子承父位,双双跑到关中来,正赶上周文王准备东伐商纣,兄弟俩拦马劝谏,希望文王以仁义取天下,不要搞“革命”。文王不听,挥师东进,竟取天下。兄弟俩于是逃隐秦岭深处的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后来听说率土之内莫非周产,他俩索性连周朝的野菜都不吃了,绝食而亡。三千多年来,这哥俩的故事影响巨大,引起的争论也巨大,孔子、司马迁等对他们都称颂有加,鲁迅、毛泽东等却不以为然。近些年,当“告别革命”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思潮,他俩又有被重新发现的趋向,乃至有学者认为,伯夷、叔齐是中国最早的拉·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
于是,首阳山的名声日隆。
在伯夷、叔齐的故事中,有人提出疑问,不吃粮食,只吃野菜能活命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甚至觉得,坡嗲人今天吃浆水菜的风俗,大概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首阳山。
坡嗲人家,居家过日子,三样东西不可缺,馍笼子,肉臊子罐罐,还有就是浆水菜缸子。我小时候从事的家务劳动,其中一项就是挖野菜,为此走遍了坡嗲的沟沟坎坎,山上山下。我们摘回来的野菜,母亲要再挑选一遍,同为绿色植物,人可食者谓之菜,人不可食者谓之草。母亲把精心挑选的野菜淘洗干净,放在锅里用清水煮熟,撒上一些面芡,再浇上一碗浆水引子,盛入一个大瓷缸里,放一两天,一缸浆水菜就“窝”成了。
能窝浆水的野菜很多,我约略还记得如下的菜名:荠儿菜、花花裹兜、鸡肠子、麦萍儿、白蒿蒿、红杆蒿、艾蒿、水芹菜、仁汉菜、大碗花、刺金牙等。刺金牙是一种带刺的野菜,摘起来扎手,吃起来扎嘴,只要鲜嫩,别有味道。最好的野菜要数荠儿菜和千里光。坡嗲谚语有云:“要吃浆水菜,最好荠儿菜;要得浆水香,揪把千里光。”摘野菜是很费工夫的,也不是总能摘到,有时就用辣子秧、红芋秧的嫩叶、苜蓿等窝浆水。不少蔬菜也可做浆水菜,如芹菜、莴苣、白菜、萝卜缨、豆芽等等,但似乎没有野菜窝成的浆水菜好吃。
过去,坡嗲人吃饭,早晚的佐餐菜品,往往就是一碗浆水菜。每次吃饭时,从浆水缸里捞两筷子菜,如果过酸,就用开水绽一下,放上盐和辣子;讲究时,再放些蒜末,泼上烧煎的菜油,或滴几滴香油。把馍泡在糁子碗里,夹上一柱子浆水菜,吃了,就是一顿饭。现在生活改善了,都煎煎炒炒的,但不管做多少菜,浆水菜还是“老大”,饭桌上不可少的。
在短缺经济年代,浆水菜为帮助人们度过饥荒,功不可没。再难吃的粗茶淡饭,有了浆水菜的佐助,一如有了开胃的药。“有了浆水菜,给肉都不爱。”坡嗲人现在还这么说。
浆水菜在坡嗲,不光是佐餐菜品,还是调味品、饮品乃至药品。浆水汤可代替醋,调配其他饭食,如浆水面、浆水搅团、浆水鱼鱼儿等。在北京城里,陕西风味的餐馆里,浆水菜都颇受欢迎。浆水汤还有生津止渴、解暑去热的功效。三夏大忙,田地归来,从浆水缸里舀一碗浆水汤,仰脖喝下,就是坡嗲人的“冰镇啤酒”了。男人酒喝多了,女人多盛上一碗浆水汤来,帮男人解酒。女人坐月子,吃浆水打鸡蛋,据说可以下奶。
伯夷、叔齐当年在坡嗲之上的首阳山采薇而食,怎么个食法?纯粹生吃,恐怕不妥;整天煎炒,也无可能。我想多半是窝浆水。薇,一说是艾蒿,一直是坡嗲人窝浆水的主要野菜之一。只有窝成浆水,野菜才能放得长久。
在坡嗲所属的周至县做过县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以伯夷叔齐为题,做过一首《续古诗》: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
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
坐饮白泉水,手把青松枝。
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
枥马非不肥,所苦常絷维。
豢豕非不饱,所忧竟为牺。
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当专制统治者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不愿为“枥马”“豢豕”的伯夷、叔齐、陶渊明们,就只能归隐南山,嚼根咽菜了。什么时候,那些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追求精神独立自由者,不再被封杀、被逼进南山,大概就是唐德刚先生所谓的民治时代了吧。
“浆水”一词,坡嗲人也用作形容词,意同啰嗦。如此说来,我这篇关于浆水菜的博文,真够“浆水”的了。打住。
一只反季节蝈蝈
钱钟书先生有一句名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话是用来描述人对待婚姻或者职业的普遍心态的。即便是从字面上讲,这话也说得贴切,不信你考察一下“五一”“十一”长假期间旅游人群的流向,一定是城里的人往外逃,城外的人往里冲。长假期间,往往是北京这些大城市交通最为宽松的时日,由此可知往外逃的人比往里冲的人还要多——可能也未必,外逃的人多驾车出行,往里冲的人则十之八九是坐汽车或火车来的。
对我这样的“半路”城市人而言,往外逃的愿望就不限于长假。我是乡村的土窑里烧制的砖,虽然砌进了城市的高楼,总不免眺望来处,回味故乡的质朴和温暖。分离日久,年岁日长,这种心思变得愈发敏感而炽热。外逃而不得,于是一阵风吹,一丝草动,都可能触发对故乡的思绪。我的工作单位位于一居民小区内,工间散步,忽然一缕熟悉的甜香扑鼻而来。举目四顾,道路两边的洋槐树上,挂满了纷纭如絮的白色花朵。于是便想起故乡早年的洋槐林,想起了每到洋槐花开,大人小孩持杆携筐去采槐花的情景……
当听到一阵蝈蝈的鸣叫时,我的心里同样一阵悸动。数九寒天,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居然响起蝈蝈的鸣叫?
那是在今年春节前,从单位一楼的小门房里传出的。我好奇地问门卫老李。老李转身从门后的暖气片上拿起一个芒果大小的小葫芦,拔掉塞子,说,蝈蝈就在里面呢。我向里一看,门口是一个螺旋状的铁丝圈,里面什么也看不见。
“是电子蝈蝈吧?”这年头,科技能模拟任何自然的东西。
“是真蝈蝈,不过是人工养殖的,不是野生的,就算是反季节蝈蝈吧。”老李还怕我不信,就把葫芦口的铁丝圈往外抽了点儿,我便看到了一只扬须蹬腿的真蝈蝈。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冬天见过蝈蝈。在我的故乡,如果说槐花是春天的使者,那么蝈蝈就是夏天的歌手。约略是在杏李挂香、麦子熟黄的时节,田间、坎畔就能见到蝈蝈的影踪。麦收被喻为“龙口夺食”,那是农民四季之中最繁忙辛苦的时节,脚踩干燥的田塍,背负如炬的日头,汗流浃背,终日劳碌。除了镰刀掠过麦子的嚓嚓声,就是坎畔的树上夏蝉们单调枯燥的嘶鸣。这时,如果传来几声蝈蝈的鸣叫,则会给人烦闷燥热的心房吹进一丝清凉。蝈蝈的鸣叫虽然不像夏蝉那么高亢,但它是有节奏的,舒缓而轻松的,一如清风拂过树梢,又如泉水淌过山岩。蝈蝈不但叫声好听,也好养活,既不吃粮食,也无需饮水,几片鲜草叶,一朵倭瓜花,三两天之间就不用去管它。它于是成为人们紧张忙碌之间的宠爱和休闲。大人在农忙间歇,总免不了要为孩子用麦秸编个笼笼,然后捉一两个蝈蝈放进去,那可是对我们听话不贪玩的最高奖赏。每到夏夜,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挂着蝈蝈笼笼,人们便在一片蝈蝈的鸣叫中纳凉、谈天、憧憬着一季的好收成……
绿褂褂,大肚肚,
蹲在笼里好快活。
长胡须,短胳膊,
不爱跳舞爱唱歌。
当我把这个谜面说给我四岁的儿子时,他张口就说是蝈蝈。这是他从谜语书上学来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真蝈蝈。这天,我就带他到单位来见蝈蝈。儿子见了很喜欢,便抱着小葫芦不撒手。老李微笑着说让孩子拿去吧。这可不行。最后只好拜托老李为我们买一只。
虽然只花了十块钱,蝈蝈却是新年礼物里儿子的最爱。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看蝈蝈,下午从幼儿园回来的第一件事还是看蝈蝈,每次看过都说蝈蝈饿了,要拿菜叶往小葫芦里塞。每次听到蝈蝈的叫声,不管他在忙什么,都会立即竖起耳朵,然后兴奋地跑前跑后,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蝈蝈叫了!蝈蝈叫了!”仿佛别人都没有听见似的。我们家一不养猫二不养狗,这只蝈蝈,俨然就是继儿子之后的又一个宠物了。
在把蝈蝈交给我们的时候,老李说,因为是反季节蝈蝈,寿命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注意两点,一是蝈蝈喜热怕冷,平时要放在暖气片上;二是蝈蝈喜欢干净,隔几日就得把它的小葫芦清洗一下。
我们便按老李的提示饲养着这只蝈蝈。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单位门房的蝈蝈不再叫了,老李说已经死了多日了,但我家的蝈蝈还在叫着。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慨万千。
妻子说蝈蝈的葫芦太小了,一个菜叶放进去,它的胳膊腿儿根本就伸展不开,太委屈了,不能换个大点儿的笼笼吗?我说大概就是为了保暖吧。正月十六那天,当我把小葫芦从暖气片上拿下来,葫芦里空空如也,蝈蝈居然跑了!分析半天,是上一次喂食后没有盖好塞子所致。我们把暖气周边找个溜够,找到了滑落在地面的塞子,却没有见到蝈蝈的影踪。妻子安慰着不住抹眼泪的儿子:“蝈蝈这下自由了,你不希望蝈蝈自由吗?”我则起了隐忧:“这蝈蝈能去哪里呢?九层高的楼,外面一片严寒;如果还在家里,它又怎么能找到吃的呢?”
第三天中午午休时分,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一阵蝈蝈的叫声。我以为自己在做梦。我睁开眼,它还在叫。我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循声来到客厅。让我大感惊诧的是,那只蝈蝈就爬在我们平日放葫芦的暖气片旁边的窗帘上,离那只空空的葫芦只一拳之距。我想,这只蝈蝈是有灵性的。它渴望自由,便离开了没有设防的葫芦。离开了葫芦,更大的外面的世界过于寒冷,不能去;这家里倒也暖和,却怎么也找不着吃的东西。在自由和生存之间,它挣扎了三天,也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还是回到葫芦里吧!
当我把蝈蝈捉进葫芦时,平日灵动的它,一动不动,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蝈蝈失而复得,欣喜之余,我却有了一丝感伤——我何尝不是这样一只蝈蝈呢?为了生存,只有待在这丰富而单调、熟悉而陌生的城市里,过一种“被安排了的生活”,只能把自由化成一种向往,对着梦中的田野,不断地叙说、鸣叫……
天气转暖的时候,妻子提出:“咱们把蝈蝈放生吧。”我同意,但儿子不同意,他舍不得。虽然白天气温高,但夜间依然很凉,我说再缓缓吧。三月中旬暖气停了,小葫芦意义也不大了,我们便拿出一个空纸箱子来养蝈蝈。纸箱子的空间是小葫芦的几十倍,蝈蝈得到了初步解放,似乎比原来更精神、更爱叫了。天气温和时,就把纸箱子搬上阳台,让它晒晒太阳。相对宽敞的空间、温暖和煦的阳光,我想,这些,或许就是这只反季节蝈蝈能够活过三个多月依然不死的原由。
这几天中午,我总是要回家去,午休之余,也是想听听这只蝈蝈的鸣叫。大概是大限将至,它身体已经开始发乌,叫声也变得短促而零落,但它还在坚持叫着。我想,它倔强地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对自由的讴歌和生命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