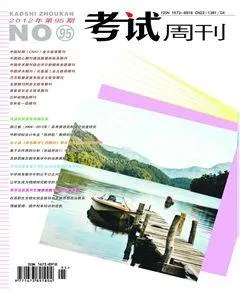以画入境,相得益彰
对于张岱《湖心亭看雪》这篇课文的处理,我力求遵循“简化、优化、美化”的原则,也就是科学地对教学内容进行提炼、精选、整合,以“短文细教”与“美文美教”的处理方式贯穿整个课堂。在最终确定的几个教学目标中,“品味白描手法,感悟文章的简约之美”成了教学难点之一。如何把文中的白描手法用更直观、更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是我在备课中思考的问题。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白描手法炉火纯青的运用,量词的精当选择,让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成了名篇中的名句。我参看了几十篇《湖心亭看雪》的教学设计,发现对于这句话的教授一般都采用诵读、点拨、讨论的方法。在学生进行品味之后,教师一般都会以“作者用绘画的手法寥寥几笔就勾画出景物特征,长与短,点与线,方与圆,多与少,大与小,动与静简洁概括。表现出悠远脱俗,苍茫静寂的情味”之类的话做总结,告诉学生这句白描的好处在这里。
第一次上这篇课文,我也是循规蹈矩地以常规方式“顺利”上完,但看似顺利,自己心里却总有一个疙瘩,别别扭扭,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未让学生在上完课后对这句白描的景物真正有所体会,并深切感受到它的美。自己的那几句对于白描手法的总结不过是隔靴搔痒,学生听来是雾里看花,但终隔一层。而这却恰恰是这篇教材存在的意义之一,我感到一丝遗憾与不甘。
于是在第二次上这篇课文前,我认真思考如何把白描手法讲清楚,如何把句子中的几个量词的精当之处讲明白。最终,我受到几张图片的启发,选择“以画入境”的方式讲授,课堂效果令人满意。
首先,我在课件上先用两幅牡丹图让学生了解何为白描与渲染:左侧一幅为白底黑墨线勾勒的牡丹,不着任何色彩,脉络清晰,简单纯净;右侧为水墨渲染画成的牡丹,浓墨重彩,以色块的深浓浅淡来表现花瓣与叶子的质感。让学生了解白描既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更是一种中国画技法。如右侧的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彩色的画法即为白描;文学表现手法上的白描则指主要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辞藻修饰与渲染烘托。而右侧则是渲染,其实文学中也有渲染的手法(由于渲染手法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一句带过)。
其次,联系旧知,发挥想象。通过对人教版七年级的《天净沙·秋思》的学习,学生对白描手法已有印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单纯景物的排列,就能让读者在脑海中描绘出几幅完整的有意蕴的画面,而不需要更多细致的形容与描绘。以此类推,一座长堤,一座湖心亭,一艘小舟,两三个人,凑成了一幅“西湖夜雪图”,这样的想象对八年级的学生来说并非难事。
最后,揣摩句子中量词的妙处。先问学生一个常规的问题:如果把原句中的“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换成“一道、一座、一艘、两三个”好不好,为什么?答出不好之后,思考为什么才是重点。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让每个学生都拿出纸来画一画“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看看怎么画才恰如其分。大约过了五分钟,大部分学生从冥思苦想中欣喜地放下了笔。我先叫一个举手的同学上来画一画,有不同意见的再上来修改和补充。
自告奋勇上来展示的甲同学是班里的画画能手,只见她三下五除二就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完成了任务:一道蜿蜒的长堤,一座精致的六角凉亭,一艘两头翘起的小船,三个并立的人。甲生画完后信心满满地下去了。这时下面有很多学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纷纷举手,没等我点名,乙生便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她画得不对,虽然画画水平不错,画得很好看,但是和句子描绘的情景不一致。”“哦?怎么不一致呢?”我饶有兴趣地听他说完。
乙生说:“我觉得她画成了一道、一座、一艘、两三个了。句子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可见这长堤不应该画得很明显很浓,亭子也看不太清楚,小船不应该这么大,人也是。”这时,丙生兴致勃勃地要求去改,只见她擦掉原来清晰的长堤,用粉笔的侧面淡淡地扫过去,描绘了一道长堤的模糊的模样,把小船改成了一片竹叶般窄小细长,把清晰的人改成了两三个抽象的小圆圈。下面的大部分同学都表示赞同。这时又有一个学生上去把那个两三个小圆圈改成了竖立的米粒状,并解释:“这才叫两三粒,人不可能是几坨,应该远看像米粒一般才恰当。”话音刚落,全班同学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我的心里更是欣喜不已:没想到学生想得比自己想得更细致、更到位,而且敢于质疑,敢于表达,深入思考的氛围也让枯燥的文言文学习活跃了起来。
表扬了这一点后,我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张岱用了“痕、点、芥、粒”这几个量词,而不用“道、座、艘、个”。其实在刚才思考、绘画与修改的过程中,学生已经自己有所感悟。甲生说:“我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画得不恰当了,张岱用这几个词是跟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当时是大雪下了三天,雪已经积得很厚了,又是更定的时间去湖上,夜色朦胧,看东西肯定是不清楚的,所以画面上的东西应该都是朦胧而模糊的。白雪世界有一种朦胧和神秘感,更有一种白昼所看不到的光线。而且当时天与云与山与水,都是浑然一体,在这个大天地里,亭子,船和人都是小小的。芥是小草的意思,所以画成一片叶子的形状更恰当。这样既创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朦胧意境,又使人感到在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听完学生的回答,我想他们自己应该可以通过这个环节理解白描手法与量词精当选用的妙处了: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数量词的使用抓住了事物的形态与神韵;而没有色彩,留有余白的画面上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一幅写意的山水画,往往能给人更多的遐想,更多的余韵。
这时候,再引出那句总结,应该就水到渠成、恰到好处了,我心里的别扭感觉也终于烟消云散。看到学生靠自己动脑思考,动手实践,积极交流品味到了本文的妙处,而不是靠自己填鸭式地灌输,我感到非常舒畅。
梁衡在《秋月冬雪两轴画》中就把此文比为画中精品:有一种画轴,静静垂于厅堂之侧。它不与那些巨幅大作比气势,却以自己特有的淡雅高洁,使人喜爱。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就垂着这样两轴精品,这就是宋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和明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以画面阐释极具画面感的美文,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遇到抽象的概念或说法,让学生动手画一画,自己思考与分析,以画入境,相得益彰,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