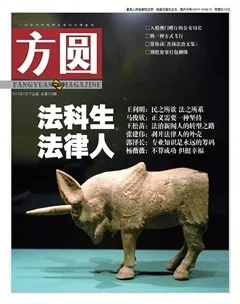法律人百年沉浮
2012-12-29 00:00:00靖力
方圆 2012年14期

【√】法律人总是有一种书生意气,百折而不挠,著名法学家江平有一句最经典的格言,可以评价法律人的共性:“我只向真理低头。”
又到毕业的季节,校园里总弥漫着喜悦与伤感的气氛。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所在的新主楼,电梯前挤满了穿着黑色学士服、蓝色硕士服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粉色垂布告诉我们他们是法科毕业生。
他们高声说笑,听来有两个主题:商量怎样在接下来的“散伙饭”中将导师灌醉;谈论毕业后各自有怎样的安排。听他们的谈笑,忽然想起听人说过,法科毕业生就像分岔的河流,一出校门总是各走各的路,有许多的职业和未来可供选择;然而又万涓入海,总逃不过汇聚到一起的命运,成为“法律人”的一份子。
其实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教育以及舆论等许多领域,常常可以看见以“法”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
他们可以是法官、检察官,可以是律师、法务,也可以是专家、学者,他们自称为“法律人”,别人称他们为“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人的概念与外延
近几年兴起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个新潮的概念,常用来指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家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这个群体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因为相同的“法”的背景聚集在一起,相互作用和联系。
在中国,法律职业成型很晚。“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职业法律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法理学研究专家孙笑侠在讲座上表示。只有一些兼职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比如讼师、书吏、刑名幕友(又称师爷)等等。
历代所谓廷尉、大理、推官、判官等并不是专门的司法官员,而是行政官员——司法者只不过是作为权力者的手段而附属于当政者。直到近代,受西方法律制度影响,才产生了律师、法官这些法律职业群体。
比较而言,西方的法律职业则诞生得早很多。意大利波伦尼亚的法学教育在11世纪末即已大放异彩,在13世纪末,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较大型大学都有一座法学学院。西方著名法哲学家韦伯曾在阐述西方专业官吏的兴起时说,由于司法程序的发展,欧洲的法律专家迅速崛起成为一种职业,司法程序的细密化要求决定了法律专家的地位。
相较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法律人”的概念更加古老,外延也更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徐家力在一次讲座上称,一般来说,“只要是具有较高法律水平的人,推崇利用法律解决问题,内心向往法治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法律人”。
在徐家力看来,“法律人”不一定是法学家,也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法律人可能的职业有8种之多,包括律师、司法官、法学家、法务、除司法官以外的公务员、有关法律的商业经济工作者、媒体记者、无关法律的工作者。前三类是法律人的核心,也是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
当然“法律人”的定义并不是唯一固定的,也有相对狭义的说法,即认为法律人就是法科学生和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人的合称。
孙笑侠曾经表示,大众思维基于生活逻辑,而法律思维基于专业逻辑。法律人和非法律人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就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大众以情感为重,法律人以理性为重;大众追求科学的“真”,法律人追求程序的“真”;大众喜欢遇事“权衡”,法律人则总是“非此即彼”……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则认为,法律人与“其他人”最为不同的地方,除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有专门的法学知识体系和普遍的社会正义感。汇聚了这三部分特点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律人。在这个范畴里,“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乡村的司法调解员,无论是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大律师还是小小的地方检察官,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还是啃着馒头咸菜在租来的房间里复习考试的法律自考生,都是法律人。”
中国法律人由近代起源
自商代以降,李悝、商鞅、张汤、卫觊、刘颂、柳宗元、王安石……屈指数来,中国古代不乏法学家,但沈家本却评价中国古代的法律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虽然有学法之人,却无安身立命之地,还遭到各种鄙视,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法学界最大的遗憾。而照现在的定义,这些没有法学“职业”的古代法学家甚至很难称得上是法律人。
真正以法安身立命的法律人诞生在近代中国,伍廷芳算是个中翘楚。他在林肯律师会馆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执业律师。1902年,伍廷芳应召同沈家本一起主持修律,可以说是法律人登上近现代中国历史政治舞台的处子秀。
法律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近代中国产生,要归结于清末大量法政学堂的设立以及留学研习法政潮流的出现。这有其时代背景和烙印:1905年清政府废除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读书人传统晋身官场之路被堵塞,而当时观念认为法政专业与为官之道相差不远,于是天下中学生群起而逐之。经济状况好点的学生东渡日本,而大部分进入遍布各省城乃至地方的法政学堂。其二,法政学堂办学成本低廉,对硬件要求不高,说办就办,办不下去就散。这与今天法学院遍地开花至少在表面上很相似。
这些历经法政学堂洗礼或留学务洋的人就这样成为中国第一批法律人。但这批人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留学派,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了所谓的卖国贼。更激进者如汪精卫,则在留学日本期间成为革命党人,在人弹袭击中一战成名,革命胜利后一度也成为党国元老。枪炮作响法无声,早期‘法律人’大都不务正业。”曾经著有《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陈夏红说,除去梁启超、伍廷芳等少数精英,最早的法律人多半沦为了时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反而是那些法政学堂,在硝烟中留存下来,奠定了中国大量法学院校的基础。如今,许多法学院校的校庆或者院庆,往往将建校(院)时间追溯到1905年左右,把当年的法政学堂当做它们的前身。
法律人群体的浮沉遭遇
一个诞生在硝烟中的婴孩值得同情。法律人群体的发展壮大,一直在战争状态下进行,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似乎法律人一出生便没过过好日子。
毫无疑问,1949年对于中国法律人来说是个分水岭。解放战争得出分晓后,摆在中国法律人面前有一个时代的抉择,“该何去何从”?
这里面,既有远走美国的,如顾维钧;亦有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如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王宠惠、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重庆《中央日报》总主笔蒲薛凤;当然还有大部分,则留在解放区,期待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这部分人很多,如罗隆基、王造时、杨兆龙、李浩培、韩德培等,甚至不乏如钱端升这样放弃哈佛访学良机而留在中国大陆的。
难以想象的是,1949年前即已成名成家的这批法律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境况竟然最差,命运的悲剧性最为强烈。
国民时代“六法全书”的废除,相当于废除了这批法律人赖依安身立命的法律体系;其次,决绝而无情的思想改造,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了他们。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调整,将传统的大学体制破坏无余,原来的法学院被拆分,然后装入革大师生主导的几所政法学院,法律学者再度丧失精神家园;同时,1951年前后掀起司法改革运动,司法系统内的从业人员全部被做为旧法人员而扫地出门。这样下来,不到三年时间,中国法律人忽如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赖以生存的体系。
到了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将几乎早已改行教外语的法律人划为异类,这里面杨兆龙、谢怀栻的经历十分惨烈。杨兆龙的女婿陆锦碧遭受迁连而划右、劳改,后因"牙膏皮事件"几近枪毙,当属惨烈者中尤为惨烈者。
与法律人的这种悲剧性命运相因应,即便如江平这样在1949年之后由政府自己送出去学法律的法律人,1956年提前学成归国后,也难逃反右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法律人的脾气
近代近百年的特殊经历,铸就了中国法律人与众不同的特质。
古罗马名著《法学阶梯》中有一句名言:“法学乃正义之学”。从沈家本开始,中国许多OlJijMTMVLFc0HHRibg2Gg==法律人就坚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治学、入仕。郁达夫的哥哥郁华,早年在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法学,卒业后任民国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后来在担任上海租借区法院法官时,罔顾自己的生命,救出了田汉、阳翰笙等当时的进步人士。即使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受非议颇多的曹汝霖,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也因惭愧而拒绝与日本人同流合污。
除了高高悬于心中的“正义”二字,法律人最为看重的是他们为社会带来的改造。法学家谈理论成果,司法官则重实践成果。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博士王利明在接受《方圆》采访时就多次表示,“法学家应当尽可能的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学智力成果”。
生于1916年的“行政法之父”王名扬,在饱经劫难之后的古稀之年连续推出了《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三部著作,开辟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阵地,在80多岁接受采访时,王名扬还说,身在一个适合著书立说的时代,他计划写出5本关于行政法的书,3本已经完成,另一本《比较行政法》已写了一半。后来虽然因身体原因,王名扬未能完成计划中的5本著作,但其法学研究的公心,已经广为世人知晓和赞叹。离开东交民巷4年之久的前首席大法官肖扬,最近在其新书《肖扬法治文集》中依然在思考中国的司法改革问题:“当依法治国已经被确定为基本方略之后,在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的今天,应当遵循怎样的推行路径?是否继续依法‘自下而上’地摸索,抑或站在国家的全局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依法‘自上而下’地推行?”
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法律学家边沁曾经说:“法律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追求正义、追求成果,成为中国法律人最大的共性。在陈夏红眼中,这也成为法律人几经沉浮而命途多舛的原因。
“法学毕竟是依赖于书本和理论的学科,所有的法律人都会带点倔强、固执的坏脾气。他们在时局混乱、崇尚武力的时代,地位本来已经很尴尬,但因为其固守的追求,使得他们的遭遇更加难堪。这种时候,‘法律人’与当权者的关系,往往就成为决定他们能否在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建功立业的基础。因此‘法律人’的基本命运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关系好时法典化如火如荼,司法建设捷报频传,‘法律人’恨不能身兼多任,鞠躬尽瘁;而关系变差时,右派、劳改、入狱、监禁乃至各种各样的被死亡、被失踪,法律界可谓是重灾区。”
陈夏红说,替法律人反省,他们气质上先天性地偏于保守、理性,但又有一颗忧世忧民企图闯出一番天地的心,这在热衷于搞运动、闹革命或动辄约架的国度,不大可能占到大便宜,于是在时局最动荡的时期受苦受累便成了必然。
曾经有人评价法律人“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法律人总是有一种书生意气,百折而不挠,著名法学家江平有一句最经典的格言,可以评价法律人的共性:“我只向真理低头。”
六代法律人
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劫后余生的中国法律人总算迎来一段不那么灰暗的日子,往日的错误被逐渐纠正,新一代的法律人才终于能站在法治的最前沿。1977年至今,法学院校的恢复和重建、国家立法的进步与完善,各种情势都显示出法律人冰雪初融的春天正在到来。
中国这崭新的一代法律人,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称为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法律人,并寄予厚望。他曾撰文《书生事业,无限江山》阐述了他划分的理由。
许章润文中的前四代法律人,许多都已成为历史,健在的也大都进入耄耋之年。这些法律人或在百年洪流里留下了珍贵的法学研究史料,或在新的时代厚积薄发,完成了为后世法学的最后一推。许章润说,当今时代,是第五代法律人甚或“第六代”法律人的时代。“如果说现代中国法学肇始于百年之前,脱手于第一、二代法律公民,那么,必最终成型于第五、六代的努力之中。”
许章润所谓的第五代法律人,即现在正值壮年、在法律界当家做主的法律人,第六代法律人,大概就是指仍在象牙塔中磨砺自己充实自己的准法律人吧。
根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法律人可能已有百万之众。这个数据也可以透过司法考试大概推理出来。
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律师资格考试在1993年以后改为每年一次,2001年以后更名为国家司法考试。然后就是这个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了当代法律人必须迈过的门槛。如今,要当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律师、大学法学教授都需要通过司法考试,甚至一些公司招募法务、个人寻求诉讼代理人也都有此要求。通过司法考试不再仅仅是律师一个行业的入行资格,它渐渐演变成为了所有法律职业的共同门槛。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相关数据,近几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数,2002年首届通过人数为24800余人,5年后的2007年这一数据增加到58800余人。一直到2011年,总共举办的10次司法考试,全国共有50余万人通过。加上在校就读的法科学生、在此之前的少数“免试”的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以及一些基层单位未通过司法考试但仍旧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员,中国的法律人也许接近百万。新时期的法律人数量如此巨大,那么这些法律人过得好吗?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潘跃新说,至少律师过得不错。
截止到2008年,中国有12万执业律师,全国律师事务所超过1万家。较大型的律所有拥有超过50个律师的,年创收能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但比起国外动辄成百上千人的大所来说仍然不算什么。另外,随着法治建设发展,律师也越来越成为高收入、高地位的职业。
还记得1997年以前,中国律师办案都按照一个律师收费标准领取每一次案件的劳务费。刑事案件50元,民商事案件按案件标的的3%-5%提成。那时候,经常会有提着破公文包上法庭啃冷馒头的律师出现。现在情况好多了,不仅各地纷纷揭开收入帽,而且在京沪等发达城市,有一些律师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几十上百万,也算得上标准的高收入人群了。
至于法官、检察官,更是年轻法律人最为醉心向往的法律职业。据相关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检察官人数达到11万人,而全国法官人数早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22万人。接受《方圆》采访的西安市中级法院法官葛峰向记者表示,法官的形象在他年少的时候就给他留下机敏而庄严的印象,当上法官之后也非常以自己的职业自豪,也许这能代表所有法官、检察官的心声吧。
在学界,法律人的势力也迅速扩大。来自201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目前已有12所高校是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30个学校将近50个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更不计其数。在立法、司法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名师参与进来。许多法学院校的教授均在法院、检察院兼任重要职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在最近的一篇回忆学生吴丹红的文章中,也有部分文字提到自己的博士生,都有不错的着落,有的毕业至今甚至有所小成。这也从侧面说明,法律人的队伍,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与培养中,不断充实和扩大着。
当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责任与期待
现在许多研究法律人群体的人,喜欢将法律人称作“法律职业共同体”,有人评价这个称谓,说它太“功利”,“应该相互对立的几个职业被放到同一个体系中去,不成体统”,不符合法律人应有的孤独和正义的感觉。
但也有人认为,法律人应当将自己置身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环境中去,才可能完成一位法律人的职责。有人打过一个比方,法学家类似于种植者,他们通过参与立法、教育法科学生,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律师和检察官则像保护枝桠的人,帮助不同角度伸展的枝桠获得阳光和雨水;法官则是最终修裁植物的人,他判断植物生长是否匀称是否有顶端优势,然后决定哪个枝桠需要被裁剪,哪个需要保留。
支持或者否定,从两个方面给法律职业共同体带来启示,即互助与制约应当并存。
然而,如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却因为其不够团结、各自为政的现状,给一些法律人带来了深深的忧虑。
有学者表示:“有时候,表面上我们在试图通过司法考试,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实际上法律人内部的结盟与敌对状况却越来越严重。说结盟,既有办案机关联合办案、不分你我的结盟,也有律师们同声相应、互相声援的结盟;说敌对,则更显而易见,司法机关与律师互不信任的状况无以复加。有些刑辩律师走投无路,要么把当事人救出来,要么自己被关进去。我认为,不管是律师、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应该先做到行业内部的自治,然后才能去管别人的公平正义,如果最该追求公平正义的团体自身不保,那还谈何其他?”
清华大学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韩世远在201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说,法治要求法律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在规则中互相制约他们行为和理想,法律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法治中国。法治中国又必须要有统一的行为方式:规则之治。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也曾撰文表示,法律人需要有共同的标准和理想。王振民认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要有顽强的毅力,要有很高的与人协作的情商和协调能力,要有高尚的品格。
无论是王利明、王松苗还是葛峰、郭泽长,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人在各行各业都呈现脱颖而出的趋势,司法界、政治界、商界以及社会各界都有法律人正在成为领袖。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种趋势。这既是许多非法律人学习法律的动因,也应该成为法律人坚守法律的理由。法律人既然已经作为上层建筑的构建者,就应当承担约束,完成社会使命。
采访中,陈夏红也说,研究所谓法律人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历史和现状,尽管无法转化为现实的GDP,但对于中国的法律环境,对于新生代法律人的启迪,有很大价值。
商鞅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他还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同时,商鞅还主张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中国法律人之最
》最早的律师: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是清末民初的法学家,祖籍广东新会。他早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在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得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
1877年,伍廷芳回到香港,当即开业做律师。他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执业律师。
洋务运动开始后,伍廷芳被李鸿章辟用,开始了一段辗转的仕途生涯。他先在李鸿章身边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等。后又担任清朝住美国、西班牙等国的公使,还主持修订晚清法律。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又陆续担任了民国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等职。
1917年,年逾70的伍廷芳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5年后,因陈炯明的叛变惊愤成疾,逝于广州。
》最富的法律人:李嘉诚
要说李嘉诚(1928-)是法律人,肯定很多人不相信。事实上,李嘉诚获得过3个国家或地区的4所高校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加拿大的卡加里大学。早在1985年,李嘉诚就被选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虽然未曾进过法律院校,但其好学的品格使他比许多科班出身的法律人更加懂法。
李嘉诚可以称得上是最富的中国法律人了,2012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诚名列第十,资产超过了240亿美元,这也是李嘉诚首次进入该榜单的前十名。
》最长寿的法学家:芮沐
去年辞世的芮沐(1908-2011),享年103岁,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长寿的法学家。
芮沐作为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学科的奠基人,曾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法学学府任教。芮沐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对待法学教育异常重视,数十年如一日。他在70岁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直到2000年,92岁的高龄的他,还在带着好几个博士研究生。
芮沐年轻时英俊潇洒,踢足球、游泳、骑马、击剑无一不通,也许对体育的热爱正是他长寿的秘诀吧。
》游学最广的法学家:吴经熊
吴经熊(1899-1986)一生的游学遍及世界10余个国家和地区,可谓中国游学最广的法学家。他是浙江人,长大后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在后来又转到东吴大学。
国内辗转多次以后,吴经熊从东吴大学毕业,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习,1921年获得法律博士以后,吴经熊又先后赴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访学。
在欧洲周游一圈以后,吴经熊回国任教,先后出任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法官、立法委员等要职。期间,吴经熊多次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等地讲学。
1937年,吴经熊皈依天主教,全家移居罗马,同时出任民国驻梵蒂冈教廷公使。
1966年,吴经熊再度移居,迁至台湾。20年后,87岁的吴经熊终于彻底停止了他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