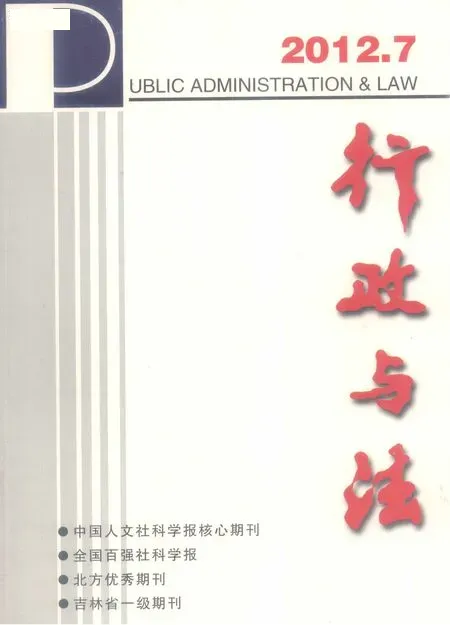灾害救济与权利保护
——我国强制农业保险的法理分析
□ 何文强
(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灾害救济与权利保护
——我国强制农业保险的法理分析
□ 何文强
(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对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规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将购买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灾害救济和其他农业资助计划前提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根据在于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彰显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基本人权地位。强制农业保险能够使农民原来无法预期的国家无偿救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预期和可以救济的权利。
强制性农业保险;灾害救济;权利保护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和灾害救助的主要工具,应当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和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法的缺位,我国农业保险没有发挥其风险管理和灾害救助的功能,目前的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又将农业保险提上议事日程。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表现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如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农业保险将不可能得以稳步发展。国家和社会需要对农业保险进行法律规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农业保险立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业保险立法对基本农业保险是否采用强制保险的原则?强制农业生产者投保的正当根据何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农业保险立法。
一、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在国外的演进
最早建立强制农业保险制度的是日本。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经常给农业带来巨大的灾难。由巨风、干旱、病虫害、夏季低温造成的损失非常惨重。为了帮助农民进行农业风险管理,日本早在1929年就制定了《牲畜保险法》,开始了农业保险的尝试。1938年又制定了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并于1939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政府就此资助15%的保险费。1947年12月开始实施《农业损失补偿法》,政府又将保险费的资助标准从15%提高到50%。依据该法,在组织形式上采用“三级”共济制度,即设在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与农协相独立),设在都、道、府、县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农业共济联合会,设在农林省承担各种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再保险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此外,还建立了以各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成员的“农业共济基金”,为联合会提供大灾之年赔偿资金不足时的贷款。
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日本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并且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农作物(粮、油等)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对其他经济型作物和宠物实行自愿投保。当一个农业共济联合会建立后,位于该共济联合会中的农民只要种植了可保农作物超过某个最大数量就自动成为该协会的会员。1957年以前,农民种植的可保农作物超过0.1公顷就必须购买农业保险。1957年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种植的可保农作物超过0.3公顷时,农业保险才是强制性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的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商业保险公司,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共济组合。日本政府在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同时,给予农业保险大量的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并为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60多年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减轻自然灾害损失、稳定农民收入、合理分派农业资源的有效手段,已被日本政府和生产者广泛认同。[1]
20世纪30年代,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美国联邦政府灾害援助政策一般是由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农作物保险;二是紧急贷款;三是直接的灾害救济。灾害救济计划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但该计划因其成本支出和鼓励高风险区生产而受到尖锐批评。因为,灾害救济计划鼓励了道德风险,以及其禁止种植条款能够刺激在贫瘠的土地上纯粹为获得补贴而进行生产的行为。[2]在1974年至1980年之间,美国政府每年大约支付了4.36亿美元的灾害救济费。[3]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此后。美国对农作物损失的援助主要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来进行的。美国《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主要目的是以农作物保险的补贴代替灾害救济,使农场主在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时获得实际可靠的保障。从1980年到2000年这20年里,农业生产者除了获得220亿美元的农作物保险赔偿外,还获得了250亿美元的灾害救济。经过多年的运行,《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暴露出以下不足:第一,由于原来的灾害救济项目的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生产者无法预先知道一旦遭受灾害将得到何种程度的赔偿;第二,在农作物收成不好的年份,生产者预期会得到联邦政府的灾害救济,这就影响了生产者参加农作物保险的积极性,降低了农作物保险的参与率,对农作物保险的精算平衡造成不利影响;第三;从1989年到1994年,特别灾害救济项目的支出每年超过预算15亿美元。因此,1994年美国国会对《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进行了修改,颁布了现行的《1994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该法间接地实行了强制保险制度:建立了农作物大灾保险项目,①大灾保险,是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一种基本保险种,联邦农业保险公司按农作物产量的50%和期货价格的55%承保,保险费全部由联邦政府支付,农民对每县的每种农作物只需交纳50美元的行政管理费,1999年提高到60美元,但一个农业生产者对所有县的所有愿投保的农作物交纳的行政管理费最多不超过600美元,并且对联邦农业保险公司认定的资源有限的农业生产者免去行政管理费。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7-AGRICULTURE Chapter 36.Crop Insurance Section 1508.所有的生产者都必须为需要的农作物投大灾保险,否则在本农作物保险年度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灾害救助利益;取消了特别灾害救济项目;参加农作物保险是获得联邦政府所提供的价格支持、生产调整服务、支农信贷、公共准备基金等项目的前提。[4]
菲律宾政府十分重视发挥农业保险在实施农业生产计划中的风险保障作用。1978年政府就开展了以增加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技术革新计划,研究推出农业保险计划并成立了专门的农业保险经办机构 (农作物保险公司)。近20余年来,农业保险计划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生产计划的实施,而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保障风险为一切险,包括:台风、洪水、干旱、火山喷发、所有病虫害,但疏忽损失除外。分别由政府和贷款机构承担保费补贴。在政府信用监管计划下为水稻、玉米生产而获得生产贷款的农民必须强制参加水稻农作物保险。[5]从实行效果看,贷款农民对强制参加保险并无不满,其主要原因是保费补贴很高。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政府农业信贷政策的鼓舞,自筹资金农民自愿参加保险的户数也在不断增加。
二、我国强制农业保险的法理依据
农业保险合同是经由意思表示而形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不得彼此强制。但从国外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看,如前所述,立法除采用自愿原则外,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实行了强制保险。在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理论探讨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应当遵循国外的做法,对基本保险采用强制原则。但对农业保险是否实行强制保险,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反对在农业保险中实行强制投保的学者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其一,我国《保险法》第4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其二,农业保险监管技术手段滞后。强制农业保险需要完善的监管手段来防止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和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与创租行为,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监管技术,以及监管成本的高昂可能最终导致强制农业保险无疾而终。而主张在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中采用强制保险原则的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寻求正当化根据。有的从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的要求、避免逆向选择、有效防止道德危险的角度论证后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应当采用强制保险原则。[6]经济学家则更多地从效率的角度论证农业保险应当采用强制保险.庹国柱认为,为了农业保险的整体效率和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应当实行强制保险。[7](p249-252)
虽然上述反对理由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这些观点并不能成为否定强制性农业保险的充分根据。其一,我国保险法和农业法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的规定是针对纯商业保险而言的,对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并不具有约束力,在未来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时,将重新确定其原则。其法律依据是我国《保险法》第8章附则第155条:“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其二,通过农业保险监管技术手段的创新,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和管理其他农业风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将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由此能够降低监管成本,从而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性、公平性和安全性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进而确保农业保险的持续、健康地发展。
笔者主张国家对基本农业保险实行强制性保险,但单纯从保险技术和经济效率方面寻找强制农业保险立法的理由实难充分。其一,上述支持观点从农业保险的技术和效率角度来论证强制农业保险,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避免逆向选择、有效防止道德危险,农业保险合同从技术上可以规定免赔额与共保条款,或者建立损失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共同分担风险的其他机制来实现。其二,通过强制保险来强迫低风险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投保虽然能减少逆向选择,但是,强制保险通常会减少这些投保者获得的好处,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8]其三,大幅度地提高对投保农民的保费补贴和行政管理费的资助,农民的参保率就会提高。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就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其四,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考虑。因为,经济原则意味着人们或者以一个预先给定的,可以支配的投资总额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或者相反,如果作为目标的收益是预先给定的,则以尽可能少的投资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况下则追求费用的最小化。但从这个原则中个别推导出来的经济规则与伦理准则或法律原则无关,在这个意义上的经济观察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在现实中,经济上的合乎规律性必须与伦理准则和法律要求相一致。[9](p92)因此,除上述保险技术和经济效率方面的理由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法理路径中来寻求强制农业保险的充分且正当的依据。
在本文语境下,强制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对基本农作物按产量的60%和期货价格的65%承保,对投保的农业生产者进行大部分保费补贴或免保费,投保农业生产者交纳适当的行政管理费,并且对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认定的资源有限的农业生产者免去行政管理费。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必须为需要的法定的农作物投保此险种,否则在本农作物保险年度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灾害救助利益,也不能获得政府所提供的价格支持、生产调整服务、支农信贷等项目的支持。
强制农业保险和一般的强制合同不同,它不与责任相连,而与权利相关。也就是说,如农业生产者没有购买强制农业保险,并不会承担私法上的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和公法上的责任 (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将失去国家的农业灾害救济、农业支持计划以及紧急贷款计划所给予的权利。但农民在灾后获得社会救济的社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所确认和保护的权利,也是国家的一种宪法责任和法律责任。其具体体现在现行《宪法》第14条第3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如果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就不能获得政府本应支付的灾害救济,对目前我国大多数还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侵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也就是侵害了农民的生存权,进一步说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农民将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购买保险,要么失去应有的救济。农业保险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农民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全面增进农村的社会福利,让农民共享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但对没有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来说,作为手段的农业保险与其目标相背离,不具有合乎目的性的本质。将购买农业保险设定为农民获得国家救济的前置条件是否与此相悖?对此问题的理性回答就是对强制农业保险的充分且正当的根据的合理求证。
当立法者为了实现一定的正义准则而拟订法律时,必须研究大量的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能轻易地从一般的正义准则中推导出。这里更多的是关于相应的规则的合乎目的性,以高效率地和同时谨慎地(顾及其他法益)实现立法者的目的。[10](p279)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本文认为,将购买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灾害救济和其他农业资助计划的前提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根据在于,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彰显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基本人权地位。
虽然农业灾害救济是国家的一种宪法和法律责任,是一种社会保障,表现为一种国家责任、一种政府行为,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救灾面较小,救济标准相对较低,农业灾害救济无法可依,缺乏必要的程序,救灾资金被截留、挪做它用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现实的图景是农业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①据民政部《2001年中国民政事业统计公报》,当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救灾资金40多亿元,受灾人口3.7亿,成灾人口2.6亿,救济了15%左右的受灾人口约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不足一百元。2006年6月25日,陕西省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仅埝桥乡受灾土地面积就超过了3万亩,经济损失至少也有1000万元。损失超过1万元的埝桥乡黄营村老赵最近拿到了乡政府发给的救灾款——一共9元。老赵家有9口人,平均每人1元钱。老赵说:“一人1块钱,你说能买啥,连1斤面粉都买不来,这不是耍咱吗?”(据2006年10月31日《华商报》报道)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却点名指出:“2003年云南大姚地震救灾资金管理使用中,截至2004年3月,中央财政下拨的1.2亿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仍有5174万元滞留在县级财政;有关部门挤占挪用救灾资金4111万元,主要用于平衡预算、兴建楼堂馆所及招待费开支等。”在现行的农业救灾体制下,农民受灾后,如果国家不给予救济(或救济太少),尽管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当然包括农民在内)的宪法权利,但农民的此项权利却无法得到救济。因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并没有将此纳入其规范范围内。农民灾后获得国家救济的权利受到侵犯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救济范围。也就是说,农民在受灾后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的救济,不能仅以自己的社会保障权受到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同时,我国宪法对公民社会保障权 (当然包括农民的灾后获得国家救济的权利在内)的保护也存在一定缺陷:第一,社会保障权在宪法中的法权性质不清晰明确,相关主体(在社会保障中主要即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也就难以分明;第二,宪法规定的许多基本权利事实上处在虚置状态,有部分长期停留在宪法文本中,缺少成为实有权利的必要渠道。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宪法的非司法化。由于没有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直接在司法中适用,因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得不到司法的有力保护,尤其是当宪法权利没有得到部门法的具体保障时,情况更为严重。缺乏可诉性的权利只是纸上的权利,而无法获得救济的权利,也不会得到认真地对待。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提出一个著名的论题:认真对待权利。他认为,“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11](p270)
保护农民在灾后获得社会救济的社会保障权根源于社会正义的思想,它是对所有旧的关于交换正义或者分配正义思想的现代重塑。托马斯·冯·阿奎那根据形式将正义划分为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法律正义。他认为,交换正义(衡平的正义)是规范个人之间的行为;分配正义是规范社会整体(国家)对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正义是调整个人在对公共福利的义务中与整体的关系,包括对法律的重视。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正义的意义尤为重要。霍恩认为,分配正义,是指国家根据其收入和适当性对其公民的财产和利益提高保障。根据社会正义和社会保障准则,国家有义务保障所有人获得有尊严的生存最低标准;另外,立法者应从社会正义和社会保障意义上来塑造社会关系。[12](p305)
用强制农业保险代替无偿的农业灾害救济可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利。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和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属债权法上契约之一种,因为经双方意思表示达成合意,合同成立生效 。农业保险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就将不确定的灾害救济变为确定的利益。当农业灾害发生后,受灾农民就可以依照合同的约定请求保险赔偿,保险公司也将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赔偿金,否则,农民可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农业保险合同将在整个农业灾害救济中为经常可发生的机会主义和未能预料的突发事件提供确定的救济,并成为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工具,为农业和农村的安全提供保证。因此,强制农业保险使农民原来无法预期的国家无偿救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预期和可以救济的权利,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就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和切实的保证。
政府的紧急救灾援助在政治上非常受欢迎,也很直接,然而紧急救灾援助计划导致了许多特别问题的出现。主要表现在我国现行的农业救灾制度既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利也没有真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正义、分配正义和社会正义没有在我国农业灾害救济中得以实现,它还给农民的灾后救济造成了不确定性,因为只有在农业灾害发生后援助才具有可获得性,但对那些遭受了范围较小的自然灾害的农民来说,由于缺乏社会关注和公共支持,他们将不能得到紧急救灾援助;那些从农业紧急救灾援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农民是来自高农业风险生产区和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地区。由紧急救灾援助存在的不可靠性、援助的数量和时间表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灾害救济非常大的随意性,使得它不能作为长期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强制农业保险能够帮助农民做出更好的长期的风险管理决定,还可以提高银行给农民贷款的愿意度。再者,根据农业保险法的规定,赔偿数额也将大于国家的无偿救济,能够真正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综上,在我国未来农业保险立法时,应在农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强制性农业保险制度,但强制农业保险不应是农业保险的全部范式。强制农业保险能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但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因此,农业保险法除了规定强制农业保险外,还应给农民更多的自由选择,即提供不同的农业保险产品,由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成本收益权衡后做出购买与否、购买何种保险的选择。此外,强制农业保险不能完全代替农业灾害救济,即使在农业保险法律制度非常发达和健全的美国,政府每年都制定农业拨款法案,进行农业灾害特别援助。对那些在高风险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种植的农作物不能得到农业保险计划支持的农民来说,在发生农业灾害后,他们将有资格和权利在国家的非保险援助计划下直接获得资助。因此,国家在强制农业保险之外,还应该建立国家的非保险农业援助法律制度。
[1]Evolution of the Crop Insurance Program in Japan Toyoji Yamauchi[EB /OL].http: //www.ifpri.org/pubs/books/Hazell86 /Hazell86ch13.pdf.
[2]Miller.T.A.and A.S.Walter.Options for Improvement Government Programs that Cover Crop Losses Caused by Natural Hazards.”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ERS.No.654.March 1977.
[3]Chite.R.M.Federal Crop Insurance: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1988”,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No.88-739 ENR.December 1988.
[4]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7-AGRICULTURE Chapter 36.Crop Insurance Section 1521.
[5]PRESIDENTIAL DECREE No.1733 October 21,1980,Section 4 of Presidential Decree No.1467.
[6]施晓琳.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原则及组织体系构建[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0,(106).
[7]庹国柱.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8](Appel,D.,R.B.Lord and S.Harrington.“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Extension and Edcation Reform Act of 1998,Section 535 Crop Insurance Study,”Milliman and Robertson,July23,1999.
[9][10][12](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M].罗丽译.法律出版社,2004.
[11](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徐 虹)
Relieving Disaster and Protecting Right——Analysis of Legal Principle of Coerc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Our Country
He Wenqiang
It is an undoubted fact that we are hunger for criterion of coerc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Taking purchas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s premise of relief of agricultural disaster and other plans of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is sufficiently and justly based on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farmers better and honors the right of social safeguarding to farmers as basic human rights.Coerc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uld make former unexpected volunteer relief transform into substantial、expectable and relievable rights.
coerc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relieving disaster;protecting right
D922.4
A
1007-8207(2012)07-0103-05
2011-12-23
何文强 (1971—),男,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保险法和经济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研究:国际比较与国内路径选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82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