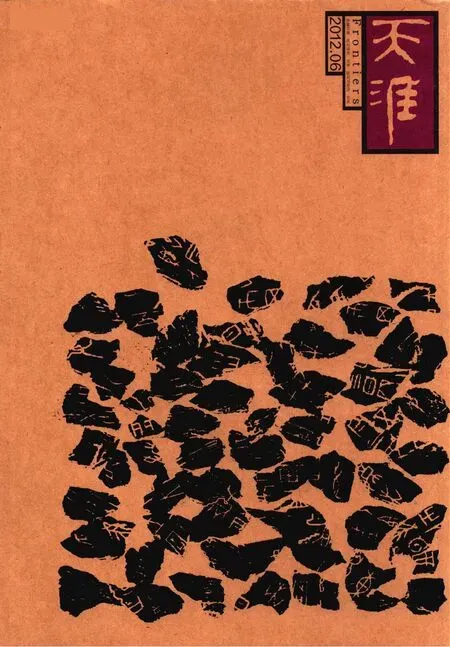势治秩序:转型乡村社会一种新的形态
陈占江
六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秩序:一种是乡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一种是工业社会中的法治秩序。在费先生看来,任何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或纽带必须与其社会性质相符合。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熟,较少发生流动,在这个熟人社会里维系秩序的主要是礼。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不像法律那样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而是通过传统和教化来濡化和规训一代代人并使其成为有效的自我约束力量。乡土社会中的民间纠纷也不靠法律解决,而是通过“礼”的化身——绅士或长老以说服、教育、劝诫等方式进行调解。礼治之所以能够在乡土社会中实现乃是由于礼治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宰的发展逻辑中,工业文明不断扩张而农业文明日趋式微,礼治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工业文明的法治逻辑通过至上而下的方式强行侵入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乡土社会。那么,法律在转型社会中所起到的功能如何呢?费先生对此有一段颇富警示意义的话:“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先发生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作为功能主义者,费先生认为在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负功能,送法下乡的弊端早已在实践中暴露出来。承费先生的余绪,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新时期对于法律在乡村社会中的遭遇和后果所作出的深刻的反思,我国法学界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派”亦持如是观。
乡土社会被费先生视为无讼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无讼与礼治是互为表里、并行不悖的。讼师的地位很低并在现实生活中被不断地污名化,无讼的理想也被儒家思想一再地强化。然而,无讼或礼治之所以能够在乡土社会中实现,其原因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和熟人社会性质的影响,与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亦有内在的关联。费先生曾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在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未将整个社会吸纳到皇权之中,反而由于地理、技术等原因导致“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县域以下的社会基本上不受皇权的直接干预,绅权成了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和桥梁,绅士在二者之间扮演着既代表皇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皇权的力量。所以费先生将乡土中国的政治视为皇权与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在这种社会中,法律扮演的功能更多的是维护皇权的稳固而非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在传统中国,无为政治既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也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和技术手段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国家的权力延伸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像毛细血管一样漫布于整个社会肌体,无时无处不有国家的影子。如果说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约束,那么新中国以来呈现的则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行政几乎完全将社会吸纳其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果是国家权力因没有有效的约束和制衡导致国家权力过度膨胀,而依靠国家力量予以保障实施的法律常常成了“政治的晚礼服”(冯象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和有力的监督,法律有些时候沦为了强者实现其意志或利益的工具。
按照费先生的理路,讨论在乡村社会能否推行法治的前提是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价值观念是否为法治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易言之,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是否存在“位育”的关系。当下的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社会结构已然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从农民的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看,费先生所言的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甚至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日渐模糊的历史剪影。仅以农民的法律意识而言,除特别封闭落后的乡村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已有大幅度提高,至少不像某些有识之士所认为的那样淡薄。当下的乡村社会似乎已为法治秩序基本提供了相应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今天的乡村社会是否实现法治了呢?
笔者近几年在安徽、湖南、浙江、河南、内蒙等地农村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调查发现,法治之于乡村社会有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法律在乡村社会中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农民在遇到利益纠纷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法律,“打官司”、“告状”等几乎成了当下的第一反应,然而究竟有多少人采取了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则值得深究。在笔者看来,纠纷解决中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法律是法治程度的一个重要判准。调查发现,农民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律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法律意识的提高而增加,反而出现了新的“无讼”现象。新无讼现象的存在显然不是因为乡村社会中的利益摩擦和各种纠纷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事实恰恰相反。农民之所以不愿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人情、面子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一则诉讼成本高,二则农民失去了对法律或司法的基本信任。诉讼成本较高一直成为阻碍农民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帝国时期如此,当今亦然。杨联陞先生在《中华帝国的作息时间表》中指出了这一点:诉讼的昂贵在中华帝国是尽人皆知的,对于容易成为官样文章和腐败之牺牲品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诉讼案严重干扰了农民的时间表,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不啻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我们的调查中,这种情况于今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当真正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农民的日常生活即被打乱,而这种日常生活更多的被打工或务农所占据,打工或务农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显然,仅时间的消耗对无闲暇余裕的农民而言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农民遇到纠纷往往经过一番理性考量后没有选择诉讼,而是选择了私了、妥协或隐忍。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时,大多数答案集中在诉讼成本上,一则延请律师花费不菲,二则漫长的法律程序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故此,一般而言,农民在遇到侵权时并不会选择法律而是寻求其他途径以求解决。导致无讼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司法的公正性由于权力、金钱甚至黑恶势力的介入而遭到严重削弱、侵蚀,从而导致农民并不相信法律。调查发现,当下农民的“冤屈”大多来自于强者的欺凌,而强者与司法机关通过利益结盟从而形成一个致密的权力网络,使得法律成了保护强者的工具而非弱者权利救济的最后稻草。调查中一个中年农民说道:现在最守法的是老百姓,最不守法的是那些当官儿的和有钱的,最可怕的是当官的和有钱的勾结在一起!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甚至认为普法运动的结果是制造了顺民,纵容了蛮官。
当下乡村社会的无讼,和费先生所言的因礼治和熟人社会而导致的无讼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乡土中国中的无讼是因为乡村是封闭自足的社区,自身有一套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无需向外借助于国家法律,那么当下乡村社会的无讼,则因为法律虽已进入乡村,但在异化的法律运作中弱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从而不愿求助于法律。有些乡村惧讼现象比较普遍,足见一斑。在内蒙的乡村调查发现,多数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却有着较低的法律期待,也即受访者虽然懂法却不愿用法,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法律是富人和闲人的游戏,穷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如出了命案或把事情捅大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眷顾。调查中遇到一村民告村支部书记的事情。该村民因受到村书记的不公正对待要将其贪污的罪行告上法庭,该书记叫嚣道:有本事你去告,你用自己的钱打官司,我用公家的钱陪你打,耗死你!结果,该村民知难而退。最近湖南的调查也遇到类似的个案。一位刘姓村民已经收集到村里组长的贪污证据,告了三年至今未果。该组长公开承认贪污事实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此期间他又到乡、区和市各级部门上访均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深感绝望。几十年前,诉讼也许在农民看来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现在反倒成了一种能力和地位的象征。若能将某人送上法庭在乡村无疑是一件相当“长脸”的事。如果说,法律从来都是各方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那么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中法律实践则是一种失衡的博弈。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能不能得到公正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如果力量均平,或许法律会以调解或公平执行的形式出现;如果力量失衡,法律的公正执行很可能变得不现实。对此,一个老年妇女愤怒地说道:现在打官司哪里有公平,打的都是关系和钱。你有钱有人法律就保护你,无钱无人就是你完全有理,法律也不会保护你。在调查中,受访者讲了许多身边法律不公平的事情,或许他们对于法律存在一定的误解,或许有夸大、歪曲的成分,但各种版本的“腐败”故事使农民失去了对于法律曾经抱有的信任和期望。
从上述讨论看,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礼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而法的“故事”正以各种形式流传,法律在乡间并未产生普遍的有效性。如果说礼治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而法治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那么礼崩乐坏法未行的乡村社会为何并未出现显性的秩序危机呢?当下乡村社会既非礼治秩序也非法治秩序,究竟属于何种秩序型态呢?一言以蔽之:势治秩序!在笔者看来,势治秩序已成为转型乡村社会一种新的型态。作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势不仅与姿势、形势有关,更多的是指势力、权力、力量等。在传统社会中,礼治的实现尽管与绅士或长老所具有的势密不可分,但这种势在很大程度上黏附在道德、等级、权威、面子之上。在纠纷调解中,更多的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非以势压人。当下的乡村社会,新旧道德正处于替嬗之间,道德空间为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伦理道德所充斥,且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而法律则存在文本与实践、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背离。乡村社会可谓是一个多元权威并存而又相互冲突抵牾的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市场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进入乡村,使得当下乡村社会出现红色、灰色以及黑色三色势力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大多数农民的弱势地位。在乡村纠纷中,礼和法几乎完全被势所取代,利益愈大的纠纷其解决愈依赖势的运作。当制度化的渠道不能为弱者提供权利救济时,弱者要么选择私力救济要么选择妥协和隐忍,而在现实中更多的选择了后者。富有隐忍精神和惯习的中国农民则为势治秩序提供了心理基础。由此可以发现,当下乡村社会表面的稳定是以弱者牺牲个人权益为代价的,而这种牺牲一旦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则可能发生悲剧性结果。势治秩序的存在折射出我国社会运行过程中潜伏的深层危机,为政者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