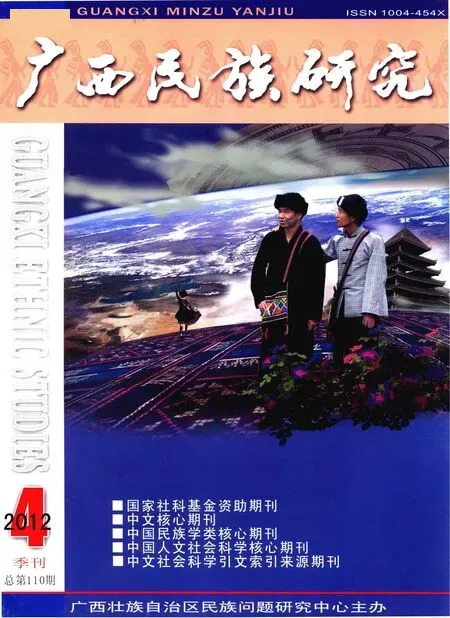意识控制与记忆建构:大众媒介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影响分析
才凤伟 刘 彤
一、引言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在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传统的印刷媒介 (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还是方兴未艾的电子媒介 (电影、广播、电视和网络等),都在潜移默化中通过无形的渗透,以柔性的手段改变着人类生存的世界。伴随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而来的全球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和观念,将世界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场域。“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正引发新的定位与迷失方向的体验,新的有区域性和无区域性的认同观。”[1](P164)而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由于文化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和背后所代表的实际利益的争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问题已被深深地纳入了民族国家的视野,大众传媒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影响问题也逐渐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
二、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民族意识的内涵,学术界的讨论有很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已经发表了有关民族意识方面的论著多达100余种。有学者认为,民族意识包括两层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感悟;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2](P142)前者可以等同为民族认同,后者则包括极其广泛的内容。熊锡元将民族意识表述为:“第一,它是人们对于自己归属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3]周传斌将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意识概念的讨论进行了总结,从内涵上将其划分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自我意识和对民族自我文化特点的觉察等6种类型。[4]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基本认定民族意识主要涉及到自身的民族认同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认识两个基本维度,前者为后者的发展奠定了基石。民族意识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产生以后,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跃在他的思维中。只有一定的外界诱因出现的时候……民族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感情才会浮现于他的思维之中,也才会影响他的心理感情、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5](P77)民族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文生态因素、大众媒介和外部政治势力等因素都会强化或淡化民族意识。“人文生态”指的是各个民族或族群在地理分布和居住格局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影响当地族群对待外族的态度和交往中的性格:四海为家的吉普赛人养成了随机应变、圆滑世故的处世态度;地广人稀的大草原,则塑造了蒙古人热情、爽朗的性格特征。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会改变既有的民族格局,对民族意识和认同产生影响。对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个具体民族,外在因素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众媒介作为影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作用越来越被各个民族国家和政府所强调。
三、大众媒介的影响手段
信息社会的到来构建了特有的媒介时空。人们在利用大众媒介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大众媒介所影响。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运用各种手段,借助媒介如影随形的特质来实现民族意识的培养和民族认同的塑造,通过对价值和信仰的控制以及集体记忆的建构,进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目标。具体来说,大众媒介的影响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凸显民族记忆
Maurice Halbwachs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6]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和民族起源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它完全可以、事实上也经常被用来塑造现实中人们共同生活的意志和愿望,以此实现民族认同的目标,大众传媒常常通过仪式和庆典的转播和直播来实现对民族记忆和集体认同的回归。
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对于作为“人文始祖”的黄帝总是在内心存在交结的记忆。慎终追远的传统,也使中华民族对黄帝崇敬有加,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来追寻民族记忆的源头,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就是典型的重拾和再聚民族记忆的仪式庆典。每年的清明时节,公祭典礼都会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轩辕殿前的广场如期举行。规模宏大的祭拜团体囊括了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大众媒介通过对仪式过程的全程转播,让所有观众领略了那曾经辉煌的岁月,聆听来自历史深处的遥远呼声,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刹那间凝聚。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或知名人物来大陆访问,也都会到黄帝陵祭拜,以此表明自己文化寻根的拳拳之心和“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大众媒介对这类事件的转播或直播,都起到了凸显和重塑民族记忆的重要作用。
类似的例子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年除夕之夜的春节联欢晚会。历年春节晚会都是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准时开始,新年“零点钟声”是春节晚会的一个重要时刻和高潮,也是春节这个节日本身的“非常时间”或“神圣时间”。这个时间由于时差的原因并不会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时间相吻合,但在春节晚会北京时间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刻,总会插播海外华人与祖国共同欢庆新年到来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中华儿女总会在这个时刻一起欢度春节这个“神圣时间”,从而创造一种国家与民族“天涯共此时”的一致性空间。中国历年的春节晚会,通过卫星转播,让全球的华人共同观赏,其目的是帮助营造一个以晚会为中心的大一统时空观,“全球华人”所具有的符号效应,在这个时刻与晚会象征性衔接,使晚会从传统习俗中获得进入中国人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并成为在普通民众中创造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手段。[7]
(二)传播特定的价值观
民族国家对特定价值观的传播,不是通过强硬的手段来推行,而是通过设置附着价值观的议程来实现。虽然大众媒介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关注的次序,大众会因为媒介提供议题的重视程度来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是渗透了特定价值观的“媒介环境”,它不但影响人们对某一议题的重视程度,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有学者根据我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分析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大众媒介进行议程设置,传播特定价值观过程中呈现的新特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主题为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分析指出,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期,中国的各种媒体都对党的十七大报道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并进行了前期精心的策划和节目安排上的铺垫,为十七大的开幕做好了“媒介议程设置”的准备,完成了媒介开启议程设置过程的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有关议题的同构、导向需要、属性议程设置以及各媒体之间的联动等方面,全方位的展现了媒介在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8]
在西方,大众媒介表面上自诩中立,实际上也不可避免的包含特定的价值观因素。加拿大虽然是移民国家,但种族歧视仍是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民众的意识到行动都有多层次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制度化,而书籍、杂志和其它形式的媒介对制度化种族主义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加拿大传播公司表示:“加拿大传播公司所真正关心的”是“塑造一种民族意识”。它声称:它的使命是要表达“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它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富有生机的结构,一个加拿大民族性的象征符号,一个将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核心要素”[9](P30)。加拿大传播公司所说的加拿大人,主要是针对加拿大的白人而言,对于其他种族,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忽视。
(三)共享重大事件的关注
由于现代媒介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远距离共享事件成为可能。它提供了一种举行集体仪式并使之永久保存的新形式,从而引起今天巨型社会里民众对重大事件的广泛关注。一些重大的媒体事件常常出现集体观看的情形,气氛或者庄严肃穆,或者喜庆欢乐。诸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伊朗的核查问题,英国王室的婚礼等这些事件中,媒介已经不再秉承客观中立的职业精神,而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进行辩护。观众在共享媒介所提供的事实的同时,也接受了媒介所携带的价值和信念。大部分美国观众通过观看媒介对伊拉克事件的报道,认为美国士兵正在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伊朗的民众通过国家媒介的引导,认为核查是西方国家对本民族事务的干涉行为,从而激起了对核查的强烈不满;而英国的观众则会和媒介一起,欢庆王室的婚礼,并以此作为荣耀。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看到了世贸大楼被撞的场面:冒着浓烟的大楼残骸,血淋淋的尸体和来回穿梭的救护车……目睹的一切都让美国民众对本拉登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充满了敌对的情绪。美国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来适时的加强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总统通过电视发表演说,将其定义为“这是整个美国的灾难”,民众的情绪更加高涨。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美国的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被再次确立和巩固。
四、大众媒介内在的作用机制
(一)创造一致的心理归属
本妮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是被构建的,因为它的成员从不认识、甚至从未听说过其他绝大多数成员,但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同一个具有至高无上重要性单位的成员。虽然所谓的民族象征符号可能是虚构的,或者伪造的,但是对于产生成员身份的意识来说,他们都是真实的心理基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常常被构想为一种深厚的、能够跨越各种阻碍的同志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印刷品的广泛传播发挥重要的凝聚作用。人们通过阅读相同的文本,形成了相互联系的读者群,从而为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的美国,普通小镇上报纸的大量发行将公民的普通生活和更广大范围内的民族联系起来。
当代大众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为创造一致的心理归属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梅洛维茨认为,电子媒介开始超越以“共同在场”为基础的群体认同,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和物理场所没什么关系的接触和联系的形式。[10]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等媒介可以通过自身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优势,引起分散在各地的隶属于各民族成员对同一事件的关注,激发起“我们大家是自己人”的心理共鸣。在一些民族矛盾突发的报道中,大众媒介对于民众情绪的引导作用非常关键。在2000年春季美国旧金山白人警察无故开枪射杀了一名台湾移民后被判无罪,当地的中文报纸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数万华人聚集在市中心抗议。在这个事件中,大众媒介通过引起本民族成员的关注和投入,创造同一的民族归属感,进而维护民族成员的共同利益。
(二)营造“优势”意见环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后现代性的显现,当今社会日益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贝克称其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在与一系列未知的行动条件“共谋”之后,往往会产生人们预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而这些被人为缔造出来的意外后果又会不自觉地构成人们下一次行动的未知条件。这种“非预期性”就是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在风险社会中,具有信息优势的大众媒介成为人们获取确定性赖以依仗的重要手段。
“沉默的螺旋”理论指出,大众媒介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经大众媒介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产生。特定的民族事件,经大众媒介的报道,会对民众产生舆论导向的效果。巴以冲突中,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对冲突场景进行转播,通过展示巴勒斯坦军民的悲惨场面使原本对以色列敌对态度不高的民众,在“优势”意见的指引下,也被煽动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在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的作用下被放大,与民众潜藏在内心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三)内化意识形态
社会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同一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特定的意识形态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所在。依据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只有全社会形成了一致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才能协调,整个社会的秩序才得以维持。
大众媒介通过象征性事务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提供共享的信念,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可以超越社会的各种属性,以各种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形塑人们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通过夹带特定的民族价值倾向和民族观念,大众媒介在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培养过程中正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本战后篡改二战历史的各种宣传,使日本青少年内化了日本是受害者的意识,从而对历史形成了错误的判断。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可以看出大众媒介通过内化意识形态,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培育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小觑。
五、结论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并行不悖的背景下,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问题成为关乎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时空的扩展使人们未能像以前一样,亲身去经历和再现事件本身,大部分只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来获取信息。大众媒介以超时空性和无与伦比的信息优势,运用凸显民族记忆、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和共享重大事件的关注等手段,通过创造一致的心理归属、营造优势的意见环境和内化意识形态等作用机制,实现了对民众的意识控制,并建构了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集体记忆,从而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今民族国家已经留意并大力拓宽了大众传媒的功用,力求最大限度的为民族意识的培养和民族认同的稳固服务。但不容忽视的是大众媒介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在大众传媒对意识控制的方面,由于网络的普及性和匿名性以及新的通讯手段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产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受以往主流媒体的影响,而是受到来自多元信息源的冲击,其中就隐藏着别有用心的敌对分裂势力的混淆和误导,在这种形势下,“小道的信息”往往更具有杀伤力,国家虽然可以出来辟谣澄清,但在循环往复中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何在网络上肃清反主流、反国家的信息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消极影响,是国家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其次,在建构集体记忆方面,在正式场合,大众传媒诚然可以通过直播和转播国家与民间各种仪式和庆典,来重拾和再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集体记忆。但在非正式空间,大众传媒也可以通过电视剧等以娱乐的方式来展现对民族历史记忆的阐释。戏说和穿越历史剧的出现,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培育罩上了一层灰影。“在失去‘元叙述’①元叙述常常被视为强调文艺作品自我指涉、自我意识的同义词。元叙述通常指向故事和叙述行为,不仅不涉及故事虚构实质,而且通过强调故事真实性引导读者认同叙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meta narrative)的娱乐化的电视历史剧中,文化的历史深度体验不再作为电视历史剧的前提和保障,而成为多余的负担,被消解、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非历史化’、‘反历史化’的逗笑取乐。‘戏说’历史剧的这种‘只管消解不问构建’的叙说方式,使传统的历史观念分崩离析,历史剧的建构集体记忆的功能被削弱…… ‘戏说’历史剧使得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也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11]
因此,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问题上,谨慎而积极的态度尤为必要。在充分认识和利用大众媒介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积极影响的同时,对于其消极功能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唯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大众媒介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影响方面的良性发展。
[1][英]戴维·莫利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3]熊锡元.试论制约民族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J].民族研究,1993(1).
[4]周传斌.民族意识研究回顾[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1).
[5]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7]吕新雨.解读二零零二年“春节联欢晚会”[J].读书,2003(1).
[8]张祥祥.试论我国媒介议程设置呈现的新特点——以国内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为例[J].理论界,2008(10).
[9][美]戴安娜·克兰主编,王小章、郑震译.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Moyrowitz,J.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1]秦志希,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J].现代传播,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