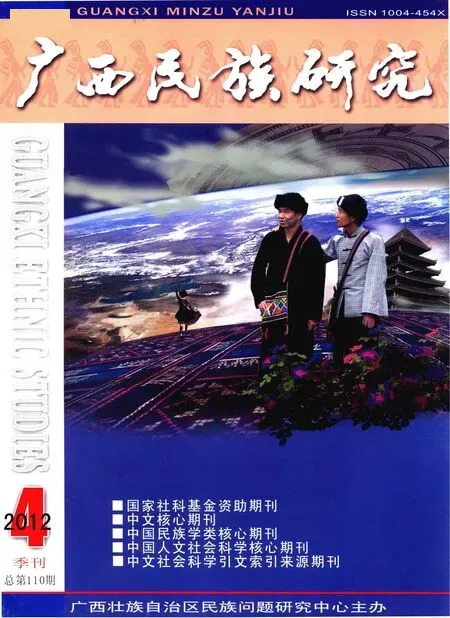城市族际交往中的 “民族心理距离”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张俊明 刘有安
作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枢纽,西宁市同时还是青海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宁市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民族成份渐趋多元化。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宁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为1635217人,占74.04%;各少数民族为573491人,占25.96%。其中:藏族121667人,占5.51%;回族359138人,占16.26%;土族57521人,占2.6%;撒拉族8505人,占0.38%;蒙古族13701人,占0.62%;其它少数民族12959人,占0.59%。在这个多民族城市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频繁、交往的领域更加广泛,但因文化传统、民族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心理距离。
一、“民族心理距离”与民族关系
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用“社会距离”一词来表示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亲疏。一般来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G.Simmel)首次将社会距离概念赋予了主观性的色彩,将距离感引入个体在现代性都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 (R.E.Park)与伯杰斯 (E.W.Burgess)等人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帕克在研究中提出,“社会距离”既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正功能,也有阻碍社会进步中起到的消极作用。[1]
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群体,在日常的互动中常常会建立或亲或疏的群体关系。国外学者在研究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常设计一系列变量来测量民族/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设计了一套测量各个种族之间亲疏关系的技术,称为“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2]Lee等人认为,博格达斯设计的社会距离量表是从大族群的立场和角度来设计回答项目,表达的是大族群对小族群的距离感受,不能用来解释社会距离的本质。因此,他们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设计了另一套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 (the Reverse Social Distance Scale),用来测量小族群对大族群所建构的社会距离的感受。[3]许木柱在研究台湾民族/族群关系时,设计了一套包含7个问题的心理测量量表,用以测量台湾原住民族 (泰雅族和阿美族)与汉族的互动模式和社会心理距离,并认为双方接触意愿越强,心理距离越小,社群隔离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4]
近年来,我们在研究宁夏回汉民族关系问题时,借用“民族心理距离”这一概念来考察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微妙关系和心理特征。认为民族心理距离“指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因民族文化、民族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在各自心理上对异民族产生的距离感。具体而言就是对异民族设防,妨碍其接纳异民族的人参与到自己文化生活中或使自己不愿参与到异民族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现象。”[5]
国内外学者的理论探究以及我们在前期研究中的探索,都为研究西宁市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中存在的心理距离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在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试图通过对他民族文化了解和认可程度、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交往频率和深度、民族居住格局和居住意愿、族际通婚意愿、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及原因等变量来深入考察西宁市汉、藏、回三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状况。
二、西宁市民族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调查
西宁市人口数量位居前三的民族是汉族、回族和藏族,民族交往中的文化摩擦与冲突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民族中,因此我们以汉族、藏族、回族为主线,设计了三类调查问卷,每类问卷100份,并在市区随机选取不同民族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问卷全部回收。经核查,针对汉族的100份问卷均为有效问卷;针对回族的100份问卷中有两份无效问卷,有效率为98%;针对藏族的100份问卷中有两份无效问卷,有效率为98%。为了使研究更具科学性,我们还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做了深入的访谈。总体而言,西宁市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民族关系和谐,但民族之间的距离感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1.汉、藏、回三民族之间的文化了解和认可程度
民族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继承性,将会作为民族特有的标志特征体现在群体或个体活动的方方面面。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进一步交往的愿望和主动性。
针对回族的问卷显示:有17.4%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71.4%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只有11.2%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同时,却只有5.1%的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56.1%的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有38.8%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
针对汉族的问卷显示:有8%的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82%的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只有10%的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有7%的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72%的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有21%调查对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
针对藏族的问卷显示:有1%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93%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有4%的调查对象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没有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很了解”,有89%的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了解一些”,有9%调查对象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了解”。
可见,由于汉族在西宁市人口较多,他们与当地藏族和回族交往频率较高,对回、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程度较深。而回族与藏族之间交流和沟通意愿不强,对他族文化的了解程度较低,尤其是大多数回族对藏族文化习俗缺乏了解。
2.不同民族个体之间交往的频率与深度
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往往会对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交往意愿产生或强或弱的影响。当两个民族之间关系和谐时,民族个体间相互交往的意愿强烈;当两个民族之间存有偏见和隔阂时,则相互交往的愿望较低。反之,不同民族个体之间交往的频率越多,领域越广,私人亲密度越紧,民族关系就越和谐。
针对藏族的调查显示:平时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占68.4%,平时与回族经常交往的仅占10.3%。针对回族的调查显示:平时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占85.7%,平时与藏族经常交往的仅占16.3%。针对汉族的调查显示,平时与回族经常交往的占39%,平时与藏族经常交往的占32%。可以看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率较高。
我们还通过调查不同民族个体朋友圈中的异民族成员的数量来考察族际交往的深度,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朋友圈中的本民族成员较多。如藏族调查对象的朋友圈中全是藏族和藏族较多的占73.4%;回族调查对象的朋友圈中全是回族和回族较多的占60.2%;汉族调查对象的朋友圈中全是汉族和汉族较多的占59%。可见,交友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每个人选择朋友时都会考虑交往对象的背景、品德、民族、社会地位等。
另外,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互助状况以及人们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也能反映出民族之间心理距离的远近。针对藏族的调查显示,认为平时对其帮助较多的主要是藏族的占74.5%,主要是汉族的占11.2%,主要是土族的占3.1%,回族、东乡、撒拉均为没有人选择;对于回族调查对象,平时对其帮助最多的是回族的占66.3%,主要是汉族的占39.7%,主要是藏族的占3.1%,主要是撒拉族的占2.0%;对于汉族调查对象而言,平时对其帮助最多的是汉族的占81.0%,主要是回族的占11.0%,主要是藏族的占5.0%。
由此可以看出,西宁市汉藏之间、回汉之间的交往频繁和领域广泛,而回藏之间交往的频率相对较低、领域相对较窄,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互动仍是西宁市民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3.民族居住格局与居住意愿
民族居住格局是衡量民族关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不同民族在某一区域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状况。彼此分离的民族居住格局会使民族之间社会文化交往和彼此了解程度相对较低,民族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也更容易显现;混杂居住的民族居住格局一方面反映了民族之间关系的和睦,也会促进民族之间进一步的交往与相互了解。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民族关系越和睦,民族杂居的程度越高;民族关系越紧张,民族隔离居住的现象越普遍。正如马宗保所言:“民族混居的程度越高,民族间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交往与互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居住越分散,与主体民族汉族交错居住的程度越高,社会隔绝程度越低,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就越高”。[6](p78)
西宁市城东区各个民族居住情况主要以混杂居住为主,间有小聚居区。聚居的民族主要以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为主,在大众街、东关大街、清真巷、林家崖、周家泉分别聚居着全区82.1%的回族人口、73.5%的撒拉族人口、76%的东乡族人口、83%的保安族人口。[7]散居的民族主要是藏族、土族、蒙古族等。汉族因为人口较多,既有与其他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居住模式,也有聚居模式。有研究者指出,在西宁市少数民族居住最集中的城东区,由于“各个少数民族还存在着一定的居住偏好,即在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教育及职业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前提下,不同民族容易形成居住格局上的小聚集模式”,“这种状况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实际感情距离的疏远,进而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
我们在西宁市城东区调查时,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应分开居住,有利于避免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调查对象的居住意愿明显反映出民族之间存在的距离感与隔阂。藏族调查对象中,邻居是汉族的占28.6%,邻居是回族的仅有7.1%;邻居不是汉族者中,有97.1%的愿意与汉族为邻居;但邻居不是回族者中,仅有42.7%的愿意与回族为邻居。回族调查对象中,与汉族为邻居的占69.4%,与藏族为邻居的仅占9.2%;邻居不是汉族者中,有70%的愿意与汉族为邻居,邻居不是藏族者中,仅有55.1%的愿意与藏族为邻居。
综合访谈资料和调查问卷,人们不愿与他民族为邻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和对他民族行为方式的不认可。藏族调查对象中,认为与汉族为邻没有不方便的占65.35%,认为汉族的行为方式与藏族差别过大的占29%。回族调查对象中,认为与汉族为邻居没有不方便的仅占21.4%,认为与藏族为邻居没有不方便的也仅占6.1%;认为与汉族为邻不方便是饮食习惯的占74.5%;认为与藏族为邻不方便的因素中,宗教差异占32.7%,饮食习惯31.6%,行为方式占35.7%。汉族调查中,仅有16%调查对象认为与回族为邻居没有不方便的因素,22%的调查对象认为与藏族为邻居没有不方便的因素;认为与回族为邻不方便的主要因素是饮食差异,与藏族为邻不方便的主要因素是行为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在城市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4.族际通婚意愿
族际通婚被国内外研究族际关系的学者视为衡量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在研究中,也将不同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态度和原因做了重点调查,从中能看出不同民族对于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原因,以及对通婚的对象选取所持的观点。
首先,藏族调查对象中,赞同“汉藏通婚”的占12.2%,反对的占67.3%,无所谓的占20.4%;对“回藏通婚”几乎都持反对态度。不赞同“汉藏通婚”者认为汉藏之间风俗习惯不同、藏族会被同化、汉藏观念不一样……;不同意“回藏通婚””者认为回藏之间信仰不同、风俗习惯有差异、藏族会改变信仰……
其次,回族调查对象中,赞同“回汉通婚”的占37.8%,反对的占48.0%;赞同“回藏通婚”的仅有15.3%,反对的占69.4%;支持回汉通婚和回藏通婚者中,有80%以上的主张通婚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改信伊斯兰教。绝大多数反对回汉通婚、回藏通婚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些调查对象反对回藏通婚的原因是藏族的行为方式与受教育水平。
最后,汉族调查对象中,赞同“回汉通婚”的占29%,反对的占36%;赞同“汉藏通婚”的占66%,只有个别调查对象持反对态度。反对回汉通婚的原因主要有生活习惯差异、通婚要改信仰伊斯兰教等,大部分调查对象支持汉藏通婚的原因主要是汉族与藏族的宗教信仰不冲突、生活习惯与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等,个别反对汉藏通婚的原因主要是藏族文化水平低、行为方式难以接受。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选择婚姻对象时往往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并与人们对他民族的认知相关。从对西宁市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可以看出,人们对族际通婚问题仍存芥蒂,特别表现在藏族与回族这两个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之间。
5.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及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实施下,民族歧视和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日益消弭,民族之间也很少有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民族个体之间小规模的冲突时有发生。究其原因,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经济纠纷引发的小摩擦。
西宁市藏、回、汉三个民族之间发生矛盾或者产生不愉快,与民族之间接触的频率有很大关系。藏族调查对象中,与汉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82.6%,与回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77.5%;回族调查对象中,与汉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76.5%,与藏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36.8%;汉族调查对象中,与回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41.0%,与藏族发生过矛盾或产生过不愉快的占24.0%。
藏族与汉族和回族之间产生不愉快的比例比较高,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藏族是新进入西宁市的人口,其接触的对象主要是人口较多的汉族与回族,故与之产生摩擦的几率较高。另外,新进城市的藏族所携带的文化很难在短期之内与都市的文化衔接,所以很容易与汉族、回族发生矛盾。藏族调查对象因风俗习惯不同与汉族发生矛盾的占34.6%,与回族发生矛盾的占44.7%。而回族因风俗习惯不同与汉族发生矛盾的仅占9.3%,与藏族发生矛盾仅占16.7%。这在一定程度说明:在城市中,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是引起民族之间个体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宁市,新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如何适应城市的主流文化,使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城市文明接轨,被他民族理解和接纳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多民族城市中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心理距离的原因
一般来说,产生“民族心理距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西宁市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
两个民族文化相似性越高,双方的心理距离越近;两个民族文化差异性越大,双方的心理距离越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度很高,如回族对东乡族、撒拉族的心理接纳要高于对汉族的接纳程度,回族对汉族的接纳程度要高于对藏族的接纳程度。信仰藏传佛教各族也是如此,藏族对蒙古族、土族的心理接纳程度要高于其对汉族和穆斯林各族的接纳程度。
藏族调查对象中,与汉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的仅有2.1%,但与回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占22.4%;与汉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高达62.2%,与回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的仅占7.1%。回族调查对象中,与汉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仅占3.1%,与藏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的占16.3%;与汉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的有71.4%,与藏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的仅有31.6%。汉族调查对象中,与回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的占2.0%,与藏族在一起“有隔阂、不愉快”的占6.0%,与藏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的占57.0%,与回族在一起“没有隔阂,很轻松”仅占37.0%;绝大多数汉族认为与回族及藏族“有隔阂,但也能正常交流”,分别占44.0%和57.0%。
2.缺乏对他民族的全面了解,对他民族文化认知有偏差
民族认知是民族心理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长期作用的结果,民族文化在其形成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不受到民族认知的影响,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又反作用于民族认知。民族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于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与对话中,总会寻求其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是民族之间平等相处、和谐与共的基础,也是不同民族频繁交往的动力。但民族文化之间也有相异之处,这种相异往往会引起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又会使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人们对他民族在认知上的偏差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并将交往对象纳入自己文化体系来衡量:与自己文化越接近,在交往中心理距离越近;与自己文化相差越远,在交往中心理距离越远。因此,对他民族文化的评判所引起的不良交往心理,是产生“民族心理距离”的重要因素之一。[9]
在西宁市,人口最多的民族为汉族和回族,且居住格局基本上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回族与汉族之间相对了解较多,但回族对藏族了解有限。人们了解藏族及其文化的渠道较窄,仅限于火车站、汽车站附近藏族饰品店的店主及偶遇的着藏装者。此外,藏族的生活到底如何,许多回族都说不清。藏族对回族的了解也是如此,了解到回族最多特点的就是回族不吃猪肉,男的戴白帽子、女的戴盖头,分不清回族和撒拉族、东乡族。一些回族告诉我们,他们听人说藏族和人交往时,言语稍有不合就会动手,自己还看到一些藏族男子留着长头发,就会对他们敬而远之。这些道听途说的传言,影响了回汉群众对藏族的认知,也拉大了回族对藏族的心理距离感。
3.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调适中的必然现象
不同文化有其独特的内核,这种内核要求其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抵御异文化的侵扰。在西宁市,文化的多元性显而易见:有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各穆斯林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的传统文化,有以儒家与道家为核心的汉文化,有以城市文化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在此传播与彰显。各种文化在西宁市不断交流、互动,城市周边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不断向西宁市辐射,试图对即将弱化的民族文化进行补给。可以说,西宁市多元文化的互动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往往会受到其它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这必然引起其文化的载体——民族的警觉,从而形成或大或小的文化瘙痒与不适。文化的瘙痒必然使得人们对他文化、他民族产生排斥、认知的偏差,与异民族或异文化拉开适当的距离,避免同化,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如我们的很多藏族调查对象不同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通婚主要就是担心因而被汉族同化。
结语
西宁市回、藏、汉三族在长期交往中,各民族民众对他者的了解正在不断增多,但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或远或近的“民族心理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进一步交往的愿望和主动性。在多民族城市中,各民族只有以平等的心态和眼光去理解他民族文化,客观分析本民族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共性,深入发掘隐藏在文化内部的隐性因子,消除残存在民族心理中的文化定势和偏见,才能达到深层次的跨文化交往,才能在尊重个体差异性和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达到统一性,形成一个稳固、团结的集体。因此,在当前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的新形势下,要注意发掘制约民族互动的“民族心理距离”,从心理层面消除民族之间的歧视、排斥,积极引导民族“民族心理距离”的合理调适,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
[1][2][3][4]王启富、史斌.社会距离理论之概念及其它[J].晋阳学刊,2010(1).
[5][9]刘有安.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解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8(5).
[6]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7][8]马晓东.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