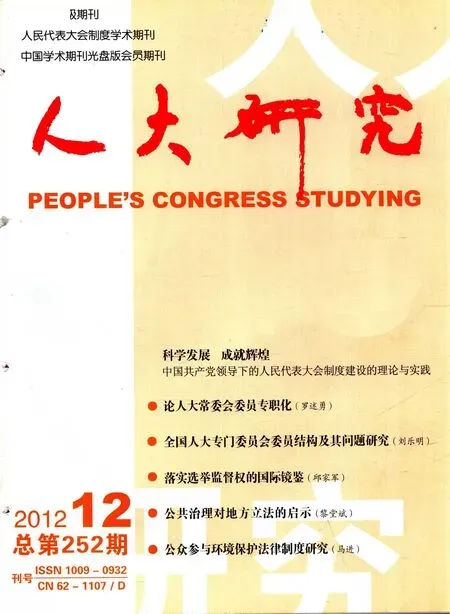公共治理对地方立法的启示
□ 黎堂斌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首次使用了“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提法,赋予了“治理”一词更加丰富的理论意涵和实践色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明确提出“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契合了世界范围内公共领域管理实践变迁的趋势和理论创新的潮流,必将对我们国家公共领域管理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以结合公共领域管理理论流变,谈谈公共治理理论对地方立法的启示。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
公共治理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公共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和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管理行为大体上经历了从国家管理模式向公共管理模式、再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前两者主要强调的是一个或多个管理主体单向度地“管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引发的包括个体、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的需要,这就为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基础。自世界银行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 r i s i s i n g o v e r n a n c e)一词,此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纷入概念,并逐渐强化、进而固化它在这些学科中的含义。到20世纪90年代,公共治理理论基本成型并奠定了广泛的影响地位。
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是由社会发展实践客观需要和社会科学理论演变主观需要双重作用的结果。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普遍面临管理危机。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过度发展,政府被视为“超级保姆”,公民无法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监督,政府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日益陷入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三重危机并发的境地。与此同时,受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传统主权受到强烈冲击,政府纷纷垮台。为形势所逼,各国纷纷掀起了以治理和善治为共同向往的政府改革和公共管理部门再造运动。二是全球公共问题凸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现了诸如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南北发展差距问题、国际恐怖活动等大量的全球性问题,引起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寻找全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三是全球公民结社运动蓬勃兴起。各种非政府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对传统的国际政治提出挑战,各国内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团的迅猛发展对国内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它们在公共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凭借其灵活多样性,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大丰富了公共管理的内涵。四是理论界以经济学视角对传统政治学、管理学进行拓展性研究。以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对国家理论、投票规则、利益集团等传统政治学主题进行研究,突破了传统政府理论研究框架,开拓了公共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由此可见,正是在各国政府改革运动、全球公共治理和全球公民结社运动的共同推动下,催生了崭新的公共治理理论[1]。
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范式,从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治理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名词的更新或对传统行政管理手段的修正,而是体现了社会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全新认识。“公共治理”中“治理”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行政”的含义,“治理”至少包含5个方面的含义[2]。国外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实质上,治理是将不同公民的偏好意愿转化为有效的政策选择的方法手段,以及将多元社会利益转化为统一行动、并实现社会主体的服从。”[3]罗豪才等认为,所谓公共治理,就其构成而言,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元素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元素整合而成——“公共治理=开放的公共管理+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开放的公共管理是前提,主要用来发挥集体选择优势,而广泛的公众参与是基础,主要用来发挥个人选择优势,公共治理模式试图通过这种整合来同时拥有两种优势,实现对公共管理模式的超越[4]。
经过梳理,笔者认为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体多元化。主张所有公共关系主体都是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各类公共权力主体,还包括私人组织和公民个人等权利主体。各种主体以不同的角色平等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形成多元治理格局,所有主体都应当权责一致,确保过罚相当、罚当其责。二是方式多样化。借鉴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在假设各类治理主体充分理性、自律的前提下,遵照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的选择标准,实现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三是过程公开化。“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5]在治理过程中提供的博弈舞台是开放的、表达机会是充分的、博弈策略是均衡的,通过博弈实现均衡,借助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并以实体正义来体现程序正义。四是利益目标最大化。公共治理的内在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和相信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和自管理能力,依靠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理念,目标是在兼顾公益和私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6]。
二、推动地方立法理念创新
我国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基础在急剧地发生改变,需要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转变,更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规范转变理念进而为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如此一来,无论在法律规范形成的主体方面,还是在其所体现的意志、借以存在的形式、约束力的强弱、与国家强制力的关系等方面,都不难找到法律规范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契合点。
地方立法处在国家立法系统的底层,直接根植于各地丰富多样的治理实践,相较于中央立法,其所调整的各类权利主体之间关系更为密切、利益更为明显,具有较强的试验性和操作性等特点,因而受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就更为明显、直接。
推动地方性法规的权利义务关系观念从“对抗与控制”向“互动与合作”转变。在传统管理模式当中,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对抗与控制性的,控制被当做万能钥匙,对管治主体来讲有再重要不过的意义。导致控制机制极度膨胀,公权力机构将控制看成是实现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控制范围过广、控制方式过硬,甚至为控制而控制,将控制异化为法律规范的目标。在公共治理模式中,各类权利主体以平等的身份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决策,要求与之适应的法律规范构建一种“互动与合作”的法律关系。一是要重新理解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与政府和强制性之间不再具备必然性,权力未必只能由政府等公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也未必只能是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保障和改善公民权益,也能弱化和损害公民权益,要靠法律规范来扬长避短,做到在遵循法治理念、公益私益兼顾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二要重新认识公民权利。传统观念中,法律规范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权利”;今后,则要强化“积极权利”意识,即在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前提下全方位拓展公民权利的种类和范围,以便给予公民更多的发展机会。三要强化公众的主体意识。法律规范在规定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应充分彰显公共治理的“公共性”,引导公众以“主人翁”的主体意识不断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处理。
推动地方性法规重塑利益基础。法律规范是对各类权利主体利益诉求的一种确认与保障,任何法律规范都只能建立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利益基础直接决定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在传统管理模式中,法律规范的利益基础只是狭隘的“公共利益”,公共机构为了追求这样的公共利益往往采取单方行动。而在公共治理模式中,强调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机构与寻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权利主体协商、合作,共同实施双方行动,这就要求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法律规范重塑利益基础,必须是各类公益和私益整合而成的社会整体利益。一要改变传统的将“公共关系”与“公益”机械等同起来的观念,淘汰那种将公益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实施强制性行为的观念,切合社会治理主体多元的实际,确立起一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多元化代表和多样化实现方式的多元模式。二要真正理解公益、私益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要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辩证地看待公益的优先性和私益的根本性,二者之间既有张力,更有内化为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性。三要重点解决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合法保护问题。既要处理好公益和私益的公平分配,又要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私益的公平分配,在此基础上赋予各种权利主体合法对抗、制裁来自其他主体非法侵犯的权利。
推动法律规范的多元化与和谐性。公共治理对公共关系领域的拓展,必然决定着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扩大。在公共治理模式中,社会自治组织和公众个人跃上公共权力运作的平台,传统的权力单向运作模式再也无法适应形势需要,只能向多向度、非强制性等方面转变,公共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和运作方式的多样化,直接推动公共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就决定了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多元化,既有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和非强制介入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有以社会自治组织和公众为主体的以非强制性为主、辅以强制性方式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时,公共治理是以“善治”为目标的,要求为其提供制度保障的法律规范本身必须是和谐有效的。一要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并重。应当在完善实体规范的同时,加强程序规范的创制,只有二者平行发展,在迫切需要医治传统管理模式重实体、轻程序留下的后遗症的当下,甚至要突出程序规范的创制,才能实现在治理过程中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二要约束性规范和激励性规范并重。在公共治理模式中,各种权力主体活跃,利益诉求充分,这就要一方面通过约束性规范来控制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实现权力的授予与控制、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通过足够的激励性规范来激励公共权力的有效行使,同时激励公众广泛、深度参与社会治理。
三、推动地方立法价值取向重构
地方立法价值取向是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因为地方立法直接渊源于地方治理实践,日趋多元的利益诉求在地方立法活动中反映就更为明显。不同的利益诉求直接导致价值层面的冲突、竞合,这就要求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必须进行价值权衡和选择。地方立法价值取向依附于地方立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地方立法实践不断发展,就必然要求地方立法价值取向始终处在变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具备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在传统管理模式中,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权力机构在公共关系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以“管治”为前提演绎出来的诸如“秩序”等各种“公共利益”被无限地放大,公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反映,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更具长远意义的社会整体利益。相对的是,公共治理模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这其中当然包括反映和满足以自由为基础的公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基于这一理念,秩序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价值,是实现自由等其他更高价值目标的手段,公共治理的最终追求是要实现“自由为体、秩序为用”[7]的和谐状态。
当下,地方立法活动正处在由传统管理模式向公共治理模式急剧转变的社会治理实践之中,必须以灵敏的政治嗅觉、前瞻的理论眼光,合理重构地方立法价值取向,适应公共治理大趋势,更好地规范、引导、保障社会健康运行。
一要改变传统法律规范的工具性价值定位。法律规范价值是法律规范这种客体对法律规范主体需求的一种满足,法律规范尽管要保障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但不能因此蜕变成只对公共机构的管治进行回应的工具,应当全面、广泛地回应公众的正当需求,彻底解决法律规范价值回应错位问题。
二要兼顾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平衡。在公共治理中,多方利益主体平等公开地博弈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律关系的设计不应囿于公正和效率的孰先孰后、正义和秩序的孰优孰劣等问题,更不能以牺牲或贬损程序正义、目标理性、实质法治、公民自由等为代价,实现实体正义、工具理性、形式法治、公共秩序,要找准各种对应关系的平衡,真正做到统筹兼顾。
三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最终价值。公共治理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作为制度保障的法律规范,必须充分尊重主体需求的多样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将逻辑起点由最有效地控制人性恶的发作转变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将“控制”当做一种必要的手段,而非唯一手段,更非最终目标,从而赋予公民享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自由的权利。
注释:
[1]参见滕世华:《公共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3年。
[2]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Beate Ko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mance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4.
[4]参见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5]参见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6]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立一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和公民广泛参与的作用。不难看出,这种“社会管理格局”其实就是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7]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