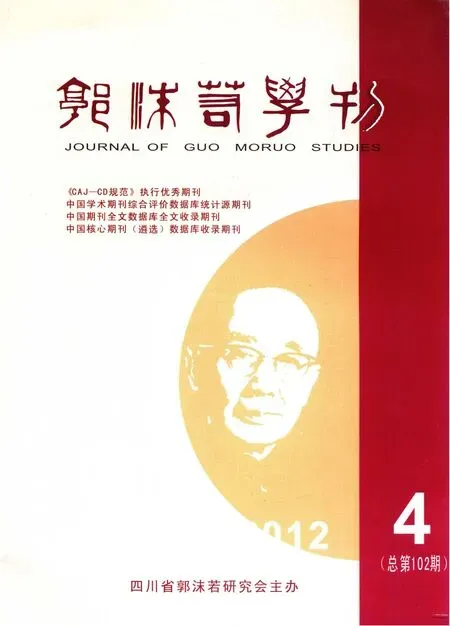关于郭沫若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崔民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大家知道,在学界对郭沫若有不同的评价。研究郭沫若的多数学者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郭沫若在学术上存在多元性,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是郭沫若学术多元的重要表现。但对于另一些学者而言,他们却总是从抽象出发,从单纯的艺术出发,脱离时代特征对郭沫若进行简单化研究。这部分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一个公共角色和普通学人之间的郭沫若的不同。我们认为不管研究者对问题研究的适度或者偏离,或是其他,研究者的成果总应该是一种学术导向性与审美性结合。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有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需求,还是学问之外的一种兴趣与偏好之选择,因此,我们的一部分研究者常常选择了投众所好,满足读者知识之外的额外需求。基于此,对郭沫若认识的复杂性,这就不但取决于郭沫若学术本身的特征,更多地取决于一些研究者本身的引导或解读。这里我们想要说明,或是想要证明的是郭沫若的价值有时是被谁绑架了,还是被一些学术研究引到了哪里?因此郭沫若究竟在哪里,成为今天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审美导向应成为研究者的目标
作为学者对学术的研究态度必须是严肃的、认真的、科学的,且符合审美要求的。之所以称之为学者是因为你代表一种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而不是等同于一般大众。学者的学术认同常常不是,也不必然是从众的,而应该是审美的。
小沈阳现象表明我们社会从众的一种心态,但绝不是艺术审美价值的取向,不是所有掌声都是高尚的。在20世纪20―30年代,世界文学上出现了荒诞派、以其后来的黑色幽默派,他们更多地是通过白描与调侃之笔法,通过描述人们的空虚、无奈,常常用人们的痛苦来开玩笑,导出一个异化或者精神缺失的时代。这说明时代生活价值观扭曲中的艺术审美之声。这种表现方法不仅说明了艺术家对时代态度,也代表了艺术家的认识深度,从一个全新角度看正是艺术独白中的审美表现,是对艺术价值的真正追求。而一些评论却说是这个时代堕落了、艺术堕落了,当然,第一个评价是正确的,第二个评价是荒诞的。艺术的大厦应该是在废墟中发现光亮的东西,黑暗中透出的一缕光芒。艺术对于评价者的要求不是看现象,应该是看穿现象,发现本质。
郭沫若早就说过:“本来文艺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什么人做的都是文艺。在这漫无标准的文艺界中要求真的文艺,在这漫无限制的文艺作家中要求真的天才,这正是批评家的任务。要完成这种任务,这也是什么人都可以做,但也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换句话说’批评也是天才的创作’”[1](P240)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郭沫若所写的所有作品都是艺术。而恰恰是他在特定的时期所写的很多作品常常是游离于艺术之外的。这正是艺术家作为公共人的基本表现,而不是艺术家永远游离于公共人角色之外,永远生活在艺术迷宫里。作为一个社会人,就特定时期郭沫若的作品看,究竟是郭沫若游离了文艺,还是郭沫若在社会舞台中角色选择的使然,应具体看待。就文艺而言,我认为有主动的文艺与被动的文艺之分。主动就是内心真实感情的真实审美表白,被动则往往是公共人作为社会角色反应之结果。我们应该在研究郭沫若时把这两种角色状况下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不能仅仅用文艺之标准来评判。
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本着对郭沫若负责任的态度研究,而绝不是根据个人偏好迎合某些社会层面某种需求,既不能把自己的思考简单化到一般观众的需求中去,也不能把自己的思维简单化到论文艺的抽象层面去,研究者应该引导社会需求,而不是跟风,重要的是界别现象背后的本质。总之,一个人一生创作的作品不能把它简单化到他的表现形式就只是文艺,或者作为这个人所从事的文艺之外的所有话语均要纳入文艺的标准中来评判,这样的逻辑绝不是正常的文艺人逻辑。我们应该需要一种真正符合审美需求的价值判断,对特定的群体作特定的审美界别,对特定的个人也应从审美中发现文艺精髓,不能简单到所有文艺人的创作都是文艺,因而所有文艺人的创作就必须是用文艺标准来评判。文艺评论者的不同就是我们绝不能把平庸的价值取向等同于一般读者偏好引进到评论中来。评论应该站在表象与细节之外去思考,他只能是特定职能场上的裁判,绝不应该是运动员,或者是观众;也不能用其他职能场所的裁判标准来裁判。
二、公共角色与个人艺术偏好之间的度量
我们研究郭沫若,是把他放在一个社会复杂背景下进行评判呢,还是把他放在一个艺术人的圈子里进行分析,这个差别很大。在每个人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参与公共事务角色较多的人身上,我们是否认为应该是公共决定的成分更多呢?还是个人选择的因素更多呢。一个社会的人尤其在特定的背景下的人,我们应该把他放在社会特定背景下与其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中考察,而不应该把他在特定时期的某首诗或某些话简化为对一个艺术人的简单评价,把一个集体角色下的人简化成一个单独的艺术人,这样的评价是真正的学术之狭隘。
由于我国社会批评的理性不足,公共选择下的艺术取舍往往被一些少数标新立异的个人选择所绑架。某些人在为个人选择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时不仅往往对客观的学术指向进行非本质解读,而且失却审美的要求把街谈巷议与羊群效应当作其评价艺术问题的标准。一些人,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宇宙观剧烈变动的时期,在社会主流意识模糊化的时期,常常哗众取宠,只对某些事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也成为我们一些学者在获取学问道路上的捷径,或者走向“一夜暴富”的通道。急功近利的个人偏好或者非理性选择代替了学问的科学性。我们认为:特定时期公共选择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冲突应该成为分析郭沫若的思想变化的重要基础。同样不同时点的社会生活及其公共角色也决定了他的学术塑造。因此社会角色特别是政治角色中的郭沫若的研究应该与个人选择下的郭沫若艺术评判严格区别开来,而不应该成为一些学者评价所谓“郭沫若对艺术背离”之诘难。
发掘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应该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与他生活外来的新朋好友之间。代表公共性时常是一个群体的约束与声音,是公共角色对他选择的逻辑安排,并非他自由艺术的发挥;代表自由个性时,他常常是一个因事因感而发的情感符号与审美符号的代表。在研究时我们必须将之区别开来。譬如对《武训传》的评判而言,不能把郭沫若简单界定为一个思想矛盾的人,他的矛盾与不一致性,恰恰表现为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之间的不可协调性与冲突之结果。所以研究是有审美性的、研究是有选择性的、研究是要具体化的。研究如果不能从他代表的公共角色与个人选择角度去分别评判,简单用游离于特定背景下艺术偏好去评说,那么这样的研究将是失败的研究。同样某些研究者只从趋炎附势之迎合观众的公共需要中评价他人的艺术,获取个人名利,却恰恰忘记自己学术水准,思想违背艺术原则,且在一些低级趣味的笼罩中,迎合公共需求评价倾向,正好成为自己忽略社会人与艺术人之区别、又让艺术人啼笑皆非的标签。
三、郭沫若研究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
社会批评理性的成熟,说明学术真正步入学术的轨道。否则没有导向性的学术评判与大众的眼光有什么本质区别。
事实上每个人在学术上的进步与他地位的进步常常不是同步的,有时甚至是分离的。社会角色特别是政治角色决定一个人公共角色的本位性,这正是一个人在主动研究与被动研究之间徘徊不前的根源。也正是一个人走进了文艺还是走出了文艺的分界。因此不能用文艺的标准评判政治的成果,也不能把政治的成果当作文艺来欣赏。
尽管完成政治的使命与文艺的使命在政治家看来常常是一致的,但在文艺者眼光中却迥然不同。因此用文艺眼光评判文人的标准,就是每个人所有作品都必须用文艺标准来评判,当然这只能是文艺人的逻辑谬误。因此说研究问题的思路常常决定了评判的结果。
作为文人的郭沫若也反思过:“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2](P77)评判是什么,自己已经做了本源的评判。离开文艺女神,在被动的文艺选择中,选择了非文艺的形式。所以我们文艺者认识郭沫若不能简单到只知道文艺的程度。对一种东西我们应该进行剥离或者疏理。不要任凭弱水三千,我任取其中一瓢。超越文艺的评价是可取的,评价也必须是有选择性的,不能以点代面,更不能求全责备。质量的取舍应该成为文艺评价的精神,但不是所有文艺人的文章都是纯文艺作品。
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郭沫若用人类的通用观点与逻辑评价过去,他认为正是基于“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但针对我们过往民族的历史偏好与通往奴隶们的道路过程中的选择“必要的条件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3](P6)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层级系统,它包括文化信仰、道德约束、法律体系、社会文明。同时一个文明的形成也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完善的。郭沫若的深厚处在于他深刻理解了不同社会的文化内涵,领悟了深藏于社会背后的历史逻辑,而人是这一逻辑的主导与主线。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过程中,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认识问题的新角度,这就是“所有中国社会的史料,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不仅仅在于整理历史,知其然,而更在于有一种批判精神,挖掘历史,知其所以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在他的领地里真正拓展开来,成为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思路与方法。与对甲骨文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客观,更是认识问题的角度,对于我们研究郭沫若的人必须把握研究他认识社会的精髓,而不应该纠缠于他某个学问局部与细节。
当一个社会缺乏理性时,所有东西均可被戏说,或重新解读,甚至出现不同解读。但对研究者而言,有必要清醒认识到要深刻了解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巨人,他给我们的真正启示是什么,须领悟的是他给我们的思想与标杆在哪里,他把什么样的方法与道理传导给了我们。
四、正确评价中应该看到的郭沫若
谢保成教授在研究郭沫若领域做过创新性贡献。他曾在《近十年研究郭沫若动态》中说“1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应当改变》的短文,在肯定前10年郭沫若研究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不客气地指出当时研究中存在的‘四多四少’:分门研究多,综合考察少;研究著作多,分析其人少;孤立论证多,比较研究少;纠缠具体观点多,分析总体贡献少。最后,希望郭沫若研究者跳出狭小的研究领域,扩大自己的视野,改变研究方法,使郭沫若研究真正深入地开展起来。”[4]
今天看来,郭沫若研究中仍然存在上述问题,究竟郭沫若在哪里,我们需要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这却仍然是每个研究者自己必须正视与回答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问题。
郭沫若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种社会想象;郭沫若是一个社会符号,还是一个文艺标杆;郭沫若带给我们的是方法,还是简单的感觉;郭沫若是未来的期望,还是现实中升华的思想。基于现象与本质的讨论几乎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中。评判的对与错往往只是个角度问题,对于每个评论者而言自己心里是有审美尺度的。我们只好借助卞之琳先生的一首诗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郭沫若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还是越来越近了?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从哪个维度开始进行评价,相信这个问题经过智慧的思考会越来越清晰。
我们认为:郭沫若不仅是一种启示,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考,而且是一部博大的中国现代史。他绝不简单是一个文艺人片段、一个政治人残缺,或是其他我们简单地看到的什么。许多人说:郭沫若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从这里认识他,开始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
[1]郭沫若.批评与梦[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郭沫若.致陈明远(1955年10月23日)[A].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谢保成.近十年研究郭沫若动态[A].郭沫若学刊,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