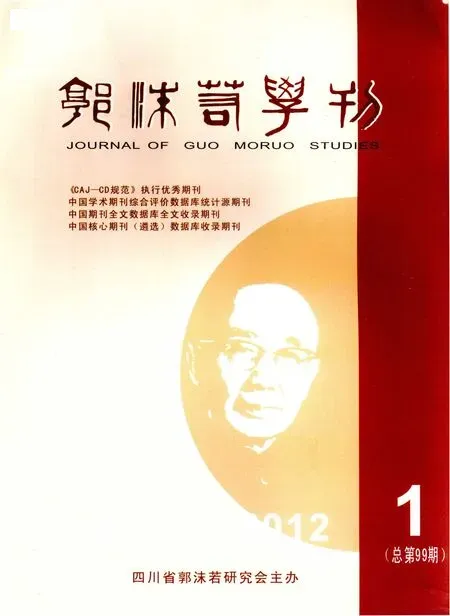一部现代版的《国殇》——从剧本到舞台的《屈原》
廖全京
习惯于将历史和现实情感化的剧作家郭沫若,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期,旋风一般连续写出六部历史剧。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屈原》。
《屈原》是一部戏剧诗体的现代《国殇》。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与“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灌溉了《屈原》,融汇成《屈原》,这部话剧恰是他的这两种思想的艺术结晶。
此前的几十年里,屈原作为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其思想中对国家命运的日夜牵挂和独立思考,对身居高位的权奸佞臣违法乱纪、昏庸腐败的愤怒斥责,早已与血液一般流贯在郭沫若的心灵中。郭沫若对乡国的苦恋,在屈原对乡国的苦恋中找到了原初的回音。冒死从日本归来,郭沫若对历史的屈原有了现实的体验:“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归国杂咏》)郭沫若的心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南后、张仪对屈原的陷害,尤其是楚王拒绝屈原联齐抗秦的建议而采纳绝齐联秦的主张,是根本的戏剧冲突。建构在这一根本的戏剧冲突之上的情节之网,将屈原置于漩涡的中心和矛盾的尖端。屈原面斥张仪而被囚禁于东皇太乙庙内,屈原的所有愤懑化为一篇《雷电颂》撕裂暗夜的长空,屈原眼见女弟子婵娟被歹人投毒致死,最终在卫士火烧庙堂之后悲壮出走……戏剧冲突的逐层递进,融入了郭沫若本人对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同时成为了照亮这一历史题材的精神火炬。长期对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使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了一些基本的设想。比如,他逐步确立了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人民本位。”(《〈历史人物〉序》)在《屈原》中,他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解剖屈原形象、塑造屈原形象的。郭沫若注意到了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解体,人的价值在不断提升,伦理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在同一时期的学术著作中谈到:“屈原是深深把握着他的时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彻底的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他的义,像他这样大仁大义的人物,我觉得实在是可以‘参天地’,实在是如他自己所说:‘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蒲剑集·屈原思想》)这里的人,郭沫若的理解便是“把人当成人”。这里的大仁大义,便是热爱民众,关心民众。屈原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根本的还是不愿看到楚国民众生灵涂炭。因此,在《屈原》中,他不仅塑造屈原形象以寄托对一位南方的儒者的崇敬和缅怀,而且塑造婵娟、卫士等形象以抒发一位民本主义者对草根人物身上的大仁大义的赞美和歌颂。屈原的悲剧与婵娟的悲剧浑然形成一部黄钟大吕的交响。如果要给这部交响一个标题,最恰当的自然是:现代版《国殇》。
郭沫若几乎将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屈原这个人物身上,他的诗人的激情在屈原身上燃烧,他让屈原成为全剧的灵魂。随着戏剧冲突的孕育、发展和逐步激化,热烈奔放与刚直清醒互为表里地统一在屈原身上,形成了他独特而复杂的个性。从第一幕起,即以象征手法赋予屈原的精神世界以动人的形象和色彩,春日桔园与朗朗谈吐,都是屈原政治态度与人生哲学的折光。随着张仪阴谋付诸实施,屈原遭受陷害,屈原的情绪爆炸进入酝酿阶段。他与张仪、南后近距离的激烈交锋,他对楚怀王的大声疾呼,是他一片沉重的爱国之心的淋漓坦露。同时,也是为屈原情绪的大爆炸蓄势。第五幕里屈原的雷电独白,一气呵成,一泻千里,在将全剧推向高潮的同时,将屈原形象的塑造最终完成。屈原的内心天地,灵魂中的世界,在这里完完全全向观众洞开。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清醒的政治家和热情的诗人,屈原复杂而统一的个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不过,如果作为孕育于古老文明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屈原这一形象似乎应当更为沉实和丰厚才好。
郭沫若笔下的南后,是一个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艺术形象。作为黑暗和邪恶的代表之一,她比张仪、楚王、靳尚等人具有更多的个性特色。南后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步是从害怕失宠这个基点上迈出去的。从这里出发,她娥眉工谗,将楚怀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恩威并施,把子椒、靳尚、宋玉都收罗到她的势力之中。第二幕里,她在宫中精心导演并亲自担任主角的那场陷害屈原的丑剧,正是她发迹丑剧更为触目惊心的续篇。这场戏,充分表现出了她身上那与聪明、才华混杂在一起的虚伪、歹毒和狡诈多变,充分写出了她身上那与人气混杂的“妖”气。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影响还远未消除的中国现代社会,南后这一形象的意义将会长久地显示出来。
《屈原》中还创造了相对比而存在的不同的灵魂——婵娟与宋玉:一个真正懂得并坚决贯彻了先生的精神,另一个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彻底背叛了先生的精神。屈原在宫中遭南后陷害,是婵娟率先站出来,公开为先生喊冤;她大胆地向南后发出责难,同她面对面地抗争。在第五幕里,这美好的灵魂化作了一团烈焰。在烈焰中,她听到了屈原对她的祭奠。与婵娟的纯真、聪慧、高洁之心形成对比的,是宋玉心地的浑浊、灰暗、肮脏。对待老师屈原态度的最后变化,是宋玉灵魂的第一面镜子。起初追随屈原,确乎出自热血青年的真心。然而,一旦这种追随带来对个人利益的威胁,便随之转化为背叛。在将灵魂高高挑起待价而沽的宋玉面前,贵为公子可以登基的子兰是第二面镜子。镜子里的宋玉——一个决心改换门庭另行攀附者的嘴脸和脏腑,赤裸裸地呈示出来。宋玉在婵娟这第三面镜子中,获得最为清晰的成相。第五幕,宋玉陪子兰探视被监禁的婵娟时,他的阴暗与无耻,可谓毫发毕见。作为丧失了人格、气节的文人和政治投机商,宋玉这个形象至今发人深省。
五幕历史剧《屈原》在戏剧艺术结构上的特色,表现为高度的凝聚性、强烈的节奏感和内在的爆发力。郭沫若将屈原三十多年的经历浓缩到从清晨到半夜的短短一天之内,如同雷电凝聚于那最浓最密的乌云中一般。在这种高度凝炼的前提下,《屈原》展示出对于悲剧节奏的独特把握和表现。在悲剧中,节奏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要素,更是剧作家情感节奏的外化或意象化。它是心理性的动作节奏的反映,是形式要素和内容要素的统一。《屈原》内部节奏的运动状态,呈现一种戏剧动作的疾、徐、张、弛,与体现在人物性格与情节结构之中的剧作家情感的抑、扬、起、伏相融合的抑扬回旋。开幕不久的那一段戏,在节奏上比较缓慢、舒展、明亮。屈原从子兰口中得到消息之后的心情变化,使节奏出现由徐缓向迅疾变化的端倪。尽管如此,南后陷害屈原事件发生之前,悲剧节奏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缓慢的。南后的丑恶表演给悲剧带来急剧的由缓而疾、由扬而抑、由弛而张的突变。紧接着,子兰与宋玉对谈,屈原因极度愤怒而丧魂落魄,群众为屈原虔诚招魂,戏剧动作与作家情感以抑扬回旋的节奏向前推进。婵娟在东门外小河边与渔夫和钓者的谈话,是一段情节节奏在外表上的小小平复。不久,屈原的上场,尤其是他与楚怀王、南后、张仪的对话,再一次使动作和情感节奏变得沉重而激烈,并在楚怀王下令将屈原、钓者、婵娟先后抓走时达到高潮。在强烈急促的悲剧节奏使观众的愤怒之弦崩得几乎断裂之际,宋玉、子兰在监狱中与婵娟的对话,使节奏又稍缓下来。这雷雨前的短暂宁静,却更加使人感觉憋闷。情感的总爆发终于到来——一篇《雷电颂》就是一曲人物的外部形体与内在情感的抑扬回旋。郭沫若曾经这样理解屈原的作品:“读他的东西实在苦闷得很,是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屈原与釐雅王》)在《屈原》中,他也是按照这种理解在把握和表现悲剧节奏的。
综观全剧的人物、结构和意蕴,可以看出郭沫若是把这部《屈原》当作《九歌》中的《国殇》的续篇来写的。作为追悼阵亡将士的悲壮祭歌,屈原的《国殇》是献给“死于国事者”(王逸语)的。屈原自己(包括婵娟),同样是死于国事者。而且,在郭沫若笔下,作为一名精神界战士的屈原以及婵娟,较之“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的征战之将士,其胸怀的宽广已不为具体的楚国境域所限,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魈雄。”将《屈原》视为《国殇》的现代版,应当是恰当的。
为将这部现代版的《国殇》搬上舞台,将郭沫若对屈原精神的现代阐释准确地传达出来,导演陈鲤庭与演员金山付出了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屈原》的演出在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留下了璀灿的一页。
《屈原》的舞台艺术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的一个高峰,也是陈鲤庭的导演艺术达到成熟的一个标志。《屈原》的文学台本大大激发了陈鲤庭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激情。在投排之前,他充分消化了历史上的屈原的人与诗,充分消化了郭沫若笔下的屈原的人与诗。他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艺术素养和生活积累、艺术经验,准确把握这部史诗剧特点;必须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从舞台艺术的整体性上把握和体现屈原这个人物和这部历史剧的剧场魅力。为此,陈鲤庭发挥他在导演艺术上高度重视舞台调度的特点,通过创造性的舞台调度赋予演员鲜明准确的形体动作。在陈鲤庭自己的舞台艺术词典中,舞台调度是导演的语言。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它的舞台呈现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导演的舞台调度,是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陈鲤庭有一个基本的导演思想,那就是“导演解释剧本的最具体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正确、细致安排演员‘走地位’,包括演员的起坐时机、动作方位的配合协调等等。”(参见李天济:《陈鲤庭评传》)因此,他一贯强调要控制好舞台调度。在《屈原》排练之前,他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钻研剧本和有关资料以及设计场面调度上。他把肥皂切成各种各样的大块小块,把自己关在屋里边思考边摆弄这些肥皂块。在将肥皂块挪来挪去的过程中,一种理想的表现人物关系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地位组合就诞生了。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为了造成这部现代《国殇》在精神上的气势和震撼力,陈鲤庭发挥他在导演艺术上的另一个特长,即从强调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原则出发,努力实现一种开放式的演出,一种舞台上下既彼此呼应、相互融合,又保持距离、冷静清醒的演出。为此,他从集中力量,重点排好《雷电颂》这一个场面入手,以期突破关键,带动全面。他首先对这个场面及其前后的每一个段落,包括重要的台词和情绪的转折,都进行了细致的设计,规定了演员的相应动作调度的位置和走向。为了烘托屈原的(同时是屈原扮演者金山的)激情,陈鲤庭创造性地运用舞台装置、音乐等重要的舞台元素,与精心设计的场面动作调度相结合,实现了他的艺术创造的整体性原则。他任用潘孑农举荐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的名家刘雪庵担任作曲,专门为《屈原》谱曲配乐。并从中华交响乐团、国立管弦乐团、中央广播电台乐队中借来二十多位演奏家组成专门的乐队,由刘雪庵担任指挥,为全剧伴奏。他专门把乐队安排在舞台正面的前下方显著的位置。当时的重庆国泰剧院没有乐池,为了放下乐队,不得不拆掉了观众席前三排的座位。事实证明,音乐恰如其分的烘托,更使《雷电颂》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陈鲤庭规划的舞台设计草图和舞台装置成为《屈原》演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雷电颂》这场戏的布景为东皇太乙庙。陈鲤庭把舞台巧妙地安排成好几个层次的表演区:前部低层是神殿,后部高层是庙廊,上下连接的阶梯转角处有平台。长廊偏右一根巨大的圆柱又间隔了庙堂。高层廊庙的下部是横贯舞台大半的诸神壁画,它同前面供桌构成了地下殿堂幽暗压抑的气氛,奠定了礼赞婵娟牺牲的悲剧场面的基调。庙廊顶端一根冲天圆柱则是屈原表演动作的有力支点。舞台最后面是开场阴沉而后雷电交加的广阔深邃的天幕。它为屈原抨击黑暗、叱问苍天的《雷电颂》提供了气势宏伟的背景。(参见李天济:《陈鲤庭评传》)整个舞台设计为演员提供了各种层次、多种意境的表演区位。通过综合运用音乐、舞台装置等艺术手段,导演丰富并深化了屈原的形象。
舞台上的屈原形象的成功塑造,将大后方优秀话剧演员金山的艺术生涯推向第一个高峰。屈原形象的出现,成为中国话剧表演艺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作为一名性格演员,金山塑造舞台形象的鲜明特征是重视人物气质的创造——通过内、外兼修即内部性格化和外部性格化同时并用的方式,侧重在外部性格化方面突现人物特定个性化气质。“金山在感应人物的身份、性格诸内部气质的同时,努力运用外部性格化手段改变自己的外貌、体态并从而抑制自己与角色不相适应的气质因素,在创造上来适应他所构思、设计出来的人物形象。”(胡导:《戏剧表演学》)金山在《屈原》中对屈原形象的塑造,是他的上述特征的最集中、突出、准确的体现。为了准确、生动地把握并传达出剧中的屈原气质,金山经历了一个由人物的外形走向人物的内心,同时由人物的内心走向人物的外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山既重视体验,也重视表现,以体验与体现的结合完成对屈原气质的传达。金山是从读郭沫若的《屈原》剧本同时读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起步的。从走入诗人屈原的内心的那一刻起,他已经下意识地进入了《屈原》第五幕《雷电颂》的形象构思之中。深入的理解使他急切地希望准确把握足以体现这种内部性格的外部形象。“我当时穿一件长袍,经常独自徘徊在嘉陵江畔,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楚辞》或《屈原》的台词,有时眺望着迷离的白云,有时俯瞰着不歇的江流……此后,我无论在江边、在人行道上、在屋内,都穿着长袍,拢着双袖,不停地、缓慢地迈着方步,默默地吟味《楚辞》和剧本的台词,……再经过一个时期,我把我的屈原形象,用中国画的勾勒笔法,分幕画成了六幅屈原像。”(金山:《我怎样演戏》)这里明显有三个步骤:一、烂熟于心;二、寻找外形;三、形之于画。这既是由内向外的琢磨过程,又是由外向内的提升过程。经过这种反复琢磨和提升,舞台上的金山已不完全是生活中的金山——他已经找准了人物的气质并向它贴近。为了让外部性格化更有民族、时代和动感色彩,让演出更有表现力,酷爱并学过京剧的金山,一边回忆京戏名宿们关于表演的卓见,一边计划着把京戏里的某些身段、说白运用到屈原身上。在演出时,他果然把撩袍、抖袖、甩发、圆场等戏曲动作、身段与台词有机结合起来。尤其在《雷电颂》、《哭祭婵娟》、《出走》这几场戏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造中,激情奔涌,撼人心魄。当年,陈鲤庭在看过《屈原》首演之后这样写道:“从银幕上饰吕布等角色,到《屈原》中饰屈原的金山,以不同角色的外形的把握见长,同时也不能抹煞他通过剧情体验的努力,可认为是在此表演门径中(指改变自己的模样来作化身的表演——引者注)走得最有成绩的一例。”(《重庆抗战第五年演出总批判》)
从案头的《屈原》到舞台上的《屈原》,这部现代版的《国殇》走了一条爱国主义与人民本位的精神之路,一条以情写戏和以情感人的艺术之路。70年过去了,这条路依然闪耀着瑰奇的光彩,现代版的《国殇》——《屈原》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