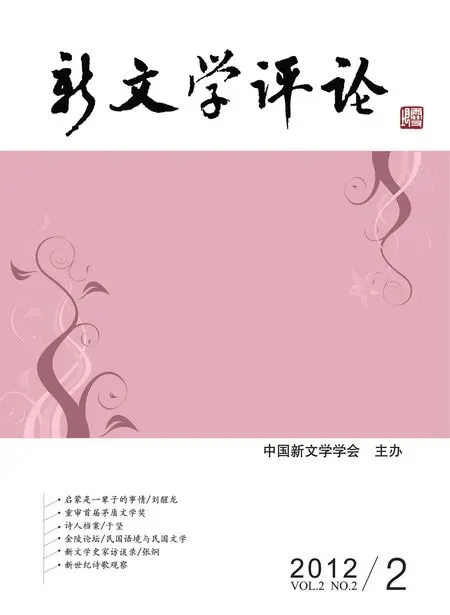对一种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的检讨
——重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 王春林
对一种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的检讨
——重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 王春林
回想起来,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1982年的事情,距今恰好整整30年时间。尽管在时间长河中,30年不过一瞬,或许是因为世事变迁太大的缘故,现在说起1982年来,已经似乎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了。30年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的文学写作,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的艺术审美观念,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重读周克芹创作于三十多年前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确实感慨良多。
第一次阅读这部小说,应该是当年上大学期间的事情。由于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关于人物和故事的诸多记忆,实际上已经很模糊了。这次有机会重读,所得的体验确实是陌生而新奇的。别的且不论,单就最表层的叙事趣味来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时下刊物上刊载的小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产品的印制等外在条件的限制,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进行评奖的时候,国内长篇小说的数量肯定非常有限。现在,中国长篇小说的数量,最保守的估计,每个自然年度都有两千部以上。尽管缺乏精确的数字统计材料,但我却完全能够推想得出,30年前长篇小说,与现在相比,数量一定少得可怜。在这数量较少的前提下,依照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所已经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准,它的获奖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后,已经到了一个时代转换的关节点上,地点是四川省一个偏僻的乡村葫芦坝。故事时间并不很长,小说开头从许茂老人准备“祝生”写起,到小说的结尾处,许茂的生日终于到来,但原先的“祝生”计划却并没有变成现实。周克芹把小说的矛盾冲突不无戏剧性地集中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显得特别凝练精悍。尽管说由于时代制约局限的缘故,小说本身在思想艺术上确实留有不少遗憾,但即使在3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部作品却依然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通过对于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重读分析,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一种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做出必要的反思和检讨。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肯定少不了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只有刻画塑造出了生动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长篇小说才可能较为长久地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重读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首先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周克芹对于若干人物形象相对成功的刻画塑造。其中诸如金东水、郑百如、许琴、齐明江、许秋云、许贞、龙庆、颜少春等人物,尽管作家所用笔墨不多,有些人物只是偶作点染,但却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然,最具人性深度,最具艺术审美价值,最耐人寻味的两个人物形象,恐怕还应该是许茂与四姑娘许秀云。
先让我们来看看许茂老人。好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要求作家必须对于该人物有新的发现。许茂老人的情形,即是如此。这是一个对于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从内心里热爱着农业生产劳动,朴实厚道中又不无狡黠自私的老农形象。许茂是葫芦坝一个家境不错的普通老农,已经去世的妻子先后给他生养了九个女儿。对于传宗接代观念甚强的许茂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少了一个儿子:“旧的传统思想压力曾使他痛苦得咬牙切齿,然而,现实主义者的许茂却并不因此悲观厌世,他不久就习惯了,他把儿子当儿子看待。……他要寻一个‘上门女婿’。”在那样一个土地早已集体化的时代,许茂对于土地的深情非常令人感动。“许茂在他的自留地里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太阳当顶。他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特别好。青青的麦苗,肥大的莲花白,嫩生生的豌豆苗,雪白的圆萝卜,墨绿的小葱,散发着芳香味儿的芹菜……一畦畦,一垅垅,恰好配成一幅美丽的图画。精巧的安排,不浪费一个小角落,细心的管理,全见主人的匠心。只有对庄稼活有着潜心研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因地制宜、经济实效的学问。许茂这块颇具规模的自留地,不是一块地,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心血和骄傲。这些年来,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庄稼越种越不如前几年,而他的自留地的‘花’却是越绣越精巧了。”只要是本本分分的中国农民,就都会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就容不得任何糟害土地的行为。正如同小说所描写的,作为一个土地情结严重的农民,许茂老人“也曾走在合作化的前列,站在这块集体的土地上做过许多美好的梦”。然而,由于当时农村政策的极大失误,集体化的道路不仅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生产力,反而极明显地暴露出了大锅饭的弊端,以至于集体的土地总是一片不理想的荒芜景象。正因为无法眼看着属于集体的土地无端地被人糊弄,所以,万般无奈的许茂老人才会倾全力于属于自己个人的自留地之上,居然把自留地侍弄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许茂老人本来正常的行为,反而被看成了不正常。按照当时的通行观念,老人之被看作是思想“落后”的农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克芹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把这种发现凝结表现在许茂老人身上,才使得许茂成为了上承糊涂涂(赵树理《三里湾》)、亭面糊(周立波《山乡巨变》)、梁三老汉(柳青《创业史》)等人物形象余绪的农民形象。尽管更严格地说,许茂老人的人性审美内涵还是无法与以上几位相提并论。
需要注意的是,周克芹并没有把许茂老人完美化,在充分肯定其眷恋土地热爱劳动的同时,作家也有力地揭示了其人性中短视狭隘自私的一面。许茂老人的短视,主要表现在他和大女婿金东水之间的关系上。“不久,倒霉的金东水又遭了一场祸事:火灾毁掉了他的住房。当时,身为大队长的龙庆跑来找许茂商量:要老汉把他宽敞的两间来给老金夫妇和两个孩子暂住。许茂先不吭声,进到自己屋里独个儿召开了一次紧张的‘形势分析会’。这位精明的庄稼人思前想后,竟得出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结论,他断定金东水摔了这一跤之后,是永远也爬不起来了。”以至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幸落气之后:“当九姑娘领着几个社员来到家里栳木料去为死者做棺材的时候,老汉却巍然站立在大门口,不让人们进去,九姑娘气得大哭也不顶用。”许茂老人何至于如此冷酷无情呢?难道他内心中就没有对于女儿一家的亲情么?问题的答案,很显然只能到当时那样一种不合理的政治现实中去寻找。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的时代,大女婿犯了政治错误而被迫下台,就意味着被打入了另册。为明哲保身计,从根本上与大女婿划清界限,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很显然,正是在此种思维逻辑的主导之下,许茂老人最终做出了后来被证明是短视的决定。
但是,与许茂老人的短视行为相比较,更能凸显其人性缺陷的,却是他对于卖油农妇的市场欺诈行为。眼看着卖油的农妇急着要把油卖掉好给怀里发烧的孩子看病,精明的许茂老人居然趁火打劫,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一元钱把油买下,然后再以大约一元五角左右的高价卖掉,好赚取其中的差价。而且,这已经是许茂老人的日常行为了:“许茂老汉这几年来在乱纷纷的市场上,学到了一些见识,干下了一些昧良心的事情。像今天,他做出怜悯的神情,用低于市场价格的钱买下那个女人的菜油,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简单而迅速地赚点外水,这样不光辉的事情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对于许茂老人的此种行为,我们可以剥离为不同的两个层面来加以评价。一个层面,是具体到小说中许茂老人对于卖油农妇的趁火打劫行为。在农妇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时候,“从前也曾窘迫过、凄惶过的”许茂,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欺诈农妇谋取自身的利益。另一个层面,则要从具体的小说细节中抽离出来,在当下的意义上来重新理解看待周克芹的相关判断。我们在这里的实际所指,就是“昧良心”与“不光辉”这样的价值判断。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许茂的行为不仅谈不上“昧良心”与“不光辉”,而且还很有一些超前于时代的商业意识。因此,从根本上说,真正思想滞后的,其实并不是许茂老人,反而是创造出许茂老人形象的作家周克芹自己。在自己笔下的人物已经挣脱时代枷锁奋然艰难前行的时候,作家自己的思想反倒停滞不前,此种情形着实耐人寻味,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在许茂老人的九个女儿中,周克芹用力最多,刻画最成功的,当数命运遭际异常悲惨的四女儿许秀云。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一位女性形象,许秀云身上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善良柔弱中的坚韧与隐忍顺从中的抗争。先来看她的柔弱隐忍:“十年前,那个只读了半年高中就被学校开除回来的郑百如,那个使葫芦坝上每一个诚实的待嫁姑娘都讨厌的花花公子,是怎样在一个夏日的黄昏,趁着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将她拖到芦蒿丛里,强奸了她。而软弱的四姑娘只能饮泣吞声,不敢向家庭、向组织透露一点儿声息……”遭此巨大打击,居然一声不吭,许秀云之软弱自然令人印象深刻。从小说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尽管恶棍郑百如在家庭生活中对于许秀云百般折磨,但许秀云却一直以顺从的姿态长期隐忍。如果不是郑百如自己试图在掌握葫芦坝的大权之后想着要换一个老婆,恐怕一贯软弱隐忍的许秀云根本就无法逃脱郑百如的魔掌。然而,即使许秀云和郑百如已经离了婚,但郑百如那巨大的阴影却仍然笼罩在她的身上。郑百如一旦预感到自己有可能陷入困境,马上施展各种手段,试图迫使许秀云答应复婚以摆脱危机的困扰。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秀云的人生困境,不仅来自于郑百如,还同样来自于自己百般眷恋着的大姐夫金东水:“她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折磨,都忍受过来了;今晚上遭到大姐夫的冷淡,比过去从郑百如那里遭到的全部打击,更加使她痛苦和悲伤!仇人的拳头和亲人的冷眼,二者相比,后者更难受得多。”不仅如此,许秀云还面临着种种流言蜚语的缠绕,面临着来自于老父亲和自己同胞姐妹的误解。面对着这么多的压力,一贯软弱隐忍的许秀云的确曾经产生过沉水自尽的念头并付诸过行动。但到了最后,还是她内心中沉潜着的一种强韧的母性发生作用,把她从死亡线上拉拽了回来。
难能可贵的是,许秀云并没有一味地软弱隐忍到底,正如同非常了解她的老父亲早就洞察到的,在她软弱隐忍的背后,其实也还有着不屈和执著的另一面:“他知道每一个女儿的脾气。四姑娘虽然心慈面软,可要真坚持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不像三女儿,那个‘三辣子’虽然肝经火旺的,吵闹之后还容易说服一些。他就怕四姑娘使那个‘闷头性’——你吵她、骂她,她埋着脑壳不开腔。以往的经验证明,吵闹的结果,十回有十回是老汉失败的。”真正是知女莫若父,许秀云的性格中确实存在着不屈抗争的另一面。这一点,极其突出地表现在她和大姐夫一家的关系上。大姐因病去世,一方面因为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照料姐姐孩子的缘故,许秀云对于大姐夫早就心生情愫。实际上,在金东水这边,也已经心有所动。但是,在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上,一直取主动态势,有情怀有担当的,却是四姑娘许秀云。小说开始不久,顶着流言蜚语的巨大压力,夜里毅然跑到金东水家门外给小女儿长秀送新棉袄的,是许秀云;在集市上,当金东水带着一双儿女因为缺钱而陷入困境时,主动伸出援手的,是许秀云;到后来,面对着郑百如他们的造谣中伤,下决心揭穿事情的真相殊死抗争的,依然是许秀云。由原初的过于软弱隐忍,到后来的不屈抗争,能够把这些对立性的人性因素糅合在许秀云这一形象身上,是周克芹值得肯定的一个地方。假若说周克芹再充分地使用一些笔墨,把许秀云性格转换的内在动力交代表现得更加具有说服力,那这个女性形象的人性内涵与审美价值无疑就会得到更强有力的提升。
人物形象的塑造之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于一些人物的描写也有其精妙之处,应该得到肯定。比如,关于许秀云,周克芹就曾经借下乡工作队的颜少春的视角来进行过描写。“过了一阵,颜少春的注意力不由得集中到一个三十左右、容颜清瘦俊俏的妇女身上去了。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留心到这个女人既没有笑,也没有跟人家答白,只是埋头狠命地挖。看那单薄的身子,好像很有一把力气,她挥动着一把大锄头,那么三下五下的,一个树疙兜就给挖起来了。”颜少春没有见过许秀云,并不了解许秀云的基本情况,借助于这样一位陌生人的眼光来看去许秀云,可以艺术性地从侧面把许秀云的容貌、气质以及性格特点勾勒表现出来。“容颜清瘦俊俏”“单薄”,描写的是许秀云的容貌气质。“很有一把力气”,凸显出的是许秀云劳动妇女长期劳作的特质。“既没有笑,也没有跟人家答白”,展示的是许秀云一贯低调内敛然而却又不失坚韧的性格特点。实际上,也并不只是许秀云一人,对于金东水,周克芹也曾经采用过这种侧面的表现方式。这样的一种人物描写方式,较之于那种直截了当的正面切入,很显然要艺术得多。
然而,尽管以上一些方面都值得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部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是打下了那个时代的清晰印痕,在思想艺术方面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是思考评价社会历史问题时一种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集中描写的是1975年的一段社会历史生活,因此便可以被看做一部关注表现“文革”问题的长篇小说,既然是一部以“文革”为反思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那么,作家如何看待评价“文革”,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周克芹对于“文革”持一种否定的批判性姿态,这个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关键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作家对于“文革”悲剧成因的思考认识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周克芹的思考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欠缺。按照周克芹的描写,葫芦坝之所以会问题成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正直高尚而且能力超群的金东水被罢职,道德行为一向败坏的郑百如取而代之,成为了葫芦坝实际上的决策者。那么,郑百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可以说,周克芹差不多把所有的恶习都赋予了郑百如。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郑百如,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再加恶棍的形象——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简直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他不仅以强奸的方式硬性占有了许秀云,迫使许秀云成为自己的妻子,然后对她肆意侮辱百般蹂躏,而且还以推荐出去参加工作为由,强行占有了自己的妻妹七姑娘许贞。为了有效保护自己,他不惜利用自己的姐姐,葫芦坝“闲话公司经理”郑百香去制造谣言,以达到迫使许秀云和自己复婚的目的。“在郑百如瓦房里,经常设酒摆宴,他们那一群家伙,怎样地咒骂共产党,怎样地挖空心思诬陷四姑娘的大姐夫金东水——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又怎样的暗地里偷盗队里的粮食,筹划投机倒把……而郑百如在干下了这一切罪行之后,又是怎样地威胁她:将她绑起来,举着明晃晃的刀在她眼前晃来晃去……”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红火起来的郑百如,竟然带了连云场上那个烂污女人回家来睡觉。”以上林林总总,归结在一起,郑百如就端的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有可能真正成为葫芦坝的决策者么?难道葫芦坝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罪到郑百如身上么?在这里,周克芹很显然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认识的误区之中。当周克芹把这一切都与郑百如个人的道德问题联系起来之后,其实他已经把社会历史反思追问引领到了一个并非根本的方向上,已经把社会历史问题道德化了。正如同我们后来所明确意识到的,实质上,我们更应该在社会机制的层面上来思考追问“文革”的问题。
其次,小说创作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种细节的艺术,如果离开了细节描写,一味地通过概括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创作,那很显然就犯了小说创作之大忌。但是,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小说中,此类“犯规”现象却很遗憾地屡屡出现。比如关于许秀云,小说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交代性叙述:“这个手板粗糙,面容俊俏的农村妇女,心有针尖那么细,任凭感情的狂涛在胸中澎湃,任凭思想的风暴在胸中汹涌,她总不露半点儿声色。她细心地拾取着那狂涛过后留下的一粒粒美丽的贝壳,认真地拣起暴风给吹刮过来的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把它们积蓄起来,藏在心底,耐心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盼望着一场透实的喜雨,贝壳将闪光,种子要发芽。”这里,叙述者明确地告诉我们,许秀云是一个内心细腻,情感丰富内敛,尽管不断遭遇逆境却总是对于未来抱有希望的农村女性形象。把这些特征赋予到许秀云身上,当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作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这些特征的。在这方面,越是高明的作家,就越是不会像周克芹这样以一种越俎代庖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把人物的性格特征说出来。一部《红楼梦》,曹雪芹一次也没有让叙述者跳出来,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林黛玉的性格如何如何,贾宝玉的性格又是如何如何,他只是非常耐心地把一个又一个小说细节连缀在一起,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让读者自己去提炼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周克芹的问题在于,关于许秀云的交代性叙述并非偶然现象,除了许秀云之外,在写到诸如金东水、颜少春、许贞、许茂等不少人物形象的时候,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越俎代庖”,让叙述者直接跳出来说明人物性格特征的现象。
第三,优秀的小说作品当然少不了深刻思想的寄寓和表达,但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叙述者总是按捺不住地要以大段大段议论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其实也就是周克芹的思想认识。比如:“七姑娘啊七姑娘:哭吧,哭吧,你这个无知的女子。你给许茂老汉丢人,你给许家的姑娘们丢脸,你为什么不能像你的众多的姐妹们那样严肃地对待人生?你为什么把你爱情花朵这般轻率地抛向泥淖?你懊悔了么?懊悔吧!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悔恨的眼泪洗净你的虚荣心以后,你也许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再比如:“四姐啊!你的悲哀是广阔的,因为它是社会性的;但也是狭窄的——比起我们祖国面临的深重的灾难来,你这个葫芦坝的普普通通的农家少妇的个人的苦楚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这些年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摧残着和扼杀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也摧残和扼杀了不知多少个曾经是多么美丽、可爱的少女!四姐啊,这个道理你懂得的,因为你是一个劳动妇女,你从小看惯了葫芦坝大自然的春荣秋败,你看惯了一年一度的花开花落,花儿谢了来年还开。你亲手播过种,又亲手收获。你深深地懂得冬天过了,春天就要来。你绝不会沉湎于个人的悲哀。”关于小说中的类似议论,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分析。其一,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小说写法,严格地说来,小说创作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一定之规。即如小说中的议论问题,尽管我们强调小说本身是一种叙事艺术,但也并不就意味着小说叙述过程中就不能出现议论的片断。然而,小说中的议论,却又不能够过于随意地穿插进来。周克芹此作中的议论问题,突出地表现为过于随意过于频繁且又有不着边际的嫌疑。翻检此作,类似于以上所摘引的非小说化的议论段落,可以说随处可见。不能够让自己所欲传达的思想认识隐含在故事情节中艺术地表现出来,更多地依赖叙述者公开现身议论的方式来凸显思想认识,说明的正是周克芹作为一个小说家艺术表现能力的有限。其二,退一步说,周克芹所发表的这些议论的内容本身,细究起来,也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前一段的议论对象是七姑娘许贞。尽管在追求情感的道路上遇到过一些挫折,但严格地说起来,许贞追求真诚情感的行为本身却很难说存在什么问题,更谈不上什么严肃或者不严肃。在这个意义上,周克芹从当时不无陈腐的观念出发的对于许贞的指责,今天看来其实很难站住脚。后一段的议论对象是四姑娘许秀云。在这段话里,周克芹特别强调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依他所见,与同样苦难深重的国家命运比较起来,四姑娘许秀云的悲哀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过于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严重地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很显然是周克芹这一段议论的致命伤所在。这样一些不仅非小说性而且本身就存在问题的议论性段落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艺术性。

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