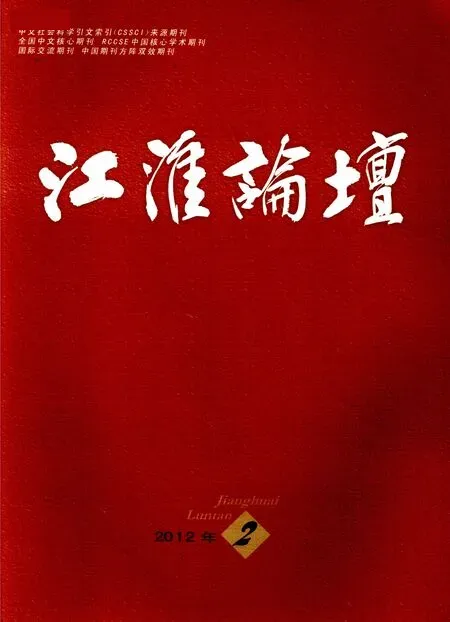试论农业审美愿景
——新农村建设与环境美学
陈望衡
(荆楚理工学院,湖北荆门 438000;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试论农业审美愿景
——新农村建设与环境美学
陈望衡
(荆楚理工学院,湖北荆门 438000;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渔猎、农业、工业是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着的三种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自然界、农村和城市是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的三种主要的生活环境。目前的城市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按城市的模式改造农村,实际上是消灭农村。这种做法体现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然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出现,实际上正在将社会推向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已有向农村回归的趋势。农业生产本来更切合人性,而农村也本具有宜居和乐居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落后的生产力的条件是低层次的,但借助了工业社会高科技的优势和后工业社会新的农业观念,它有可能发展到新的水平。未来的农村将成为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未来的农业应让人类更幸福。
农业;农村;环境美学
中国现在社会所存在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城乡差别。为了缩小城乡的差别,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许多重要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为新农村建设工程。新农村如何建设,主要问题有二:一、新的农业朝何处发展?二、新的农民住宅如何建设?这两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也涉及众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笔者仅就环境美学的角度对于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供有关部门和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们参考。
一、农业——环境美学之母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生产方式最早是渔猎采集,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所必需的资料,其后人类不再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所必需物质了,改为种植和豢养。种植和豢养可以看成是人从自然界间接地获取生活资料。人工种植的植物如稻麦、豢养的动物如牛羊,虽仍然是自然物,却不是野生的自然物,而是人造的自然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作物和牲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农业的本质是人部分地代自然司职。
人类另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工业是在农业基础上的再生产,工业的原料来自农业。工业的本质也是人造自然,但是,农业与工业有重要的区别:一、农业是直接与大自然对话,其中主要是人与大地对话;工业则不直接与大自然对话,它是人与农业产品的对话。二、农业所生产的作物、畜类均是有生命的,因此,农业生产的这种“对话”不是一般的人与物的对话,而是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的对话。这里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人与真实的生命物——农作物、牲畜的对话,二是人与被人移情化了的自然界对话。所谓移情化了的自然界即被人情感化了的自然界。农民对于影响农业收成的大自然诸如太阳、月亮、雨、露、风、霜等都将其情感化了。这种情感化既有原始宗教的意味,也有审美移情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农业劳动在人类所有的劳动中,是最具审美意味的劳动。劳动过程既是人的意志的对象化,更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
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环境,环境是人的家。渔猎采集、农业、工业是人类三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之相应,人类就有三种不同的家园——自然界、农村、城市。
当人类主要靠渔猎采集为谋生的方式时,人直接生活在自然界中,或洞居,或巢居,基本上不需要盖房子。无山洞可居时,也只是搭建临时的窝棚。那时的人们居无定所,哪里有可渔可猎可采集的食物,就到哪里去生活。这个时候,人们没有家园这一概念。
农业生产就不同了,农业要种植谷类食物,要豢养牲畜,不能不定居下来。定居就要盖房子。汉字“家”上为一个宝盖头,那就是房,中间有一个豕,代表着农业。当然,汉字“家”字只是说明农业与家庭产生的重要关系,房子主要还是让人来住的。人如何住,就涉及社会结构了。母系氏族社会时候,人们主要还是靠渔猎采集生活,氏族中的男女是分住的,当时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部落中的人一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人们主要靠农业来生活了。农业劳动需要男女配合,这时,相对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出现了。一对夫妻共同从事农业劳动,既有所分工,又互相配合,所谓“男耕女织”,这样,就出现了家庭。
在对偶婚姻出现的背景下,“家”的概念产生了。“家”的概念延展有两个系列:一是社会学系列,最基本的家为一对夫妻,它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有小有大,最大的家为家族。家本是血亲关系的联合体,当家的概念突破血亲关系时,家就成为了有共同利益的社会了。自古以来,就有“家国”的说法,将国也看成是家。另是哲学系列,将自然纳入思考的视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看成是人类的家。这种家的概念虽然突显的是精神的意义,但因为它实际上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自然作为人的家,并不只是象征性的。
在当代,当我们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很自然地将影响我们生存的自然、社会看作环境。自然和社会既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却又是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世界,当我们不再将自然与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时,实际上我们是将自然与社会看成是我们的环境了。美国哲学家阿诺德·伯林特认为“人与环境是统一体”[1]。芬兰环境美学专家约·瑟帕玛也认为“环境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中的观察者和它的存在场所紧密相连”[2]。而在笔者看来,环境与人的关系具有一种类血亲关系的性质。人类来自自然,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所以,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自然是人类的家。而就个人来说,任何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可以说,社会是人的家。自然也好,社会也好,当我们思考它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均是环境。环境美学作为环境哲学的一部分,它侧重于研究环境与人的情感关系,环境美的本质在家园感[3]。
既然人类最初的“家”是农业的产物,有农业才有家,既然我们将环境的本质看成是“家”,将环境美的本质看成是“家园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原始农业实际上是环境哲学包括环境美学的胚胎。现今农业源自原始农业,那么,在当今环境美学建设中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注环境美学的母体——农业了。
二、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农村所具有的审美优质
农村是作为人类的最初的家,目前,尚是主要的家。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农村具有四种重要的审美优质:
第一,它能让人比较多地与自然相亲和。农村,举目就是自然,不是原生态的自然,就是农作物的自然。人来自自然,天然地具有亲自然性。渔猎生产时期,人直接住在自然环境中,这固然可以跟自然有最直接的交往,但是,由于人极大地受制于自然,因此,这种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不都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亲和,在许多情况下,倒是会感到对自然对人的生疏与恐惧。工业社会造成的城市,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自然赶出城市,市民远离了自然,人的亲自然性得不到实现,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异化了,诸多的城市病其实根源于人与自然的疏离。农村这个家,一方面,因它与自然有着充足的接触,能较好地满足人亲和自然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这个家,因为毕竟不是安放在原始的荒野上而是安放在田野——人造的自然中,因而可以排斥原生态自然对人性压抑的负面效应,较好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可以说,农业在满足人性的自然需求和文明需求两个方面均有它特殊的优势,而在强大的工业文明背景下,农业的亲自然性更显得突出。
第二,它能让人直接地与自然生命进行交流。农业生产重要性质之一是人直接地参与培育自然生命的活动。生命是地球上最高意义的存在,地球上的活动最具意义的莫过于生命的活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生命与生命间的交流。农业生产中的种植谷物、豢养牲畜,既是人的生命在培育物的生命,也是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在进行着交流。“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还有什么比生命与生命的交流更具审美意义呢?
第三,农村有更为丰富的人际交流。众所周知,工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是分离的。生产中,工人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机器。工业化程度越高,人对机器的依附就越强,主体性就越弱。工业生产中,工人与工人的关系均是建立在机器的运转上的,是机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实质是机器中的部件与部件之间或者说是机器运转中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关系。自然,这种建立在机器运转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只能是理性的,绝无感情可言。
在农村,生产与生活虽然也有所分开,但是,生产上的伙伴往往也是生活中的伙伴。农业生产也需要使用机械,机械操作是要讲理性、讲规范的,这方面,它与工业生产有类似之处。但是,农业生产有着更多的手工活。在手工劳动中,生产伙伴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不仅有工作上的协作,而且有情感上的交流。特别值的一说的是,由于这种劳动多为家庭性的合作,如杨万里在《插秧歌》中所写:“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因此更具情感性。正是因为劳动者在生产中有这样的密切关系,使得农业生产较之任何一种生产更审美,更自由,更愉快。
第四,农村的环境特别广阔。现代人对于生活环境,非常看重个人的自由空间,因此,环境的审美评判,疏朗感显得很重要。这方面,城市有许多无奈。太多的建筑、太多的汽车、太多的人,将个人的生活空间挤压到难以容忍之仄。这方面,农村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一般来说,农舍多散落,不那么集中,环境多恬静,不那么喧嚣。由于建筑不那么密,不那么高,人们头顶的天空就显得特别地开阔,而脚下的大地则更多的是树林,是草地,是溪流,是田野,而不都是水泥路面。显然,生活在农村这种环境,人的心胸是易于开阔的,而思维也会更为自由与活跃。
三、新兴农业的审美新质
虽然农村这个家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某些方面更切合人性,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下的农业,对于人性的满足与实现,均是低层次的,
就满足人的自然性这一面而言,农业生产与大自然有充分的接触,但是繁重的农业劳动以及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让人们不能以轻松的心情实现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就满足人的文明性一面而言,农业劳动的科技含金量是比较低的。农业受制于自然条件远比工业严重,“靠天吃饭”的局面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生活在农村的家园里,不能说没有快乐,但那种快乐是有限的。翻检几千年来农业社会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人类对大自然的抗争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其实也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神灵,迷信与愚昧不可避免地主宰着人类的心灵,而贯穿于整个农业社会的主旋律不能不是绵长的忧伤、迷茫与痛苦。农业生产力的落后,造成了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于是,人们对于农村这个家,人们的情感态度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是深沉的依恋,另一方面又是无奈的诅咒。
农业的美与农村环境的美,首先是对农民而言的,农民才是农业审美的主体。然而数千年来,赞美农村风光的,欣赏农业美的,主要不是农民,而是城里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不是农民,不能充分体会农业的艰辛,也不能充分体会农民们对农业、对农村的复杂感受。这种对农业的审美是片面的。要让农民真正成为农业审美的主体,必须将他们被压抑了审美需求释放出来,让他们在不再以唯功利的眼光还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产对象和生活环境。不仅从国富民强的意义来说,而且从释放农民们的审美潜能来说,农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的改造。而农业的改造首先是观念的改造。农业是什么,过去的基本定性是产业,它是人类的一项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生产活动。具体来说,农业有两项任务,一是提供人类的生活资料,其中主要为食物。二是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两项任务仍然是经典性的,现在仍应该固守,但是,新的时代又为农业增加了两项使命,一是生态使命,二是审美使命。
农业的生态使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为人类提供绿色食品。关于此,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其理论为 “有机农业(Organic Faming)”。英国学者巴弗尔(Balfour)认为,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他主张通过调节土壤的办法来让农作物良性生长,以保证农作物不含有害于人类健康的元素。上个世纪中叶,日本学者吉田茂提出“自然农法”,所谓自然农法,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的秩序与法则,“充分发挥土壤本身的伟大力量来进行生产”。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这样做,似乎是回到了原始农业,原始农业是没有化学肥料和农药的。这样,产量是不是很低?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产量无疑是很低的。但是,有机农业不只是采取“减法”,也实行“加法”,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促使作物朝着人需要的方面发展,提高作物的品质与产量。[4]
然而,仅仅这是不够的。生态农业不只是为人类提供绿色食品,而且要为改善地球的生态质量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做出贡献,这就是农业生态使命的第二方面,应该说它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关于这方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维护双赢,也就是说,既维护了自然生态,又获得了良好的收成。另一种情况则是维护了自然生态,但影响了农业的收成。前一种情况当然好,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这第二种情况的出现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农业有时需要做出这样的牺牲。2003年笔者参加在芬兰召开的农业美学国际会议,会上就有这方面情况的介绍。中国其实也早有这方面的实践,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这样的工程,实际上也是以牺牲农业的代价来换取生态的修复。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原本的两大使命,相对过去会逐渐变得较为容易。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就是证明。但是,由于整个地球的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能不增加维护生态平衡这一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农业由于人类直接在地球上的劳作,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它在修复地球生态,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上有它独特的优势。目前,农业这一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农业的生态使命的日益凸现,使得它本具有生态美这一性质得到彰显。生态美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美,而是一种审美性质,它存在于诸多的审美对象中,自然界中有,社会界中也有。在自然界与社会界相交融的农业世界中,具有最为丰富的也最为深刻的生态审美性。
农业的审美使命也是时代赋予的。农业由于主要是手工劳动,又由于是在天地间进行的劳动,因此,它原具有浓郁的审美的潜质。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没有地址的信》中举了大量的地球上残存的史前部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巴戈包斯族,这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土著部落,在种稻的日子里,“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将一把铁镐插入地里。妇女跟在他们后面,把谷粒撒到男子所挖的沟里,用土把它盖好。这一切都是严肃认真地进行的。”[5]尽管古代农业具有准艺术的性质,但不具审美性。普列汉诺夫强调巴戈包斯族人的种稻劳动是在“严肃认真地进行的”。显然,舞蹈只是协调动作的节奏,以减轻疲劳,并不是为了娱乐。如果要说这中间也有审美,那只能说是潜审美。新兴的农业则有可能将这种潜审美予以释放,让农业劳动兼具两种性质:功利性和审美性。功利性,就是说,劳动还是劳动,它创造价值;审美性,就是说,它可以与功利不挂勾,而给人带来愉悦。这里具体可以展开成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过程具有审美性,另是劳动成果具有审美性。这两种审美性均可以说成是“如艺术性”。前者作为动作,可以说是农业艺术;后者作为成果,可以说农业景观。两者不仅成为农民们的审美生活,而且均可以在农业的观光、旅游中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到农村去观光,不仅是欣赏农业景观,而且可以参加农业劳动,这种劳动虽可以创造财富,但对于观光客来说,却是为了快乐——超越功利的审美快乐。这种劳动更多的像是艺术。丹麦学者玛琳理·哈斯勒提出了“耕作艺术”这一概念。她说:“如果你认为耕作的过程是一种精致的对待风景的方式,是耕作的艺术,你就可能区分这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的、生物的严肃方面;另一方面是索伦森斯说的产物形式,即美学和社会学方面。”[6]哈斯勒说的“耕作艺术”侧重于农业景观的审美意义。在现代观光农业的发展中,农业景观的审美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新的两大使命——生态使命和审美使命的提出,意味着与农业关系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土地,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将农业仅仅看成是生产,土地它是资源。农业与其他生产一样,均以掠夺资源来获取财富。而如果将农业不只是看成生产,它还具有维护生态、提供审美对象的使命,那么,它就不只是资源,还是环境。资源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而环境与人的关系是亲和的,因为环境是人的家。农业观念的改变是一场革命,它实际上已经到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它。
四、新农村建设的审美愿景
农业的发展与农村的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村该如何建?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农村建成小城镇。农村就是城市的缩小版。对于此种做法,笔者是忧虑的。城市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病,难道还要侵染到农村去吗?
笔者认为,农村建设除了坚决执行国家的土地政策,尽量不占用可耕地以外,在环境美学意义上,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必须保持农村的特色,突显农村的优点。
首先,农村特色的问题。农村作为生活环境,其突出的审美优质是拥有更多山林、草地、河流,而且它主要不是人造的,而是自然原本就有的,野生的。新兴的农村建设一定要突出这一点。与这个问题相关,农村建设要充分注意与自然山水相结合,依山傍水,显山亮水,突出人与自然的亲和性。
从景观来说,农村景观的特色是农业景观,那就是田野、牧场,种植基地等,不要让新兴的农村离开这些景观,反过来,倒是特别需要亲近这些景观。不可设想,到农村去,看不到水稻,麦地,看不到牛、羊。如果这样,那就是农村建设最大的失败。
农村特色与农业劳动的这种生产方式相关。农业劳动主要是以家庭为本位,为了适应这种生产方式,新农村建设宜以家为本位,一般一家一栋,屋宇以院落式为主,一定要接地,以便于农民停放自家车辆和农具农械。
农村特色还与农家生活方式相关。新农村建设一定要突出农家生活主题,以舒适、宽松、自由为特色,让农民们有更多的交际空间。
基于农业劳动与农家生活的特色,农村建设宜散聚结合,既有相对集中上千户的乡镇,也不妨有一两户、三五户小的村落。不宜一律集中,全建成城镇。
其次,村庄特色问题。农村建设要求各个村庄都要有自己的特性,万不可一套图纸,各村克隆。平原地区农村,地理特色不鲜明,如果村庄建设成一个样式,那就很难分别了。
这里,美学的和谐性问题仍然值得农村建设者的注意。农村建设不仅要注意与地形地貌的和谐,而且要注意与传统文化的和谐。我国东南地区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在建设自己的新村庄时,盲目搬用西欧或北欧一些村庄的模式,弄得不伦不类。中国农村一定要像中国农村,不能将欧洲农村的风格搬到中国来。美国当代环境美学学者阿诺德·伯林特说:“没有考虑到本地的建筑传统而采用外国的地区或种族设计风格的作品从不会让人觉得舒适。这就如同在缅因州的海滨村庄里建造西班牙的庄园或是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一样。”[7]阿诺德将这种美学上的大忌称之为“不适宜性”。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模式改造农村,实际上是消灭农村。这种做法体现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然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出现,实际上正在将社会推向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已有向农村回归的趋势。农业生产本来更切合人性,而农村也本具有宜居和乐居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落后的生产力的条件是低层次的,但借助了工业社会高科技的优势和后工业社会新的农业观念,它有可能发展到新的水平。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得利最多的是农村,农村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前提下,要尽量地吸取城市的优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当农村日益富裕起来,农民享受市民的生活方式,不是太遥远的理想。
在现代化的今天,农村不仅不应该被消灭,而且要建设成人们的乐园。未来的农业劳动在高科技的武装之下将变得轻松。农业生产天然具有的直接与生命交流的特色不仅会继续保持,还因高科技的参与变得浪漫而有趣。农村,不管是小镇还是村落,都不仅拥有优越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定然成为许多人的追求。未来的农村将成为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未来的农业应让人类更幸福。
[1]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9.
[2]约·瑟帕玛.环境之美[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3.
[3]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9.
[4]席运官,钦佩.有机农业生态工程[M].北京工业出版社,2000.
[5]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85-86.
[6]玛琳理·哈斯勒.耕作的艺术//环境美学前沿第二辑[C].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4.
[7]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5.
(责任编辑 焦德武)
B834
A
1001-862X(2012)02-0015-006
陈望衡(1944-),荆楚理工学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