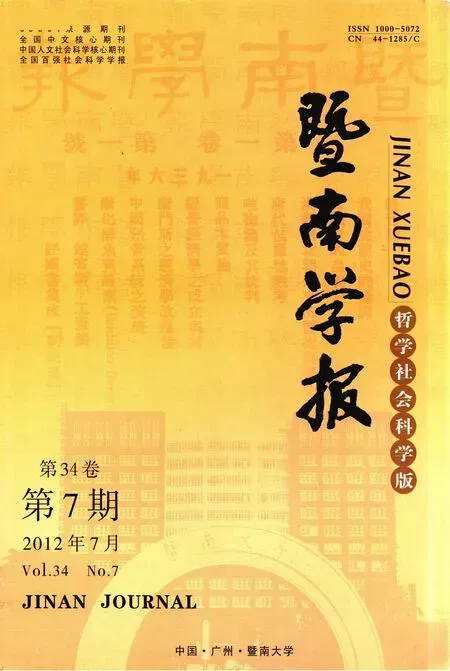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袁 韵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袁 韵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镜花缘》;李汝珍;科举制度;八股文
《镜花缘》是清代乾嘉学者李汝珍倾注毕生精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著作,充分表现了作者丰赡的才学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讽谕。《镜花缘》以落第士子唐敖、多九公的海外游历、众才女天朝应试以及中试后的欢宴为叙事主体,篇末以太后归政于中宗后下懿旨“来岁仍开女试”绾结全书,从这一角度来说,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部以科举为核心结撰的关于“考试”的小说。作为生活在清代中期科举社会中的封建文人,李汝珍却“不屑章句贴括之学”(余集《李氏音鉴序》),终其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将全部的精力和才华用到了文学创作和音韵学研究上,为后人留下了文学名著《镜花缘》和音韵学著作《李氏音鉴》。在那个普遍以科举功名为人生追求的科举社会,李汝珍的确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超逸流俗的文化学者。基于自身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不同的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科举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一生屡遭科举挫败“椎心剔骨”之痛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揭露了科举考试的黑暗,也表达了自己“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叶生》)的不甘;对科举由热衷而终至绝决的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表现了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和心灵的异化。那么,一生未涉科举之途的李汝珍,到底对科举有着怎样的态度和认识?作为一部“消磨了二十多年层层心血”、寄托了作者全部才情与生命的作品,《镜花缘》究竟折射了李汝珍怎样的科举心态?通过《镜花缘》透视李汝珍的科举观,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的创作心态以及文本的思想意蕴,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科举遗落人才的憾恨
始兴于隋唐、废弃于清末,历经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改变了以血统、门第为基础的选官制度,为出身中下层的士人提供了一条平等的进身之道,也为统治阶级选拔了大量的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以及文化的发展。然而,在经历了两宋时期的发展和明代的鼎盛之后,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清代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各种弊端暴露无遗,最终只能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镜花缘》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曾被科举黜落的文士唐敖与多九公,还是被贬下凡尘后应试高中的众才女,遭际命运几乎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李汝珍通过笔下人物与科举不同的关系和纠葛,表达了自己对现行科举制度遗落人才的憾恨,说明了清代中叶的科举制度已不能有效地担负起遴选人才的历史使命。
(一)唐敖与多九公:被科举黜落的才士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讲,唐敖并不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若从道德、品行、人格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形象却是作者李汝珍刻意塑造的一位“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与徐敬业、骆宾王等举兵勤王,兴复大唐,在海外遨游期间多次救助、接济忠臣之后;入小蓬莱成仙后还要交代女儿改名为唐闺臣方可应试,“以明并不忘本之意”,体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他劝多九公将药方传世,传给林家荒年济饥辟谷仙方,无时无事不恪守着仁义良善的做人原则。他博通经史,谦谨好学,而且洞明世事,具有安邦济世的才干,在女儿国就曾有为百姓治河之义举……唐敖像当时绝大多数士人一样,本来也是希望走一条由科举而入仕的常规道路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德兼备之人,“屡次赴试,仍是一领青衫”,后来终于高中探花,却又遭人弹劾而被黜落,以天朝之大,竟然没有可以一展才华的地方,功名之想、济世之志全都付诸流水,最终只能遨游海外,遁迹仙山,这岂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剧?正如46回中吕氏所言:“谁知这样一个好人,偏偏教他功名蹭蹬,若早早做了官,他又何能到此访甚么仙山、炼甚么性呢”?因此,李汝珍之所以刻意将唐敖塑造成一位才高德馨、几近完美的人格典范,并为其安排了逃遁现实、寻仙访道的人生归宿,其深层用意就是以这一形象来寄托科举时代无数满腹才华却功名蹭蹬的失意士子的一腔郁愤。
前后两次随同唐敖父女出游海外的多九公,博闻多识,“满腹才学”,却也是一位科举的失败者:“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弃了书本”。当然,经历了科举失意的唐敖和多九公并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科举之路上执著下去,而是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放下”,“立誓不谈功名”,并最终在道德的恪守以及生命的本真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人格完善,从而表现出一种由儒向道的人生追求。唐敖和多九公的科举遭遇,形象地表达了李汝珍对现行科举制度的失望:当年唐太宗曾引以为自豪的通过科举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愿望,在清代中叶的社会现实中,早已成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的梦想。
《镜花缘》中,真正超脱于科举之外的是唐敏和林之洋。唐敏虽也是一位秀才,却“无志功名,专以课读为业”。林之洋则一生以海外贸易为业,无意科举,甚至经常对科举进行调侃和戏谑。如对明清时期每年针对秀才的岁考制度李汝珍就多次借林之洋之口进行嘲讽:“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生平又未做甚歹事,为甚要受考的魔难”?(第23回)在女儿国,林之洋被选作王妃,强行被缠足,后来放足之后,“这一畅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岁考一般,好不松动”。(第33回)总之,无论是唐敖和多九公经历了科举挫败之后毅然“放下”的潇洒,还是唐敏对科举的淡泊无欲、林之洋对科举的鄙弃不屑,都表达了李汝珍对士人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倾毕生心力于科举的人生选择的彻底否定。
(二)众才女:香草美人的寄托
与唐敖、多九公等人对待科举的淡定洒脱不同,《镜花缘》中的众才女们则表现了对科举应试的热衷和执著。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正说明了李汝珍本人对科举的热衷与痴迷,“是一个富于才学而功名蹭蹬的士子不可化解的功名情结的幻梦”[1]。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说,考察李汝珍一生行迹“现存所有有关李汝珍的材料中都没有李汝珍参加科考的点滴记载或迹象”[2]17。李汝珍没有像蒲松龄、吴敬梓那样在饱尝科举挫败的痛苦和屈辱之后才转而开始对科举的反思和批判,而是在年轻时代就毅然决然地摒弃了科举之路,以治学和著述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因此,不能认为众才女对科举的热衷就是李汝珍本人不可化解的科举情结的证明。对于众才女热衷应试的情节,我认为,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的角度去理解,似乎更切近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屈原、曹植等人是以女性作为政治理想美的寄托,曹雪芹以女性作为人性之美的象征,那么李汝珍则是以百花幻化的女性作为才学之美的象征。
众所周知,科举社会中的大多数读书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奔竞科场,其实是被科举背后的官职地位、权势富贵所诱惑而欲罢不能的。而《镜花缘》中的才女们却与此不同,她们之所以热衷于应试,其根本的动力并非科名背后的富贵利禄,而仅只是对自我才华、自我价值的一种确认和证明。在《镜花缘》所虚构的艺术世界里,众才女都得到了应试的机会,她们的才华都得到了证明和承认。而现实社会中的女子,不要说应试权、参政权,连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权都无法得到,即使再有才华,也无法得到证明和展示的途径。这种命运和现实社会中无数才华横溢却久困场屋的士人,不正有着本质的相同吗?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科学家宋应星、文学家蒲松龄,这些在不同领域才华卓异的士人,不是都曾被科举功名无情地摒弃在外吗?“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聊斋志异·叶生》)。在以功名富贵为士人唯一价值标准的科举社会,科举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仕途无望,更是对士人人格、尊严、价值的彻底否定与打击,这种满腹才华却被体制所否定的痛楚、抑郁和悲愤,成为科举社会中落榜文人内心深处积淀最深的一种情愫。虽然李汝珍摒弃了科举之路,没有蒲松龄那样久困场屋的切肤之痛,但满腹才学却不能为现行体制和文化传统所认可的沉郁,仍然是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隐衷。“世人只知‘纱帽低下好题诗’,哪里晓得草野中每每埋没许多鸿儒!”(第18回)——唐敖对黑齿国卢老秀才怀才不遇的感叹,其实不正是李汝珍对普天下所有落拓偃蹇的失意士子的慨叹吗?李汝珍以镜花世界中才女高中的幻笔,反衬了现实社会中女子无由展才的悲剧命运,寄托了对科举社会中所有才华横溢却得不到现行体制认可的文人的悲慨。鲁迅先生认为“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其芳烈”[3]209。其实,作者创作《镜花缘》的更深层动机,乃是“悲己之销沉”,不甘自己的旷世才学埋没不彰,所以才会在《镜花缘》中痛快淋漓甚至有些过犹不及地炫示自己的才学。《镜花缘》“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学问汇流,文艺列肆”的创作特征,如果仅从李汝珍本人乾嘉考据学者的身份这一角度加以解释,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借此书以确证自己未能经由科举“正途”验证的才学,方是形成此种文本特征的深层原因。《镜花缘》虽是一部风格轻松戏谑的“游戏之作”,但从深层意义上说,它与《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一样,都同属作者宣泄一腔孤愤的“发愤”之作。
二、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
那么,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为什么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选拔人才的功用?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一位富有卓识的知识分子,李汝珍以其旁观者的清醒冷静洞悉了清代中期科举制度的弊端,并在《镜花缘》中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从《镜花缘》文本来看,这种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腐败的科场风气;二是僵化刻板的八股文风。
(一)科场腐败之弊
造成科举考试不能选拔真正人才的原因是什么呢?在《镜花缘》中,李汝珍通过黑齿国卢老秀才一家的遭遇表明:考官的腐朽是造成真正的人才被遗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根本原因。
黑齿国卢老秀才的女儿卢紫萱和女弟子黎红薇的才华,曾让博学多才的唐敖、多九公都甘拜下风,也让才女唐闺臣钦佩不已,至于卢老秀才本人的才学,自然就无需赘言了。可就是这样的饱学多才之人,却榜上无名,功名无分,最后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正如黎红薇所言:“如果不识真才,所谓无心之过,倒也无甚要紧;无如总是关节夤缘,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51回)身为考官却心盲目瞽、“不识真才”,本已令人愤恨不平,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更令人痛心疾首。钱财势利、关系夤缘成为能否取中的重要因素,在这样黑暗腐败的世风之下,难怪“既无钱财,又无势利”的卢老秀才一家永无出头之日了。卢老秀才终其一生“不过是个诸生”,妻子缁氏“自幼饱读诗书,当时也曾赴过女试,学问虽佳,无奈轮他不上……”。难怪年已六旬的她还要伪饰面容、虚掩年龄,务必要到天朝女试中一试身手了。
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公正,这也正是科举制度生命力的体现。宋代的科举全面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其公平性与客观性进一步得到保障,被认为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明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万历十七年,礼部郎中高桂断言:“我朝二百余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明代科举也获得了“天下至公”的美誉。而清代统治者虽然“慎重科名,严防弊窦”,专门颁布《钦定科场条例》以防止作弊,无奈科场舞弊仍然层出不穷,科场大案接连出现。而在各种舞弊行为中,影响最为恶劣、最为人痛恨的作弊手法就是贿赂权贵、互通关节。《清史稿·选举志》称:“交通关节贿赂,厥辜尤重”。清代中后期,科场舞弊更是愈演愈烈,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关节“大小试皆有,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而科举考试一旦丧失了其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生命力。科举在清代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场腐败。《镜花缘》中黑齿国卢老秀才一家的科场遭遇,正表现了李汝珍对清代中叶科场腐败的抨击和愤恨,可以说切中了科举制度的要害。
(二)时文八股之弊
明清时期规定以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八股文成为士人博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致使“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即谓学问,此即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4]317。《镜花缘》对时文八股之弊虽未像《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但也通过幻想和戏谑之笔给予了嘲讽,从而表达了对八股文的否定。八股文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破题作为文章的开头部分,需用二句单行文字点明题意,向来被视为研习八股文的重中之重。而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多次以戏谑之笔对破题进行嘲讽:白民国学塾中,那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教书先生的高足对“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破题是:“闻其声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第22回)有位“才子”对“三十而立”的破题是:“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第66回)李汝珍“少而颖异,不乐为时文”[3]208,从他对破题的调侃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对这一死板、僵化的应试文体的反感和厌恶。
作为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规定的标准文体八股文在其发明之初,目的还是为了公平客观地选拔人才,但发展至清代,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八股文的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由于命题时间已有几百年之久,自然考题重复的机率就比较大,为防止考生互相蹈袭,考试命题越来越走向琐碎险怪,再加上这种文体本身的刻板僵化,八股文从命题到答卷都日渐走向死胡同,走向甄选英才这一初衷的反面。正因如此,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一直到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再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都对八股文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如顾炎武就曾痛心疾首地批判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5]591。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八股文的嘲讽,表现了一位超脱于现行文化体制之外的文化学者的清醒见识。
科举取士制度不仅蒙蔽了知识分子的心灵,造成他们脱离现实、心灵空虚,无暇顾及其他的营生和学问,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积习流弊也渗入到普通世人之中,使得原本古朴醇厚的世俗民风熏染上一股酸腐之气。在《镜花缘》中,李汝珍特意通过对淑士国的艺术虚构,讽刺了八股取士制度对普通民众精神的腐蚀。这个淑士国不但空气中青梅、齑菜的酸气令人掩鼻,民风世情之酸更令人难以忍受。在这个国度里,无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皆是儒者打扮。连小酒楼里的酒保也是戴着眼镜、手拿折扇,说起话来酸文假醋:“三位先生光顾者,莫非饮酒乎?抑用菜乎?敢请明以教我”;“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那位“举止大雅”、“气宇不俗”的老者,离开酒楼的时候,竟然还要酒保将未吃完的酒和酱豆腐、糟豆腐寄存好,以便下次来时享用。见到别人残桌上被人丢弃的一根剔牙杖,竟然“闻了一闻,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一个小小的漫画般的动作,揭穿了这位老者儒雅外衣下的鄙俗。
以“读书、应考、做官”为全部人生指南的科举制度,不仅异化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渗透到各行各业人们的心灵中,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金榜题名后巨大的利益,诱惑着千军万马挤上科举的独木桥,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4]194的现象。这个酸腐不堪的淑士国,以“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为训诫国民的信条,正是对科举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心理的影射。在以功名富贵为唯一目标的科举制度下,读书本来所具有的求知、益智、明理、治世等内涵已然发生了异化,成了应考做官、博取功名的敲门砖和妆点门面、卖弄斯文的粉饰剂。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难怪连酒保都要满口“之乎者也”、连那位驼背老者都要“之”字连篇了。
三、对理想科举的构想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表达了自己对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但事实上,他并非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科举制度,没有因科举制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的摒弃而走向偏激,而是表达了自己对较为理想的科举考试制度的构想,尽管还比较朦胧,但仍然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意义,充分表现了作者不凡的见识和超前的眼光。
(一)考官清廉,慧眼识才
如果说黑齿国卢老秀才一家怀才不遇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科举制度弊端的深恶痛绝,那么,作者对于天朝科举的赞美则充分表达了他对于理想的考官与考风的期望。以礼部尚书卞滨、礼部侍郎孟谟、印太守为代表的天朝考官们不仅具有一双不昧人善的“看文巨眼”,而且清正廉洁。唐闺臣这样介绍天朝科举之风:“我们中原乃万邦之首,所有考官,莫不清操廉洁况国家不惜帑费,立此大典,原为拔取真才、为国求贤而设,若夤缘一个,即不免屈一真才,若果如此,后世子孙岂能兴旺?所以历来从无夤缘之事”。(51回)科举考试内容再合理、制度再完备,若不能有效保证考官的廉洁奉公,也必将腐蚀科举考试的肌体,李汝珍虽未对考官廉洁的制度保障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设想,但已充分认识到了考官素质是决定考试公正、公平与否的重要因素,表达了对于清廉整肃的科举考风的期盼。
担任部试主考官的礼部尚书卞滨、礼部侍郎孟谟、吏部考功员外郎蒋进等人,虽然家家有才女,但都因自己担任考官而主动让女儿辞考回避。而武后听说此事后,则又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特发谕旨“钦赐才女,至期一体殿试”。对于在部试中“污卷”的花再芳等三名女子,武后也能体谅其少年要强之心,“姑念污卷系属无心之失,着加恩附入册末,准其一体殿试”。由此可见,“天朝”的科举考试既有着严格的条例规范和制度保障,又处处本着呵护和爱惜人才的原则,而这无疑正寄托了李汝珍对理想科举的一种美好愿望。
(二)诸科全备,发现各行各类人才
第24回中,淑士国一老者对唐敖道及本国的考试制度:“考试之制,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辞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这其实是作者李汝珍对理想科举的一种美好构想:以分科考试选拔各种人才,无论是文学、音韵、艺术、医学、数学、法律,只要具备任何一种专长和才能,都能有机会通过考试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进而施展才华、服务社会。
《镜花缘》号称“学问汇流,文艺列肆”,“兼贯九流,旁涉百戏”,其中所涉及到的学问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唐敖、多九公虽是儒生,但唐敖还长于水利学,多九公精通医药学,已不限于科举考试所限定的传统经学。至于百位花神,作为作者才学之美的艺术象征,更是代表了多方面的学问:史幽探、哀翠芳、唐闺臣长于诗赋,黎红薇、卢紫萱长于经史之学,枝兰音长于音韵学,潘丽春长于医药学,米兰芬长于算学与物理学,孟芸芝长于占卜之学、六壬术……而魏紫樱长于连珠枪、徐丽蓉长于弹弓,颜紫绡长于剑术,其才更是超出文举,属于武功的范畴了。在普遍重治术、轻技术、重道轻器的传统社会中,“经学”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甚至是惟一的学问,李汝珍的才学观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学的拘囿,而且延伸到了算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其眼光和见识的超前性实在令人钦佩。至于《镜花缘》的“旁涉百戏”,如以现代眼光视之,其中的射箭、蹴鞠、棋艺、双陆等属于体育的范畴,而琴棋书画则属于艺术学的范畴。
李汝珍的才学观以及分科取人的科举构想是对传统学问观和科举思想的一大突破,是极富进步意义和现代精神的。其实,“科举二字的最初含义便是分科举人或设科举人”[4]59。唐代的科举考试承隋之余绪,科目众多,设科取士有很大的灵活性。常科就分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此外还有童子科和道举科。制举的科目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根据需要随时由皇帝下制诏设科选才,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度初创时期的生机与活力。但是唐以后进士科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包容了所有科目,明清时期更是成为科举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科目,在内容上成为以四书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旨的阐发,形式上则采用了死板的八股文的形式,从最初的分科考试、选拔各类人才最终走向了单科考试、遗误人才的反面。正因如此,中国科举史上才会发生多次关于科举制度的存废之争。李汝珍关于多科考试并举以选拔各科人才的构想,昭示了以多种专业选拔人才的现代考试的发展方向,显示了作者超前的眼光与卓越的识见。
(三)主张女子应试,选拔妇女人才
在对于理想科举的构想方面,李汝珍关于女子应试的设想无疑是最富有反封建意义的《镜花缘》第七回,唐小山问叔叔:“当今既开科考文,自然男有男科,女有女科了。不知我们女科几年一考,求叔叔说明,侄女也好用功,早作准备”。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男权社会,读书应考做官向来是男子的专利,至于女子参加科举,真乃亘古未闻之事。因此,唐小山关于女科考试的这一问,真是堪称“千古一问”了。在这里李汝珍借唐小山之口对一千年来作为男子专利和特权的科举考试发出了自己的质问:为什么女子不能得到科举考试的权利?
李汝珍笔下的黑齿国集中表现了他对于女子教育及女子应试的理想。为鼓励女子读书每到十余年,该国就有一次“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其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第16回)在唐代武后当权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李汝珍又大胆地构想了一个众女应试的“旷世盛典”。(第41回)武后颁布恩诏“令天下才女俱赴朝廷试,以文之高下,定以等第,赐与才女匾额,准其父母冠带荣身”。(第42回)则进一步展示了作者对女试的具体考试程序的构想:先经县考,取得文学秀女资格;再经郡考,取得文学淑女资格;再经部试,取得文学才女资格;最后经过殿试……
极力讴歌妇女的才华,为妇女得到平等的教育权、考试权而奋力一呼,是《镜花缘》进步思想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才女应试的情节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于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女子才华的奖掖,也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科举制度的构想:科举考试应该不拘男女,给予女性以应试的权利,以发现妇女人才,这无疑表现了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意义。
在科举被废止百余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之是非功过、得失利弊的评价,已由20世纪初的猛烈抨击日渐趋于全面、客观、冷静、理性。“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6]503。如果我们不过多讨论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而仅就其所昭示的以考试方式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本质精神而论,科举的确“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7]68,科举考试传统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对于现代考试制度的完善亦颇多可资借鉴的成分。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表达了对清代中期科举之弊的认识,但并没有全然否定这种以考试甄拔人才的制度,而是提出了自己对理想科举的构想,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昭示未来的现代意识。我认为,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特立独行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毋庸讳言,就小说艺术而论,《镜花缘》尚存在着种种不足,尤其是其后半部分“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3]209,偏离了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然而,若从思想倾向上看,《镜花缘》在中国小说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它继承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小说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性精华,其所昭示的现代意识更是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镜花缘》进步的科举观,正是这部小说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
[1]王学钧.功名情结的幻梦:《镜花缘》主题论[J].明清小说研究,2010,(3).
[2]李时人.李汝珍及其《镜花缘》[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4]刘海峰.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5]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6](晋)陈寿.王昶传[M]∥三国志·魏书.长沙:岳麓书社,2002.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Li Ru-zhen's viewpoint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The Marriage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
YUAN Yun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China
〈The Marriage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not only expresses the talent of the author Li Ruzhen and the irony on the social reality,but also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point on imperial examination.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ang Ao and Duo Jiu-gong,Li Ru-zhen explains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s lost its role on selecting talents in the late feudal society and criticizes the corruption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abuses of stereotyped writing.However,the author doesn't entirely den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e to its abuses and his own abandon.He expresses his expectation and conception on incorruptible examiners,different subjects selection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As an intellec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riented society of Qing dynasty,Li Ru-zhen's cultural pursuit is admirable,and his understanding and rethink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under his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impersonal fair and estimable.
〈The Marriage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s〉;Li Ru-zhen,Imperial examination;Stereotyped writing
I206.2
A
1000-5072(2012)07-0096-07
2012-03-01
袁 韵(1970—),女,山东济宁人,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