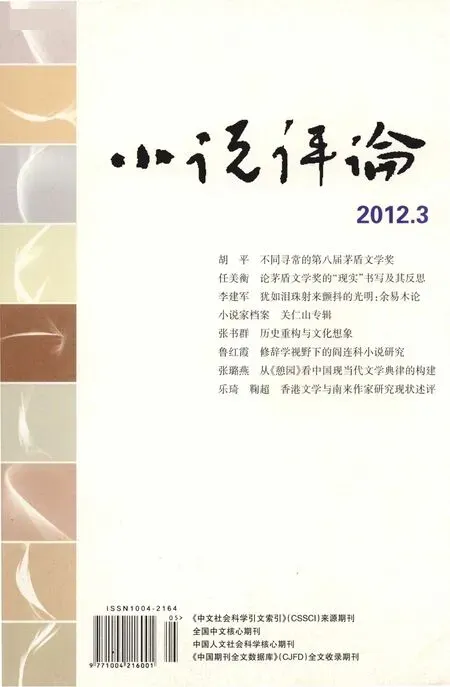论王小波小说的思想魅力
付清泉
王小波,一位在“落满蓝蜻蜓的花径”①间走过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一个崇尚理性、自由和富于奇思异想的人。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他像流星一样划过,生命短暂,却绽放出了眩目的异彩。正如著名学者戴锦华所言:“王小波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坛、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位极为独特且重要的作家。”②在王小波成就最为突出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一方面,王小波对小说写作的无限可能性的探讨和追求,使他的小说表现出对于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全面反叛;另一方面,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对西方现代派小说叙事模式的借鉴却并没有让他走上与中国80年代的先锋小说叙事试验相同的道路,与先锋派在形式的狂欢背后完全抽空了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走上文化的虚无不同,王小波的小说依然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批判。这使他的作品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文坛,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思想魅力——对奴役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一、自由主义精神
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无疑来自西方。在对“自由”的定义中,柏林的界定被大家广泛接受,他把“自由”的概念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消极自由”,更注重于个人性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宏大主题”。他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基本底线的基础上,独立而多元地追求人生的幸福。学者许纪霖曾这样评价王小波:“从思想脉络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③
王小波的自由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即“王二”系列的塑造上。“王二”群落是王小波小说一大景观,其中包括名为“王二”的“王二”系列;另一群则是非“王二”的“王二们”,如《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万寿寺》中的薛嵩,《红拂夜奔》的李靖,《寻找无双》里的王仙客等。他们虽然身份各异,但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与社会格格不入,不务正业,不守常规,思想自由,遗世独立,完全不顾世俗的功利和其它规则,努力逃避眼前的死气沉沉、平庸、一切都被政治化或计划了的世界,个体的精神自由发扬到最大限度,无限的开放、延展,追求并醉心于创造性的劳动,追求有趣的、充满诗意的生活。他们简直就是一个个自由的精灵,在王小波的文本中翩翩起舞。
在《黄金时代》里,充满青春躁动的青年王二与管制体制发生了激烈冲突,当个人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时,王二逃往深山老林,和陈清扬一起,在性爱的自由中喷发着生命的激情。即便是下山后受到专制强权的围攻,王二依然以他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虚伪的神圣与庄严,宣告了他作为反抗者的不可战胜。《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选择了离群索居的独特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2015》中,生活在未来世纪的王二,画着谁也看不懂的画,却仍然心无旁骛,如痴如醉。“王二”们可谓智力超常,有着无穷无尽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所做的事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技术,一类是文学艺术,主要是写小说和画画。他们从事这两类活动,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因为从中能够得到思维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从中能够找到神奇。他们在进行思考,进行创造发明时几乎不由自主都走进这样一种状态中,李先生研究西夏文只觉得读懂它是自己的“乐事”,写小说的王二一心沉醉在多种翻写与虚构的可能中,画画儿的王二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画别人、甚至自己都看不明白的画,觉得很快乐。正是通过这些对个体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的叙述,王小波表明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
二、反面乌托邦——对专制的反抗
人类曾经对未来寄托了无限的希冀与憧憬,用梦想构筑了一个个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但乌托邦一旦付诸实践,性质往往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的乌托邦恰恰是对幻想的乌托邦的背叛。王小波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④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中也指出:“乌托邦自身含有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的规划,魅力正在这里,同时也正是这里彰显了它自身携带的奴役力量。”“乌托邦总意味着一元论,而客体化世界中的一元论又总是奴役人,因为一元论总是强制性的一元论”⑤。
王小波对乌托邦社会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他的众多小说中,乌托邦永远是作为一个书写的反面对象。《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公共权威对私人生活空间的践踏、侵犯可谓怵目惊心:无休止的传唤、审讯、批斗、写检查、认罪占据了主人公的全部生活。《未来世界》里博士“我”因为写了舅舅的传记被重新安置:作为蹩脚中学的毕业生去当建筑工人。《黑铁时代》中,领导们都是“数盲”,而知识分子们被关进监狱一样的公寓,像狗一样被视为私有财产,彻底丧失了人的价值和尊严。《2015》中艺术家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制度化、计划化,中规中矩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无疑是一座监狱。在经过习艺所的摧残后,艺术家彻底丧失了艺术创造力,沦落到平庸得可以用字母替代的地步。
王小波不仅仅揭示了极权专制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压制和奴役,更揭示了面对奴役,人们的麻木和习以为常。哈耶克曾经指出:强制是一种恶,因为它否定个人选择与实现自己的能力与权利,把他降低为别人的工具,这就构成了对他人的奴役,乌托邦主义者想象不到他们精心构筑的理想一旦付诸实施,竟成为对社会中每一个个体从思想到肉体的奴役和迫害,而它的吊诡之处在于:奴役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奴役他人,他倒诚心诚意地把自己看作救世主;受奴役者并不以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是走在天堂之路上,心甘情愿地按照奴役者的设置生活。比奴役人的生活方式更恐怖的是对人思想的奴役,是建造关押思想的枷锁和牢笼,让少数人的思想信仰灌输成为全民的信仰,让每个人放弃个人的思想,让思想国有化、全民化、一体化、专利化。⑥
王小波不仅通过描写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揭露了乌托邦的虚伪及专制的本质,更通过其小说中的人物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反乌托邦社会思想。他的“王二”系列人物形象,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无一不是对极权和专制的反抗。《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面对专制,以性和游戏对之消解;《白银时代》中,王二宁可“在剧痛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好得多;”⑦《未来世界》里,艺术家舅舅一直都在逃跑;而《红拂夜奔》中,红拂用生命实践对了专制和无趣的逃离。
王小波通过乌托邦这个末世神话揭示出了我们民族历史记忆中的荒谬的生存体验,在叙事者幽默和反讽的叙述中,对这段荒唐历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站在了一起,显出作家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
三、自由女权主义——王小波的女性观
王小波笔下,出现了众多个性鲜明、独具异彩的女性形象。陈清扬、小转铃、线条、红线、红拂、无双、彩萍、鱼玄机、妖妖等等,她们自由、奔放、言行出格、不守规范、无法无天、同“王二”们一样叛逆,甚至比王二更充满着生命的自由气息。她们不是单个的出现,而是几乎充斥了王小波的每一部作品。她们独具异彩的形象,鲜明地表现了王小波的女性主义观。
在传统男性笔下,女性形象往往不是天使,就是妖妇。纯洁美丽的天使,是男性心中的理想女性。但是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这实际是变相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对女性来说,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⑧而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则被描写为妖女或者恶魔,受到唾弃。无论天使还是妖女,都毫无二致地表现了对女性的压抑和歪曲。
王小波笔下的女性,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是一群个性张扬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诸如贞节、温婉、恭敬、顺从等对她们的束缚了,她们甚至没有所谓清白的名声:陈清扬被称作“破鞋”;彩萍被宣阳坊众人称为“绿毛妖怪”、“绿毛婊子”;鱼玄机是风流成性的女道士;无双是一个“女霸王”;红拂是“淫奔”的歌妓;红线是毫不遵守教化的“蛮婆”。她们甚至满嘴粗俗言语,动辄“操你妈”。但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因张扬的个性,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她们首先自然、率真、充满活力,藐视制度,是规范、规则的破坏者和嘲笑者。她们的生活不是那种被规范和权力设计好了的常规而又平庸的生活,而是一种充满新奇和极大自主性的生活,是真正属于自我、个人的生活。她们是乐趣的制造者,是创造发明生活的人。《黄金时代》的陈清扬,以自己是破鞋里面最漂亮的为自豪;她和王二一边“出斗争差”一边发展“伟大的革命友谊”,也就是说,几乎在众目睽睽之下,尽情享受男欢女爱——那个时代被剥夺掉的、因而也是最神奇的东西之一。我们惊奇地发现:女性在非常时期和非常情境下竟然能这样地我行我素、继续着她的主体性追求!《红拂夜奔》中的红拂,从杨素的府邸逃出,又随李靖逃出洛阳,奔来奔去,寻找的也是有趣味的生活。她最后的自杀,与其说是殉夫,不如说是对无趣无性枯燥乏味的长安生活的反抗。
其次,她们不仅和“王二”们一道追求着自我的主体性并反抗着社会对人的奴役,她们更反抗着几千年男权社会积存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她们因此更富有主动性,甚至往往大胆得让人咋舌。《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小转铃、线条、小孙,《万寿寺》中的红线等在性问题上比男“王二们”更主动,更野性,更加肆无忌惮,并且常使男王二们变得被动、窝囊。在权力关系中,她们常常是男女关系的权力主体,《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与X海鹰之间,X海鹰是支配者,王二是被支配者,《我的舅舅》、《2015》的男女权力关系也都有此特征。《万寿寺》里的薛嵩显然有男权中心的行为倾向,但这种倾向在实施过程中却总受到红线的嘲弄,戏耍和否定,处处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作者借此对儒家传统中男尊女卑的落后的伪善道德伦理进行了无情挖苦和讥讽。
王小波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寄托了相当多的美好理想和人生价值,但并不表明,他是一个激烈的女性主义者。在《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里,他坦言:“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⑨
总之,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流露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批判,其自由主义精神、对乌托邦的批判以及自由女权主义等思想,无一例外地传达出了反抗奴役的主题,从而独树一帜,呈现出迷人的思想魅力。
注释:
①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
②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J],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
③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④王小波:《〈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王小波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⑤(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⑥(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⑦王小波:《白银时代》,《王小波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425页。
⑧(美)吉尔伯特、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耶鲁1979年版,第25页,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
⑨王小波:《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王小波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