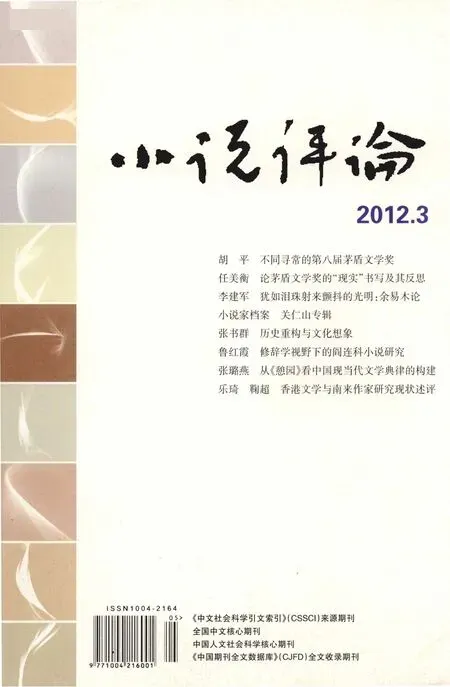论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书写及其反思
任美衡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领域,更出现了“勃发”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已出版了3万部,还不包括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产品,相关的长篇小说奖项也就层出不穷。这些作品广泛地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类题材,当代题材尤其独占鳌头。①就以具有象征意义的茅盾文学奖为例,当代题材的作品占了19部,达50%,这种比例深在地体现了茅盾文学奖乃至长篇小说对“现实”书写的情有独钟。不过,由于水平参差不齐且争议较大,甚至出现了“评价的悖论”。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茅盾文学奖究竟如何审视“现实”,书写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将会是怎样的?在此,我们将循此路径,辨析它的优势、特色及难以规避的局限,从而尝试理清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势。
一、茅盾文学奖的“现实”哲学及其实践
无论就反映的广度、力度还是深度而言,长篇小说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是空前积极的。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阶级、家庭等不同层面,从政治家、商人、教育工作者、改革派、白领、公务员等各类人物,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申办奥运会、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社会题材到普通的日常生活,长篇小说以无可比拟的巨大容量,全景地纪录了当代中国不平凡的崛起历程及精神变迁,并形成了创造性的现实哲学及其实践形式。茅盾文学奖对“当代题材”的遴选,虽然争议不少,但也代表性地聚焦了不同领域的优秀长篇小说,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度分析的文学范本。通过它,我们庶几可触摸到当代中国书写的若干深度问题。
(一)直面现实的“在场”精神。无须讳言,在各类题材的创作中,当代题材遭到的“批判”最多,或认为粉饰现实,或认为力度不够、或认为缺乏哲学意识,等等。这种批判有其合理性,也触及到了事实的部分真相,但显然也忽视了当代题材书写的难度及其复杂性。由于未拉开审美距离,也由于创作主体知识储备、才情和视野的有限性,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反映变化的、持续展开的和波澜壮阔的当下生活,就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之,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由于身处其中,是不可能彻底地打捞历史的本质的,也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不过,面对这种巨大的“未知性”,许多作家还是秉承着为时代立言、为百姓鼓与呼、为文学献身的神圣精神,前赴后继地投身于社会变革,直面现实的丰富和残酷,用青春和激情、用血与火、用爱与恨抒写着中华民族的传奇。茅盾文学奖也在评奖条例中特别指出,“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从而不断地张扬“干预生活”的锋芒。从莫应丰“冒死写于文家市”之《将军吟》,到《抉择》《都市风流》“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再及刘醒龙的叙述民办教师之《天行者》等作品,无不表现了茅盾文学奖深刻的“在场性”。
当然,这种积极的“在场”精神所包括的内容、方式及其原则是多样的。首先灌注了《史记》的求实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以匍匐的姿态,贴近大地,关怀人们,本真、混沌、苍茫原生状态地呈现日常生活;这种还原,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是生活现象的还原,是生活整体的还原,是生命情感的还原,是文化精神的还原,如《秦腔》通过对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的鸡零狗碎的泼烦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就有如茫茫的流水,又犹如茫然的浑然一体的大山,整体性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汤汤水水、草草木木,似乎不加任何修饰,原汁原味,原生状态。从而隐蔽地、坚硬地切入现实。②《湖光山色》也通过回乡探病、自主结婚、婚后的平淡生活、怀孕生儿、暗遭算计、惨遭侮辱、旅游致富、感恩回报、打官司、开办公司、村主任选举、引进外资、性情初变、夫妻离婚、犯罪被捕等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了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以及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③它们努力地夯实着长篇小说的现实哲学。其次,逆市场经济之潮,捍卫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如《推拿》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歌颂了他们那种执著、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④都表现了茅盾文学奖坚定而分明的审美立场。再次,这种“现实的姿态”还是主动的,它不是被动的顺应,也不是无奈的等待,而是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energetic”:在批判地审视生活之时,更多地强调现实的逻辑性与可塑性;讲究现实的原生性,在良知和道德的挑战中,直逼芸芸众生的生存之真。如《将军吟》的彭其,果断勇敢,足智多谋;面对着黑暗势力的多次利诱逼迫与软硬兼施,他宁死不屈,依然保持高洁品质;……他从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肉体的折磨丝毫没有打垮精神意志,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毅力,始终坚信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光明的一天即将到来。⑤
应该说,“现实”的内涵是复杂的,茅盾文学奖对这种姿态予以了“绝对的”肯定,也深化了文学应有的担当精神。不过,这种姿态也会有缺陷的,由于更倾向叙事的全景性,反而削弱了它在某些方面的深刻性与特色性,甚至会导致“事实的罗列”和“经验的匮乏”之现象,也使其对于现实的反映不自觉地打了折扣。
(二)深刻地把握时代本质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和概括了时代的本质,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长篇小说对当代题材的书写来看,都贯穿了“爱国主义与改革创新”的基本脉络,都凝聚了崇高的奉献精神与牺牲意识,也表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内忧外患之时,无论担当什么样的代价,承受什么样的委屈,他们也无怨无悔,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之中。如在《东方》中,使人感到有一股强劲的暖流奔腾回荡,一阵阵拍击着人们的心扉——这就是渴望为人民为祖国而献身的英雄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这种献身精神产生于22年人民革命战争的火的年代,而灌注于人民民主政权的艰苦建设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中国50年代令人难忘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奔流在《东方》的英雄人物血管之中: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纯洁的情操,崇高的理想,对光明带着执拗的追求,对明天怀着美好的憧憬。⑥这一切,都构成《东方》每个英雄人物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灵魂本质。如郭祥,为了保家卫国,奋不顾身地来到了朝鲜前线;当因为伤病而无法重返前线时,他决然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在家乡任县委书记,继续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他人物如郑子云、陈咏明、阎鸿唤、岳鹏程、孙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陆承伟、金月兰、秋玲等人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也完全地褪下了卡里斯马英雄的炫目光彩,但他们却通过行动,义无反顾地担当了时代所赋予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在不见硝烟的商场上,成了充满沧桑、性格复杂的平民英雄。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发挥着无穷的智慧,他们不仅敢于反抗陋规陈习,反抗自身的惰性因素,反抗一切的阻碍力量,顺应时势,努力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理顺、预测并推进社会的发展趋势,努力增强时代主潮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改革创新不仅“打乱”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权利分配,而且还“破坏”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然而,这种“阵痛”不仅使中国人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更赢得了发展的能力。茅盾文学奖也深刻地关注并剖析了改革创新带给中国人的综合效应,这从诸多的“授奖词”可见一斑,如《秦腔》所说的:透过疯子引生的眼睛见证了清风街近二十年来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清风街的大户白、夏两家的兴衰成为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农村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⑦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时代的发展前提的话,改革创新则成为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茅盾文学奖由此借鉴、深化并创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原生态地反映出来。如孙少平、暖暖等人在时代的大潮中的颠簸流离及其奋斗,《钟鼓楼》围绕着“北京市民社会生态的群落图”,表现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革新的诸多矛盾,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者日常平凡的工作岗位,不论性格、经历、命运、业绩如何,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捍卫者,都体现了大无畏的主人翁精神和历史首创精神。
(三)社会主义新人的“动力”机制。在“祝词”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活动。”⑧金东水、孙少安、李高成、史天成等人多方面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形式及其内涵,尤其是“乔厂长”之后,“现代化的创业者”则成了新人的主流范式,如李向南、刘钊、陈抱帖、杨昭远、杨秋英、李辰等人。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开拓精神、革新精神、务实精神和理想精神;他们是新时代产生的,是四化事业的干将,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他们都折射出了某种时代精神,甚至还达到了人物的心灵同时代精神的交融,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的印记。而田保耕、孙少平、吴明雄、段启明等普通人虽然没有李向南们的叱咤风云和咄咄逼人的锐气,也没有以变革天下为己任的雄图大略,多是为着改变个人的命运,不自觉地卷入改革的大潮。他们以各自大小不等的能量,为大潮推波助澜,有时也难免呛几口水,甚至被大潮中的旋涡所吞没。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无不折射出改革大潮的光辉。⑨这种探索虽然后来遭到了质疑、批判乃至不乏内在的困境,然而,却迎合了社会对英雄人物的急切呼唤,因而在人们的期待中风起云涌。
社会主义新人预示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使现实书写不再碎片化、无序化和低俗化。由于社会主义新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尽管遭受了现实的磨蚀,但他所焕发的理想主义却契合了世界文学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及其书写,也契合了整个社会对人类的信心。从孙少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进步的艰难步伐和人之解放的可持续性;从李高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维系整个社会存在的正气和良知。柳建伟在《英雄时代》中慷慨激昂地提出:工人阶级永远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永远不会等于零;同时又气壮山河地描绘了那些下岗工人绝不甘心于命运的摆布,而是逆势而动,团结起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办起了“都得利”商场,与命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搏击与抗争,不仅找回了自信,而且以新的面目、新的精神和新的智慧成了别种的社会主义主人翁。
社会主义新人反映了社会的基本面及其丰富性。社会中所存在的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俗、真善美与假丑恶、进步与反动等质素附丽在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上,并通过生活的搅拌呈现出来,如“出淤泥而不染”的暖暖。黑格尔也说过,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助矛盾对比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新人仍能坚持住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生动和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环境中能保全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⑩如《天行者》就既呈现了民办教师的艰难并歌颂其无私的奉献精神,又站在整个历史发展和社会层面去思考问题,把乡村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延伸,从某种角度说是为默默奉献的一个群体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通过社会主义新人,文学走出了现实的迷失和焦虑,真正地有了是非之心,有了批判性的眼光,有了辩证的态度,有了综合分析现实的能力,有了提纲挈领的哲理性,也为我们对未来的形象构型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性。
(四)问题及其应对。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各种社会问题为视阈,长篇小说努力抓住“现实”的诸多症结,全方位地寻找文学与现实的各种关联,并生动地建构了自身的现实哲学。概括地说,茅盾文学奖以中华民族之崛起为主轴,以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等社会变革为关节,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存在,来凸显现实的平均值及倾向性;有意识地选择重大题材,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关于现实与历史、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与现代化文明的深刻思考,发掘具有普遍意义或重大社会价值的问题。⑪
同时,在原生态的叙事中,又把家长里短、世态炎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这些牵涉着个体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予以“重现”。在《钟鼓楼》中,我们会发现詹丽颖、慕樱、韩一谭、李锴、潘秀姬等小人物在复杂的人生中所面临的诸多小麻烦之时,那种无奈、痛苦、惶惑,或者是爱情遭遇到挫折,或者是事业的平凡化乃至琐屑,或者是邻里之间的关系遭遇了某种障碍,或者是升学成为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等等,他们牵动着小四合院里每个人的神经,以卑微的生存状态显示了社会转型在缓慢而不可抑制的撕裂中所联系的千万个家庭之存在。
茅盾文学奖还以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如国企改革、司法腐败、环境污染、三农等具体问题为对象,发掘在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有些症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被转化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它启迪着人们对现实的深刻关注,如《浮躁》《骚动之秋》;有些则源于不同的条件而凸显出了问题的不同方面,如《你在高原》《推拿》;有些则穿越了现实的具体性,形成了不断重启问题的哲学,如《蛙》《一句顶一万句》《都市风流》,茅盾文学奖力图以此担当起对现实的承诺。不过,囿于现实的限制,它们也错过了、淡化了、避开了许多亟待迫切解决的问题,如当代的移民潮、同性恋、自杀、毒品、恐怖主义、失业、中国的乡村贫困,以及中国城市居民的信用与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也削弱了它对现实的针对性与有效性。⑫
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势中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总的方向及趋势是稳定的。长篇小说由此深深地嵌入了现实,书写着现实的命运,积累了审美现实的丰富经验,并再次严肃地昭示我们:生活不仅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更是创作永不衰竭的动力。
二、现实书写的限度、难度和不确定性
虽然当今的文学创作比较自由,但由于与现实的过度切近及其他复杂的审美关系,茅盾文学奖仍从多个方面表征了现实哲学及其书写的局限性。
(一)潜在的理念化倾向。在批判上世纪末的“伪现代主义”时,有人曾客观地评价过这种理念化的缺失:以主观自我作为表现主观对象的同时,脱离客体的理念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有些艰深莫测的观念来自某种哲学体系,自然与创作的主观意识缺少真正的沟通,这是它们的致命弱点,所以为了增强理论意识的可感性,他们不得不稀释和淡化理念的明确性,赋予理念以恰当的感性符号和形式载体,从而走向象征。⑬
不过,与这种“伪现代主义”在类似西方社会情境的幻想中寻找“情感的对位,主观感觉化,时空背景的淡化、虚化,故事的被情节化,结构的零散化”等象征体系不同的是,茅盾文学奖的理念化主要表现为: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如《沉重的翅膀》《骚动之秋》《英雄时代》《湖光山色》等作品,尽管叙述各异,但核心的内容却呈现出“原型化”的倾向,这就是:改革开放在各个层面充分地展开,引起了各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冲突;由于来自于党的伟大力量及其方向性指引,社会发展尽管遭遇了巨大的考验和挫折,但仍然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处身于其中的人们,与时代共振着,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蜕变,有的沦落,有的升华,有的在平均的水平上进行充分的自我演绎,总之,都成了社会主义事业会延续千秋万代的有力“证明”。②对生活的图解冲动。生活是动态的、复杂的、质感的,然而许多人都批判地认为,不少长篇小说则难免有过度戏剧化、简单化和修辞化的嫌疑,甚至为了史诗的规模,有意识地弃置了生活的“细枝末节”,把所谓的重大现象“硬块化”地拼凑,以便实现某种崇高或者伟大的目标,以致于本末倒置,生活被裁剪,成了国家意志的证明了;呈现的都是粗糙化与框架式的宏大叙事,表现的只是历史的骨骼,鲜见毛茸茸的生活的血肉。③未能摆脱传统的制约,直接在著作中进行情节之外的哲理性的阐发,如《抉择》等作品所出现的理念化的语言,等等。
公式化使获奖作品在获得深度模式的同时又失去了它的在场性、原生性、本真性,充满了“隔阂”和“障碍”。阅读它们,仿佛是透过纱幕来接触生活,却往往缺少了置身其中的滋味和震撼,缺乏应有的生动、活泼及灵性,带来的是说教和冷漠,甚至潜在地拒我们于现场之外。
(二)对于负面价值欠缺必要的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是多样的,但却从不同方向潜在地建构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茅盾文学奖而言,“条例”先在地规定了评奖对象必须要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不过,在具体的评奖实践中,由于评委会对这种“主旋律”的理解总是歧义丛生,从而也就无形地制约了部分获奖作品在价值方面的拓展;尤其是在负面价值的取向方面形成了巨大的空洞,如对“丑的、恶魔般的、扭曲的、奇形的、怪异的、非规则的、癫狂的、厌恶的、阴森恐怖的、假的、恶的、颓废的、拜金的、粗俗的、歇斯底里的、龌龊的、残忍的”价值基本上予以拒绝了。
这些价值的缺席,使茅盾文学奖在合理性和正当性之外,无端地丧失了充分把握现实的有力的杠杆与支点,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审美的“偏执”:如对现实的反映单向度化,丧失了对现实的形而上之思,也导致了现实的“非原生化”,如《檀香刑》因暴力叙事、《私人生活》因私人化写作而被拒于茅盾文学奖之外,为此,茅盾文学奖的气度、包容能力和美学眼光也遭到了诸多人严厉的批判。
(三)道德主义的局限性。作为国家文学实力的象征,长篇小说无疑有着特殊的道德担当与伦理判断,如对人性的描写是否符合逻辑,对个体性的追求、对性的文化思考、对家庭的变迁是否符合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如何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格理想,是否在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中指向终极关怀,等等,这些都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积淀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道德构成。
不过,考察它对于现实的审美把握,也不乏这样一些道德难度:①情感化。在作家们的主体精神里,非常明确地凸显出了某种道德化的情感立场——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⑭如路遥就把孙少平对现代生活的追求置换为对惠英的追求,再置换成了对责任的担当,颇有“铁肩担道义”的阵势;对反面人物的否定,也欠缺深入的灵魂挖掘,从而导致了它的虚化,也导致创作的符号化与概念化的盛行。②道德本身具有的相对性。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和立体的,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是非、善恶、好坏的道德区分和臧否;在社会转型之时,视点的迥异也使道德主义的表现千差万别,如《你在高原》就纠缠了宁伽在动荡年代的酸甜苦辣,他的经历、思考和行为往往与时代的道德价值发生着强烈的反差;《蛙》中的姑姑在人性与政策之间不断游移,接生与杀生在她身上形成了奇妙而疼痛的组合;《英雄时代》的陆承伟尽管自私、贪婪、没有责任心、私生活不检点,但又充满了野心,懂得用适当的权力为自己牟利,也不讲究规矩,尽管出身于红色家庭,但他却把自己划在资本家之列。他是复杂和矛盾的:从旧的传统来看,他是应该遭到唾弃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魔性”的人物;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他却恰恰拥有了现代人的优秀质素,能够顺应潮流,应势而上,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时代的英雄。因之,当作者试图用道德主义来判断他的行为之正确和错误时,却又面临着这样的“二难”:在情感上,他是该诅咒的和否定的;在理性上,我们却又无法为之定论。③道德判断的有限性。由于道德判断常常基于某个具体的人物和行为,当涉及超乎日常经验的更高的更为深邃的终极关怀时,道德判断有时又显得力不从心。⑮茅盾文学奖致力于人们在实践层面的道德对抗性,所以就不自觉地把人物划入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中,而恰恰忘记了对“人之为人”的终极追问。如人性是否生来为恶?假如人们掉进了地狱,该如何得到拯救?我们对他究竟是怜悯还是憎恨?当代社会该如何去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概而言之,这些问题曾不断地削弱着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制度、文化、心理等层面冲击着文学奖的合法性;不过,这些问题也在不断地开启诸多机会,如茅盾文学奖就不得不创新方式来重新把握现实,《秦腔》《暗算》《一句顶一万句》的获奖就说明了这点;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与时俱进,未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就能够真正地提升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此而赢得永生。
注释:
①在此文中,当代题材作品特指反映共和国历史的文本。还有一些作品虽然也涉及到了1949年以后,但“当代”的内容却并非作品的核心部分,因而不算是此文所说的“当代题材作品”。
②雷达、韩鲁华等人在《秦腔》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3日。
③参见黄娟的《理性反思,寄予未来——〈湖光山色〉导读》,见《我想留下你的脚印》,http://blog.stnn.cc/zhjangel/Efp_Blog.aspx。
④廖翊:《〈天行者〉等5部长篇小说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新华网2011年8月20日,http://gz.jxcn.cn/news/2011-08/20/content_654285.htm。
⑤参见《〈将军吟〉,崛起于血雨腥风的年代》,http://www.jyszgh.gov.cn/reading/go.asp?id=4539。
⑥王春元:《浅谈〈东方〉英雄人物的个性化》,参见王晓梅主编的《记忆长河:怀旧七十年代(1970-197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⑦见《秦腔》的封底“简介”,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
⑧政治部文化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文学艺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⑨牛运清主编:《新时期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6页。
⑩【德】黑格尔:《美学》卷一,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2页。
⑪王达敏:《新时期小说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⑫吕庆广,王一平:《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目录”。
⑬张永祎:《文学在理念化倾向中的失落》,《人民日报》,1990年4月24日。
⑭洪治刚:《底层文学:未完成的讨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⑮汪正龙:《文学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超越——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一个悖论》,《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说明:此一小节“道德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借鉴了本文的观点,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