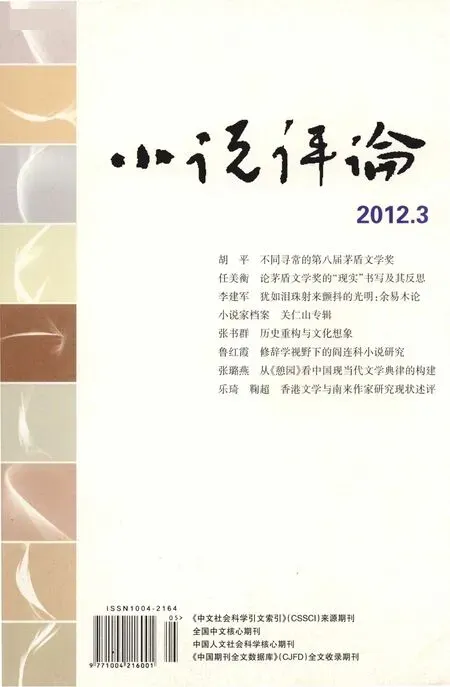在地为泥,在天为翔:自述
关仁山
春天来了,土地知道。面对土地,该付出怎样的爱……
我爱土地。我于1963年出生在冀东平原上一个普通小村庄。我从小喜欢故乡五月的麦地,时常钻进麦地里玩耍,搓麦粒,闻麦子的味道,那是一种享受。土地是沉重的,有时,还带有禅一般的明澈。我十岁那年,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棵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母亲领个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给我算了一卦,算着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瞎子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瞎子给了我一颗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我在作品里多次对小麦进行描述,但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说到土地,它就是点燃我心灵的火焰。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神小,可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因为这棵枣树有一个树杈无法锯掉,工匠就给他雕了一根拐杖,连安手里多了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我的眼前激起了种种幻象。传说中的连安手里的“麦穗儿”,总是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就找到了力量的根基。
我想起了那一年麦收二叔的死。二叔有点倔,喜欢种地,本来子女都到县城打工了,可以搬到城里去,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靠土地了,可他还是想种地。我的一个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转”,几次给他做工作,他都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谁也说服不了他。说到土地流转,他有好多担忧和困惑。二叔耕种土地,一头牛,一架铁犁,牛拉着犁,二叔扶着犁,一点点翻动着土地,配合是那样默契。他家的粮和菜都能自给自足,过着与“市场”无关的小日子,自得其乐。二叔对我说:“别看你在城里住高楼,坐汽车,山珍海味吃着,我不眼热,哪如我这一亩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麦收,二叔赶着马车往麦场拉麦子,二叔拉的麦子在河岸上与河南来的收割机相遇,不料马惊了,二叔从高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头朝地,后脊椎折了,当场就死了。这是咋样的交通事故?二叔尸体放在丰南县城医院,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后来二婶找到我,我拖托在乡政府当书记的同学给调节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终于入土为安了。这件事情给我震动很大,二叔满可以离开土地的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是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但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面对土地流转大势,他忧心、愤怒,成为农村变革的“钉子户”。这类农民身上,自私、狭隘、固执,把土地当作命根、没有长远眼光的传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像梁三老汉、许茂、这样勤劳而糊涂的影子。我的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农民。我有一种担忧,如果都是这样农民留在土地,现代农业从何谈起?
那年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我给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纸。二叔下葬的第二年,二叔没有埋在我们家族坟场,我顺便到二叔墓地烧点纸。二叔的坟头上,有金黄的麦穗儿铺着,二婶说二叔死在麦收,坟头要铺满麦穗儿。坟前还摆着酒菜、水果。二婶和堂弟用土把坟堆填高,用铁锨挖一个园形土块儿,做一个坟帽儿放在坟尖上,压了几张黄纸。二婶跟我说,他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过来给二叔说说话。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说话?二叔能回话吗?二婶说她能听到二叔的答话。我淡淡一笑,也许是二婶的幻觉吧?这是我写《麦河》中瞎子白立国与鬼魂对话有一个启发。小时候,我对乡村坟地非常恐惧。可是,这些人都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人。他们曾经有血有肉,有叹息,有歌声。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滦河畔的白羊峪村捡石头,那里河床的石头很有特点。听说到这样一个风俗,村里有点德性的人死了,就给捏一个泥塑立在坟头,这个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传神。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说法,让我对乡村的生与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们打着呼噜,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为后人祈祷,饶恕一切,超块了时空。他们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历史的复活,也是人性的复活。我对这个秘密感动着、鼓舞着。这个小小民俗,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但是,这种尝试也让我惶恐不安,读者会接受吗?
我小时候,农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没有啥娱乐生活。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但是,一走到田野里去,看见了广袤的土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土地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让人感奋、自信、自尊,给心灵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气。正是这方土地、这条河水滋养,才有了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瞎子白立国与桃儿,他与曹双羊,他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鹰嘴里叼着一根麦穗儿飞翔。苍鹰是麦河的精灵,麦穗儿是土地的精灵。这让我很兴奋,最初,瞎子只是书中的人物,我想用鹰的视角来叙述全篇。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因为我把握不好鹰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就重新启用瞎子来叙述,让老鹰虎子充当瞎子的“眼线”,替瞎子洞察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熟悉鹰,也熟悉很多艺人,包括乐亭大鼓艺人,我还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用工业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一切都在瓦解,乡村变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份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瞎子白立国呼唤乡间真情,抚慰受伤的灵魂。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瞎子白立国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寄托着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远与弱者站在一起,让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失地农民得到安慰,找回属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想他的力量来源于土地。我的心情与农民种地一样,是在惶惑、绝望、希望中交替运行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
有人问我,为什么执着地写着农民和土地?我想,描写农民和土地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需要它。创作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都是孤独的,面对土地,我们有巨大的孤独,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想起了我在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中有一段描述:“在情感上她是失败者,岁月耗尽了她的全部激情,遮住了她的视线,是田园又把一切补偿给她。自己一意孤行地热衷于土地是对的,好好感谢它吧,感谢啊!她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像个淘气孩子,双手深深地插进蓬松的泥土里……”
农民与土地。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国事”。我们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今天的农村了。我们的农业文明和农业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农村题材文学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今天,农村是农耕文化气息、现代城镇工业气息和科技信息杂揉融合阶段,农民艰难地行进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半路上。现实是我们文学的土壤,文化则是文学的精神。如何把握今天的农村生活?今天的农村生活五光十色,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我们的创作如果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其活力和价值就会减少。但是要表现好这个时代,还要多一些真思考。我想,要把握今天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就首先要深入下去,但是光有深入和贴近是不够的,走马观花式的贴近只能使我们茫然。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呢?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作家应该怀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农民每天都在投入一种新的生活,不仅要凭借好政策的外力,更需要战胜自身的障碍。这障碍包括历史渗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们就是要揭示这种历史复杂状态。如果用同情式和批判式的态度都会失之偏颇。通过农村变革的具体事件来分析,透过这些事件前就能洞察到那条时缓时动的时代之河,可以感受到沉重的历史同改革浪潮的剧烈冲突以及相互制动。
台湾作家陈映真说过,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我们的农民兄弟不仅有物质需求,更有精神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来自生命本身的呼唤。他们怎么表达自己的意志?怎样表达他们的理想?这就让我们重新提起现实主义与理想的问题。今天面对乡土应该呼唤这种理想。我们企盼给乡土以美好的环境,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乡村还有什么希望?时代还能进步吗?我们不能否认,当前文学有嘲弄、亵渎理想的倾向。当然,我们崇尚的理想不是脱离农村实际的“乌托邦”,真正的理想应该建立在现实的深刻真实的洞察上,只有真正透析了“三农”问题,在现实揭露与批判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理想。盲目的理想可能使沉重的问题被消解,理想就显得廉价和泛滥。在这里,现实主义的人道力量和悲悯情怀非常重要了。深沉的感染力和超越精神,是我们所渴求的。
创作时使我心情苦恼,因为我认知农民和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有人说苦闷是我们创作阶段上的否定过程,自我否定会带来突破吗?农村题材作品的市场有问题,我们不应该全怪市场本身,还要在创作上找原因。文学发展到今天,好多艺术探索到尝试过了,作家依照自己的惯性在写,刊物依照自己的惯性在编,读者那里还在惯性在地读。在这种惯性中,文学更加多元,读者越来越少了。现实世界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大量信息的强刺激,不久就来一个震惊,每个作家都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写作,就少不了要思考,文学面对时代,面对市场,面对各种诱惑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市场使我们更加理智和清醒了。我不再相信过去的一些虚幻的东西,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有了一个恰当的评估。我不再梦想虚幻的东西,更加实际了,我只是想根据自己对生活不断变化的认识,用我能够驾驭的艺术手段,为喜爱我作品的读者写作。市场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东西,绝不能说面向市场就可以快捷和草率。市场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市场是对普通读者感受力、理解力和审美能力的更大尊重。我们乡村的生活在改革中变化很大,农民的内心都经历着从没有过的震荡,他们都在思考,他们有时在借助阅读思考,他们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面对喧嚣、复杂的时代。我的小说情节还应该再复杂,复杂得令人炫目。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种兴趣,一种自信,重新发现土地的秘密。我们态度首先是真诚的,最后体现在艰苦的劳动中,体现的独特的眼光上,体现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艺术思考上,体现在创作勇气和艺术魄力上。我们有理由对明天的创作进行期待。苦难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们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内心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才会写进人的心灵深处。文学精神在于共享许多价值。一切文明层面上的努力,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万万不能写丢了这种美好。美好是精神的,温暖而高远,显示出某种超越和飞翔的品质。
有人说,写作本质上更接近农业的劳作。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春天来了,土地知道。该耕种了,我们应该付出怎样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