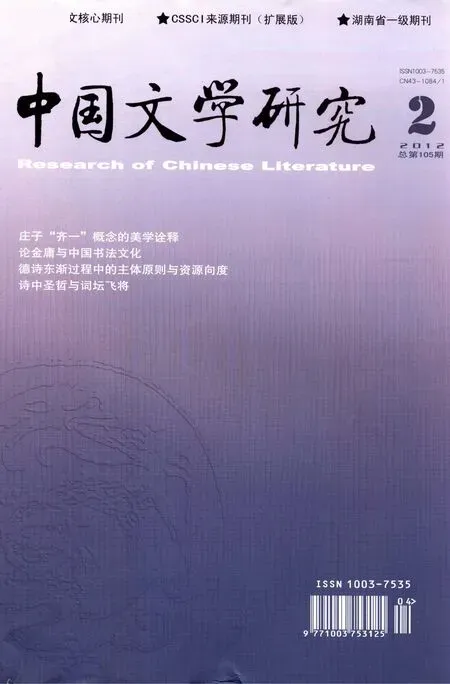对寻根文学中文学性批判之不足的反思
——以《爸爸爸》、《小鲍庄》为例
刘淮南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山西 忻州 034000)
一
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说,1985年前后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是倍受人们关注的一次创作思潮。就这次创作思潮中所涉及到的作家和创作内容而言,都是广泛的和空前的,自然,它也将以其所取得的成绩和暴露出的问题而引起人们的一再反思。然而,如何反思“寻根文学”之不足,却依然是存在于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一个明显的问题。
我们知道,就文化寻根思潮的创作起因而言,既与当时兴起的文化热不可分割,也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后,必然要求对之的接续,更何况,世界发展的大势也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上,影响到文学创作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上。而且,就历史来看,从来就没有离开文学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文学。可以说,这是寻根文学产生的外部原因。而再从文学自身来说,长期以来对政治性和道德性的强调,使得人们对文化问题不能予以正确的对待,政治性和道德性对文学性的挤压,使得本来很正常的文化内容也在文学中受到限制,自然,当政治性的情绪平静之后,人们必然要求在文学中对文化问题的继续表达。更何况,政治反思必然要导致文化反思,而文化反思也必然应当在文学中有所反映。
因此,当一些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了有关的文化问题时,当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此文被认为是“文化寻根”的“宣言”)、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等文章明确喊出了文化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时,文化寻根作为一股强劲的创作思潮便在中国的文学界蔓延开来。应该说,文化寻根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取得的创作实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中都是少有的。但是,当这一思潮过去之后,我们又遗憾地看到,寻根文学其实算不上是一次成功的文学实践,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寻根作家对如何建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认识并不清楚,在于对文学、文化的感受与理解上存在着迷惘,而且,这种迷惘对寻根作家来说又是内在的,这种内在的迷惘在寻根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也是非常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寻根文学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遗憾的,因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在承认寻根文学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看到它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寻根文学以及未来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着益处的。为此,这里就寻根文学的两篇代表作进行分析,通过其文学性方面问题的解剖来求得对文学发展的认识。
大家知道,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不可小视的代表作。说它们不可小视,是因为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的劣根,从文学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的惰性进行了批判,因而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换句话说,也正是《爸爸爸》中塑造的丙崽这一丑陋形象和《小鲍庄》的在不动声色中对“仁义的堕落”的暴露,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所以说,它们均是文学批判性质的文本,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在承认韩少功和王安忆所取得的“文学批判”成绩的同时,却又应该看到它们在“文学性批判”上所存在的不足,或者说它们并没有达到文学性批判。而以往的批评还没有在此方面进行过应有的区别和分析。
在《从文学批判到文学性批判》〔1〕中,我曾经就“文学批判”和“文学性批判”做出了划分:以文学的形式对于生活中、社会上和传统中的问题予以揭示、暴露,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讽刺、批评和谴责,这就是文学批判。文学批判是常见的、广泛的,而文学性批判则是显示了高度文学价值的批判,自然它是可贵的、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又由于,有些文学批判确实提供了之前人们所没有看到过的形象和想象,或者由于这样的批判给人们的情感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拓展了新的空间,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然体现了新的文学价值,为此,我们就称之为文学性批判。就作家方面而言,之所以能够达到文学性批判的地步,重要的是能够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个性”来,因为只有这种“自由个性”才是不可重复的〔2〕。所以,文学批判是一般的、容易做到的,而文学性批判却是独创性的。它不仅离不开作家丰富的积累、娴熟的技巧,更需要作家对世界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思考和表达。
那么,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在文学性批判方面的不足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或者说,他们的“自己”究竟表现在了哪些方面,而哪些方面又是他们所欠缺和不足的呢?
二
我们先来看看韩少功的《爸爸爸》。
首先应当承认,《爸爸爸》中塑造的丙崽形象,对于感受和理解民族之根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多得的,这一形象的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学中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值得称赞的。一个丙崽,再加上产生丙崽的鸡头寨,既有了叙事性作品中的中心人物,也有了这一中心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因而,二者的典型性对于理解传统的滞后、理解这种滞后的心理实际和行为习惯对现实的不可低估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面对丙崽这一永远穿着开裆裤、智力并不随着年龄而增长的小老头,甚至是喝毒药都不死的人间怪物时,传统的顽固更是不能不令人警惕的。也正是从表现和暴露负面传统上,从批判落后的国民性这一意义上,人们将丙崽与阿Q联系、并列起来予以考察〔3〕。
然而,当我们平心静气地、仔细地将丙崽与阿Q放在一起比较时,又会发现:尽管韩少功在丙崽形象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己”,可也同时暴露了他并不充分的“自己”。
说韩少功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己”,是因为在寻根作家中,他能够独树一帜,就自己所寻找到的“根”——也就是“劣根”,通过丙崽和鸡头寨进行了深刻的表现。大家看到,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以冷峻的笔调、不乏讽刺意味地叙述了丙崽的生活。这个生下来两天两夜都是死人相的生命,一出生就是个不祥之物。而当他逐渐长大之后,也仅仅是学会了两句话:“爸爸”和“×妈妈”。由于这两句话是丙崽个人的,没有确定的具体意思,因而已经离开了作为社会语言的实际含义,成为丙崽式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了。自然,我们可以因此而联想到很多很多,联想到儿童式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好恶,联想到民族历史中以及现实中很多类似的情感化和简单化的行为方式等等。因此,一定程度上,丙崽的情感化和简单化就是对我们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很多心理的和行为的象征。也就是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丙崽,与他所生活的鸡头寨芸芸众生的行为和心理又是和谐一致的。我们看到,鸡头寨寨民们那种原始的、落后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是十分突出的:丙崽娘弄死了一只蜘蛛,以为那是蜘蛛精;烧窑前要举行必要的仪式,以取得神灵的保佑和帮助;打仗之前又要砍下牛头来占卜,接受神灵的昭示;打仗后还要举行分吃敌人尸体的巫术般的仪式,认为吃了敌人的肉体,就会占有了敌人的勇敢和智慧。等等。特别是,当寨民们打仗失利后,因为怀疑丙崽的那两句话“莫非就是阴阳二卦”,从而将丙崽当作“丙相公”、“丙大爷”、“丙仙”顶礼膜拜时,一种集体的冥顽不化可以说表现到了极致。因此,丙崽个人的冥顽不化一定程度上正是其所处群体冥顽不化的代表,而群体的冥顽不化则补充、丰富和完善了丙崽这一个体,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丙崽进行了注释,使丙崽的象征意义有了直接而现实的阐释。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承接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思路,而且比起阿Q来,既使得丙崽具有了更为突出的象征性,也使其具有了明显的抽象性,从而,使国民性寻根和国民性批判这一思路在新时期呈现了新的亮点。
问题是,当我们进一步将《爸爸爸》与鲁迅国民性寻根的代表作《阿Q正传》进行比较分析时,却可以发现,虽然前者承接了后者的思路,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并没有在鲁迅已经走出的道路上予以有效的超越,而且其文学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所以,韩少功所表现的“自己”也就是并不充分的。
这样说的原因有三:一是丙崽的象征性、抽象性超过了阿Q,可是其形象性却比不了阿Q;二是《爸爸爸》虽然进行了文化批判,可是这种批判中却缺乏韩少功“自己的”独特“发现”;三是有关文本之间的互相拆解使得《爸爸爸》在内容上潜伏着并不一致的成分,因而它同样比不了《阿Q正传》。
说丙崽的形象性比不过阿Q,首先是因为前者的描写缺乏阿Q那样强烈的现实感。在《爸爸爸》中,韩少功把故事的时间感故意隐退了,虽然小说里也间接说到了汽车的时代,但是鸡头寨的寨民们基本上是生活在一种原始氛围中,或者说,现代气息与鸡头寨的寨民们基本上是无缘的。这与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阿Q相比,现实的针对性就有所逊色。换句话说,丙崽和鸡头寨的寨民们作为“根”之一支,其“根性”是不如阿Q的更为现实和直接的。当人们在读了《爸爸爸》之后,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将之作为一个遥远的故事来对待的。而对待一个遥远的故事,可能就会产生与己无关的感觉,就会使得文本的批判性有所削弱。其次,丙崽的两句话“爸爸”和“×妈妈”已经符号化了,虽然这样的符号中凝结了丰富的内涵,可符号化必然意味着简单化(虽然这样的简单化绝不是说韩少功处理这一形象时也简单化了)。因此,当四处造访的丙崽只是操持着那两句话时,也就比不了阿Q语言和行为的丰富性。尽管说,丙崽喝毒药而不死,阿Q却被杀头,可阿Q在被杀头之前那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自言自语,又使得他的悲剧性在喜剧色彩中有所增加。可见,丙崽的悲剧性显然是不如阿Q生动和丰富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发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由于这一“发现”,使得《阿Q正传》取得了文学性批判的成功。我们可以想象,假如《阿Q正传》中没有“精神胜利法”这一“发现”,阿Q仅仅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并且受到了革命影响的一位普通人物,那么,其文学性必然要大大减弱,小说的分量也必然要大大降低。因此,有所“发现”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狂人日记》中,作者还“发现”了历史的“吃人”本质,而在与许寿裳的信中就说到:“《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4〕(P41)
在我看来,政治反思必然导致文化反思,文化寻根同样应当进行人格寻根,文化批判也应当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表现出作家在人格问题上的“发现”(其实也就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表达),这样就能够使得历史与现实打通,也才能够达到文学性批判并体现出文学性批判的深刻来。特别是,作家有了自己的“发现”之后,批判的分量就会在文学性的层面上有所深入。只有这样,寻根和批判才能出新,人们受到的启示也才可能更为明显。由于鲁迅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吃人”性质,因而使得《狂人日记》具有了批判的深刻性;也由于鲁迅发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而《阿Q正传》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而《爸爸爸》中的丙崽究竟体现了韩少功的什么“发现”呢?如果只是“冥顽不化”的话,那么它与“精神胜利法”的距离还是存在的。因为“精神胜利法”可以包括“冥顽不化”,或者说“冥顽不化”只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具体体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韩少功的“发现”是显然比不了鲁迅的,正如《爸爸爸》是显然比不了《阿Q正传》一样。由此可见,《爸爸爸》中所体现的韩少功的“自己”还是不够充分的。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爸爸爸》有关文本之间所存在的互相拆解问题,客观上也使得文本的批判性或者说文学性批判明显削弱。读了《爸爸爸》,感受了丙崽和鸡头寨寨民们冥顽不化的特征之后,人们自然会追问丙崽的父亲和祖先。小说中也没有回避这一问题。我们看到,丙崽的父亲是德龙,他是一位“唱古”的能手。根据唱古中的说法,鸡头寨人们的祖先是:由姜凉→府方→火牛→优耐→刑天。这位刑天又是开天辟地的英雄,他的后代原来居住在“东海”之滨,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了,才在凤凰的提议下高兴地全部迁徙到这里。显然,丙崽和鸡头寨寨民们的祖先是光荣的和神圣的。然而,这只是唱古中的说法,因为小说中还写到:曾经有个史官来过此地,说他们唱的根本不是事实。史官说,刑天的头是因为争夺帝位时被黄帝砍去的,而此地的彭、李、麻、莫四大姓原来居住在云梦泽一带,只是因为黄帝与炎帝大战,难民们才沿着五溪往西南方向逃亡,进了夷蛮之地。可奇怪的是,在古歌里却一点也没有战争逼迫的痕迹。很显然,鸡头寨寨民们的来历是有问题的。虽然,“鸡头寨的人不相信史官,更相信德龙”,可是,又有谁能够证明他们的祖先和来历不是如史官所说的呢?或者,又有谁能够证明他们的那些传说不是文过饰非的呢?很显然,这样的来历,来历上这样的互相拆解,客观上可能导致人们对丙崽和鸡头寨寨民们的冥顽不化在根底上的怀疑: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光荣和神圣的呢?这与阿Q对自己祖先的介绍:“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简单(而不是简单化)比起来,就显得有些纠缠。而且还应该看到的是,《爸爸爸》中对丙崽和鸡头寨寨民们祖先的叙述又是与韩少功的寻根意图分不开的。还在1985年1月,韩少功就提问过,自己以前经常想:“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当听到一位朋友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活着的楚文化后,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对湘西多加注意,果然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族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之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问题是,韩少功的思路是:“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个‘寻根’的问题。”〔5〕既然如此,作为韩少功寻根代表的《爸爸爸》文本就应该表现出他所推崇的“绚丽的楚文化”以及“悲壮”式的“根性”来。更何况,他还认为:“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按说,这种“自我”也同样应该在文本中通过“发现”充分体现出来。可是,就创作实际而言,却是对这种信念和“热能”的消解,或者说,由于小说文本内部以及理论文本和小说文本之间的不协调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客观上明显地削弱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因此也可以说,《爸爸爸》中是表现了韩少功的批判,但是在批判中又流露了他对批判对象的眷恋,而在眷恋中自然就削弱了这种批判的锋芒,从而存在着文学性批判之不足。
三
我们再来看看王安忆《小鲍庄》中的问题。
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小鲍庄》是王安忆最好的作品之一,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自己的局限了,恰恰相反,认真阅读了该小说并进行思考后,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文学性批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
《小鲍庄》基本上是采取了在历时态中共时态叙述的结构方式,在“仁义”的线索中,一方面讲了捞渣(鲍仁平)和鲍五爷的故事、文化子和小翠子的故事、拾来和二婶的故事、鲍秉德和疯妻子(武疯子)的故事、鲍仁文(文疯子)如何当作家的故事;另一方面,又讲了一个比较大的洪水的故事。也就是在洪水中,捞渣对鲍五爷的“仁义”故事达到了高潮,为了救五爷,捞渣牺牲了自己幼小的生命,完成了他短暂而“仁义”的一生,“仁义之庄”小鲍庄也因此更使得自己的“仁义”名声大震,一个现代的“仁义”故事也就最后完成了。
当然,这毕竟只是小说的表层,也大概是因为有些批评者仅仅看到了这一层次,所以认为《小鲍庄》是从闭塞、安分、愚讷的文化氛围中讴歌了小鲍庄人善良、仁义的道德品质,意在制造捞渣这一仁义的模型。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文本时,就可能发现,在其深层则是对仁义的深刻批判。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其一,小鲍庄人虽然讲仁义,但是对自己的贫穷却从来没有正视过,而是不足却知足,自己不想变化、不想创造,也容不得别人的变化和创造。他们难以理解在种地之外的其他生活方式,也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现代观念和意识。鲍彦山关心小麦超过了对妻子分娩的关心;鲍仁文只是因为想当作家,就被人们称呼为“文疯子”;因为寡妇二婶所找的拾来不是鲍姓人,就被村里人狠狠打了一顿;捞渣妈虽然出于恻隐之心收留了小翠子,可是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让她做自己家的童养媳……。可以说,是贫穷和“仁义”导致了他们的冷漠,也导致了他们的狭隘。其二,捞渣的“仁义”行为本来只是儿童时期善良本性的反映,只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阶段而已,并没有多少后天的、社会的因素,然而在上级的布置下和鲍仁文的努力下,却被打造成为具有“仁义”教养的“少年英雄”,而打造这一英雄的打造者们又都是为了自己的直接目的。其三,尽管小鲍庄被称为“仁义之乡”,“方圆几百里都知晓这庄的人最仁义”,庄上“自古是讲究仁义”,“祖祖辈辈……就是敬重个仁义”,等等。可是,小鲍庄人的真正祖先却是一位有劣迹的被贬黜的官员。而对鲍仁文“文疯子”的称呼,对小翠子的收养,对在改革开放后经商者的说法“心要狠才管用”,也都与“仁义”无关。因为鲍秉德的妻子连续几个孩子分娩不成功,就说人家“兴许是做姑娘的时候不规矩来着”的怪话,等等。可以说,“仁义”只不过是小鲍庄的虚名,究其实际而言,却是“仁义”之名掩盖下的愚昧、狭隘和不思进取而已。因此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小鲍庄》的表层是“建构”了一个“仁义”的神话,可深层却是对“仁义”的“解构”、对“仁义”的批判。就此方面而言,王安忆自己就说过:“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把农村写成伊甸园”,〔6〕“从逆向上去找,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为了什么呢?”〔7〕“你想,当仁义需要制作榜样时,仁义是否岌岌可危?在树立榜样的同时,每个人都抱着从捞渣身上大捞一把的功利目的。”因而,“《小鲍庄》是写仁义的堕落。”〔8〕而且,小说中从小鲍庄人祖先的劣迹和被贬谪写起,也体现了这一文本文学批判的力度;又因为,这一批判并不只是针对着现实,它还针对着整个历史,也说明了其深刻性。
然而,在承认《小鲍庄》批判的深刻性的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尽管王安忆没有与那些把农村写成为伊甸园的作家一样,而是进行了自己的批判式的写作,但是,在批判性的写作中,王安忆又表现了自己批判上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其一,针对中国历史的文学批判在现代以来的创作中已经是层出不穷,并且这种批判往往会从人性的深度上着手,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然而,将《小鲍庄》与《狂人日记》放到一起时,我们就又会感受到《小鲍庄》在深刻性方面毕竟还是存在遗憾的。这种遗憾在于,《狂人日记》挖掘了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而《小鲍庄》在“吃人”的深度上是明显不如前者的。前者针对的历史包括了这一历史中的“仁义”,而“仁义”却包括不了整个历史。固然说,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儒家思想是占主要地位的,但是,导致中国人愚昧、落后的显然又并不只是“仁义”等儒家文化,而“吃人”的历史却既有儒家文化,也有其他文化。因此,只是针对着儒家“仁义”的批判比起对“吃人”的整体的、可以让人想到的方方面面的批判来说也就明显不如。这也就是说,王安忆的“发现”是不如鲁迅的“发现”深广的,甚至算不上是“发现”。其二,《小鲍庄》的批判中还有着“哀怨”的成分在内,小说中对小鲍庄人贫穷和愚昧的介绍也好,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叙述也罢,都是在一种不动声色中进行的。这种不动声色虽然可以显示出必要的文学特色,但是同样也是在这种不动声色中,又包含着作者明显的“哀怨”,这一点在王安忆的“中国人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的询问中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就有着“诗可以怨”的传统,但是,在看到“诗可以怨”的同时,我们却还应该看到,同样是在中国的古代,对这种“怨”又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就是连“丽”这样的文学性追求,杨雄都有“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往往是有限制的,应当遵守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而受到各种社会规则限制的情感和思想又是难以达到自由境界的,或者说,尽管人们的个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在受到的限制上又是共同的。所以,能够突破既有,使得自己的个性抒发达到自由地步的也就十分稀少、十分可贵。从此而言,历史上很多作家的批判力度也就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创作成绩也就具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而王安忆的《小鲍庄》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对既有的突破上力度不够。我们知道,既然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整个历史予以了“吃人”之定性的批判,《阿 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对封建社会如何“吃人”予以了具体的批判,那么,新的批判只有以不同于原来之批判的角度和超越于原来批判的力度,才能够取得文学性方面的新的成绩,作家的“自己”才能够在这样的、新的批判中凸现出来。就此而言,王安忆的《小鲍庄》在角度上有了新的改变,可是在力度上却并没有达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文本。或者说,王安忆在“发现”上暴露了自己的有限,从而也使得《小鲍庄》暴露了它在文学性方面的不足。
四
上面我们只是分析了《爸爸爸》和《小鲍庄》在文学性批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足。还应该看到的是,从创作动机上说,寻根文学的出现又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小说《百年孤独》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关系的。拉美文学的走向世界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范例,也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可是在模仿中寻根,却又是间接地使用了拉美的逻辑,受到了拉美的制约。在《爸爸爸》和《小鲍庄》中,都有着神秘朦胧的传说,通过这些传说来象征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此表达所附加的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和有关未来文化方面的想象。自然,在这种西方式的思维中寻找自己民族文化意味的思维方式,已经先在地束缚了寻根作家的自我,使他们的创作成为受到了这样那样左右的行为,自然在创作中也就难以使自己的表达达到新的、自由的地步,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对别人的仿照,让别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的束缚。而在束缚和制约中,“自己”的成分必然要减少,自己的“发现”也必然会受限。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文本中,韩少功和王安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关于寻根的观念,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而这也就使得他们在文学性批判上出现了上面所指出的不足。
问题还在于,当附加的东西成为了创作的目的之后,必然会冲淡作家应有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换句话说,此时的创作就不是以感受为主,而可能是以附加的东西为主了,也可以说,是理念的东西大于感受的实际了,而这样带来的必然是文学价值的削弱。尤其是,当附加的东西中渗入了明显的西方因素时,又使得寻根中的自己被西化,也使得“自己”更为丧失,从而只能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徘徊。
这就又意味着,如何进行“自己”的创作,在创作中体现出自己的“发现”,这恐怕是寻根作家考虑得并不充分的问题。我们不是不可以参考西方作家的创作经验,也不是不应该继承五四的国民性寻根传统,可是这些又应该立足今天,通过自己的“发现”,进行富有新时代特色的、能够区别于别人的寻根和能够区别于前人的创作。然而,寻根文学在这方面恰恰做得不够。比如,鲁迅在谈到《呐喊》的创作时,曾经这样说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4〕(P92)而韩少功也曾经谈到过他塑造丙崽和《女女女》中幺姑的一些情况:开始时认为“曾经是他们的邻居或亲友”,可是“当我在稿纸前默默回想他们的音容相貌,想用逼真的笔调把他们细细刻划出来时,自觉是在规规矩矩地现实主义的白描,但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给丙崽添上了一个很大的肚肌眼,在幺姑的身后垫上了一道长城,甚至写出了‘天人感应’式的地震什么的,就似乎与其它什么主义沾边了。”〔9〕很明显,与鲁迅的说法比较起来,就是语式上的类似痕迹也是存在的。但是,就鲁迅而言,虽然有着“听将令”的一面,而在具体的创作中恰恰非常注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理解与思考来,并不只是听从别人的。这又恰恰说明,当时的韩少功倘缺乏“自己”对国民性寻根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就难免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和创作思潮的影响,而没有在更大的程度上突破已有影响的束缚,也就没有形成“自己”对“根”的理解和“发现”,自然也没有突破寻根文学的共同思路。
因而,如何使文学批判走向文学性批判,是存在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中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离不开文学批判,就如我们离不开文学一样。然而,就如我们需要其他方面新的“发现”一样,我们又需要文学方面新的“发现”,所以,我们又需要文学性批判,因为只有文学性批判才可以使我们的文学能够产生具有经典意味的佳作。这样,一般性的文学与具有标高性质的、更有价值的文学的共同存在,才可以使得我们的文学园地更为丰富、更为可观。而且,也只有具有经典性质的文学,也才能够在人类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标志。
〔1〕刘淮南.从文学批判到文学性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0(5).
〔2〕刘淮南.对丹纳艺术价值论的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03(5).
〔3〕比如方克强.阿Q与丙崽:原始心态的重塑〔J〕.文艺理论研究,1986(5);孟繁华.启蒙角色再定位〔J〕.天津社会科学,1996(1).
〔4〕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韩少功.文学的根〔A〕.进步的回退〔C〕.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6〕王安忆.我写小鲍庄〔N〕.光明日报,1985-8-15.
〔7〕王安忆.我在逆向中寻找〔J〕.文学自由谈,1986(3).
〔8〕王安忆等.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变〔J〕.当代作家评论,1991(6).
〔9〕韩少功.好作品主义〔J〕.小说选刊,19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