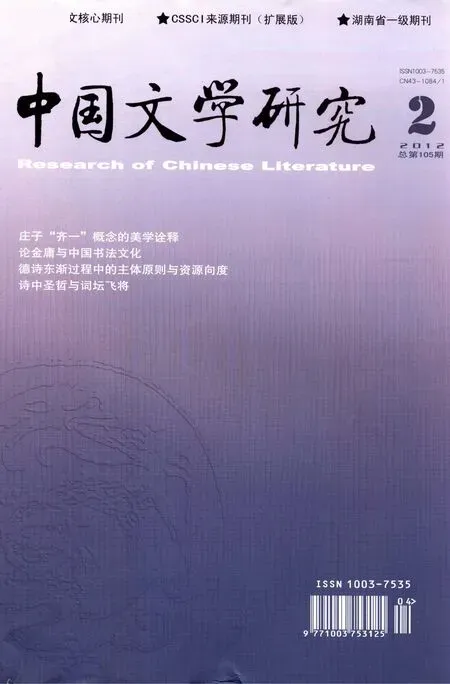论金庸与中国书法文化
李继凯 马 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金庸与书法文化的结缘
中国传统文化以长期耳濡目染的浸润和习以为常的实践,逐渐沉淀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并对其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文学创作为主要使命的作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其精神世界自然难以摆脱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传统文化的制约,在其文化生活、文学生产等诸多方面均留下了传统文化的印记。这一文化定律不仅对中国古代作家有效,而且也同样作用于现当代作家。可以说,现代文明的自觉追求与灵魂深处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依赖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贯穿于现当代作家创作生命的始终,以一种亦张亦驰的矛盾形式存在于作家的精神内面,这不仅提供给作家文学创作以全新的原初动力,而且对其生命存在亦产生或表或里、或深或浅的影响。
金庸是香港著名作家(这仅为其人生复合身份的一个方面),八面来风的文化环境对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中的一员,其精神世界里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切。不仅如此,源于渊博家学以及个人文化喜好的影响,金庸似乎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表现出更为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这方面的史实在很多传记及金庸自述中都很常见。如金庸自己曾说:“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1〕(P175)金庸的武侠小说“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2〕(P172)“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百科全书’。”〔3〕(P3)他将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巧妙地融入文学创作当中,使他的武侠小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貌。严家炎说:“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2〕(172)。的确,传统雅文化元素的融入使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技巧、品味等诸多方面显现出对旧派武侠小说的超越,成就了亦俗亦雅、雅俗共赏的高品位新武侠小说。金庸的新武侠小说能够达到如此境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介入确实功不可没(与“女金庸”郑丰相比即可看出金庸这方面的相对优势)。由此也体现了金庸对武侠精神和文侠气质的复合性追求,在别一种意义上,显示了金庸对“文武兼备”人生境界或生命哲学的依归。大哉金庸,纵情舞剑挥毫,融通文武之道,兼具雅俗之妙,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4〕(P50)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以汉字为基础、以毛笔为书写工具、似诗、似画、似舞、似乐的四维审美艺术形式,既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天地和谐、阴阳相合、中庸匀齐之美的基本体现,更是创作个体精神境界与气质修养的真实反映。因此,在“琴棋书画”这四项代表传统文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修身技能中,“书”有着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地位。而在号称中国四大国粹的武术、中医、书法、京剧中,书法也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由此也生成了重要的书法文化现象。文人修身四大文化技能与四大国粹的交合凸显出书法、书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标签之一。中国书法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形式,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书者文化精神的浸润使书法创作充满了“文人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感情、思想、个性、操守、品格的表现形式。“书法不是后来变成和文人有关,而是在源头上本来就是文人的。书家本来就是文章之士。写文章的人,不仅擅长使用文字,且能把一般的实用文字组合变成具有文学美的文章。一个字本来也是实用的,但是把字写成具有构形的美感的艺术品时,它跟文学是具有同构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法从本源上就跟文学,跟文人、文章之士是同在一块的,它是文人的基本能力。”〔5〕(P20-21)的确,书法与文学在本源上具有同构性,是展现创作个体生命存在的两种形殊质同的文艺形式,因此,自古以来诸多文人雅士兼具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双重身份,例如王羲之、苏轼、黄庭坚、郑板桥、龚自珍、鲁迅、李叔同、沈尹默、郭沫若等等,都在文学与书法两个领域有不俗表现。除此而外,对众多中国文人和作家来说,书法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一种最基本的素养修为,是一种和其日常文化生活、文学创作紧密黏着而无法泾渭分明的文化形态。即使在钢笔书写早已代替了毛笔书写、钢笔书写又面临被键盘书写替代的当代文坛,仍有不少作家痴迷中国书法,甚至将书法文化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书法与文人、书法与文学的紧密关联使书法可能成为介入作家及其创作研究的重要元素。笔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研究迄今在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被忽视的学术视域,“书法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就是其一。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意义上,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无疑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不仅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可以提示很多开放性的学术话题,昭示着相当深广的拓展空间。从文化学或“大文学”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现当代作家,即可发现仍有较多的现当代作家有意无意地将书法书写与文学书写结合了起来,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其文学文本与书法文本化合为“第三种文本”,并成为“中国创造”的艺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与一种活力资源。由此也可领略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的融合,体现着文学介入书法、书法传播文学的文化特征以及多种文化功能。〔6〕(P186)
金庸挚爱中国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也包含着来自书法文化的熏陶。因此,金庸既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位谙熟书法的优秀书写者,他虽然并非著名书家,但起笔落笔之间自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本真表达,质朴俊逸,人字合一。作为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者,他深悟中国书法文化之真谛,并将书法文化之基本精神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甚至是生命体验之中,从而使之成为贯穿其文学创作始终并最终与其生命哲学相融相通的文化元素。在当代文坛,能将书法的文化功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并且在文学创作中将书法文化演绎为一种基本的文学手段,金庸当属具有典范性的一位文化名人。探讨金庸与书法文化的关联,可以涉论很多方面,如金庸书法创作及特色、金庸手稿收集和研究、金庸书法与诗文、金庸书法文化观、金庸书法交际与传播、金庸与书法养生、金庸与书法装裱、金庸书法与书籍装帧、金庸书法与文房四宝、金庸与印章篆刻、金庸书法与市场营销等等,都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仅从若干方面包括结合武侠小说对金庸与书法文化这一命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金庸书法作品的魅力与功用
在名人题字文化风尚的影响下,本应属于金庸个人修身养性之书法创作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逐渐成为金庸及其小说研究的新切入点。除了金庸自书心境的书法创作外,目前公众可见的金庸书法作品多为题赠性作品。这类赠字内容相当广泛,赠友人、艺人、媒体栏目、商业店铺、文化活动、体育比赛、名山大川、旅游景区、赈灾义卖……在大众商业文化的新语境中,可以说金庸几乎从不吝惜笔墨,他以书法题字的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被赠与者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书法题字成为金庸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从而使其书法创作的文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一)以书法题字为武侠代言
纵观金庸书法创作,笔者发现首先有相当一部分题字与其文学创作的武侠世界相关。例如金庸墨宝中广为人知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联便是由其十四部武侠小说的首字构成,可谓是其书法题字的统领之作。除此而外,凡关涉中华武术以及武侠文化的场所、文化活动大多会邀请金庸先生题字留念,而这些场所与文化活动也多与金庸武侠小说存在着某种渊源。例如,在陕西电视台策划的“华山论剑”文化活动中,金庸应邀题于华山北峰的“华山论剑”四字即源于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著名的“华山论剑”情节;题于浙江舟山桃花岛的“桃花岛”三字也似乎意图化虚为实,为东邪黄药师坐实在现实中的安身之所;香港艺人刘德华因在《神雕侠侣》中扮演杨过一角而获得金庸“神雕大侠”题字;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将其头等舱所用波尔多新酒命名为“周伯通”,也因源自《射雕英雄传》人物周伯通而请其著者金庸亲自题写酒名;金庸先生题于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少林秘籍,国之瑰宝”以及赠与湖北武当山的“武当山头松柏长,武当武术、中华瑰宝”题字也皆因武当、少林是金庸小说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场域元素和武侠符码;在北京百工坊展出的铸胎珐琅工艺品“佛宝天龙八部”由金庸题名,不难使人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故事种种;题于广东东莞袁崇焕纪念园的“崇焕故园”四字也易使观者与金庸作品《碧血剑》以及《袁崇焕评传》发生切实可触的感性关联。除了上述与小说中武侠世界直接关联的题字外,金庸还有部分和中华武术相关的书法题字。例如赠与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栏目的“武林大会“题字,赠与全国第五届崆洞武术比赛的“天下英豪、各显身手”、“崆洞武术、威持西陲”题字以及赠与北大武侠协会的题字“北大武侠”等。这些栏目、活动、社团对中华武术精髓、江湖武侠精神的传承、弘扬与金庸小说武侠世界紧密契合,因而获得了金庸以书法题字形式给予的肯定和褒奖。
综上所述,被尊以“金大侠”称号的金庸,其身份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已由一名武侠小说作家转化为中国武术与武侠文化的代言人。而上述书法题字,正是金庸的武侠代言人功效得以充分发挥的一个佐证。金庸以书法创作的具体形式为武侠代言的种种努力,在客观上增强了这些地域、文化活动及栏目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充分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武术和武侠文化,是一种可贵的书法文化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书法题字的方式,金庸为他的武侠小说以及小说中建构起来的金庸武侠文化进行了最有效的宣传。他以化虚为实的技法为小说中虚幻的武侠世界寻找现实存在的依据,使读者在华山、武当、少林、天山、桃花岛等这些现实处所中产生主人公们似曾来过,并在此演绎过一场场江湖恩怨的幻觉。换言之,金庸的书法题字使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获得了曾经存在的时空感,并进而在读者的潜心阅读和莅临现场的结合中获得历史感和现场感。这样,金庸的小说就有了一种由传说而走进历史、由虚幻而走进真实的趋向,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诸多故事、情节、人物也就有可能从小说之中而小说之外成为超越小说的独立存在,并进一步沉淀为经典,融汇到民族文化工程的建构之中,成为了解中华民族无法绕过的文化符号。
(二)以武侠想象为笔墨增韵
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在其著作《艺舟双楫疏证》中说“学书如学拳”,证明了书法与武术的相似性与相通性。书与拳的的相互贯通使借助书法通内气而出外劲、在书法挥洒中尽显武术之理成为可能。历史和现代生活中武学与书学皆通,借武学成就书学之名者不乏其人。东晋王羲之能够成就一代“书圣”的美名,与其在武术方面的深厚造诣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沙场戎马经历也是使其书法“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瞋目,力士挥拳”的重要因素。当代有“武功书法创始人”之称的王世清先生以及号称“武功书法第一人”的大师王厚堂先生更是通过自身习武的深厚体悟将武术的搏击技艺和武学之道直接运用于书法创作之中,创造出了别具新意的“武功书法”(笔者以为命名为“武术书法”更为恰切,体现了“术”与“法”的契合)。
金庸并无实际的习武经历,但他在小说中的武术描写却极为丰满有趣,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黯然销魂掌、一阳指、乾坤大挪移、打狗棒法等等不胜枚举,俨然形成一个严整缜密的“金氏武学”系统。“在金庸的小说中,从道家的武术中可以看到‘易’,看到恬淡和超然;从佛家的武功中看到‘禅’,看到仁和善;从邪恶者的武功中看到恶,看到妖邪和自私;从情人的武打中可以看到情,看到缠绵……金庸的武功设计不只是满足感官的刺激,不只是简单招式的拼凑,而是囊万物于胸臆,熔天地于一炉。”〔7〕(P101)可见,小说中凭借文学想象创造出的无数绝世武功不仅仅是金庸在对中华武学理论理解下的艺术创造,更包含着金庸在文学想象中对人生、人性的深透参悟。小说中武功招数的创作虽然是虚假的,但缔造武功的文化心理历程却是真实可感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金庸虽非以身习武,但恰似以心习武,是一个精神的习武者,他在文学创作中所获得的对武理武道的深切领悟,通过武功创造传达出的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人生哲理的参悟,加之他能够将武学与书学相互融通,从而使金庸书法同样尽显武学之神、武侠之道,具有了与“武术书法”相似的独特神韵。
金庸的书法用三个词比拟最为恰当:侠气、剑气、仙气。欣赏金庸的墨宝,常常觉得很像江湖大侠在剑舞身动之际用剑锋在苍石上刻画的印痕,力道雄浑、苍劲刚毅,颇有铮铮骨感,如同小说中的郭靖、乔峰一般,内功朴拙深厚但却并不张扬,既有豪气云涌、侠肝义胆的气韵,又有“侠之大者”忠孝仁义、为国为民的根本所持。然而金庸的笔墨并不拘泥呆板,豪健浑厚而外又兼具些许放恣之态,其中似乎隐藏着一套高妙的剑法,每一笔似横空而出的长剑、劈空而斩的刀戟。腾挪跌宕之中充满飘逸剑气。似小说中的张无忌、令狐冲一般,有着笑傲江湖、自由洒脱的性灵追求。除此而外,金庸的笔墨还颇具仙气,笔力瘦劲,像武当山上的张三丰、华山思过崖上的风清扬一样有一种老当益壮的遒健,在江湖山水的隐匿中,有着阅历人生之后终超然于外的仙风道骨。经历了无数的江湖恩仇,“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经历了年少时郭靖们的朴拙忠义与令狐冲们的自由洒脱之后,在老年终于获得了了然于心的豁然开朗、获得了来自生命悟彻后的返璞归真和化有为无、化实为空的通达。
由此可见,金庸的书法创作既充满江湖武侠之气,同时又兼具儒、释、道的中国文化精神。铮铮刚毅中有着儒学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基本坚守;飘逸放恣中又有道家恬然虚静、独善其身的性灵追求,遒健风骨中又见佛家参禅悟道、清净明觉的人生意境。在书法创作中将儒、释、道基本精神合三为一,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内蕴。另外,“书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下,以自身独特的理论样式和结构完善了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体系,为中国哲学找到了一种客观、形象的表现形式。”〔8〕如果说书写是一种哲学表现形式的话,那么金庸的书法创作也正是其参悟人生之后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生命哲学的表现。
(三)以书法题名为小说装帧
文学作品的外在装帧并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独立存在,它与作品的内容以及作家通过作品而实现的自我精神表达具有相通性和统一性。因此,文学作品的艺术装帧除了必要的审美功能呈现外,还应该具有追求与作品内容以及作者文化气质浑然天成的和谐一致的目的。惟其如此,文学作品的装帧才能成为呈现作品内涵与作家精神世界的窗口,并成为多种审美要素合一的装帧艺术。正是因为文学作品的装帧追求需要与作者精神世界和谐一致,故而让有能力的作家亲自参与其中便是实现这种一致性的可靠途径。
书法在文学装帧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以书法题写书名形式应用于书籍封面装帧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书法既是文字,又是图形,所以在书籍装帧中具有表意和写神的双重功效。如前所述,金庸的书法创作中有着与其文学世界相一致的武功味儿和武侠气。充满侠气、剑气、仙气的书法作品中包含着对武侠精神的精准演绎以及对自我精神内面的深刻表达。这使得金庸以书法创作的方式介入文学作品装帧不但可能,而且有效,其个性化的书名书法与机械的美术字(包括字库书法)书名效果明显有高下之分。自1975年起由香港明河社、大陆三联书局、广东花城出版社、台湾远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修订本《金庸作品集》,可谓金庸小说版本中流传最广的几种,这几个版本的封面设计均由金庸亲自题写书名,以明河社《金庸作品集》为例,作者金庸以颇具碑意、亦收亦放的行书亲自题写书名,再在封面、封底配以水墨国画背景,在扉页附以书家印章,浑然天成一种行走江湖间、来去无影踪、抚剑独行游、豪气冲云天的中国大侠气象。金庸通过书法题名的方式将其所题书名演变为一种有姿态的视觉语言,以书法的形态之美把小说的韵味气息传递出来,从而充分实现了作品装帧的艺术韵味与作品内涵以及作家精神气质的高度和谐,使小说外在的书法装帧和内在的武侠世界有了互文性的融通。
三、金庸小说中的书法文化元素
武功和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均是一种显内于外、累技成道的技艺。内与外、技与艺、力与美的结合以及由内而外、由技而艺、由力而美的转换最终成就由技而道的悟彻。书法与武功的同源同理性使它们的修习有一种豁然贯通的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有可能由相通而走向相融,成为中国文化中相得益彰的两个方面。金庸曾说过,“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9〕(P139)。
金庸不仅在书法创作层面上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难能可贵的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也将书法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使小说充满盎然的雅文化意趣。特别是在小说中借助文学想象将书法艺术演绎为一种基本的文学表达手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小说基于文学想象的武功创造中,他将对书学之悟移挪至对武学之悟,以书法之道诠释武功招数,从而创造出了充满文化气息与哲理韵味的书法武术,并以书法武术的形式“寓文化于技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10〕(P31)
(一)书法武术的缔造
所谓书法武术,即以书法为武术,书法的书写过程即为武功招数的一一展现过程。据传盛唐“草圣”张旭因偶观唐宫第一舞人公孙大娘“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西河剑器之舞,茅塞顿开,由剑意而悟书意,终得草书之神,成就了奔放豪逸、洒脱恣意、落笔龙蛇的绝世书法。金庸在小说中则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反其道而行之,改“因武生书”而成“因书生武”,书法与武术在理论与审美层面的相通之处助其将书法艺术融入武功招数之中,由一幅幅书法作品及其特点、内涵演绎出一套套书法武术,增加了小说的审美性与文化内涵。
小说《笑傲江湖》中,以一杆笔头缚着一撮羊毛的判官笔为武器的秃笔翁就既是武者亦是书者。他以笔为剑,以书当武,有着较高的书法造诣。他凭借对所使用作品《裴将军诗》书意的领悟与令狐冲过招,诗文中“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凌何壮哉……”所描述的万军从中将军的豪放慷慨的与将军舞剑潇洒俊逸的张弛之美皆由书者演绎为书法作品中激越与静止变换的灵动书意。而武者秃笔翁,亦将领悟到的书意转化为剑意,并借手中“笔剑”来礼赞裴将军慷慨豪壮的生命存在、释放豪洒奔放的胸中剑意。
《神雕侠侣》中,有“天南第一书法名家”之誉的朱子柳亦兼武者与书者的双重身份。在大散关的英雄大会上,他以一杆竹管羊毫毛笔为武器。将大理神技一阳指的点穴手法和书法融为一体,在与霍都王子的打斗中,以笔代指,分别使出褚遂良楷书《房玄龄碑》、“草圣”张旭之狂草作品《自言贴》、隶书《褒斜道石刻》以及大篆等四种书体。书楷书则法度严谨、一丝不苟、书狂草则如疯如癫、指走龙蛇、书魏碑则运笔迟缓、瘦硬通神、书石鼓文则银钩铁画、刀刻剑划,完全将对书学的深刻领悟挪移至武功招数之中,直“写”得霍都王子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无论是书法还是一阳指法皆功力深厚、无论是书学还是武学皆学养超群,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三侠俞岱岩为奸人所害,全身瘫痪,武功全废。身为师父的张三丰眼见徒儿遭此大劫,悲愤难抑,深夜在庭中凭空临写王羲之《丧乱帖》,将满腔悲愤赋予指端。张三丰以与当年王羲之“以遭丧乱而悲愤,以遇荼毒而拂郁”相契合的悲愤心境将“丧乱”、“荼毒”、“追惟酷甚”等拂郁悲愤的开阖书意移植于武功创作之中,达到了人、书、武的最佳结合。而后张三丰情之所至,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二十四个字演绎为一套极高明的“倚天屠龙”武功。丧乱的悲愤使王羲之创造出行书书法的新体式,也同样助张三丰在书剑结合、无我两忘的境界中创造出一套缩也凝重、纵也险劲、雄浑刚健、俊逸飘洒的绝世书法武术。
(二)书法武术的艺术之美
陈墨有云:“金庸的武功、技击,是‘借武而立艺’。借写武功而创造出一种奇妙的艺术天地与境界。”〔11〕(P4)此言不谬,金庸小说中书法武术的展现的确如此。书法艺术之美首先在于汉字字型的匀齐和谐,其次在于书者运笔力道与心境情绪的完美结合。它的“点画线条,有起有伏,有收有放,有高潮有低潮,力度上有强有弱,有刚有柔,速度上有急有缓,有断有续;感情上有紧张有松弛。”〔12〕(P8)唯有如此,才能用笔抑扬顿挫、用墨淋漓生动。源自书学的书法武术之美似与之同。作为一种表现性艺术,武者刀剑行走间“手、眼、身、法、步”的协调以及“精、神、气、力、功”的表现都使书法武术有着源自书法艺术的形态美、力量美、节奏美、韵律美以及雅趣之美。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创作出“倚天屠龙”的书法武术后,他的弟子张翠山而后在王屋山上再次演绎这套绝世武功时就武得煞是好看,小说中如是写道:“只见他身形纵起丈余,跟着使出‘梯云纵’绝技,右脚在山壁一撑,一借力,又纵起两丈,手中判官笔看准石面,嗤嗤嗤几声,已写了一个‘武’字……他左手挥出,银钩在握,倏地一翻,钩住了石壁的缝隙,支住身子的重量,右手跟着又写了个‘林’字…… 越写越快,但见石屑纷纷而下,或如灵蛇盘腾,或如猛兽屹立,须臾间二十四字一齐写毕。这一番石壁刻书,当真如李白诗云:‘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雷,状同楚汉相攻战。’”〔13〕(P174)充满了武者笔舞形动时时而舒缓、时而疾驰、时而飞动、时而顿挫的艺术美感。
《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以书法武术与霍都打斗时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家。当他使出张旭狂草《自言贴》时,就仿佛“草圣”之精灵魂魄附于其身,“突然除下头顶帽子,往地下一掷,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见他如疯如癫、如酒醉、如中邪,笔意淋漓,指走龙蛇。”〔14〕(P418)完全是一场兴之所致的现场书法创作,连一旁观战的黄蓉也忍不住斟三杯酒给他助兴,充满盎然的文化趣味。
(三)书法武术的三重境界
金庸在小说中不仅仅将书法当作缔造武功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还运用书法武术来描写人,将不同人书法武术的表演和他们各种的个性、趣味甚至境界联系在一起,这样,书法武术在小说中就不仅仅外在于形,而且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意味。领悟书法与剑法的同理性、追求书学、武学的结合、书意与剑意的相通是金庸小说中书法武术的真谛所在。不但如此,只有当书法作品的韵味内涵与武者所需之情绪、心境相契合,并用武功招数将其再现出来,通过由技而法、由法而道的逐步领悟,最终达到人、书、剑的完全融通,从而在情之所至的创作中物我两忘,才能达到书法武术的最高境界。而书法武术的最高境界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以此而论,《笑傲江湖》中秃笔翁的书法武术就是一则失败的例子。秃笔翁虽然号称写秃毛笔无数,对自己以书法为武功的创意极为自负,但是在将书学融入武学的领悟层次上却显得生硬呆板。虽然写秃毛笔无数,也许书法技艺甚高,但他的“以书当武”仍停留在临帖描摹的初级阶段。他的书与武在技艺表象上虽然相合,但是在内质精神上却是分离的。这使得他的书法武术沦为观赏性强但实用功效差的花架子,虽有技但不得法,因此,当他以有招之技应付令狐冲的无招之道时,便出现了两不搭界的尴尬。令狐冲不懂书法,便以简御繁,只见笔动便攻其虚隙,逼得秃笔翁满肚笔意,无法施展,“只觉丹田中一阵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15〕(P690)最后只好借丹青生的酒在白墙上大笔书写那《裴将军诗》的二十三字,方才痛快淋漓,抒尽胸中块垒。可以说,秃笔翁的书法武术是单维的,只具其形单并无其质。因而以最初书武相合只求却终得书武相离之果,成为一个人的孤独表演。
《神雕侠侣》中的朱子柳较之秃笔翁因境高一界,所以其书法武术也技高一筹。朱子柳本是大理国状元、大学士,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因此,他的书学以及书法武术的创作颇受其文化修养的影响,有着较高的修习层次,不是刻板的一味模仿或者花式展示,而是真正懂得书法与指法的结合,能够突破他人窠臼,融自我领悟于其中。并能做到临场发挥,活学巧用,灵活多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使书法武术真正能够为我所用。例如在与霍都的过招中,他能以取胜为目的,根据现场状况不断变化书体笔法,时而中规中矩、干净利落、时而长袖飞舞、飞奔疾走,时而又银钩铁划,劲峭凌厉,不拘泥于任何书体形式,只求神韵相通,使得对手难以琢磨,方寸大乱。朱子柳的书法武术修习实现了由技而法的转变。达到了书法武术修习的第二层境界,因而能够在高手过招中发挥其长,克敌制胜。
将书法武术演绎得臻于佳境,实现修习书法武术的最高境界者莫过于《倚天屠龙记》中的百岁老人、武当派开山始祖、武林泰斗张三丰。史载张三丰是一位善书画、工诗词,艺术修养极高的道者。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放大其长,将其擅长之书法与武功完美结合。他在极其悲愤的心境中借助书法创造出绝世武功,他的书法武术与上述二者相比较是三维的,不但具性、具质,而且寄情,将个体阅历人生的深透感悟融入其中,达到了书、武、人的最佳结合。从悲愤而书《丧乱帖》到情之所至的“倚天屠龙”书法武术创作,个体的生命体现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书法武术,已经超越了搏击技艺的层面,而渗透着生命个体无限的人生参悟,从而使之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面。
四、书法文化与金庸的生命哲学
西汉文学家扬雄有云:“字,心画也。”即以为书法创作是一种描绘书者德行、品性、情感、心境的艺术形式。人与字之间存在一种鱼水相融的和谐一致,因而书法创作具有觇人气象的文化功能。即所谓“字如其人”。宋朝苏轼《答张文潜书》又云:“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将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容、风格与其性格、追求、处世哲学等紧密关联,从而使文学创作成为解密作家精神世界的钥匙。即所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与“文如其人”的相似比拟使得“文”与“字”之间具有了基于同构相通的互文可能,文学气韵与书之神气、文学体验与书法感兴、文学之“言”与书法之“线”的同构性使文学与书法都成为关乎人的心灵境界、表现心灵情韵的艺术形式,也使书法、文学与人之间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关系。〔16〕由此可见,无论是金庸的书法创作还是他的小说创作其实最终均指向其精神世界、都是其生命哲学的外化形式。因此,他的书法创作中所展现的书理、小说创作中所展现的武理都与其人生境界的最终获得有着殊途同归的一致性。
(一)千古文人侠客梦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侠”有着毋庸置疑的热忱和挚爱。可以说,每一个文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侠客之梦。侠客们独立洒脱、无拘无束、豪放仗义的生命激情和人生境界使“侠”成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17〕(P6)文弱书生因力所不能及而心向往之,从而形成了文人内心深处关于侠客之梦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这种侠客梦的实质则是文侠与武侠的生命复合所完形化的“神话人生”,是别一种现代传奇和文化创造。
金庸的书法创作有着力道雄厚的侠气基骨。这种艺术特征可以说是金庸精神意识深处“文人侠客之梦”文化信息的外化与再现。书法创作中侠气的存在表现了儒家忠义厚德、积极入世、为国为民的根本所持。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这种对“侠之大者”境界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金庸的意识之中,并伴随着他的人生阅历逐渐沉淀于精神深处,从而成为其人生哲学的根基所在。
金庸书法艺术中的侠气,准确地说是一种与剑气相结合的剑侠之气。剑素有“百兵之君”之誉,在传统兵器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剑在兵器中的至尊地位使其成为“武”的代名词,并与侠文化结合,被赋予正义、责任、慷慨、风度等文化涵义,从而成为武侠世界的精神代号。文人喜欢佩剑,愿将家国情怀以及侠客之梦寄予三尺长剑。剑之于文人,是一种情结。一剑在手便觉扬眉吐气,豪气干云。自古文人多追求琴心剑胆的精神境界,既有对艺术的细腻颖悟,又有对英雄精神的向往。陈平原先生也说:“龚自珍的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可以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于文人来说,‘箫’易得而‘剑’难求,于是诗文中充斥着剑的意象。”〔17〕(P12)由此可见,剑对于中国文人而言具有特别的文化内涵,它象征着文人精神世界里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剑器在文化发展中逐渐被赋予的风雅气度和浪漫诗意使之成为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一个文化符码,表征忠贞、信义的内心坚守和潇洒恣意的性灵追求。金庸作为中国文人的一员,其书法创作飘洒、俊逸、放恣的艺术韵味颇具“剑气”,如同文人诗文一样充斥着剑的意象,表征着个体生命内心落寞的的剑侠情结和家国情怀。
金庸的书法创作除剑侠之气外还颇具仙气,有着道法自然的古拙之意。似乎展现着一种经历沧桑人生之后的某种老年心态。但并非垂老暮气,而是一种饱经磨难和上下求索之后的豁然开朗及宁静明澈。这种意蕴的融入使金庸在书法创作中所展现的侠客梦显现出更多的文人气质和较高的精神境界。
由此可知,金庸作为中国文人,其灵魂深处侠客之梦的向往和追求在他的书法创作中有着充分的表现。而书法作品中侠气、剑气、仙气兼具的艺术韵味也说明了金庸所崇尚的“侠客”之梦是以侠为其底、剑为其形,仙为其神,三者共聚而成的剑侠精神,是以“儒”为根基,在“道”与“佛”的观照中有着生命参悟的侠客之梦。
(二)书法、武侠与人生境界
金庸的书法创作既有侠气、又有剑气、更有仙气。从而形成一种别致的武侠气息。这种气息不单单是书法作品的气息,同时更是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展示。金庸在他的书法创作中展现的是一种阅历人生喧嚣之后而到达的虚静境界,这种虚静既是艺术的、也是人生的。
金庸的小说中,行走江湖的几类英雄侠客与其书法世界里的意境层次显现出一定的对应性。在早期创作中,陈家洛、袁承志、郭靖们具有最典型的“侠气”标志。他们有入世的积极寻求,有强烈的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他们全身心投入家国抱负当中,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有着儒家的根本精神和“侠之大者”的可贵追求。而后继而来的杨过、令狐冲、张无忌们,他们自前辈继承而来的正义、使命和责任已经消融、隐匿,成为一种不再凸显、张扬的人生背景,而在人生的前景舞台上,他们表演的则更多是追求自我价值、自由性灵的独立精神。他们的人生,在“侠气”之外更具飘逸洒脱的“剑气”。而在小说中,能够达到武功与人生的至高境界者,常常是有着非凡的人生阅历,兼具侠气、剑气和仙气的独孤求败、风清扬和张三丰等。他们在年少时分走过了郭靖们的仁义厚德、家国理想、走过令狐冲们自然率真、不拘礼法,在老年获得了武功和人生的至高境界。不但武功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人生也同样达到了化有无为的清澄虚静。
金庸的人生历程也有着与其书法灵韵相通的、和作品中人物相同的人生轨迹。1941年,17岁的少年查良镛因一篇影射性的文章惹怒学校的训导主任,被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开除;抗战后期,怀着外交官的梦想,却因“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而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1949年,青年查良镛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北上外交部求职,寻求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1958年,写成《射雕英雄传》,以三十四岁的年龄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1959年,35岁的中年查良镛自立门户创建《明报》,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以《明报》为中心的报业托拉斯;1993年,年近古稀的查良镛宣布退休,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一职;如今,“‘淡出江湖’的金庸过着平平淡淡、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18〕(P195)金庸说:“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19〕(P80)金庸自己的人生也正是如此,从少年轻狂到名贯香江、再到功成名就后的大隐于市,有过血气方刚、有过踌躇满志、有过轰轰烈烈,最后归于闲云野鹤般的逍遥,以此而论,金庸的人生不可谓不精彩。他的人生何尝不是由侠而剑、由剑而仙的逐步演进。如今的金庸一脸佛相,“偶尔,他亦会张口大笑,笑得前倾后仰,眼睛眯成一线,笑声挥洒出孩童般的纯真无邪,而脸上也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佛光……”〔18〕(P1)阅历人生飞扬之后终获平淡冲和的心境更显可贵。金庸的人生在经历喧嚣飞扬之后已经渐入佳境,平淡冲和、清静无为、致虚守静、明觉知心。
综上可知,书法文化与中国文人作家的精神家园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渊源,因而书法文化可以成为作家及其创作研究的一个新切入点。对新武侠小说宗师金庸而言,书法与书者精神世界的紧密结合使他的书法创作充满了“侠气、剑气、仙气”兼具的“武术书法”的韵味,在文武之道运演中显示了讲求“文化法术”的意趣,从而既彰显其意识深处对于侠客之梦或文武兼备生命境界的追寻,又成功地在文学创作的实践层面,实现了将武侠精神和文侠特质的结合性体现,在叙述学意义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使人世间的文武之道能够在文学世界呈现出互为镜像、互为表里的融合关系。同时,书法与文学创作的结合又使他在武侠小说中创造出了别具新意的“书法武术”,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审美性和文化意蕴,更使其成为展现武者精神境界和文侠审美意趣的重要方式。总之,金庸的文人书法、武侠小说与生命体验之间大致呈现出了三位一体的契合关系,书与武相通,武与书相融,并最终指向其精神内面,展现其以儒为底,在佛与道的观照中致虚守静、明觉知心的艺术境界与人生境界,也由此臻于“文心雕龙、墨舞传神”的人文新境界,从中体现了金庸对武侠精神和文侠气质的复合性追求。
〔1〕严家炎.金庸答问录〔A〕.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A〕.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4〕刘再复.人文十三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5〕王岳川,龚鹏程.文化书法与文人书法——关于当代书法症候的生态文化对话〔J〕.文艺争鸣,2010(4).
〔6〕参见李继凯.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7〕贾耘田.破译金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年.
〔8〕张瑞田.文人书法与文人情怀〔N〕.美术报,2009年2月14日.
〔9〕张大春.金庸谈艺录〔A〕.诸子百家看金庸(伍)〔M〕.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10〕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陈墨.金庸小说之武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
〔12〕沃兴华.中国书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金庸.倚天屠龙记〔M〕.广州:广东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2.
〔14〕金庸.神雕侠侣〔M〕.广州:广东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4.
〔15〕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东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2.
〔16〕参见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精神〔M〕.韩国:新星出版社,2002.
〔1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8〕冷夏,辛磊.金庸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19〕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