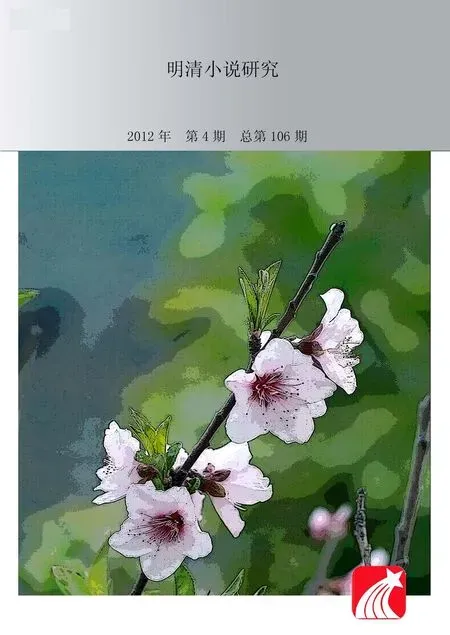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淫僧形象
——以明代话本小说为讨论中心
··
晚明时代的通俗小说中出现了一批“淫僧”形象,与此前中国文言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胡僧、圣僧(疯僧)等形象不同:淫僧们失去了神圣的品格,变得平凡普通;在“酒、色、财、气”四毒方面,较之俗人似乎更有过之。他们纵情声色,为佛门之异类。这些人物形象虽大多雷同且略嫌单调,但其于明末俗文学之涌现,亦有着深刻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一、古代小说中的淫僧形象简史
中国古小说的志怪传统,意味着它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偶尔破戒的僧人故事,原不关心。魏晋时代风气所及,人们于印度传来的佛教,还颇含崇敬与“好奇”。故此,汉魏小说中,未有所谓的“淫僧”①。至于“作意好奇”的唐人小说,也只对神僧与异僧更感兴趣。
宋代文言小说的当下性明显增加,对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更为广泛的纪录。宋洪迈的《夷坚志》中涉及破戒僧人的各类故事开始增多,其中有叙事中一笔带到的,如《游节妇》(支甲卷第五)中提到游氏与山僧通奸。也有作为题材关键因素的,我们选择两篇较有特色的作品来略加探讨。
《奉先寺》的故事叙述得阴森恐怖:京师城南的奉先寺,每年办祭祠时有鬼物前来窃肉,庖人与吏卒按血迹追到寺后荒穴之中,众人凿开穴室,见“有裸而据案者,肌理粗恶,若异物然。细视乃妇人,正食庖中之肉”,询问之,妇人答道:“姓某氏,家去寺远。未嫁时,僧诱我至此室,夜由地道过其房,与僧共寝,晓则复还。凡十余年,僧忽绝不来,地道又塞……无从可归。既久,自能穴土而出……夜则不觉身之去来,随意便到;昼则伏藏,不复知如几何岁月也”②。小说中的奸僧因已死亡,未被追究;其地室藏匿妇人的细节,极其典型。而此篇的讲述重点并不在僧人之淫行,而在于妇人“变鬼”的诡异与真相揭晓的过程。
《夷坚志》丁志卷第十九“盱江丁僧”所记之事尤奇:
绍兴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间黄氏客邸有僧过其家,体貌轩昂,云:“俗姓丁。”留数日,白主人:“入城中行乞,夜即还。”凡数月,所得钱物,亦分以与黄。黄异待之,相处益久,出入无所疑。间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质,既喜僧姿相,又以数得财,故心许而佯拒之。迨暗,僧排闼而入。房内无灯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栏袈裟,坐壁间青莲华上,类世所画佛菩萨然。妻惊慕作礼,僧遽跃下,语之曰:“吾非世人,将度汝,汝勿泄。”即留与乱。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黄知而诘之,不敢隐,尽以直告。黄怒,设计将捕治,托故出宿,密反。人定后,妻又诣僧,摘语之曰:“我夫欲捉汝,为之奈何?”僧曰:“汝无忧。”阖户就寝。黄伏户外侧听,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骂之。初亦相应答,已而其声渐远,俄寂然无闻。坏壁入,执火照之,室已虚矣。四壁枵如,僧与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窗壁牖户无少损处,呼集邻里,追寻到明,窅无音迹,竟莫知所向。③
这位体貌轩昂的和尚与人妻淫乱,却自称是“度人”。洪迈没有痛斥此僧,反而在“房内无灯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栏袈裟,坐壁间青莲华上”的笔调中,略含赞颂称美之意,实在耐人寻味。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提到,隋朝密宗修法(“男女合杂,妄承密行”)传入中原时,朝廷曾为之邀请佛教人士讨论,并察检佛经以核对此法是否合于如来法教④。隋朝的官方做法如此低调与谨慎,确实难得。而洪迈或许认为这位僧人是密宗法师,故叙述之中优容至此。
总之,僧人的淫行,在宋元文言小说中皆未有正面描述。“志怪”兴趣所在,仍在情节本身的离奇;而叙述中对于宗教的谨慎与敬畏,亦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厌僧”立场大有不同。
至宋明时代的话本小说中,淫僧形象开始激增,以下我们从四部最为有名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一型”)⑤中各取一篇加以探讨,以概其余。
《简帖和尚》作为宋元旧作,收于《清平山堂话本》中。述某僧以投递书信的方式离间了皇甫夫妻的感情,并在还俗之后娶了皇甫的休妻杨氏。二人的婚后生活原本平稳,只是这位小娘子在得知骗婚的事实后,选择了告官,最终将“简帖和尚”送上了刑场。此僧倒也算不上十足的淫僧,小说也没有出现男女交欢的场面。
从小说叙述中看来,民间对于僧人拆散他人婚姻的手段颇感兴趣。《泾林杂记》中记录了一则僧人以“偷鞋”手段来破坏他人婚姻的故事。明代的《情史》、《国色天香》诸书转录了此事⑥,叙述中都未着意批判僧人的淫荡。但在白话小说的改编中,“简帖僧”的淫荡本性,渐为凸显:明代《龙图公案》卷二中的和尚“其性奸淫暴烈”,见到妇人遂“两眼瞧着,无意诵经,须臾,欲心悚动,展转难禁,意图奸淫”⑦。这等罪恶欲念,是宋元话本中未曾描述的。
冯梦龙《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讲述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故事:广西南宁府的宝莲寺中有一座子孙堂,凡来求嗣的妇女须于此处居住祈请。寺中和尚遂趁机在半夜从暗道入堂,轮流奸宿这些妇人,因此求嗣者往往得子。新任县令汪旦知事有蹊跷,遂令两名妓女伪装求嗣,趁机将前来奸宿的僧人头顶涂上墨汁。以此,汪大尹查获奸情,剿灭了这一寺僧众。宝莲寺淫僧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他们集体奸淫妇女的行为,也同样匪夷所思。
这篇话本中“子孙堂”供奉着的女神,实为鬼子母,这是佛教中保佑妇女生育的神灵。其信仰在唐宋时代尤为兴盛⑧。人们曾经虔诚地相信,在佛寺中向她祈求,即可孕育满意的后嗣。唐人小说《黑叟》中称:唐宝应年间,越州观察使的妻子在宝林寺魔母堂祈得男嗣一名。此鬼子母神非常灵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⑨。虽然都在广西,寺名相近,神灵一样,但比较这两篇小说的内容,变化明显:佛教神灵送子的神迹,被和尚奸淫致孕的“人为”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信仰的陨落也是促使淫僧故事出现的一个原因。
有学者们认为该话本的价值“在于它对佛家禁欲主义的虚伪与丑恶,作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揭露”⑩。不过,作品对禁欲主义的揭露显然不足,倒是小说中妓女与和尚交欢场面的描写,却媚俗明显。判词中的“紧抱着娇娥,兀的是菩萨从天降;难推去和尚,则索道罗汉梦中来”,戏谑之中也饱含情色意味。
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夺风情村妇捐躯》讲述的故事很简单:村妇杜氏素来嫌弃自己丈夫粗蠢,一次在回娘家的路上因避雨进入太平禅寺,遂与寺中老和尚大觉、徒弟智圆二人发生奸情。后此师徒二人争风吃醋,老和尚怒将杜氏杀死,埋于后园。案发后,县吏林大合设计诓吓僧人以使之招供,后二僧被刑罚至死。陆人龙《型世言》中《妙智淫色杀身》讲述的则是:某寺庙中僧人师徒不守律戒,养了婆娘在庙内淫乱,后因小和尚圆静得罪了州里的礼房吏田有获。田有获遂与徐行(州里徐署事的公子)前来捉奸以敲诈钱财,以至生出纷争。徐署事后竟设谋以盗贼案诬攀僧人,以此将庙中二僧冤枉处死。此后,这三位作恶的官吏一一受到鬼神报应,尤以徐行父子受报最为惨烈。
“二拍”与《型世言》中这两篇“淫僧”题材的拟话本,前人未有明确考知本事所出,但据论者看来,两篇作品的情节多有捏合之处。凌作中假托与神灵对话的审案方式,当袭自《古今小说》之《滕大尹鬼断家私》。陆作中徐行因害死僧人后“心性乖错”,每疑妻子与外人有染以至错将妻子杀死,此事明显仿袭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其他例证,此不赘列。总之,这两篇拟话本作品的情节粗糙,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
总体说来,淫僧的故事,在晚明时期的通俗小说中渐呈泛滥之势。约在崇祯初年有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摭拾流传的小说中有关僧尼淫行的内容汇辑成书”,收集了大量此类故事;而后明末清初又有一部《风流和尚》,它描写了一座寺庙中的五位淫僧的种种淫事,实则是抄集改编他事而成,而前面提到的《夺风情村妇捐躯》的内容即为其所掠;《欢喜冤家》也属此类,创作中几乎都是剽窃他书以为已有;此类小说屡屡被禁,皆因其内容过于污秽。
与此同时,淫僧形象似乎也成了公案小说的新宠。万历二十二年刊行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其中有关淫僧的故事便不少,发展到乾隆年间的《龙图公案》,新增故事中有关淫僧的作品便有:《阿弥陀佛讲和》、《观音菩萨托梦》、《卖真靴》、《三宝殿》、《桷上得穴》、《和尚皱眉》、《西瓜开花》等。
这些明末清初的各类小说作品,或专以淫僧、色情作为吸引人的关目,又或将其作为公案作品的噱头。可见,淫僧故事颇受欢迎,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要补充一点的是,《水浒传》中有位与潘巧云通奸的裴如海,他或许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名气最大的一位淫僧。不过潘巧云的故事远不及同书潘金莲、阎婆惜的故事来得精彩。这段故事中作家的通身气力又更多地放在了潘巧云与石秀的形象塑造上,作为“他者”的裴如海,其形象就更显得单薄与乏味了。他“温饱思淫欲”的经典作派,倒与话本小说中的其他淫僧形象有着交互影响的关系,叶昼将《水浒传》中描写淫僧的大段文字评为“俗”、“可删”,可见此类文字在万历年间通行的俗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为人所厌。
二、话本小说:淫僧形象的世俗化与作品艺术分析
本节将视野集中到话本小说中,它们才是晚明时流通最大的通俗小说作品。这些小说的艺术性也相对较高,有些作品自宋元以来便在民间流传。
(一)从宋元到晚明是一个僧人逐渐世俗化乃至放浪的“过程”
其实,话本中的僧人,凡与“性”有周旋纠缠的未必都是淫僧。这在宋元旧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中一位戒行端正的僧人遭到了世人的误会与污蔑,与郡王小妾实无通奸之事,却替人背了黑锅。这位陈可常被描写为罗汉转世,具有圣僧的品质;《醒世恒言·佛印师四调琴娘》中的佛印也未与琴娘有肉体接触,他这种“道是有情却无情”的行径,属于士人情调中那种超越肉欲的另类风流。看来,他们与“淫”并不相干。
《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与同书中《明悟禅师赶五戒》也都是宋元旧作。这两篇故事中的玉通禅师与五戒禅师皆是修行中人,只因一朝不慎破了淫戒,转世之后或为妓女、或为文人;他们经高人指点接引,复又皈依佛法得以彻悟。这类禅师故事的宗教气息相当浓厚。禅师触犯淫戒,或因一时把持不住,或因他人勾引陷害;其内心则往往有挣扎、会反省。作品对他们也多带同情,给予了他们“回头是岸”的机会。总之,宋元时代的淫僧故事,“戒淫”意味反而浓厚;此时的僧人品质正直可取的多,简帖僧之流只能算是害群之马。
而晚明作家编创的话本中,僧人们多与俗人无异,甚至有与土匪无异者。《二刻拍案惊奇·迟取券毛烈赖原钱》中的智高,“头一件是好利,但是风吹草动,有些个赚得钱的所在,他就钻的去了,所以囊钵充盈,经纪惯熟。……分明是个没头发的牙行”。而同书中《许察院感梦擒僧》中杀死秀才王爵的无尘,杀人的动机竟是:“委实一来忌他占住尼姑,致得尼姑心变了,二来贪他这些财物”。而《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中,正德年间宝华禅寺的僧人们竟以酒肉招待客人,他们贪图钱财,将投宿的举子们一一杀害。总之,贪财贪色、易瞋好怒的僧人们,毫无佛家修为可言。作为红尘中的痴迷者,作家甚至是更乐于从他们身上,去探索俗世之中欲望本身的顽固与劣根性。
随着晚明世风的浸染,僧人头顶的神圣光圈也渐趋消逝。与之同步,晚明话本中的僧人似乎都成了淫荡的代名词。《初刻拍案惊奇·顾阿秀喜舍檀那物》中,王氏逃难至一寺庙,她担心道:“这里头不知是男僧女僧,万一敲开门来,是男僧,撞着不学好的,非礼相犯,不是才脱天罗,又罹地网?”这段心理刻画是本事中所没有的。再看《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苏云之妻逃难来至庙前这般想道:“闻得南边和尚们最不学好,躲了强盗,又撞了和尚,却不晦气。”
连淫僧们的性能力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夸大。如《夺风情村妇捐躯》提到“空门人手段高强”,“一向闻得僧家好本事”。《汪大尹火烧宝莲寺》明写道:“那和尚颇有本领,云雨之际,十分勇猛。张媚姐是个宿妓,也还当他不起。”妓女李婉儿想道:“一向闻得和尚极有本事,我还未信,不想果然。”有研究者认为,佛教密宗文化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小说文本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我们知道,明中后期“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以此,小说中僧人性力强盛的描写,既与风气有关,又不过是俗文学叙事中正常的虚夸罢了。还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凌濛初与陆人龙创作的拟话本作品中,淫僧之间同性恋现象也变得普泛起来。
(二)淫僧形象简析与作品处理艺术简论
固然,话本小说中的淫僧形象,大多乏善可陈;他们的形象过于扁平,往往只是被故事驱使的“他者”。不过,不同作家对淫僧故事的艺术处理也有明显不同。此处,我们对冯、凌、陆三人的作品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所选择的还是前文所举的三例。
冯梦龙(1574-1646)编创的《汪大尹火烧宝莲寺》属于公案作品,宝莲寺集体纵淫的和尚们,其个性特征都模糊之极。正话虽然无足称道,但话本的头回却很有价值。此中描写着杭州金山寺僧人至慧,他平时“遇着一个美貌的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恨不得就抱过来,一口水咽下肚去。走过了十来家门面,尚回头观望,心内想道……若得与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这种赤裸的“好色”心理,在通俗小说中实不多见。他最终选择了还俗、娶妻、生子。他的那段内心独白,确实是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大胆驳斥:
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
这段文字明显受到冯惟敏(1511-1578)杂剧《僧尼共犯》的影响,至慧不愿以佛戒自律,更对世人与官府的歧视甚为不满。作为淫僧中的“反思者”,他是晚明社会中追求自由、肯定情欲的思潮的产物。他这种对普遍人性的渴求,正合于冯梦龙的“情教观”,其时代进步性不容置疑。
假如说冯梦龙作品中偶尔闪现出了对僧人情欲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凌濛初(1580-1644)则在作品的风月描写中,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塑造出了有着生活质感的淫僧。
《夺风情村妇捐躯》中老僧大觉由好色到想占有、由欲到怨恨、再由恨到杀人这步步的转变,在小说中均有明晰的心理剖析。在师徒二人(他们是同性恋关系)与村妇淫乱的场面中,作家还能描摹出大觉的内心情绪变化:他因忌恨妇人对他的厌恶、对徒弟智圆的喜爱,而逐渐变得疯狂。可见凌氏在淫僧题材的处理上,始终关注和尚“人性”的一面,体贴其性情与情感的内在走向。凌氏这种成熟的处理技法,对于性爱心理的准确刻画,确实体现出了晚明小说在性爱描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
相比较而言,陆人龙(至少小凌濛初八岁)的淫僧题材的处理就无足称道了。《型世言》可能与《二刻拍案惊奇》同年出版,但《妙智淫色杀身》叙事凌乱,交待繁琐,似乎完全缺乏剪裁的能力。作品开篇详述,贵州镇国寺有位老病在床的悟通,其徒弟妙智四十岁,徒孙法明年三十,还有个十八九岁的玄孙圆静,“标致得似一个女人”。妙智、法明与圆静三人之间有同性肉体关系。他们与菩提庵的尼姑们(师父、徒弟及徒孙)的性关系极为错乱,聚麀乱伦,无所不至。再者,法明与妙智还勾引了两位寡妇到庙中,四人时常共同宣淫。此外,年青的圆静与乡绅田有获之间也是同性关系,他因又与田有获的小妾通奸,这才致使寺庙的僧人被假案牵连,终被恶意处死。事实上小说中的叙述头绪,比本处的介绍还要杂乱!而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小说的后半情节与僧人们的淫行毫无干系,叙述的重点转移到三位作恶的官绅如何遭受报应。
与冯、凌二氏的作品各有优点不同,《型世言》对淫僧形象的描述,更像是一种无谓的罗列与展示。在陆人龙眼中,除了因果报应,实在找不到淫僧题材的价值亮点。
这几部小说也有共通的缺点:一方面是笔墨有涉淫之嫌;另一方面就是“说书人”或作者喜欢跳出来,评论甚至是“谩骂”和尚们温饱思淫欲的恶劣品行。此类文字在《容与堂本水浒传》裴如海的故事中同样存在。而这些通用的评论文字如果过多地出现,正说明了作家已然对“淫僧形象”有了先入之见,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很难对此类人物有自己真正的观察与细致的刻画。
三、淫僧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传播内因
上文从小说史内部考察了淫僧形象的演变轨迹,分析了几位话本作家对淫僧的人物塑造及题材处理的不同。本节则拟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所谓的淫僧现象,并讨论他们在俗文学内部的传播内因。
(一)晚明的僧界乱象以及民间的厌僧情绪
先来谈谈僧人娶妻的乱象,这在唐宋的局部地区或个别寺庙中早有存在。“唐郑熊《番禺杂记》:广中僧人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穀《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宋人庄绰《鸡肋编》提及岭南地区的僧人,既行商“坐估”又“例有室家”。当地“妇女多嫁于僧”,这让初来此地的北方人倍感惊异。
结婚已非佛法所容,而和尚们还有通奸与嫖妓者。宋代两浙地区的妇人为了“服饰口腹”,会选择与附近寺庙的僧人私通。而元朝两浙地区的嘉兴,僧人居然包养妓女:
嘉兴白县尹得代,过姚庄访僧胜福林,间游市井间,见妇人女子皆浓妆艳饰,因问从行者。或答云:“风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宠。下此则皆道人所有。”
元时喇嘛教鼎盛,若元顺帝之流甚至在宫中效习密宗之“大喜乐”法。此处纪录的嘉兴风俗,或许是密宗僧人所为。元代僧人纵淫的对象甚至包括尼姑。据《西湖游览志余》:“元时,临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来,多投是寺,每至,则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主苦之。于是专饰一寮,以贮尼之淫滥者,供客僧不时之需,名曰尼站”。豪僧权势所在,尼姑们只能陪侍共寝。
明代,尤其是晚明时的僧众乱像,更为让人忧心。明初虽然对僧人在各府、州、县的数量以及出家的年龄有着清晰的规定(《明史》卷七十四),但明王朝多次出售度牒以度过财政难关的事实说明,僧人的质与量其实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与保障。万历中期,中原僧界让人忧心:
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覆,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
而早在成化年间马钧阳的上疏,就已经说到“军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看来僧众中的假和尚不少,其中鱼龙混杂,几乎无人讲究“僧行”戒律。
话本小说中于此也多有描绘。身披袈裟者,实有遁世而不满朝廷的;更有“游方僧人”为方便乞讨,招致世人厌恶的;白莲教因与暴动祸乱有关,其在民间甚至被描写成与淫乱密切相关。而凌濛初的拟话本中,僧人追逐财利,与商人无异。凡此,分明都是晚明世俗僧人的真实写照。
明代僧人其与性欲、女色的关系,又究竟如何呢?
成化年间,明宪宗好色多欲。臣子们有不少以进献房中秘术而得其赏拔。上行下效,“士习遂大坏”。据《明史·佞倖传》载僧人继晓在宪宗时以秘术被封为国师,想扳倒他的大臣反而多遭贬斥。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僧继晓者……其术得售,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发内库银数十万两,西华门外拆毁民居,盖大镇国永昌寺。大臣谏官默默。”其嚣张腐坏也如此。正德年间的明武宗更是“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风气至此,则僧人士子放涎狭邪,甚至认为嫖妓蓄妾都不妨碍他们修行佛法了。
万历年间的南京,更有一个持续十几年、让人瞠目结舌的风俗:
所可恨者,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箠之且死。迩以法严禁之,十数年恶俗一清矣。
太监们“以妓舍僧”,“浮棚满路”的壮观场面,可能与密宗修法有关。但僧人们集体纵淫的恶行,又与朝野上下的风习紧密相关。
禅僧圆澄(1561-1626)曾在《慨古录》中如此痛批明代僧人的腐坏:“……故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从这个角度说来,明代话本小说中出现这么多的淫僧形象,实是当时的僧界乱象的必然反映。
而对“淫僧”的痛恨,则尤以士人最为决绝。据《万历野获编》称:明代有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对于蓄妻的僧人道士,任何普通人见到即可敲诈银两(数目有一定的限制),若不与,则打死勿论。而沈德符针对晚明僧道蓄妻者甚多的现象,也很反感,称“若二法得行,其于除淫荡秽所裨不小”。同书“女僧投水”条还纪录着:洪武帝曾一怒之下,将引诱贵妇人的女僧、“行金天法”的西僧,包括被引诱的功臣华高、胡大海妾等数人一并投河。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不经审讯的简便方法让沈德符如获至宝,他称此为“万世良法”。当时官员周中丞,因江南吴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捕获境内诸尼,并“以权衡准其肥瘠,每觔照豕肉之价,官买与鳏夫”,此种武断做派,也被儒家立场的沈德潜称为“一时快心事”。真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文人之痛恨淫僧,堪称典型。
虽然僧人们不守清规、腐坏堕落的情况,在佛法初传的南北朝时期已有显现,在民国初年也难避免,但都未有如明代中后期如此严重与普遍的。此种僧界乱象反映到小说中,便是我们关注到的这般局面。
(二)通俗文学的审丑倾向与其特殊的文学趣味
淫僧形象在宋明时代不仅活跃于通俗小说中,在其他的民间传闻,以及某些杂录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俗文学中的淫僧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产品,其被制造、包装以及被消费的过程,呈现出一些共通的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淫僧犯戒”的内容方面满足了人们“传奇”的嗜好与谈资的需要:人们愿意去嘲讽、批判这种不法不伦的行径,这一点毋庸多论。此外,个别淫僧故事的离奇结局,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如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僧行因祸致福”条云:与某妇私通的某僧,后被其夫捉奸并施以腐刑,此僧却因此“得高寿,享年九十六……剃小师凡五人”。此事结局果然哑然,细思则也大有深味。
其二,这些俗文学的艺术性较强,满足了不同阶层的审美要求。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甲、淫僧故事的相关描写中多含有戏谑之趣。此种戏弄的意味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与修辞手法等方面,而尤以暗喻手法来嘲讽僧人外形与性器之间的暧昧联系,最为常见。
如《初刻拍案惊奇·西山观设箓度亡魂》描写男女交欢,云:“百花深处一僧归”、“这里小和尚且冲头水阵”,则是将僧人的光头与男子性器做比附。清程世爵所辑《笑林广记》中,类似手法的笑话数量更是指不胜屈!而《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中述胡僧外形“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正是此类传统的典型。再,《醉翁谈录》丁集卷之二有“王次公借驴骂僧”条,也是嘲骂之恶俗典型!至于讥讽僧人好色贪财的,也成为民间文学戏谑的乐趣之一。
乙、淫僧故事的传播,往往依赖于传闻本身情节之离奇、细节之细腻。换句话来说,民间对于“故事性”的要求非常高。明人田汝成(约1503-?)《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了一些明中期还流传在钱塘的淫僧传说,最能说明这一点。本文对其中三条略做分析如下:
第一条,绍兴年间,杭州鹿苑寺中的北地流僧有不法者,在元宵节将入寺观灯的官人妻女骗邀入密室饮酒,后杀其母而留其女。半年后此女寻机托庙中扫地的仆人通风报信,这才将庙中的不法僧人正法。此女子的脱身手段让人觉得侥幸与离奇,此与宋元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收于《警世通言》)中女主角脱困于焦吉庄的手段相似。两篇故事的讲述重点都在女子的脱困过程。
第二条,宋代某士人妻子坐于车中,居然于临安府闹市之中被人直接扛去,关入某庙暗室中长达年余,后被昏暗之中送回。此寺之方丈终被“送狱推问承服,戮于市”。故事详细描述了妇人如何求返以及最终寻得原凶的原因:此女子曾趁机在庙内某观音像的脚下暗中刻下划痕。
而“湖州士人”条与前条相似:只是密室之中居然关有美妇三十余人,参与奸淫者共有二十余名僧人。后幸得几位勇健妇人伺机逃亡。这才有临安府尹率部前来,捕杀僧众,并焚其寺庙。
从这三则可能始于宋代的传说来看,赤裸的色情描写显非重点。人们的关注点乃在情节之曲折与事件之发展:既要让人惊异又要能让人信服。这些故事中精彩的环节,会被反复地采用于其他作品之中,其独立的审美功能与拼接功效非常明显,这些才是通俗艺术引人入胜的关键。而淫僧形象本身在这种艺术审美之中,只能退居次席。
丙、还有一些淫僧传闻,乃以妙趣横生的韵文为欣赏重点。其意趣亦在戏谑,而形式格调却显得高雅得多,故更容易得到文人的赞许。此类韵文包括判词、诗、语录等等。
《西湖游览志余》中叙及:灵隐寺某僧因贪恋妓女致使衣钵荡尽。此僧见被妓女嫌弃,竟酒醉后一怒将之打死。此事亦收录于宋代《醉翁谈录》及《绿窗新话》之中。诸书收录的主体实为苏东坡的这首判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踏莎行》)罗烨《醉翁谈录》庚集“花判公案”中收录的和尚事件有三条,其中《判僧奸情》条中僧人奸骗年少尼姑之事被一笔略过,判词成为文学鉴赏的全部。其判词《望江南》云:“江南竹,巧匠织成笼,赠与吾师藏法体,碧潭深处伴蛟龙,色即是成空。”
说到诗歌,前文述及宋代岭南特有的僧人娶妻风俗,篇中有讽刺绝句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元人陶宗仪讲述嘉兴僧人包占妓女事,主要也是为了纪录白县尹的这篇佳作:“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寺庙中的仆人也学会了折取野蔷薇,怎能不让人艳羡与愤怒呢?
此外,如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五《禅林丛录》之首条“贺叶僧下山娶尼疏”,文笔诙谐幽默,佛典运用得巧妙精熟,俗事做出如此“雅趣”文章,自然让文人叹赏。
于此可见,此类作品中淫僧传闻倒成为“素材”或陪衬,而戏谑性的诗词,才是后人欣赏的“主体”与“内容”。其实,在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以及明代通俗类书《绣谷春容》中收录的讽僧骂道的韵文,也颇不少。即便在淫僧题材的话本小说乃至《水浒传》中,此类韵文亦多有收录,显然它们也为小说增色不少。
故此,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淫僧故事与其中的诗词,有相互陪衬、帮衬的效果,并因阅读者的不同,而各有其艺术功效。
四、淫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先天不足、难成大器
综上所述,宋代俗文学中淫僧形象已然出现,只是僧人的淫行多被一笔带过,人们着重欣赏的往往是文辞之妙与情节之险。至明代话本,淫僧们的“淫行”、“淫思”得以有公开与露骨的描写,他们身上全无禅僧们的那种佛学修养与伦理自觉,而成为有意作恶之辈,无心忏悔之徒。
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僧界乱象的原因之外,晚明“承平日久,民佚志淫”,部分地区发达的商业经济与奢靡的消费文化,也成为通俗小说中情色描写渐趋增多的原因之一。此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对于人的情感与欲望的肯定,也前所未有,以致文人拟话本在描写士人爱情时也敢于直笔男性的性爱冲动。从这个角度说来,“淫僧”题材中本也包含着一些时代的进步因素,如人性、欲望以及伦理禁忌等主题。然而,如同当时思想界对于情欲的肯定偏于激进一样,淫僧故事往往逾越了“风雅”的边界,只有淫思而无有深情的和尚们,显然无法承担“追求合理情欲”这样一个时代主题。
要承认,淫僧故事的传播过程,也可能正是读者借助于小说文本,建构性幻想,释放自身利比多(性能量)的一个过程。但是,淫僧身份的特殊性,意味着他们追求情欲,既易引发争议,也难以取得社会的同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痛斥乃至处死淫僧的行为中,也正在潜意识中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或性本能进行着镇压。而这显然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必须。
由于冯梦龙与凌濛初对于淫僧题材的处理已经各臻其至,后人很难再从淫僧题材中挖掘出更多的新鲜价值,故经过了明末繁盛一时的涌现之后,淫僧形象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最后,要补充两点:首先,就描写方法说来,大部分的淫僧形象,在小说中都缺乏细腻的内心刻画,他们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粗俗而庸劣,以致成了淫欲的代名词。这也使得他们在小说中任由作家涂抹,而无法“辩白”。其次,就作家身份来说,宋元时代的“说经”与“说参请”皆占据着说话艺术的重要一席,僧人们也是说书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晚明的拟话本作家皆为儒生。创作权的转移,也意味着佛道人物任人贬损、遭人嘲弄的命运难以改变。
小说史中高僧消逝而淫僧泛滥的现象,既反映出宗教信仰的时代变化,也与明代话本小说片面地追求耸人听闻的“拍案”效果有关。“云散高唐”之后,“淫僧”题材却没有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一篇名作、一个经典人物,其中之得失成败,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反思与总结。
注:
① 有学者将这个时期小说中与“情”有关的僧人定义为“情僧”,参詹丹《简论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情僧形象》,《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②③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28、695页。
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见《大正藏》,第50册,第436页
⑤ 本文所采用的这几部小说集的版本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王一工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冯梦龙“三言”,《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凌濛初“二拍”,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陆人龙《型世言》,覃君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为行文方便,正文中涉及到“二拍”与《型世言》的具体篇目时,只引其对称句式的前句为小说篇名;再,下文亦不再注明具体引文页数。
⑧ 项裕荣《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观音——从“三言二拍”看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⑨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9页。
⑩ 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