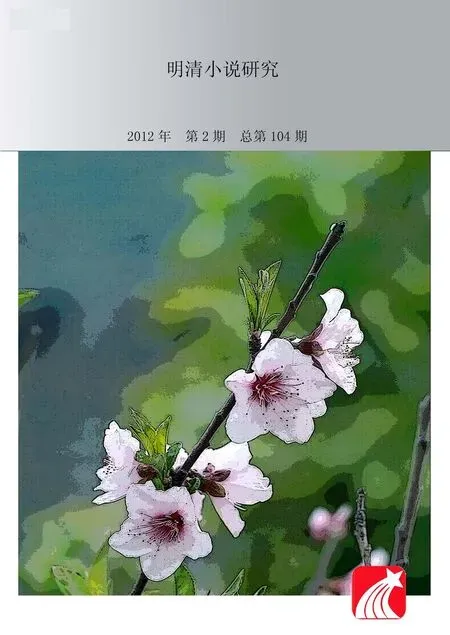《水浒传》的小说史定位及文化谱系探源
··
在侠义小说发展史上,每一代作家都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不断调整着对“侠”的认知,“侠”的文化内涵也一直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在这一“侠义精神”的嬗变过程中,《水浒传》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这一嬗变提供了一个“典范”——这就是侠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结合,也即“义”与“忠”的结合。但我们对此的定位,一般仍着眼于该书的社会意义(农民起义)及其它的传奇色彩,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在侠义精神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演变的深层内涵;即就宋江而言,着重关注的是他的社会身份(义军领袖),而忽略了他的文化身份——“任侠”。本文试就此作一探源性的描述,其目的在于正本清源而已。
一、“侠义”向“忠义”的演变
“侠义精神”中之“义”作为侠客所遵奉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贯穿于“侠义精神”发展的始终。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侠义精神”发生了一个由“侠义”向“忠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对侠义精神内涵的扩大和提升。虽然在魏晋至唐的咏侠诗中,已出现侠与捐躯报国热情的相互联系,但这毕竟还只是文人理想的表达和气概的抒发,与民间所崇奉的侠义精神尚有一定的距离,普及与流传的范围,也有很大的阶层性和局限性。真正明确地给侠赋予“忠”的内涵、将之与“义”熔为一体、以“忠义双全”为侠格之最高境界的侠之重构,始自宋代。这在白话侠义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究其原因,盖在于有宋一代,民族矛盾上升,内忧外患不绝,再兼之以文治国,理学兴盛,于是精忠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这不但表现在“士”的责任承担中,也表现在侠格的扩展上。这种“侠义精神”的升华,便是在“义”之上又添加了一个更高的价值理念——“忠”。换言之,为在民间行侠仗义的侠客,添加了政治关怀的行为指向。于是,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受整个时代的风气的浸染,“侠义”开始逐渐演变为“忠义”。其中明确将“忠义”并举作长篇演绎的,首推《水浒传》。
元末明初出现的《水浒传》,尽管后世多以“英雄传奇”而非“侠义小说”来为其定性,但《水浒传》在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史上的地位已为古今学者所肯定,毋庸置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纳入“元明传来之讲史”内,主要是从该故事的流传和长篇白话小说之源流上着笔的,长篇白话小说主要源自宋代说话中的“讲史”一科,虽然如《水浒传》之类的缀段式作品兼具说话中“小说”一科的形式,但总体而言,其架构仍不失“讲史”特征。鲁迅的如此表述,正是追根溯源之论。另外他在讲到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派”小说时云:“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的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①此处已分明道出,《水浒传》也当是“侠义小说”无疑。刘若愚也曾明确指出:“《水浒传》是从说话发展成为侠客小说的最著名的例子。”②丁锡根编著之《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也将《水浒传》列为章回编“侠义类”第一③。
众所周知,往往在天下无道、公理不行的时期,才更能显示出侠客存在的价值。《水浒传》中无论是单个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如鲁达、武松、宋江等人,还是团体的“替天行道”、共同对抗官府等行径,都体现了主持正义的侠客精神和“以武犯禁”的游侠特征。因此明人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说宋江等人:“聚啸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④另一明人天海藏在《题水浒传叙》中也持同样观点,谓梁山好汉:“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⑤可见,一部《水浒传》,诚可谓是一幅形形色色的侠客图谱。
除了塑造出一批生动鲜活的侠客形象,《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整部书以“忠义”为纲,统摄全书。而这又得分开来讲。在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最能代表侠义精神的“义”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义”将梁山一百单八将归聚拢来,又是“义”使他们团结一心。“义”既是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又是维系他们的精神纽带,此即所谓“同声相应归山寨,一气相随聚水滨”(《水浒传》第五十七回)、“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赛珍珠女士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翻译《水浒传》时将其书名定为“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译名,传神地体现了“义”之一字在水浒群豪中的纽带作用和价值意义。
但是,随着宋江上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之后,指导梁山的人格指向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实则是对梁山群豪“侠格”的整合与改造。于是“忠义”并举,便成为衡量“侠之大者”的主要标准。何谓“忠义”,明人天海藏《题水浒传叙》中的解释最为明了:“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⑥借用金庸的话来说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借其笔下人物郭靖之口发论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杨过)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⑦
“忠义双全”、“为国为民”的实践行为,便是被书写在梁山泊杏黄大旗之上的四个大字——“替天行道”。这是梁山义军的行动纲领,宋江上山执政后,便明确提出:“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⑧在这一纲领的指引下,梁山队伍不仅日益壮大,所行之事也得到百姓的拥戴,不仅单独的侠士常怀侠义之心,扶危济困,锄强扶弱,而且在梁山义军整体出战时,也是但凡攻克城池,便打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所过州县,分毫不扰”,因此“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天海藏《题水浒传叙》所谓“事宜在济民之谓义”,正道出了梁山义军“替天行道”的实质,同时也是对梁山好汉们侠义行径的最好注解。而这一点恐怕正是水浒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的原因所在。因此有学者指出:“《水浒传》故事虽有历史的影子,但对游侠精神的追怀,对救世英雄的渴盼,恐怕才是它得以流传的原因所在,也是该故事的灵魂所在。准以此观,我们与其说它反映的是一场农民起义,不如说是为历史上退处边缘的游侠招魂,来的更为恰切。”⑨
至于现在将之称作“英雄传奇”,也不无合理性,因为我们已将这类侠客,抬至“英雄”的高度来看待,这是对其“侠格”的提升与扩展;另所谓“传奇”者,是因为这类故事已远离了真实的历史记载,更多传奇的色彩,故以名之,亦合乎实际。但以之归类,恰好忽略了它的渊源所自和文化谱系。换言之,忽略了它的正脉和源流,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这里,不是要纠缠它究竟应该划归到哪一类型中去,而应该辨明的则是“侠义”向“忠义”的扩展,“侠”与“英雄”的合流。即使我们仍称之谓“英雄传奇”,也要看到它的文化传承及其与“侠义小说”的内在关系,更不能将二者视作不相干连的殊类。
二、“侠”与“英雄”的合流
唐君毅先生曾将中国人格世界的类型,分为十一种,其中将“豪杰之士、侠义之士、气节之士”与另一种“儒将与圣君贤相”,视为“中国之社会政治性人格”。这是很独到的看法。他辨析道:“豪杰之异于英雄者,在英雄以气势胜,而豪杰则以气度、气概胜。”他更赞扬的是豪杰而非英雄,并与西方人所崇尚的“英雄”相比说:豪杰“则可成功,亦可失败”,“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英雄如之何能及也”。另外指出,豪杰、侠义、气节之士,虽名为三,实“同表一风骨,而为义不同。豪杰之精神,乃一身载道,平地兴起,以向上开拓之精神。侠义之精神,乃横面地主持社会正义之精神。气节之士,则为一以身守道,与道共存亡之精神”,尤其“豪杰恒兼侠义之行,侠义之士恒兼豪杰之行”⑩。如此云云,独未单列“英雄”一格,只是与豪杰相比时,略有言及。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豪杰、侠义、气节三者,相通之处甚多,也都与“英雄”有相合或相重的地方,只是境界不同而已。古代小说中,“英雄豪杰”常常并称为一,不作区分。豪杰、气节二者,也常是后世在侠格重构时,附加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对侠义人格的改造,正是将三者融为一体而塑造的,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性人格”,故小说称他们为“英雄”。况且小说家不会像哲学家或思想家一样,详细辨析其异同。
冯友兰先生根据古人倡导的“三不朽”盛事,也有一个中国人格类型的划分:“立德的人,谓之圣贤,他们有很高的境界,但未必即有很大的学问事功。立言的人,谓之才人,他们有很多的知识,或伟大的创作,但不常有很高的境界。立功的人,谓之英雄,他们有事业上很大的成就,但亦不常有很高的境界。英雄又与所谓奸雄不同。英雄与奸雄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的,可以是合乎道德的,但不能是道德的。”将英雄归入“功利境界”,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后世小说称侠义人物为“英雄”,也主要是从他们的事功方面立论的,至于其行为是否完全合乎儒家道德,则一般不作计较。这从《水浒传》的人物表现上,可以分明见出。曾朴在《孽海花》中也借人物之口发论道:“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第十二回)此亦可见,英雄的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的,可以是合乎道德的,但不能是道德的”。《三国志演义》也曾借曹操之口给“英雄”下过一个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二十一回)所谓“良谋”中,不可能不隐藏着“权诈”。今人大批《水浒传》中李逵、武松等人嗜杀成性、时迁等人偷鸡摸狗的行径为不合道德,实则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恰是今人将“英雄”道德化、楷模化、平面化、类型化了的缘故。
其实,在古代“英雄”一词是分开讲的。魏时刘劭《人物志》专门列有“英雄篇”:“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为文昌,雄为武称。”并解释道:“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但后世“英雄”并称,已不作详细辨析了,文可称英雄,武亦可以称英雄。《水浒传》将一百八人都称为“英雄”,这仅从回目上就可一目了然——“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他如写宋江出场时,先作介绍云:“有分教:郓城县里,引出个仗义英雄;梁山泊中,聚一伙擎天好汉。”(第十七回)第六十九回回前诗云:“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如此等等,在作者眼中,“豪杰”、“好汉”和“英雄”,是同义词,所以在大多数人物出场的赞词中,都冠以“英雄”二字,其“英雄”的使用频率之高,在同类小说中实属罕见。明末雄飞馆主人(熊飞)曾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合刻为一书,取名曰《英雄谱》。从这一取名和小说中大量使用的“英雄”字眼中,可大致窥见当时人看法的转变:在民间和文人圈内,已有将《水浒》人物视为“英雄”而非绿林江湖之盗的观点了。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已具有了“辅国安民”的热忱和精神。因此,“侠”与“英雄”的合流,实则也即“侠”与“公”的合流。于是,历史上侠所承担的“私义”,开始向公共领域的“公义”迈进,快意恩仇的“私剑”一变而为尽忠报国的“公事”(详后)。
除了《水浒传》,在明代的其他侠义小说中,“侠”与“英雄”的合流、“私义”向“公义”的转变,也在在可见。如《禅真逸史》以南北朝后期南朝梁与东魏对峙争战为时代背景,叙述了林澹然及弟子杜伏威、薛举、张善相师徒两代行侠仗义、举兵封侯、羽化登仙的故事。这一小说在精神上是直接上承《水浒传》而来的。在第三十五回《元帅兵陷苦株湾,众侠同心归齐国》中,义军领袖杜伏威对官兵将领面陈衷曲曰:“杜某兄弟三人,因朝廷昏乱,百姓倒悬,起义兵除暴安良,非为私也。”此与宋江的话,如出一辙,表明他们行的是“替天行道”之事。军师查讷一力促成招安,他劝杜伏威云:“自古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如且将计就计,曲从段绍(官兵元帅)之言,解甲休戈,受了招安。一来归服齐王,取功名于正路,身居荣显,名垂竹简,亦是风云际会之时,不可错过。”第三十六回杜伏威接受招安时再次申明道:“某等皆因势豪逼迫,以致谋动干戈,无非济困扶危,替天行道,不敢妄为。蒙大元帅(指段绍)赦宥纳降,情愿执鞭坠镫,以报殊遇。”该小说分明有因袭《水浒传》的地方,并杂糅有《三国志演义》匡扶汉室的意旨,只是结局吸取了梁山泊英雄的教训,改为急流勇退、集体归隐而已。且不论该小说艺术成就如何,就其内在的结构而言,分明含有一个由“侠义”向“忠义”、“私”向“公”的转换,因此才将他们视为“英雄”。
而短篇白话小说,如《二刻拍案惊奇》之《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的开首之诗即曰:“剧贼从来有贼智,其间妙巧亦无穷。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场不立功。”并在“入话”中议论道:“孟尝君平时养了许多客,今脱秦难,却得此两小人之力。可见天下寸长尺技俱有用处。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没处设施,都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随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气力,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凌濛初还在《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谈侠》(《拍案惊奇》)中,通过女侠十一娘之口特别提到,侠客必须维护公德、不讲私义,应过问国事,诛奸除贪,并将之视为“做的公事”。这些记叙和议论,也显示了对侠义精神的扩充,只是角度不同:是站在侠客的立场上,抨击政府的用人制度,希望英雄能有用武之地,为国效力;同时消解世俗之人对侠客的偏见,并对“侠盗”作出新的界定——此即所谓“江湖有义终非盗”。
至此,我们可以说,宋以后所塑造的“侠客”是一种“英雄”式的人物,他们和最初“不轨于正义”的“游侠”已有了本质的区别,走的是一条由“游侠”向“英雄”的蜕变之路。这无疑是对侠的文化规训和精神锻造,对侠之面相的重塑和价值的提升。此正如(明)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所言:“盖正史不能涉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云。”就“义”与“忠”的结合而言,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拼凑,而是“忠”中有“义”,“义”中见“忠”。如果把“忠”和“义”分别视作一种价值符号的话,那么在忠的“能指”中有义的“所指”,而在义的“能指”中有忠的“所指”。“侠”与“英雄”亦同此,英雄必具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内涵英雄品质。
三、“任侠”:宋江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
“侠”向“英雄”的转变与合流,又内涵着一个对其豪侠之性和狠戾之行的整合向度,我们可将之视为对豪侠精神的文化洗礼。这一“洗礼”不仅表现在“义”与“忠”的结合上,以此培植他们的“公忠报国”之心;也表现在领袖人物宋江的身份塑造上,说到底,他应是一个“任侠”一流的人物。
关于“宋江起义”一事虽有历史根据,但现存文献大多语焉不详。石昌渝先生在考察《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时,结合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宋金民族战争的社会现状指出,金兵占领北方后,溃散在北方的宋军和北方民众的自卫武装聚集在山林湖泽与金朝政权对抗,这些抗金救国的民众,南宋朝廷以“忠义”相称。南宋统治下的百姓,怀着抗金的情绪,对宋江的故事不但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讲说中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和新的体验。可见对“忠义”的提倡,渊源有自。而《水浒传》最早的书名就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人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引袁无涯之言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这一取名,恰好典型地反映出成书过程中“忠义”观念大盛的实况。在该小说的研究中,自容与堂刻本提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以来,这一情节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以至毛泽东在关于《水浒传》的谈话中,主要就这一改动而立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不论古人和今人的看法如何,这一切恰好说明,由“侠义”向“忠义”的转变是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故最能体现侠义观和侠义精神的新变。毛泽东将之视做“修正主义”,正一语破的,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窥探到了当时对侠义精神的“修正”和扩大。它之所以能导致招安,就在于在这一改动中,隐含着“义”与“忠”,也即侠义精神和政治伦理的结合。
如果说“义”是侠义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代表的是“侠道伦理”;那么“忠”代表的则是一种“政治伦理”。在“义”前加一“忠”字,在今人看来,是“修正主义”,应该批判;但在当时人及作者看来,则无疑提升了“义”的行为价值,扩大了“义”的伦理内涵。招安进京时打的两面旗帜——“顺天”和“护国”,就是由此而来的,前者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后者代表他们的行动目标。
准此以观,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便是对豪侠“大忠”品阶的提升,对豪侠精神的文化洗礼,对豪侠行为的政治扩展,对豪侠人格的双向完善。这一转变也是古老的游侠传统中“不轨于正义”向“轨于正义”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变,“以武犯禁”的侠客终为主流社会所接纳,成为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都乐于接受与亲近的人格典范,以至一变而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种“大侠精神”正是侠义传统与儒家人格价值的完美结合。
领袖人物宋江便是这一“忠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对此形象的论述已经很多,毋需多言,但大多数论者都将之视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主要是从其社会身份和阶级身份着眼的。此处笔者想特为指出的是,对这一“忠义双全”的人格型塑,实则是对历史上“任侠”形象的拓展。换言之,从该人物的文化谱系来看,他无疑属于“任侠”一流人物。
在历史上,“任侠”和“游侠”应当是有区别的。《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载季布云:“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如淳注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又记季布其弟季心云:“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旅美学者杨联陞先生引明末清初方以智的《任论》云:
“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名”,“盖任侠之教衰,而后游侠之势行”。保任爱护人民,本是在上者的责任。政治力不足,社会力起来接应,可以说是好事,近代民主国家,也有很多人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中国自宋代以来,有人主张保富,说富民可以为贫民之主,患难有所依托,意思与此相近。又,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应有区别。他虽然没有说得很清楚,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尤其是后两者)等能养士结客,有很多人依附者为任侠,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则为游侠。任侠可为游侠之主。章太炎所谓“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大侠大约相当于任侠,而击刺之萌即剑客,相当于游侠。好像也主张有这样一个分别。
余英时先生也指出,“任侠”不但是好结交豪客、赡养武士的“领袖”人物,而且还具有“社会集团的性格”。他引《史记·季布传》中如淳所作的“任侠”注曰:“如淳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指出了‘任侠’是一种团体,不但互相信任,而且有共同的是非。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它扼要地揭示了‘侠’的社会结合的本质:‘权行州里’指‘侠’的地方势力而言;‘力折公侯’则指这种势力和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地位。”《水浒传》第八十三回回前诗云:“壮哉一百八英雄,任侠施仁聚山坞。”其中“任侠”一词既是对梁山泊集团行为及性格特点的概括,也是对其首领宋江文化身份的定位。这在宋江首次出场的赞词中亦可窥见:“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并在其人物介绍中云:“……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第十八回)这不正是一篇“任侠传”吗?孟尝君是历史上“任侠”的典范,以此比拟宋江,不正是对其“文化身份”的确认吗?又称宋江为“呼保义”,所谓“呼群保义”,不也正是对“任侠”解释吗?晁盖亦是一位“任侠”式的人物,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言。他二人之所以能做梁山领袖,就在于他们都属“任侠”而已。因此与其说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如说他是招揽四方豪杰的“任侠”,可能更准确一些。
不仅如此,《水浒传》又在“任侠”之上,赋予了宋江“忠义双全”的人格,并同时将之设定为梁山人格的最高标准。所谓“忠义双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实乃“儒侠合流”而已,这是对“任侠”行为和人格的进一步拓展和改造。余英时先生指出,宋代以来,“侠”的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不但与“武”分家,而且与“儒”渐次合流,《儒林》、《文苑》传中出现“侠”的人物即是明证。所以“自宋以后,‘侠’的精神不但继续进入文人学士的灵魂深处,而且弥散在整个社会,影响及于各阶层、各行业的人,连禅师与医师也深染侠风”。这也正好说明宋江起义的故事为何在宋元时期的流传中,为其附加上许多“侠气”、“侠节”的原因所在。更由于“侠”不但出自“士”(武士),而且和富于批判精神的“儒”有相合之处,尤其儒家传统中“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这种儒、侠合流的现象,在明清之际更为明显,不少儒生文士因此而获得了“任侠”的声名,“其学学孔,其行类侠”,表现在许多儒者身上。这从汤显祖品人的标准中亦可见出:“人之大致,惟侠与儒。”
以此来看宋江,他的文化身份就很清楚了,作者对他的“任侠”行为之所以附加上“忠义双全”的要求,就在于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儒而侠”的人物。其中,“忠”是对其“儒”者形象的塑造,而“义”则是对其“侠”者形象的塑造。对此,前引明代天海藏《题水浒传叙》的解释最得要领:“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为国”和“济民”的结合,将“任侠”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游侠”之“游”,是一股社会的“离心力”,那么“任侠”则把这种“离心力”聚拢起来,转换成了“辅国安民”的“向心力”。这不正是对“任侠”的政治提升和文化洗礼吗?所谓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内涵着这样一种对“任侠”行为和人格的改造。这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宋江对众人的昭告中也可窥见:“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并拈香起誓曰:“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第七十一回)至此,我们可以说,整个梁山义军是一个具有“任侠”特征的社会集团,完全符合“任侠”的团体性质。至于宋江左顾右瞻、畏首畏尾的行为表现,说到底,是由“儒/侠”二者之间内在的紧张造成的。换言之,“儒/侠”之间,既有可“合流”的有机成分,也有相互冲突的矛盾之处,譬如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二者就很难相合。也许正因如此,后来的《三侠五义》才改由一清官统领,并给清官本身赋予了“任侠”的特点。换言之,清官之所以能聚拢众侠,并使之心服口服,受其指使,正在于其“清官”加“任侠”的身份使然。
这种“儒侠合流”、“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终于将历史上的“游侠”和“任侠”抬升到了一个新的境地。而此后的侠客不仅仅是匡扶正义、路见不平的“勇力”的代表,更成为心怀天下、精忠报国的“忠义之士”。传统的“侠义观”一变而成为“忠义观”。侠客不仅保留着传统的江湖义气和民间精神,同时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侠义小说的创作。
综上所述,《水浒传》作为“经典”作品,对它的解读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到了对它的文化传承和历史内涵作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如果远离了它的文化谱系,再怎样的阐释,总觉隔了一层;再怎样的拔高,只能流为不着边际的人云亦云和过度诠释。
注: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② [美]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7页。
③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金庸《神雕侠侣》第二十回,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页。
⑧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六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4页。以下凡引到《水浒传》之原文,皆出自该书,故不再一一注明。
⑨ 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⑩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