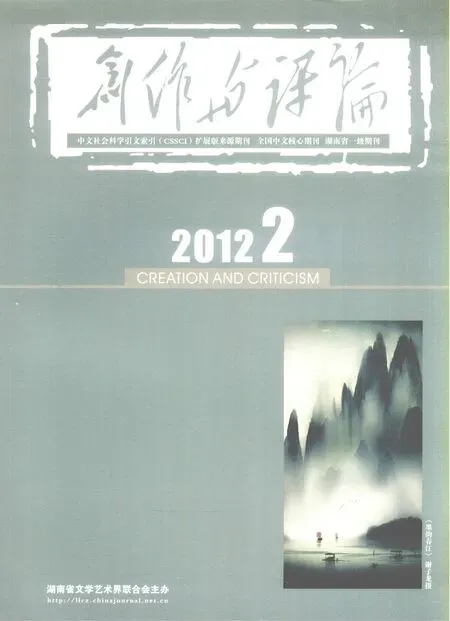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玉女身份”*——试论张悦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 王涛
一、“FEMINISM”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FEM IN 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泛指关涉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的主张,后传至英美,逐渐流行起来,经日本中介传至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用“女性主义”代替“女权主义”。在这场被爱德华·赛义德称作的“理论旅行”中,理论和思想正是在国际环境中从此处向彼处的运动中出现了创造性地借用、挪用,从而不断地衍生出新的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FEM IN ISM旅行至中国后译名的两次改变,隐喻着其原有的急进的政治色彩开始逐渐减退,其研究关注点也从早期的以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全盘清理与唤起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来追求妇女的社会政治权利为目标逐步转向对“女性”本身的高度关注。而从实际的创作层面来看,“FEM IN ISM”在中国大陆女作家笔下的具象化历程经历了从最初集中在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即:女性作为母亲或者作为妻子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命运变迁的探讨上,日渐转向对女性生理特征即:女性生理上的性征和女性的心理特征的关注上。
自五四时期提倡男女平等观念开始,延续到当代,仍然有一大批女性作家在以宏观的视角观察女性的命运,在她们笔下活动的女性大都是和一定历史背景紧密关联的女性个人,在讲述她们的幸与不幸之中,常常是在渗透着身不由己地受制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单薄的女人”。无论是萧红《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对婚姻的抗争,还是铁凝《永远有多远》中通过对白大省两难处境的叙写,都质疑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给女性命运带来的精神痛苦,在她们淡淡忧伤中表达出的是女性作家对女性个体命运的关注,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关注始终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1980年代以后,文坛上在王安忆、铁凝对女性命运表达中表现出的女性特有的清婉的笔调的影响下,女性创作开始关注女性的内部世界,她们发现了一个与以往大家所熟悉的致力于对外在世界开垦的男性世界所截然不同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情感的细微变化、情绪的飘忽不定,都代表着女性独特的心理世界,需要我们的女性作家工笔画似地描绘人们细致微妙的心理世界,捕捉内心转瞬即逝的感情涟漪。此期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的女性自白和黑夜意识的表达,陈染、林白、海男自传体与独白式的个人化写作姿态,如林白独白式个人化写作《一个人的战争》,她们竭力开发有别于理性、暴力、控制的男性气质的女性气质,试图从直觉、私人化,黑夜意识此类女性意识来体察世界。
另一批被冠名为“美女作家”的“70后”的年轻美女们开始大肆渲染“私人写作”,她们不约而同地遁入“女性之躯”,突出男性文本中被批判被扭曲的女性欲望,她们强调女人的身体不是只能用来愉悦男人,或者是仅为男人传宗接代,延续烟火的,而是有着女性特有的性征,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欲体验和体会。在她们的创作中,身体成了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中青春女孩在酒吧、派对、沙龙、小资、颓废、前卫、疯狂女人的关键词中,在“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的宣言中恣意表达和男人一样具有性自主的女性性欲。将女性生存体验中的性欲体验夸大为女性和男性最大的区别。
而在“80后”女作家的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呢?以张悦然为例,她被媒体喻为“玉女”,而“玉”性凉、色冷、通透、灵气。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常常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一片冰心在玉壶”“水晶如意玉连环”都象征着表里一致的廉洁高尚美好。它隐喻着:干净整洁美丽和隔绝。在她的女性创作中表现出了与其紧承的“70后”截然不同的形象,那些女主人公大多是未成年人,所用的指称也多是“女孩”。在她的笔下,我们常谓的女性的命运似乎还没有开始,所以还算不得女性意识。另一方面,她的性征似乎也还没有发展成熟,青涩的躲在华丽的衣服下,不得不用各种美丽的服饰来遮掩它。因此有论者质疑她是否有自己独特的女性意识:“这些八十年代后的女作家大多身处象牙塔之巅,长相秀丽、个性鲜明,她们的文字执著地表达真实的自我。只是,这些依旧被打上了“美女作家”标签的年轻女孩,她们会不会重新坠入本世纪初“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穷途末路,还需拭目以待”①但是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差异彰显出了张悦然女性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她通过对自身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表达,为女性创作的自我表达开拓出了一个新空间,在“玉女”的喃喃自语中张悦然笔下的“她”只是个在大雨滂沱中寻求安置自己情感的无助女孩,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逐步推向成熟的小女孩成长中的困惑和忧伤。
二、“玉女”的女性意识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这部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中,细腻而生动地给我们描述了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由自我感觉处于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发现自己处于劣等地位的失落期。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她们发现男孩子被要求不依赖他人,独立行事,而她们自己则是个拥有特权的人。但是在随后的成长道路中,她逐渐会发现男孩子们之所以被苛求是因为被寄予了担当社会重任的厚望,而女孩之所以拥有特权实际上是社会对她性别角色的定位为处于劣等的那一方所享有的弱者的被保护权。社会需要的与其说是她们能力的展现,倒不如说是更需要她能通过自己努力来讨人欢喜即可。张悦然的大多数创作中所弥漫的浓郁的忧伤情调,正是这种突然发现地位失衡时的情绪体验。与此同时,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她一方面在向社会所期待的性别角色靠近,努力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如她对笔下女主人公父亲、母亲“丑陋”不堪的形象塑造中以求惹人爱怜,对物质所展现的“美好”体验的过度关注以及完成对忘我爱情的描写中追求一个惹人喜爱的“女主人公”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表现出了试图脱离这种社会认定的女性性别角色,彰显女性性别优越的努力。正是在这种悖论的张力中,她在自身成长的伤疼处真实地表达出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自我性别角色认同的困惑,以及无力摆脱这种困惑的尴尬。
1.惹人怜爱的“女主人公”形象
尽管在张悦然的作品中,我们还是会偶尔看到一些她所塑造的慈父慈母的形象,但是总的来说,给我们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是这样一些不堪入目,惹人憎恶的形象。《吉诺的跳马》中的父亲是个粗俗的人“她一度怀疑父亲的前世是个类似马之类的牲畜,所以咀嚼时才会有格外响亮的声音”“他的脾气很坏”“不过自此大家都知道,那个凶神恶煞的看门人就是吉诺的爸爸”。“有时候吉诺觉得她爸爸是四面阴森森的大墙,把她严严实实地圈在了里面,她是完全孤立的,甚至无法要求救援”《小染》中的小染受迫于父亲要求她做模特画画,耽误了她的约会,她只能想象着“娃娃还在跳舞。她又转了七个圆圈,玫瑰裙子开出新的花朵”哀叹着“一切都将与我擦肩而过”最后忍无可忍地杀死了父亲。《昼若夜房间》中对父亲的描述是“暴君一样自以为是”。对母亲的感觉是“她厌倦了母亲那张皱巴巴如吸水海绵一样能够无限制地吞下屈辱和疼痛的脸。”“璟当然记得,两岁的时候在大床上睡觉,曼丢开她出去跳舞,她从床上滚下来,头上肿起大包。璟当然记得,四岁生病,曼任凭她高烧,后来在她奶奶的督促下给她喂药,却把脚气水当作止咳糖浆灌进她嘴里,嘴上瞬间长满烧灼的大泡。璟当然记得,六岁的时候曼带着她去公共浴池洗澡,曼照例在前面昂首挺胸地走着,璟在后面大步甚至跑着追随。曼兀自走进浴池的那个大弹簧门随即向后甩开了门,忘记了璟就在身后,门重重地弹了回来,门上的铁把手恰好撞在璟的头上,她眼前金星直冒,险些昏倒,曼却大声吼她,你怎么不看路……”张悦然作品中对父母不堪的形象塑造是她笔下女主人公在即有的现实处境中得不到爱和关心的情节设置的需要,更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突然被推向地位失衡时期情感不适的激烈反映。正如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然保持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惹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②
而此时,由于女孩也开始逐渐意识到,长大到一定程度后,在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在父母之外的人在等待着和她建立起另一种类似她父母间的亲密关系。而要顺利地获得这种亲密关系,需要的是她能够获得有吸引人的女性美丽。她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走向社会对她的性别设置靠拢,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除了美貌,不要求他们有别的特长。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容貌的关注会如此入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只有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③因此,在张悦然的笔下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女主人对物质的过度迷恋,如她写到女主人公新买的玫瑰紫色的新裙子“有一层阳光均匀地洒在裙裾上,像一层细蜜的小鳞片一样织在这锦缎上面。它像一只大风筝一样嗖的一下飞上了我的天空。”穿上新买的玫瑰紫色的新裙子“玫瑰骤然开遍我的全身。我感到有很多玫瑰刺进了我的皮肤里,这件衣服长在了我的身体里,再也再也不会和我分开了”。
同时在她的笔下,女主人公们对爱情的追求表现出了近似病态的迷恋,似乎获得爱情业已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目的。《竖琴,白骨精》中作者通过奇思异想构思了一个乐师用他妻子身上的骨头制作各种能发出美妙声音的乐器的故事。乐师无视白骨精的痛苦,整日沉浸在打磨骨头以制造乐器的喜悦之中,而他的妻子在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沦落为“白骨精”的时候,也就丧失掉了自身生存的独立意义,但是,与我们以往见到的女性的奴隶地位不一样,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传统的无所欲求,默默奉献,忍气吞声的祥林嫂般的女性形象。至少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小说名为《竖琴,白骨精》而非《乐师》,以及小说的叙事视角也是从白骨精的视角展开叙述的,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并非处于失声状态。但是,让我们深感惊讶的是,张悦然笔下的女性给自己找到的意义竟然是依附于爱情。如果说,以往我们看到的多是被迫奉献的女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主动请缨的女性,她给自己找到的生存的唯一意义仅在于爱情。白骨精将她的生存的全部赌注都押在了爱情的获得上。因为身体失去骨头的支撑不得不整日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在“丈夫拼命地亲吻她的脸,不断地说,亲爱的,我该如何感激你呢,我是多么爱你呀”的甜言蜜语下,她可以在痛失左肩下的锁骨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芍药颜色”的鲜艳。“很久之后,他才奔向床这边,抱起柔弱无骨地小白骨精,充满怜爱地抚摸着她所剩不多的骨头,用颤抖地声音说,宝贝,你是最棒的你永远是最棒的”尽管她丢掉了右肩锁骨,当丈夫做出“亲爱的你不要难过啊,你失去了所有的骨头又怎么样呢,我永远爱你啊。宝贝你永远是最棒的”的承诺的时候,她会很快认同丈夫事业的价值感“丈夫身后是很多件无价之宝的乐器。小句的它们像大个的家具一样占满了整个房间它们是来自她身上的吗?它们看起来是这样巨大呀”当她的最后一根骨头都被丈夫取走后,她在策划用自己的骨头作为自杀的利器的时候,她把自己已经送给丈夫的骨头看成是丈夫的了,想到的居然只是“我只是借用一下,他不会生气吧”。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个我们自小就熟悉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的故事模式。他们笔下的爱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以绝对美好,真诚的面貌出现,以致于无一幸免地烙上了强烈的乌托邦想象的痕迹。这似乎就是西蒙·波伏娃所谓的“女人的最大的需要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④最佳注脚。
2.无能为力地尴尬
我们能够看到张悦然在塑造女性的美好、优越,除了要获得“讨人喜欢外”的女性“美好”的女性气质外,更在于她潜意识中渴望社会能够对女性性别较男性气质优越的认同。特别是作品《二进制》中对性别错乱的女角男同性恋角色的塑造“他的裙子成功地模仿了我从前的那只,我幸灾乐祸地觉得他没有圆翘的屁股把裙子撑起来。”更是基于她心底深处对女性更美好的认同上。
她让物质装点着自己的同时,也在于她试图通过物质的美好,彰显出女性较男性气质优越的一面。她笔下的物质消费是不同于前辈美女作家们的对物质的失去判断的盲目占有,把“物质消费”误设为自己在新时代下的历史使命,从而颠倒了物我的正常关系的位置,使自己的躯体沦落为物质们精彩亮相的场所,让无机的物质支配了有机的躯体。取代了美女作家笔下以“大麻”、“酒精”、“名牌服装”向我们炫耀物质的物质性作为财富象征。张悦然对物质的关注已不再着眼于物质本身的实用价值和它的物质性所带来的财富价值上,而更多的是看到了物质背后的审美价值。我们看到她在作品中多致力于选择一些精致和华美的物质细节,诸如:马蹄莲、咖啡、气球、陶瓷、美丽的蛋糕、五颜六色的发卡……旨在通过对物质本身审美价值的凸显来印证作为主体的“我”自身存在的美好和诗意。“我”对物质的占有并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我”对物质的挑选。作者试图通过“我”的挑选来展示“我”的喜欢,又正是在“我”喜欢之中,打上了“我”个人的痕迹。当物质的审美价值得以展现的时候,“我”的审美世界才会在一瞬间洞开。那些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物质细节,从精美的服饰到华而不实的生活用品再到甚至毫无实用价值的装饰品,无一例外地成了替作者彰显自我而会说话的物质群落。它们都将带着“我”个人的气息,作为“我”自我经验内容的保存者来帮助我抵抗外界如此浩繁庞大的物质体系对自我的侵蚀。张悦然在其短篇小说《陶之陨》中对“我”和梵小高合力制作的陶不厌其烦地反复描摹“它纯圆,胖的发喘,只有一个指甲大的心形瓶口,我要求它有单薄的罐壁”这种对陶的精心制作,其实正是作者对爱情的一次完美想象:美好圆润。而在张悦然的其他作品里通常出现的“美丽的发卡”,“橘黄色的伞”等它们又都以其色泽鲜丽,耀眼夺目,不同于简单的男性气质。在体现出作者个人的审美追求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张悦然的自我设计:优秀美好,能从人群中走出来。
对爱情的追求中,张悦然也表示出了犹豫,她喜欢能够获得伟大的爱情,但同时,她又无比希望,无论使得她获得爱情的是什么,是她的美貌抑或是她的才华,她只有个那么渺小的愿望,她多么希望她能够在这些爱情中占据一点主导作用。她多么希望,在爱情里,即使被伟大的爱覆盖成为一个失败者,她都很真诚地希望,她能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以此来成就自己的美好和优越。在《这些,那些》中有一段女主人公对自己爱情生活的追忆:“很久很久之后的现在,回想起来,巷子那头等我的人是谁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的头发,脸和功绩都没有这条巷子重要了。等我长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恋的是从我家到那个人身边的这一段路。它们像极了我的一场表演,一场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张悦然在《真话》中写道:“很多孩子确实跑起来了,可是谁又给过他们一场详尽的目光呢……他们在需要关怀的年代没有得到一丝关注,他们平白地自己点着了,平白地那么跑了一场。”在这样一个女性社会性别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里,以张悦然为代表的每一个小女孩的成长之路,在那充满成长的伤疼和迷茫中,她们的每一丝挣扎都以失败告终。
张悦然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社会成就性别的质疑,为女性创作开拓了女性成长的纬度。提醒着我们,也许对于女性创作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女性是如何成为女性的。“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以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⑤在那个孤单无援地小女孩在路口徘徊之时,我们应避免将她引向“美丽动人的爱情小奴隶”也要避免“身体展示”(服装淹没身体、子宫以局部代替了女性的整体形象的性欲展示),我们应该引导她的女性最本真的女性意识,在成长为女性和母亲的过程之前,这些都只是女性的身份之一,而不应当取代了女性存在的所有价值,她应当是美好的,有女性特点的,但更重要的是她是健康和向上的,对女性特征是习以为常的,并以之为骄傲,而不是在性别认同边缘的黯然神伤。
注 释
①吴素萍:《和谐社会的多元创作——二十一世纪初女性文学创作概说》,《名作欣赏》2007年第11期。
②③④⑤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第二性Ⅱ》,中国书籍出版社,第312页、第336页、第336页、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