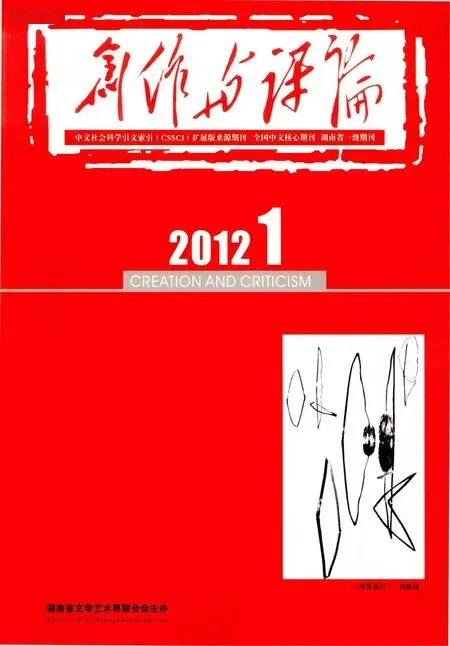像蝙蝠一样穿过夜及夜的黑——徐则臣夜系列小说解读
■ 张英芳
在徐则臣的小说系列中,从长篇《午夜之门》到《夜火车》到中篇《夜歌》,作者近乎偏执地表达着对夜的偏爱和喜好。作为读者我们无从得知作者这种对夜的迷恋和痴迷是出于一种信仰,还是出于一种对缠绕生命和生活的许多让自身困惑问题的追问,但是当我们走入这几个以夜为主题的系列小说的文本中,作为阅读者,那种由于夜意象引起的阅读兴奋像被点燃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彻在热切的阅读欲望中。徐则臣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是蝙蝠的飞翔姿态,是夜莺的歌唱状态,抑或是夜行者的贴地匍匐状态,都成为一个让读者既迷恋其中又企图穿越的一个谜团。无论谜底能否被破解,作者带给阅读者关于生命,关于幽暗的生命,关于渗透了灌注了历史激情和现实宿命的生命的存在状态,犹如一条深埋地下的突突燃烧的岩浆,迸发着作者乌托邦的理想之火。在徐则臣的审美世界中,“夜”之于时间,之于生命,意味着什么,又指向那里,在对夜的不停的追述中展示着作者什么样的内心图景,当我们随着作者穿越夜及夜的黑也许这些问题已经成了答案。
《午夜之门》由《石码头》、《紫米》、《午夜之门》、《水边书》四个部分组成。“我”——木鱼,是整个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体验者,从《石码头》中的“花街”,《紫米》中的“蓝塘”,到《午夜之门》中的“左山”,再到《水边书》中故事重回“花街”,随着木鱼的成长,他所处的环境和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转换,木鱼象一架流动的摄像机不断拍摄着生活的变化,岁月的变迁,人事的消涨,同时记录着作为一个历史个体在历史空间跌宕起伏的命运,通过木鱼的出走,流浪到回归完成了一个个体的成长史,木鱼的成长不仅代表着一个个体心灵的磨难,心智的成熟,更是身处其中的历史变化的一个缩影,这种个体的成长带有深厚的历史胎记,由此一个个人的成长具有了民族变化的历史意味。
在第一篇章《石码头》里,作者讲述了少年的“我”——木鱼,在运河的花街张望着生活,故事从“我”夜晚爬上院落里的一个大槐树,然后看到了很多白夜无法看到的秘密作为开始,从此开始了一个个体的成长之旅,当他用孩子的眼光打量熟悉而又陌生的生活时,他碰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成人的世界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犹如幽暗的黑夜,让他困惑,又让他着迷,有一种探索的冲动。所以后来他经常在夜里爬上那棵大槐树,眺望成人世界。夜在此成为了一个少年探索生活的起点。夜,夜的黑,夜的故事已不单单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一个明确的主题,而且成为一个丰富的意象。透过夜这样一个意象,作者将可见的尤其是不可见的生活真相暴露出来,而这些真相是作为现实的人在阳光下无法面对的,也无法承受的,由此小说通过夜这样一个复杂的意象将生活的阴暗面晾晒出来,也由此挖掘出人性的最深处。当你读到木鱼爬到高耸的大树,阅览着生活中无法看到的另一面时,夜突然显得如此可爱,而不是害怕和紧张。当木鱼看到堂叔和继女花椒之间的乱伦以及婶婶白皮跟酸六之间的偷情,他对成人的偷窥带给他最初的刺激和兴奋变得如此沉重,而当堂叔的另一个继女茴香试图与“我”尝试禁果,由此遭到了“我”的拒绝,这种拒绝既是一种无法面对的害怕,更是一个少年的无所适从,在一个人无法掌控一件事件的时候,逃避成了最好的选择。也许这是作者选择将夜作为小说主题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借口,面对无法解决的却又必须面对的生活,夜成为无能无力的一个光鲜的遮挡,更显示出作者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直视生活,却未必要抵抗,因为有些抵抗对于复杂的生活是无效的,只能更加一败涂地。与其强硬地对待生活的粗暴和戏谑,不如真实挥洒个体对生活的软弱无力,这种真实的投降比抵抗更能显示内心的强大。就像我们面对昆德拉的《生命无法承受之轻》,就像我们面对库切的《耻》,面对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梭罗的《瓦尔登湖》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第二篇章《紫米》讲述的则是“我”离开花街到他乡漂泊的故事,当院落中的那棵大槐树再也无法引起“我”的冲动去攀援的时候,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更精彩的生活成了漂泊的理由,在漂泊的旅程中,“我”无需再需要夜的掩护,可以直面一些故事,因为“我”已经开始长大。“我”看到了大水因与他人争一个妓女而被杀死的生命的陨落,对死的恐惧成为心灵的另一个黑夜,而这只是开始,“我”后来跟随大水生前的朋友——沉禾一起去看守大户人家蓝老爷的紫米库。在这庭院深深的大宅里,下人沉禾与蓝老爷三太太之间的“偷情”,老得不行的蓝老爷把自己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与白猫生活这些溢出了生活正常轨道的事件在“我”那里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刺眼和别扭,“我”在寻找生活逻辑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的悖论,这些悖论就像白天与黑夜的对峙,自然地存在着,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真实情状。在《紫米》中,蓝家少爷与当兵的熊步云的“同性恋”关系更是超越了我们对于生活原本的设定,在浩瀚的生活原野上,驰骋着美丽的白马,也有顽皮的四不像,他们拥有一样生存的权利,谁也无法蔑视生命的这些真相,也无法驱除人心的黑暗,这些人性的深处放射着我们生命内部的“夜之光”。在《紫米》里,夜褪下了黑色的外衣,直接潜伏到人性的深处,同性恋、乱伦这些见光死的情感注定了一种悲剧的宿命。
第三篇章《午夜之门》讲述了“我”在逃离左山的途中意外地救了青年马图,从此开始了“战争、死亡、爱情”之旅。作为切近生命本真的战争、死亡、爱情,“我”在《午夜之门》描述的的历史潮流中已经成年。这种成年仪式的开启是以爱情之门的打开和性的觉醒为标志的。在《午夜之门》中“我”混沌的“夜”的生命状态以爱情的到来和性的体验被打破了,“夜”在此意象的意味已经压倒了夜的主题,超越了《石码头》和《紫米》中夜主题的具象,而升华到生命的“夜”与“光”,也就是“我”的成长已经脱离了蒙昧的“夜”状态,个体在生活的磨练中日益成熟。当“我“在与水竹肌肤之亲后实现了一个男性的性的成人礼,这个时候一个个体的成长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成了两性的一场决斗。而当水竹倒下之后也意味着“我”成人礼仪式的结束,“我”的生命将随着仪式的结束开始真正的行动之旅。作为标记着个体成长的《午夜之门》,“我”在生活的考验中似乎已经穿越了生命的“夜”,对生活的理解达到了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为何要选择“午夜”,这个最黑暗的时分来标记故事的进展,是一种跨越还是一种阻挡,是一种冲破还是一种还原,突然间“夜”的意象倒显得暧昧不清。当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去寻找自己的魔术师丈夫,去寻找属于每个人隐藏在夜里的痛苦时,也许《午夜之门》的意向也在于此。表达一种生命的磨难,一种面对磨难的执着的寻找,寻找一个信念,寻找一种力量,这大概是午夜里最强大的舞蹈者赐予心灵的魔力。
小说的最后篇章《水边书》,讲述的是“我”返乡的故事。“我”在经历了五光十色的漂泊后,企图回到原初的状态,然而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过去再也回不过去了,当“我”在返乡的运河船上,与已经当了妓女的堂姐茴香相逢,一起回到故乡花街时,过去的花街变成了曾经,曾经的花街已经弥散了,而“我”对茴香少年时的拒绝也转变成了一种一起结伴过一种庸常的烟火生活。那个让“我”悸动,让“我”兴奋的攀上大槐树的对夜的迷恋破灭了,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黑夜。即使还有太多关于黑夜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之于老了的“我”而言,已经不再是故事,这个被夜揉碎的故事,暴露出他生活的本真。夜未变,夜的黑一如既往,只是那个在夜里攀援,在夜里进行“成人礼”,活动在夜里的人没了,已经被淹没在琐碎的生活里。一个人的夜晚变成了所有人的夜晚,这也许就是成长,对夜里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秘密,一个人的生活视而不见,却也能做到心平气和,这种生命的穿越是一种成熟还是一种悲剧,答案就凝聚在丰富的“夜”意象里了。长篇《午夜之门》将夜作为一个个体探索生命的起点,在穿越夜及夜的黑的生命体验里来凸显个体的成长和历史的成长之间的关系。由此夜不仅仅只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作者更是将夜作为一个丰富的意象,支撑起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和一种情怀。
《午夜之门》通过一个个体流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人的江湖,《夜歌》和《夜火车》则抽取了一个横断面来深入解剖生命的情态。《夜歌》从书宝和布阳藏于夜里的爱情开始,通过对二人从爱恋到结婚到变故到陌生到渐远串起了整个故事,但这并不是小说叙述的中心,深夜里吟唱的动听的歌声才是小说所聚焦的关键。书宝多才多艺,而布阳热情,美丽,活泼,因而书宝与布阳的相爱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但是他们的恋爱却遭到了书宝母亲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布阳的妈妈曾经在花街做过妓女,另一个原因就是布阳的身份,因为布阳是一介戏子,而书宝的母亲曾经也是一个戏子,她对布阳的鄙视到底是对自己过去的鄙视和告别,还是对布阳夺走他儿子的嫉妒,似乎都有吧。在布阳的母亲患病即将辞世的时刻,书宝和布阳偷偷领证成了夫妻,因此也造成了书宝与母亲母子关系的断绝。后来书宝被迫加入齐云社,他和布阳在一次演出结束后的夜里遭到了带着白面具的对手的暗算,布阳流产,而且神志不清,为了唤醒布阳,书宝的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尤其是在书宝与齐云社的王玉南相好之后,她对布阳的怨恨变成了同情,代替儿子来照顾儿媳妇,两个女人在历经同样的命运之后,惺惺相惜,尤其是书宝的母亲发现唱歌能唤醒布阳的意识之后,她坚持不懈地唱呀唱,在寂静的,寂寞的夜里通过歌声倾诉自己的哀愁,传达自己的爱意。当布阳在歌声中被唤醒,两个女人在深夜里仍在吟唱,吟唱她们的不幸,她们的哀愁,吟唱属于她们自己的那首《水上船》。
《夜火车》,以陈木年晚上由于饱受楼上画家金小异的凉拖鞋声音的折磨开始,开始了陈木年烦恼的生活。很久以来陈木年有一个出逃的梦想,乘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走走看看,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为了从父亲那里骗到出逃的费用,他不惜虚构了一个杀人事件,利用父亲对儿子的亲情骗到了出逃的钱,开始了第一次流浪,这成为了整个悲剧的开始,由于虚构杀人,他被审问,并且毕业证被扣押,而才华横溢本能被保研的他成了一个临时工,因此他被鄙视,被周围的人嘲笑,自己也丧失了主动追求青梅竹马的秦可的勇气,但是在这种夹缝和难堪中陈木年内心涌动的那个乘坐夜火车流浪的梦想一直都在燃烧着,当陈木年所在的城市即将通火车的消息犹如一根火柴重新将他出走的欲望点燃,当小城市的火车试运营的时候,他用尽所有的力气放肆的奔跑,追逐着呼啸而过的火车,他在漆黑的夜里追逐着梦想的亮光,他像失重了一样,扒火车,从小城市到南京,再从南京扒火车回到小城市,代价就是被发配花房做苦力。陈木年放逐了自己的梦想,生活却放逐了他的命运,更令他不可捉摸的是他的精神导师原来也是伪道士,遭受精神困境的陈木年在失手杀死自己的情敌后再次出逃。这一次的出逃终于从形而上的精神需要变成了形而下的亡命之旅。《夜火车》以夜为起点,以夜为终点,生命似乎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这种玩笑和戏谑似的对命运的挤兑和捉弄,是在借夜来嘲笑生活本身的无意义,还是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黑色的幽默,注定要将理想的光芒遮挡住,将一切交出去,交给混沌的夜来主宰,让驰骋在夜里的夜火车将生命带向不可知的未来。在这里,夜既是意象,是要表现的主题,还是为表现而表现的本身。
如果说《午夜之门》中夜的意象还只是作为一种成长的背景,《夜歌》和《夜火车》中夜则直接作为人物和故事推进的一个加速器,夜歌是婆婆为了唤醒与她同病相怜的媳妇的记忆,夜火车则是陈木年逃跑的一个直接的证据,也就是说从2005年的《石码头》对夜的狂热的书写开始,徐则臣自己也在不断穿越意识的黑夜,到2009年,四年之后,他用两个长篇,一个中篇回答了自己对夜的提问,而且通过这三个文本完成了对“在故乡”的回望。不知道徐则臣在回望的过程中是否感到疲倦或者懈怠,感到惊喜或者狂热,作为读者,我们透过这三个厚重的文本,看到了复活的花街,醒来的运河,听到了木鱼的惆怅,看到了布阳的淡淡的哀愁,还聆听到了陈木年奔涌着英雄主义的呼喊,在徐则臣的夜主题系列文本的引领下,读者和作者一起得到了那个“故乡在哪里”“我从哪里来”这个深奥的问题的答案,这是这三部小说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和财富。
当徐则臣将夜作为一个武器横扫生活的真相和生命本身情状的时候,同时扣动了历史的扳手,无论是夜系列的《午夜之门》《夜歌》还是《夜火车》,当个体在浓重的夜里舞蹈自己生活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分子。木鱼是一个具象的回忆人物,还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代表,布阳是现实的存在还是虚构的设定,陈木年是个体还是他者,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作者回忆中的故乡,他们是活在花街历史中,见证着花街斗转星移,见证着运河起起落落的真实的个体。在这三部作品里,当夜作为主题浮现的时候,在此背后历史的幕布也逐次拉开。
历史与现实究竟是为何而共存,现实是历史的虚构,还是历史是现实的倒影,在他们之间是一种历时态,还是共时态,《午夜之门》依托一个个体的成长来展开对历史全景式的陈述,《夜歌》和《夜火车》则是一个横断面,但是无论是全景式还是断面式的,徐则臣在处理这些文本和故事的时候,只是赋予了人物性格的真实,细节的真实,但是时间是不详的,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恍惚之感,这些故事到底发生在哪个年代?读者之所以有这种恍惚感,在于作者对时间的虚化和间离化处理。这种叙事常常让读者在现实与历史中迷茫,这些故事已经发生了,还是正在发生,是已经过去还是就在此刻。当然也许会有人质疑徐则臣是在故弄玄虚,故意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制造一种混淆,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文本中获得了对生命的真实感悟,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那么作者构造的叙述圈套已经不再是难题,当作为读者的你、我、你我随着历史一起共舞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的是文本带给我们的另一种生命体验。
2008年徐则臣因《午夜之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获奖演说中作者有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诠释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是在呈现一部与他有关的‘历史’。因为写作是回忆,正在发生的‘当下’,可能发生的‘将来’,都需要转化为‘过去’才能进入小说。小说在本质上是一个完成的时态。”作为一个作家,在徐则臣的历史中,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往,而且是有体温的,鲜活的,历史的体温还在,那么依靠历史存在,并借助历史发言的现实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勾连,历史到底是想象的,虚构的,还是被记忆风干,然后经由真空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消费呢?在《夜歌》中,当婆婆推着已经神志不清的布阳穿过石码头,吟唱《水上船》,当书宝将萨克斯引入传统的二胡中并且获得新的感受的时候,历史与现实突然联通了,汇合了,他们依靠一种秘密的通道,在被过滤和被筛选中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态”。这就是作家叙述的力量。现实能否穿越历史,历史能否抵达现实的深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的通道,可以无隔阂,无障碍地穿梭,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呢,在《午夜之门》中当木鱼穿行于战争、死亡、爱情,人伦、道德这些关乎人类普遍情感的高地时,历史与现实通了电流,成了接通的导体。当《夜火车》穿过陈木年浪漫的想象,压抑的激情,携带着他奔跑,再奔跑,历史与现实已经重合。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即将过去的历史,现实在与历史的共舞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午夜之门》的木鱼在历史的漫游中,从历史出发,最后回到故乡,终于将历史与现实串接在一起。历史不再是任意的拼贴,他是曾经真实的存在,而现实作为历史的对应,一直在延续着历史。而在历史与现实的连缀中,夜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叙事的空间背景而存在,夜是历史的另一面,也是现实的面影,当历史与现实遇合的时候,夜成为寓意含蓄的一个原点,使得现实与历史实现了感应。
《午夜之门》、《夜歌》、《夜火车》这三个对建构作者的文学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本不约而同地将叙述的节点安置在“夜”,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是作者内心的一种情怀,当这些故事不同的文本被并置在一起进行对照的时候,“花街”、“运河”、“人家”、“码头”、“成长”这些镌刻了作者生命和生活印记的词汇勾连起作者“在故乡”的一种叙事图景,并由此构建起属于“唯一的那一个”的故乡书写。在徐则臣的创作序列中,前期创作主要从故乡出发,通过对故乡的运河,故乡的花街,故乡的人事的追忆,定格凝聚对生命原初的追问——“我从哪里来”,并以此问题为出发点,反复地追问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否存在着秘密的连接通道,历史与现实之于一个单独的个体又意味着什么,个人在历史和现实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徐则臣的故乡系列完成了对这些问题的叩问。而以“夜”为主题的《午夜之门》、《夜火车》、《夜歌》在作者的故乡系列中,在对历史的再现中重现了生活的真相。由此可以看出“夜”在作者的前期故乡叙事中是眼睛,起着点睛的作用。而当作者远离故乡,在北京流浪漂泊,构筑“在他乡”的《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伪证制造者》、《我们在北京相遇》、《三人行》、《天上人间》等文本的时候,“在故乡”不仅是叙事的背景,也是“在他乡”的起点,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后来徐则臣孜孜描述的“在他乡”并没有走出“故乡”,故乡是他乡的影子,他乡是故乡的投射。当作者在故乡中透视历史,透视生命的时候,他寻找到了“夜”作为透视点,通过黑暗中肆意奔放的原野,幽暗的夜里心灵的搏动,拨动着命运的琴弦。而当作者视线远离故乡,依然执拗地书写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大都市的生存状态,但是似乎作者的透视点已经虚化了,至少从目前的文本创作来看,作者在后期并没有找到一个聚焦的透视点,当然这只是个人的阅读感受,也许只是一种阅读偏好,无论是哪种情结在作怪,徐则臣的这三个小说都让作为阅读者的我流连忘返,忘却归路。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
——到壮族花街节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