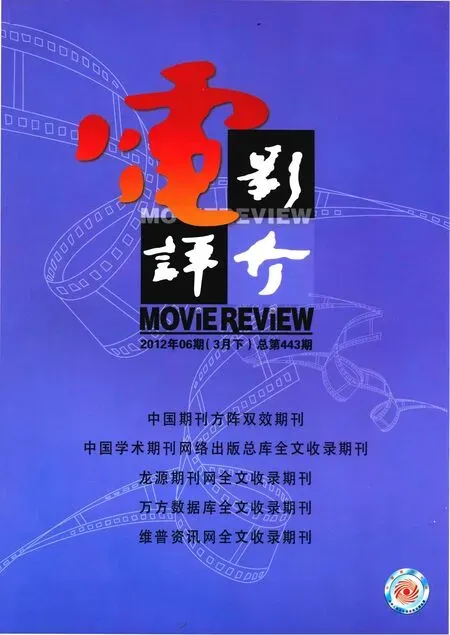论中原文化独特性的文学表现
人们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讲,“中原”一词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地讲,“中原”就是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或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朱仲玉先生的《试论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一文中说:
“中原”这一地域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是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指整个黄河流域,也有人认为禹定九州,九州即中原。本文讨论的中原文化,是指在广义的中原地域内产生的文化。
狭义的“中原文化”则主要指河南文化,如有学者说:
我们研究中原文化,则应从现代人理解的中原、中州出发,主要去考察古代中原腹心地区,即现在的河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种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文化的特点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探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
陈飞先生在《“中原文化”涵义概说》一文中,对中原文化的涵义有精当的评述。按陈飞先生的辨析,“中原文化”有层面高低大小之别。一、“中原的文化”:这是基础的层面,着重于中原“地域”的文化。二、“中国文化”:这是“地域”的扩大,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代表。三、“中原文化”:这是超越的层面,中原已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具有诸多象征的和抽象的涵义。主要有:(1)“传统文化”:由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生活方式等等的主要发祥地和起源点,因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乃至正统文化的主流和代表。(2)核心文化:由于中原是区位上的中心所在和长期的王权所在,遂由现实的四方所归渐演化为天下所仰、万国所宗,于是中原文化也就具有了核心的地位;(3)“先进文化”:由于具备上述诸多因素,文化上的创造和创新也往往发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率先达到最高水平,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先进水准的代表;(4)“根原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意识里,始终认为中原文化是“根本”和“原点”之所在,因此,不仅具有不断产生、再生和新生的生命力,同时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上的向往和归宿之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力地联系起来;(5)“和合文化”:中国人视中原为“中心”乃是将其视为“天下”的中心,因而这个“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天下”,在其为天下所归的同时,也心怀天下,二者的统一便是“合和”:既关怀、开放、通达,又辐射、包容、和谐,所谓兼容并蓄,多元一体;(6)“寄托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原文化包含着全面的、无限多的寄托因素,既是现实的寄托,也是理想的寄托,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精神的寄托;既是回归的寄托,也是发展的寄托;既是个人的寄托,也是群体的寄托。总之,中原文化既像太阳,给大地以生命和力量,也像月亮,引人无限思恋与向往。
河南文化的独特性,河南作家们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在河南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表现。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中,写春义和凤英这对年轻的夫妻从黄泛区逃难到咸阳,咸阳男子张口闭口说脏话,不回避女人。而“在河南乡下,对着年轻妇女,男人们是不准说这些脏话的。”凤英开饭馆,就必须容忍陕西风俗,而春义不能“入乡随俗”,最后的结果是夫妻离异,春义随着一些乡亲回到河南黄泛区,重建家园,凤英则留在咸阳。以前的研究,往往从性格、心理的角度解释这对夫妻离异的原因,认为春义代表的是保守、落后,凤英代表的是先进、进取。其实,春义认为不可在年轻妇女面前说脏话,未必就是保守、落后,相反,春义尊重妇女的理念倒非常符合社会文明化的要求,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至少说,春义顽固坚持的河南风俗和凤英能够很快适应的陕西风俗并没有高下之分。那么,要更合理更全面地看待春义和凤英的冲突,除了要看到春义株守农业、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凤英性格中的现代因素之外,还要注意这对夫妻冲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会解释得更符合情理一些。孙方友的《小镇人物(三)•小上海》也注意到了河南文化和上海文化的鲜明不同。上海知青朱阿歌下乡到颖河公社插队,他“每天穿四个兜的中山服,留着分头,一尘不染,一丝不乱”,吸烟从不让别人,父亲从上海寄来的香肠也是偷偷地独自享用,处处显出小市民的吝啬、个人本位,和“我们豫东那地方人穷归穷,但穷大方”炯然不同。由于地域文化不同造成的不同性格,“小上海”和大伙格格不入,大伙提起“小上海”都咬牙切齿。在这种人际环境下,“小上海”被开除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去挖河,出事故而死。表面上看,“小上海”之死,是一场事故,但从深层次看,可以说是地域文化冲突造成的悲剧。试想,“小上海”如果稍有入乡随俗的观念,对自己的行为和作人风格稍作变通,哪怕在微小程度上“向贫下中农学习”,何至于弄得自己如此孤立,被开除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呢?又何至于在挖河的繁重劳动中出事故而死呢?可见,尽管当时“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宣传盛行一时,而人们自小浸染于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地域文化鲜明印记在短时间内是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的。田中禾的《印象》写二哥娶了一位四川“蛮子二嫂”,在过年祭祀祖先时坚持用四川的做冥钱方法,她与二哥形影不离,即使在生病卧床的婆母的面前还与丈夫搂搂抱抱,亲热狎昵,表现出一个川妹子的火辣辣的性格,这是与河南女子不同的。周同宾的《皇天后土•榴花》写主人公黄小豆娶的四川“蛮子”,十年前到村里相亲时在十几个男青年中大胆泼辣地选中黄一豆,结婚闹房时不怯生,唱民歌“绕着弯儿骂那些娃子们”(想娶其为妻而不得的年轻人),也写出了川籍女子不同于河南女性的特点。张一弓的《东北情话》专门比较了中原人与东北人性格的不同,一位东北的南下干部,坦言他十三岁就在大车店与一位十六岁的女子的风流韵事,三位在酒店饮酒的年轻人真诚地邀请“我”一处共饮,并毫无保留地谈论他们的“相好的”,一位和“我”有着“艳遇”的表面温婉而内心火热的东北女子,都让张一弓体会到东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东北人的祖辈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被迫闯关东,就顾不上包装自己;而中原人因为上千年的诗书驯化,包装得太多太厚太沉,故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刘庆邦和张宇对河南人的独特性似乎有着更精细入微的体察。《到城里去》中,宋家银的丈夫在北京捡破烂被抓,她到北京找丈夫,遇到了很多拾破烂的。宋家银一看见那些女的,就知道是同乡。只有她那地方的人,才在头上包那样的毛巾,才是那样的包法。有两个妇女坐在地上啃干馒头,“这种直接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坐法,也是她们那地方所特有的。”刘庆邦这里虽然写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也反映出作家本人对河南文化的地域独特性的精细体认。张宇反复读王钢的处女作《野花瓣儿》,“就觉得不像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写的”,果然,王钢祖籍河南,但生于湖北,长于江南。张宇第一次见到二月河,就直觉地认为二月河不是南阳人,因为南阳作家“一般来说大都是胸怀大志而认真刻苦的主儿,并且一定是言谈谦虚而谨慎的”,而二月河“却有啥说啥,还有点儿口满,甚至说他常常口出狂言也不为过”。阎连科是张宇的洛阳老乡,张宇能从其作品中读出“河南西部山区特有的生活气息,”“我能够听到我们贫困山区老太太拉响的风箱声,我能够听到冬天里饥饿的老牛的拉长的无奈的叹息声,我甚至能够闻到房前屋后粪堆的味道”,可见作为豫西老乡,张宇和阎连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
河南文化和其它区域文化的不同,在二月河这个“生在昔阳,幼居洛阳,老蛰南阳”的作家看来,更是明显。山西和河南在自然地貌、语言、人文景观、民风民性等方面的不同,二月河都注意到了。“昔阳县是土石岭式的地貌。这里多是旱天,你别想在这里观什么烟雨,树木最多的是荆和棘”。而“整个豫东是一马平川,连个小土包也难以见到”。这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同。简易的腊八粥,是山西的“百合饭”,河南的“糊涂粥”,这是吃食的不同。步行,昔阳人叫“步偏”,我们,山西人念作“俄蒙”,这是语言的不同。“冬天山西人下身穿得厚,上身宁肯薄一点,利索一点,这是既保暖又好干活的。河南人顾上不顾下则下身单,上身穿个厚棉袄。这很适合蹲在墙根晒暖。……倘论起勤劳这一条,山西人似乎强了一点。”“老家的窑洞住起来比河南的舒服”。“山西老抠能聚财”“吃呀!来山西,吃呀!”能聚财和会吃,是山西人显著的特点,与河南不同。这是风俗习惯和民性的不同。由于故乡是山西,又长期生活在河南,故二月河特别留意山西和河南的不同,他的确是道出了河南、山西的不同特点。
[1]刘乃和主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二月河:佛像前的沉吟[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3]张宇:张宇文集[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