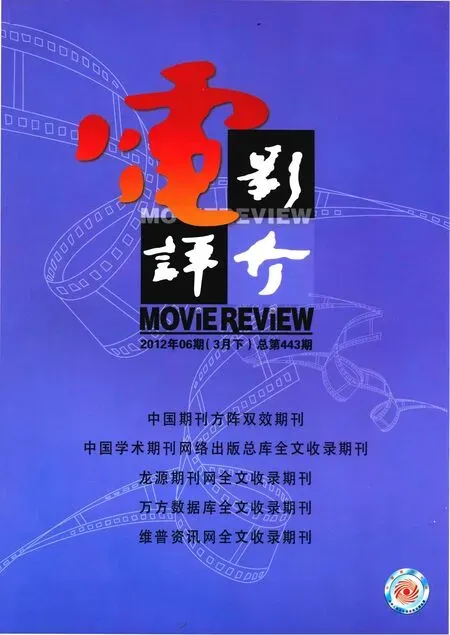艺术的唯美着光——评安哲罗普洛斯的“希腊”三部曲
2012年1月24日,希腊国宝级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在一场意外车祸中遽然离世,为充满末世意味的2012首添不祥之兆。留在他身后的不仅仅是痛惜的影迷,更有他未竟的“希腊”三部曲大业。
在安哲罗普洛斯76年的生命里,电影生涯占据了40多年,他一共创作了13部剧情长片和2部纪录片(除去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后拍摄了一半的遗作)。安哲对电影艺术的忠诚和执着在这个日益喧嚣和浮躁的时代里可称为一抹弥足珍贵的“雾中风景”。他对电影艺术的不竭探索也一直延伸到了他最后的作品里,其对历史、政治、个体、生存、死亡等重大生命主题的思考愈发坦诚、深挚,对各种艺术元素与影像技术的运用、糅合也更为圆转自如、浑然一体。他那辩证流畅的影像语言依然坚守着其一贯的反思性修辞和诗意性画面,但却增加了美学上的晦涩和欣赏上的难度。他并没有进入人们通常所谓和谐、圆融的老年境界,而是更为沉痛地揭示着历史的残酷性,更为彻底地暴露着生命的悲剧底色。这一切都“刺痛”了我们。然而,他要启示的不仅仅如此,对无奈的尘世之爱的信守也许是一种隐秘的希望。
“希腊”三部曲是安哲在完成《一日永恒》(1998年“金棕榈”大奖)之后,歇影四年的回归之作。在被普遍认为其电影事业已臻终结之际,安哲又重新开始了第二次奥德修斯式航行。安哲的睿智目光与勘探脚步越出了从前念兹在兹的希腊,将镜头摇到更为广阔的国际性时空,从希腊到俄罗斯、美国、德国,从20世纪到21世纪,在对历史的史诗性回眸中去重新体悟生命的秘密,去肯定那些最重要也是最美丽的事情:爱、信念以及微渺的希望。
“希腊”三部曲虽未完成,但在已公映的《悲伤草原》(The Weeping Meadow,2004)、《时光之尘》(The Dust of Time,2008)两部影片中,安哲将原定第三部的故事跨度已经讲完。他说,第三部《永恒归来》将是留给未来的一部电影。安哲的离世将这部未来电影永远留在了静默之中。静默是终极的一种属性,但两部影片的观看让我们无法沉默,结束也就是开始。
一、你的名字:共性信念的坚守
名字似乎代表着一个人不可混淆、无法替代的独特性,但它有时也只是个符号,掩盖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在安哲的电影中,同一个名字可以反复出现,穿越不同的电影,像是某些挥之不去的回忆的灵魂在人世逡巡,带着某种神秘命运的印记。父亲斯皮罗的名字成为他多部作品男主人公的姓名,如在《塞瑟岛之旅》、《养蜂人》、《悲伤草原》、《时光之尘》中,父亲多半是背负历史伤痕、与当下疏离的形象;早夭的妹妹伍拉的名字也是《塞瑟岛之旅》、《雾中风景》中姐姐的名字;《养蜂人》和《一日永恒》中的妻子都叫安娜,善良而充满爱心;亚历山大的名字出现在《亚历山大大帝》、《塞瑟岛之旅》、《雾中风景》、《一日永恒》里;在《雾中风景》、《鹳鸟踟蹰》等片中都有出现的亮黄色雨衣先生,总是处于移动中,并不断反复,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个擦身而过的拾垃圾老太太,带着某种神秘的象征意味……名字的延续性和重复性是安哲电影系列的一个典型特色,这一策略与选择也寄寓了其哲学上的沉思和美学上的考量。你既是你,你也是他(她),安哲的“名字美学”要求既要深深沉入个体的独特性之中,这样方能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完整;同时也应尽力扩展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和共通感,这是同情心和悲悯心的基础。这两者共同作用,方为更理想的人性。“名字”其实是安哲的“自我辩证法”。
《悲伤草原》中艾莲妮伏在儿子优格斯尸身上仰天长哭,口里喃喃诉说着“你就是他,你就是你”,那时她想到的可能是她同样死于战争的另一个儿子雅尼斯,还有她那加入美军而死于冲绳战役的丈夫。影片中的艾莲妮少女生子,两个双胞胎儿子因在希腊内战中加入敌对阵营的军队而互相厮杀、双双战死;丈夫怀抱音乐梦想去美国发展却卷入二战冲绳之役而战死;苦苦守望丈夫归来的艾莲妮因藏匿受伤的游击队员而入狱多年,出来时落得两手空空,亲人丧殁已尽,就像她小时候被斯皮罗收养前也是孑然一身。片尾,艾莲妮伏在儿子优格斯尸身上向上苍咆哮哭喊,撕心裂肺,身旁是汩汩流过的河水,冰凉而辽阔。安哲以其一贯节制、冷静的长镜头反复书写着个体生命中所遭遇的巨大孤独、难以抵御的战争和无法扭转的命运,这一切就如他影片中压抑、迷蒙的灰色调和寒冷、凝重的水意象一样,忧郁而苍茫。
《时光之尘》中,艾莲妮1949年作为希腊政治难民逃到塔什干,因和追寻而来的爱人斯皮罗发生情事(被共产党人发现)而被苏共流放西伯利亚。在那里,她与另一犹太难民雅各布发展出同病相怜的扶携之情,但却忘不了所爱的是斯皮罗。艾莲妮1974年获释后即追到美国寻找斯皮罗,与之生活在一起。时光飞逝,步入老年的雅各布不能忘情于艾莲妮,重新见到艾莲妮之后,跳水自杀(详后)。重病的艾莲妮冥冥感应,指尖渗出泪水。这个同样饱受战争伤害、执着于爱情的艾莲妮在片尾仰卧窗前,头部被一束奇异的光照亮,像是悲悯而慈祥的圣母,窗外雪花飘散于天地之间,苦难、死亡和爱情之痛都被这束光融化了。
安哲“希腊”三部曲已完成的两部中,女主人公都叫艾莲妮,而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安哲第一部剧情长片《重建》中,总是那种在历史与政治枷锁下受侮辱、受损害、被压抑却坚强地为爱而活的女性形象。两部曲中的父亲形象也都叫斯皮罗。人物的名字制造出一种想象的故事的连续性和似曾相识的幻觉。我们如果为此入迷,将会强迫症似地去追索《悲伤草原》中艾莲妮的丈夫、出色的手风琴乐手到底叫什么名字,《时光之尘》中的电影导演怎么称呼,从而陷入迷惑,名字是名字是名字……这些反复出现的人名,似乎代表着人性当中可反复书写的某种共性的信念,这也许是作为“现代主义坚守者” [1]P58-60的安哲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方面。后现代推崇差异、不同、解构,而安哲强调的是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这也可见诸他的多次访谈。从他对名字的反复“书写”中可以见出他对人性或命运之中某些共性、普遍性的坚守,这些使他自然地拒绝那种庸俗的线性进化史观,甚至也部分参与了他那悲剧世界观的形成。
穿过孤独、战争和死亡的洞穴,艾莲妮的名字悬挂于安哲晚年深邃思考的星空之下,启示给我们里尔克的诗句:
“主啊,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死亡。
这个死,来自他的生命,
有他的爱、思想和苦难。”
——《时辰祈祷书•贫穷与死亡》之6,(奥)里尔克著,Dasha译
二、时光剧院:“无边界”时空体
就像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时所说,艺术家对死亡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进入作品之中,那悲剧性的维度,带有秋天般的、挽歌似的特质[2]P149。但晚期风格并不承认死亡的最终步调,晚期作品拒绝接受时间,以此来反抗死亡[2]P5, P22。
《一日永恒》曾就生死边界、人生终点这一主旨进行过深度拷问。老诗人亚历山大罹患重病,进入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并没有畏惧死亡,他恐惧的是面对死亡时心灵的空虚、希望的枯竭和无根的漂浮感。[1]P280此时,曾经的爱人和亲朋好友都已离他远去,剩下的只有对旧时光的美好回忆。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如何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与黄外套小流浪儿的接触和交往给了他最后的存在感,并在寻找词语以续写19世纪希腊诗人狄奥尼索斯•索洛莫斯(Dyonisios Solomos)未竟诗作的游戏中找到了超越死亡的幸福感,希望即存在于对“生命是甜美的”这一狄奥尼索斯式肯定之中。影片中对于现实、回忆与虚幻在单个长镜头里的并置呈现已经炉火纯青。老年亚历山大一推开阳台门就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游向海边小岛,展读妻子遗信时年轻时的妻子已站在他面前,“虚幻公车”上不同年代的年轻人交替上来、下去,没有淡入淡出,也不用什么闪回、剪切,不同时期的历史在同一空间里自由穿梭,时间像连续不断的河流在空间里流动。现在和过去、真实与虚幻、客观与主观都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安哲构建的“无边界”时空体让观者在时间的怀抱里畅游无阻,“时间”本身甚至成了多余的概念,纯物理性的时间被超越了。[1]P300
“希腊”三部曲面世的两部对于时间结构的处理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两部电影的开头都用了模拟古希腊戏剧开场(一为戏剧性,一为抒情性)的画外音。《悲伤草原》的开场白沧桑沉郁,富于戏剧性,像荷马式的说书人开坛演述:“第一场。在萨洛尼卡湾的大河河口,1919年前后。一点薄雾笼罩在泥泞的土地上,放眼望去,空旷的如同草原……一群人出现了,缓步前行,带着各种行李。他们的服饰,破旧且满是尘土,却显示出一点旧日的高贵。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在前面领路,和他生病的妻子,他们之间有两个孩子,他们的五岁大的儿子,和一个女儿,比婴儿大不了多少。小女孩时常把手伸向哥哥。当他们到达河边时突然停了下来。河对岸有人冲他们叫喊……”紧接着插入片中人物的对话,画外音再次加入,添加背景信息:乌克兰敖德萨被苏联红军占领,城市毁于一旦,这群希腊裔族人逃到萨洛尼卡湾大河河口人烟稀少的绿地,建起村庄,故事由此开始。实际上,影片主要人物在开场的画外音中都已出现,领头的男人是族长斯皮罗,他在妻子病逝后欲强娶已长大的养女——也就是那个时常伸手拉哥哥的小女孩——艾莲妮续弦,但艾莲妮与哥哥早已暗结连理,并偷偷生下了双胞胎儿子……。故事整体上遵循了线性时间顺序,但由于情节模拟了好几个希腊神话而使得故事意蕴大为丰富,并在现实和神话的回溯、对照、引用中让线性时间不断分岔、折返,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这是否预示了安哲未及完成的第三部《永恒归来》的意图?艾莲妮、养父斯皮罗与哥哥三者的关系可明显看出对《俄狄浦斯王》的影射(哥哥注定要弑父娶母);《七将攻忒拜》中俄狄浦斯两个儿子发生争战的故事则应验在了艾莲妮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身上;还有艾莲妮和哥哥送养父遗体回村时,夜半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族人围着篝火跳起祭祀舞蹈,以为“黑暗的诅咒已经降临”,因为希腊神话里大洪水是宙斯对人类罪行的惩罚。
相比《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的片头画外音则抒情而诗意:“没什么会结束,一切永不结束。我回到尘封着往事的地方,在时间的灰烬下失去了当初的纯净,却又突如其来地在某个时刻浮上水面,犹如梦境。一切永不结束。”这个“我”的声音应该来自片中的那个电影导演,他的抒情性声音在片尾——老斯皮罗牵着孙女小艾莲妮的手在雪中迎着影片画面奔跑时——再度响起:“外面在下雪,雪花静静落下,城市仍在沉睡,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运河之水流淌,流过逝者与生者。旧日已逝,时光荏苒,天地默然……”这也把影片显示为片中那个导演的作品——影片中的影片,剧场中的剧场。安哲曾自述其影片设想,“《时光之尘》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斯大林去世时刻的俄罗斯,就是他在电影厂里的冲印机上看到的内容。从那儿开始,他进入了想象。他不知道这部电影会怎么结束,他试着寻找,搜索记忆、想象未来,自己进入故事,所以他也成为电影里的一个角色。”[3]其实,“戏中戏” 的结构安哲在早期的《流浪艺人》中已经实践过,片中的流浪剧团走街串巷表演希腊人家喻户晓的剧目《牧羊女高尔芙》,安哲将这出戏剧的表演与国难家仇、俄瑞斯忒亚神话结合起来,呈现了戏剧、历史、神话的三层重叠。[1]P117
《时光之尘》开场不久,1999年大年夜前夕,那个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他在指导乐团排练片中要用到的音乐时提到,他的影片中有艾莲妮,“艾莲妮会说:‘最近我每天早上醒来时,水从我手上滴落,有那条河的味道。’”到了片末,雅各布来向斯皮罗和昏迷中的艾莲妮道别,雅各布说:“活在过去里,却无法再回头,这对我来说,才是事实。我不会泪流成河,悲伤时我会想起艾莲妮。”说完离开去乘船,在凄风苦雨中从船上跳水自杀。艾莲妮突然醒来,说新年到了她要布置桌子,然后数点亲人座位。但是数到雅各布时颓然而坐,伏案不适,指尖滴水,像是泪珠。这似乎就是那个导演设想情节的再现,但那个导演也是影片中的人物,艾莲妮就是他的妈妈,这些人物到底是在“表演”还是在真实地生活?
而且《时光之尘》采用了比《流浪艺人》的历史回环“编年体”(从1952年倒回到1939年,中间偶尔再回到1952年)更为复杂的书信纪年体。它由艾莲妮写给斯皮罗的信、导演写给妈妈艾莲妮的信中所提到的时间与事件来组织情节线索,人物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来回穿梭:1999、1953、1949、1999、1953、1956、1999、1974、1999、1974、1989、1999; 有 时是过去情景的客观再现,有时是人物主观视角的内在想象。如1989年11月10日,柏林墙被推倒后一天,导演和父亲斯皮罗于午夜找到妈妈艾莲妮工作的多伦多的安大略酒吧(Ontario Bar),一开始艾莲妮不愿现身相见(当年,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年轻艾莲妮手拿写有斯皮罗地址的纸条到纽约寻找斯皮罗,发现斯皮罗已有妻室,当即离去),斯皮罗在空旷的酒馆内向艾莲妮求婚,当他夺门而出时,爱莲妮追出叫住他,二人相拥热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注意到,镜头里的斯皮罗一直是现在——也就是1999年的老年斯皮罗,而艾莲妮却是年轻时的她,这是为何呢?这一幕之前是1999年12月31日大年夜将至,艾莲妮、斯皮罗和雅各布三人走入柏林街头一家小酒馆,庆祝新年,是这家酒馆的内部空间让老斯皮罗想起了当年的安大略酒吧,他径直走入了当年那一幕,镜头呈现的是发生在他想象的记忆里的,但镜头没有任何切换。时间没有被切断,它一气呵成,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这是蒙太奇或其他高科技特效所无法实现的,属于安哲的独特创造。一头一尾的画外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时光剧场,其中真实的虚幻化了,虚幻的却如此真实,时空浑然一体,往复流动,循环不已。因此在片尾,雅各布和艾莲妮的死接续的是小艾莲妮(原是问题少女,离家出走,曾想跳楼自杀)的新生:老斯皮罗牵着小艾莲妮的手在飞舞雪花中向着镜头前的我们跑来,慢镜头中两人的表情和脚步一样欢欣而轻快。
三、两滴泪:超现实意象
安哲电影中那种似真似幻的超现实性一次次震撼着我们,它并不借助炫目的好莱坞特效,也无意哗众取宠,追求“眼球效应”,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貌似不可能的奇迹和启示,徘徊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这些意象并不是梦境,而是与现实相关,是现实的奇特时刻。如《雾中风景》中从海中吊起的巨大石手雕塑、突然降落的雪和死掉的马,《一日永恒》里边境线上那地狱般的场景……它们把一种超越性的梦想给予了我们,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平庸与恶。
在《悲伤草原》和《时光之尘》中,安哲的超现实手法仍在继续。如《悲伤草原》里,作为老父亲形象的斯皮罗之死,伴随着一只只吊挂在树上的死羊和淹没村庄的洪水,这里死亡隐喻着罪恶的发生和神的惩罚,足以震慑老百姓的人心,却阻止不了罪行的继续发生;工会领袖尼科斯被法西斯士兵枪杀,鲜血染红了铁轨与海岸之间阵列似的白色幔布,让人感到白色恐怖那蔓延开来的压抑;艾莲妮的丈夫带着与她约好的美好梦想,死在了太平洋最后一场战役中,梦中的绿色草原成了永远无法到达的源头;艾莲妮的两个儿子则死得荒诞而无辜,只因隶属于不同的阵营而不得不互相残杀。艾莲妮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死亡吞噬,爱在死亡面前只是无言而无助的哭泣。这是政治的捉弄,也是命运的诡谲。艾莲妮的梦中草原流的是绝望之泪。
《悲伤草原》中,生命在战争机器的铁蹄之下脆弱不堪一击,短暂易逝。《时光之尘》中,人仍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是政治波涛中一片载沉载浮的树叶,但是爱更坚韧、更顽强地突破死亡的围追堵截。雅各布一生中经历了西伯利亚流放、集中营的恐怖残忍和亲人接连不断的死亡,但他活了下来,因他不能忘怀对艾莲妮的爱。雅各布曾说他是“活在过去里,却无法再回头。”过去对于他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死亡帮他卸下了这一负担,不失为一种解脱。艾莲妮心里有更多的爱,她的斯皮罗,她的雅各布,她的儿子和小孙女。《时光之尘》中艾莲妮死时头部出现的圣洁光芒,好似慈悲的圣母。在感应到雅各布去世时,手指尖滴出泪水。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意象,给我们以悲悯、希望和爱的指引。
《悲伤草原》呈现的是一个完全悲观绝望的人世,艾莲妮所爱的人——丈夫和两个儿子——全都在战争中死去,她自己也因政治原因遭受多年牢狱之苦。她那唯一的慰藉——如果算是慰藉的话——只有她丈夫从冲绳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他俩儿时的梦想:沿着河溯流而上,找到河的源头,那里有青青绿草沾着露珠的草原,那是最初的美好世界。但她在现实里能握住的只是儿子冰凉的尸体和漠然流过的河水。她已无人可以爱,无人再去惦念。到了《时光之尘》中,生活的颜色稍显明亮了一些,虽仍充满战祸、流放、牢狱之灾、家庭烦恼,但主要人物都被爱包围着,鼓励着。他们经历了一切,活了下来,并将爱的微弱光芒作为希望传递给下一代。
《悲伤草原》里故事的时间跨度从1919年到1949年,《时光之尘》则涵盖了1949年到1999年,时代在发展,但总有摆脱不了的阴影。安哲如果拍了第三部,将会如何?死亡并不是终点,此时的安哲也许会说,重要的不是如何去死亡,而是学习如何接受死亡的必然性,并与之交友。[4]秘密就在于把无情的历史变成有情的时间,这需要爱及其所提供的希望,它们是时间的眼泪。
注释
[1]诸葛沂:《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阎嘉译:《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6月。
[3]李宏宇:“别要求电影做它做不到的事——专访安哲罗普洛斯”,《南方周末》,2009年2月18日。
[4]哈罗德•布鲁姆:“论诗人们最后的诗”。本文是哈罗德•布鲁姆为他编选的《直到我停止歌唱:最后的诗选集》(Till I End My Song: A Gathering of Last Poems)写的序言,由豆瓣网友mouse翻译,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note/19915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