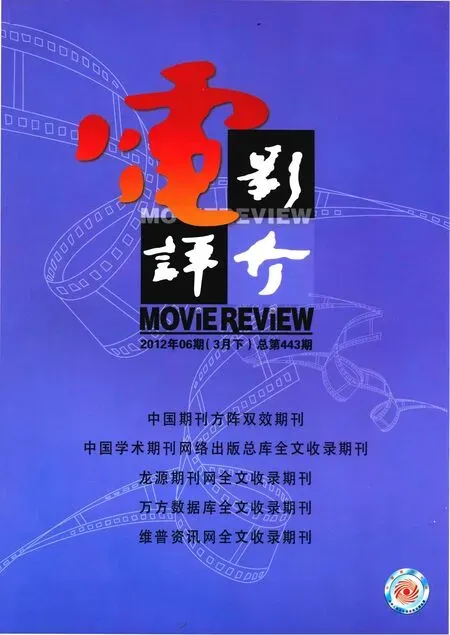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浅析西班牙电影《捆着我 绑着我》
里奇,23岁,刚刚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三岁时失去父母,性格凶猛单纯,偷窃技术很纯熟,建筑、水管手艺也不错,和精神病院女院长还有女护士寻欢作乐,但是只爱着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演员。
玛丽娜,色情片女演员,艳丽而又寂寞,吸毒,经常牙齿疼痛,有一个叫罗拉的姐姐,脑海里设想过的爱情绝对不是影片里描写的这样。
里奇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后,就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一个妻子,组建一个家庭,以及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为了得到玛丽娜的爱,里奇用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办法——绑架她!用暴力制服心爱的人后,他开始诉说自己的爱意:“我今年二十三岁,有五万比塞塔,在这世上我孤身一人。我愿意做你的好丈夫,你孩子的好父亲。”在面对玛丽娜“你想侵犯我吗”的逼问时,里奇一厢情愿地说出了“就是希望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的”的呓语。
但是当里奇一次又一次的为玛丽娜的牙痛和毒瘾冒险时;当里奇温柔地把束缚玛丽娜的绳子和封口胶都换成最柔软的那种时;当里奇最后一次出门去弄海洛因前,把玛利娜捆绑在床上,打开天花板上的遮蓬,说“你一边看星星,一边等我回来”时,玛丽娜已经慢慢沦陷。当里奇遭遇流氓报复,遍体鳞伤地回来,玛丽娜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爱与欲望,两人疯狂地做爱。里奇成功了,他不仅得到了玛丽娜的肉体,也得到了玛丽娜的心。当姐姐罗拉发现了被绑架的玛丽娜并带她逃走时,玛丽娜手上还紧紧抓着里奇最初送她的礼物——一盒心形的巧克力。
其实早在影片的最开始,里奇便完成了从前俄狄浦斯阶段向俄狄浦斯阶段的转变。这个心理过程由弗洛伊德提出,被女性主义理论家伊丽莎白•格罗茨被阐述为“父亲禁止孩子与母亲的(性)接触,由此,父亲控制了孩子对母亲的要求和接近母亲的途径。男孩意识到,父亲是潜在的阉割者;自己要求母亲的爱和关注,但遇上了父亲这个(无可挫败的)对手。他把父亲(或母亲)的禁令理解为阉割威胁,由于惧怕失去自己的性器官,即惧怕父亲作为阳具‘拥有者’的权威与权力,这些威胁最终使得他断绝对母亲的欲望。他现在认识到,母亲是被‘阉割’的,男孩牺牲他与母亲的关系,作为交换,他认同由父亲授予的权威。通过压抑欲望,‘打碎’那种俄狄浦斯式的依恋,男孩内化了象征性的父亲的权威,开始形成超我。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上,通过最初的压抑行动而完成的。”[1]
影片一开始刻画的里奇与精神病院女院长的暧昧关系正类似于男孩对于母亲的依恋。女院长在里奇离开前泪眼婆娑地说:“但自由也意味着孤独,我不能再照顾你了。”这意味着里奇与母体的分离。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电影片场里,里奇开始偷窥玛丽娜之前有一次小偷小摸,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个假发并迫不及待的将假发套在自己头上,并且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形象。这个体现其恋物癖的细节隐喻出里奇在与母体分离后“男性气质”确立起来了,同时他自身也通过观察镜像中的自体形象意识到了。
“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性别化身份的公开,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主体产生‘阉割恐惧’。通过窥淫、施虐和恋物维持其情欲载量。”[2]自然而然的,里奇的欲望对象由女院长转变成了玛丽娜,并且整个绑架过程是典型的窥淫、施虐和恋物的过程。绑架过程中里奇对玛丽娜几乎寸步不离,目不转睛地凝视,为了控制玛丽娜,里奇也不乏使用暴力手段例如殴打、捆绑等。
玛丽娜妖艳又性感,并且有一个那人浮想联翩的职业——色情电影演员。在男权体制下,这个尤物具有文化赋予的充分资本成为男人的“性幻想对象”。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里奇对玛丽娜的窥淫,也可见于半身不遂的老导演马克西姆对于她的追随,尽管这种意淫和偷窥被玛丽娜所不耻。
与此同时,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里奇对玛丽娜的偷窥始于电影片场。
这种偷窥不仅仅是男性对其“性幻想对象”的窥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众与银幕关系的体现。这时的男主人公里奇本身也是一个电影的观众,他具有自体男性气质形象和电影观众的双重职能。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凝视的对象是双重缺席,因为对象是被银幕形象再现出来的,尽管与此同时它感觉上的‘完满’使之显得更‘真实’。”[3]这说明电影里的主人公和电影观众在空间上以及时间上是相互缺失的,“电影快感也被认同于‘恋物癖’。电影观众既认识到又否认不在场,而这正是电影银幕所投射的形象特点。我们都是既‘相信’电影的虚构,同时又明白它‘不过是电影’”[4]。电影观众要获得快感就要在窥淫的过程中把自体欲望投射到电影主人公的身上。
玛丽娜在被里奇偷窥的同时,也完成了被观众窥淫的过程。这一过程使真正的电影观众对男主人公的认同更加自然。更加顺理成章的,当里奇绑架了玛丽娜时,他们可以把自己假想成里奇,从里奇对整个绑架过程的控制和窥淫的主动性中获得快感。
在影片发展到玛丽娜被绑架之前沐浴的那场戏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女性自慰工具。作为一名色情片演员,按理说欲望的宣泄与放纵之于玛丽娜应该如家常便饭,但这个自慰工具的出现恰恰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玛利亚对内心性欲望的强烈抑制。回归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发现,在阐释女性性倾向表现之时,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女性在由前俄狄浦斯阶段向俄狄浦斯阶段的过渡过程中没有经历“阉割恐惧”,因而其具有“性抑制的天性,女性的性潜抑倾向也较之男性更为明显,性冲动亦多呈被动形式。”[5]这也使女性的被动性成为受虐的心理基础。玛丽娜在浴缸里自慰的场景已经为后面整个绑架过程(即受虐过程)之后义无反顾的爱上里奇埋下了伏笔。
波伏娃的《第二性》中阐述了“真正的女人”要接受自己作为男人他者的身份。她可以拥有什么力量要通过她的被动性和自甘卑贱来得到:“她从自甘接受极度征服的受虐癖中得到快感” [6那么玛丽娜从被绑架最初的反抗到最后心甘情愿地与里奇媾和的过程也就是她慢慢在受虐中感受到快感,并确立对这种快感认同的过程。
波伏娃还认为,妇女与压迫她们的文化串通合谋,她们没有“自己的宗教或诗:她们依然是通过男人的梦想来梦想的”[7]。 里奇曾说过:“我的生命是一幅地铁图。在你之前,我的生命是不正常的,除了逃跑就是回到精神病院去。可是遇上你,法官说我痊愈了,可以得到自由了。我的终点站是,玛丽娜!”在这个层面上,玛丽娜似乎是里奇的梦想。但是到影片最后,逃跑的玛丽娜说服姐姐罗拉与自己去里奇的故乡寻找他,因为在此之前里奇告诉带玛丽娜自己的梦想就是带她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玛丽娜最后还是身不由己的把自己融入了这个男人的梦想,深深陷入了这场温柔的捆绑。
纵观整部影片,女主人公玛丽娜都是以一种被窥视的状态呈现在在男主人公和电影观众面前,她的反抗最终淹没在里奇充满男子气概的征服之下。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出发,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动地位在这部影片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1][2][3][4](英)休•索海姆著.艾晓明等译.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3,6,71,71
[5]隋少杰.弗洛伊德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启示——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性别”阐释.河北学刊,2007:27(1),233
[6][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19,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