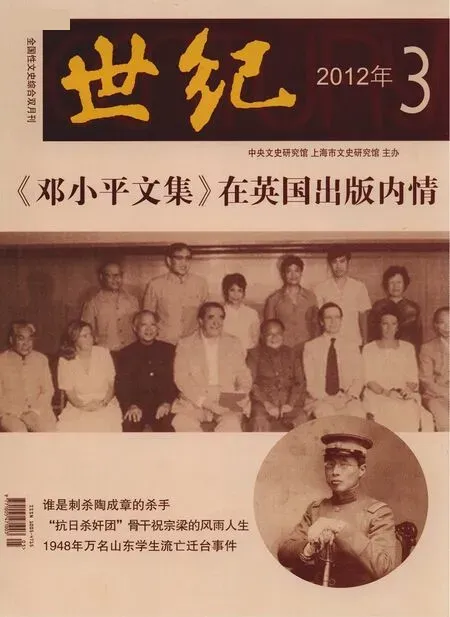抗战时我在重庆的蜗居生活
徐之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名誉所长)
妻在路上奔波月余,经闽、赣等七省到达重庆
1942年夏,日寇从杭州沿浙赣路南侵。先陷我妻读高中处义乌,继陷金华、衢州、江山,一直进到浙闽边境的仙霞关,才因败兵撤退。日寇在我乡进兵时,怕有抵抗,所至之处,先炸后烧,沿途许多地方,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我妻娘家广渡,在通往仙霞关路上,也遭同样命运。我妻父兄,日寇退后也无家可归,只得分散居住荷宅边、保安、廿八都三处的仓屋里,生活十分困难。我家虽在日寇后退的路边,但日寇仍一路烧杀掳掠,村中多人被杀被奸,许多房屋被烧毁,我家也被洗劫一空。逃至距我家20多里廿七都源深山避乱的我妻及家人,一时也不能回家,生活十分不安全。
是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其住房正好空着,我便与同学、同事、好友严晋(君默)迁入暂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便寄了一封书信叫妻前来重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路上奔波月余,经闽、赣、湘、粤、桂、黔、川七省,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严晋只得去住宿舍,妻便和我团聚在一起了,久别重聚,其欢乐无以名状。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要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四哥他们那组房子,是他和二哥及其妻舅王学素共同建造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北的一座小山半腰处,马路南就是冠生园及资委会办公处。这组房子是标准的抗战时期“临时住房”。梁柱是木头的,屋顶是瓦的,但墙壁是竹篱笆糊上水泥构建而成的。共有五间,三间在较高处,是王家人住房,两间在较低处,是二、四哥的住房,旁边有个石岩,筑有坚固石墙,有窗户采光,当时供二哥的“勤务兵”居住。日寇空袭时,供三家避乱用。没有自来水,三家用水全靠此勤务兵从下面嘉陵江挑来。我和妻在此安居了两月余,不久四嫂回渝,我俩不得不迁入各人的单身宿舍暂住。1943年,日寇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华东较为平静,学素舅调动至浙江省任省府委员,二哥也去闽任“东南区银行监理官”,四、五月先后离开重庆,四哥在朝天门上班也十分不方便,他们协商后便将这组临时房子卖了。四哥在林森路另租了一间房子住下,静候中信局高职公房的落成。
我们在重庆重聚不到两个月,就分居两处了,想想真不是滋味。但上班仅数月,没储蓄,租房子要花费很多,又不想借债,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我们想到旅馆团聚,得知有许多人租小旅馆安家,我们算算月收入,觉得还负担得起,便找到一家小旅馆租房住了下来。此处在两路口旁一个小路边上,下面是一个小山谷,房子靠马路是用地板和竹子搭成的高脚楼,数人同时走进去,便有摇摇欲坠之感,很不安全。但对我们来说,可以每天住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夜里,妻突然叫着惊醒,对我说她爸追她用泥沙撒她,是不是爸爸病了?她很担心。奇怪,不数日,就接到她爸去世的来信。自从日寇烧毁了岳父家的村子以后,岳父一直住在廿八都的仓屋里,生活当然不如前了。妻来重庆时,曾路过廿八都,但因随人行动,无自主权,只住了一夜,竟未能去向父亲辞行,真是悔恨终身。
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们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

1945年夏,徐之河在美国留学期间游尼亚加拉大瀑布时留影
1943年9月,中信局高职公房建成了,二室一厅,在当时重庆,算是高级住房了,四哥一家便匆匆搬进住了。他们原租住的林森路房子,则让给我俩居住。住房在一个传统帽店的楼上,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有一排临街窗户,街上人来人往,人声噪杂,但对我们这对渴望有个窝的乱世小夫妻来说,无疑是个天堂。妻特别兴奋,用刚到手的工资,买了一个床、床头柜、写字台、四只凳子以及锅碗煤炉等物,一个小家庭就建成了。自从有家可归开始,我和妻有过一段胜似蜜月的美好时光。家在重庆市中心的山下,要到市中心如不坐车走小路,要爬一个山坡。这个山坡上植有草木花,算是个公园,休假日我俩常去闲坐散心。家离长江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每当明月当空,我俩便去江边溜达闲坐,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我们常一起到附近温泉家庭浴室洗浴休息,这是重庆特有的,别有一种风味。
妻是小女儿,在家没有做过家务事,嫁到我家后由于母亲的偏爱,也只做过烧火等粗事。为了吃饭,现在我们要自己烧煤炉了,妻从未生过小煤炉,我从单位分到的又是硬煤,生煤炉成了我俩的难事。有一次,妻好不容易生好炉子,忽然有个同乡要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晚饭,临走时妻舍不得让煤炉熄灭,我却怕出去数小时不安全,竟强行用水把火熄灭了,从而使我们争吵起来。记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妻脾气耿直,但知道我脾气急,总是忍着让我的。这次的确是我不对,人家花了多大的气力才生好火,你竟无理的强行熄灭,还用水去浇。
小家庭组成后,妻白天上班,回家要做家务,晚上还要到重辉法商学院上夜大,十分劳累。记得有一次日机来袭,她睡得很熟,我叫醒她进防空洞,她说她太累了,她不想逃,她命很大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一定要她逃,最后还是进防空洞了。在洞中她告诉我她逃日寇的经历。那是1942年夏,她还在义乌读高中,听说日本人来了,她和几个同学乘小舟逃命。日机追逐她们,并向她们开机枪,她们把头蒙在被窝里。及日机走,她们发现,一串子弹,打穿了棉被,真危险。
妻没有理家的经验,却把我们这个小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同她爸一样好客,凡是到过我家的人,都喜欢再来重访。记得有几位哥哥们的朋友,有的虽是身居部长级的高官,但因工资增加大大落后于通货膨胀,收入有限,却又自命清高,穷得连家眷都养不起,平时只靠护工在办公处烧一点好吃的。见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可以起火做饭,他们更知道妻父的为人,加上我妻儿和她父一样好客,星期日他们常常带了小菜和酒,约几个常来我家的老友,到我们家来吃饭谈天说地。他们当时大约五六十岁,清高骄傲,目空一切,但很喜欢我们,把我当作弟子,把妻当作儿女。有一个高官甚至要妻叫他干爹。妻不习惯此事没有接受。一个同乡同学女友听说此事,说妻真呆,如果是她,早就认那高官为干爹了。当时常到我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李、郑、严、陈等,妻的女友邵某、戴某等。李、郑、严、陈常到我家吃饭,有时我们工资用完,他们就把我们请到外面吃火锅之类。有事他们总是帮忙做。在我成家时,李兄陪妻去买马桶、锅子、扫把,并帮她搬回家。有一次妻的鞋子坏了,陈还找出榔头、老虎钳给她修呢!我同邵某等也亲如兄妹,亲密无间,有时竟做出现在想来不可理解的事。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戴某忽来我办公室,说是和家人闹意见(当时她父在外地工作,她寄居在一个亲戚家中),要到我家暂住,我便把钥匙交给她,她说房东不认识她,恐进不去,要我陪她回去。我竟不假思索跟她一起回家了。她到我家后说:昨天未睡好,竟脱衣上床休息了。我只好坐在窗前读英文,直到妻下班回来她才起床。小邵更常到我家留宿,有时挤一床根本没有想到此事有何不妥。小戴在我留美时因病去世。小邵在解放前夕,经沪去其夫处,即失去了联系。李、陈在数年前去世,严、郑等同学,迄今还有往来。
去美国留学,又与妻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年冬天,政府公开招考公派留美学生,我报名参考并考取了,我先是要复习功课备考,后又要复习英语准备出国,家务全部落在我妻身上。她白天上班,回家料理家务。那时我妻年轻漂亮,有个同事竟跟踪到家里来,看到我始知妻已结婚,便自觉无趣地走了。对此,我并不介意。青年男女,总有异性追求,只要自己立场坚定,是不会出乱子的。

徐之河在上海华东医院花园(时年95岁)
1944年春,政府为了拉拢我们这批百多人的公派留学生,要我们进中央训练团,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听说受训期间,不能随便回家。我们这对小夫妻经过近半年多的小家庭生活,真是如胶似漆,哪能忍受一个月的分离。当我拿着行李坐上马车开路时,妻恋恋不舍,泣不成声。手攀着车后档跟着马车奔跑,见此情景,我也流下泪来。到团后当即写信,表述别离之痛。这次集训,受到了一部分反国民党人士的攻击,说国民党是给我们洗脑,并告到美国参议院去,要美国不要给我们签证。结果使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等待时间,到九、十月份才恢复签证。
在我出国前夕,大约是1944年10月,我和妻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以后我一直保存着。到美国后,我把它反拍放大,放在房间里,天天看着。我回国时把它带了回来,1947年秋我们有了新居时,把它挂在客堂中。1956年秋,我们迁入河滨大楼,又把它挂在卧室里,一直到现在,已成我们恩爱的象征了。希望它能永远陪伴我度此一生。
在上飞机去印度那一天,妻一起来就两眼泪汪汪。恰过了近两年的恩爱生活,现在又要分离了。美国是那样的遥远,连做梦也要远涉重洋,在这战火弥漫全世界的时刻,何时才能再团聚啊!我口中虽安慰她说:一两年就会回来的,但心中的确也无底。回想我已忍心两度离别爱妻,远去重庆,现在第三次还要远出重洋。我真是个只重学业、事业,不重爱情的俗夫啊。在菜园坝飞机场上,妻哭个不停,连怎样告别也记不起了,我也痛哭失声,无言以对,挥挥手就告别了。那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大约只能坐十多个乘客,经昆明加油后过喜马拉雅山,再在缅北某地加油后直飞加尔各答,到印时已是次日上午了。为了早日到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孟买。等了近一个月,才乘上去美国的运兵船。在去美的船上,妻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夜里睡在床上,有时还似乎听到妻叫我的声音,有时看到她在做饭,有时在撕我的脚皮,梦醒后茫然若失。船经印度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到美国洛杉矶。在船上足足有一个月,12月底才辗转抵达纽约的。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多的留美生活。
——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