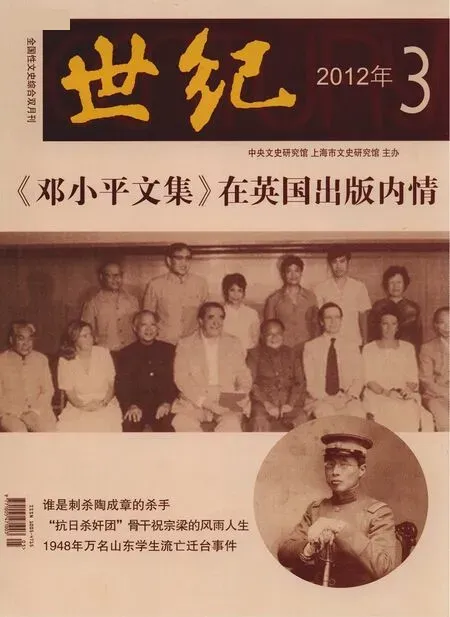为盟军当翻译的难忘经历
陶 昌
(作者原为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中方董事副总经理)

作者近影(陈发奎摄)
我时常回忆起曾在抗日战争后期为盟军当翻译的一段难忘的从军经历——
为杨中尉做随军翻译
那时我二十刚出头,在重庆中国银行工作,亲眼目睹日寇狂轰滥炸,老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对日寇的暴行十分愤恨,但一时无法直接抗击日寇,随着二战深入,机会终于来了!美国军队作为盟军来到中国战场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打击日寇,大批美国军事人员包括多兵种的部队陆续来到,语言沟通是一大难题,迫切需要一大批懂英语的翻译人员配合工作。当时由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从事涉外工作的海关、航空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征调一批合格人员前往受训——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招募消息,立即报名参加了考试。由于我在母校金陵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经过考试,被录取,后外事局向中国银行以征调的方式让我参加了在重庆复兴关举行的中央训练团1944年第三期译员训练班,接受为期六个星期的短期训练。
在受训期间,军事化管理相当严格,英语课程共40课,教材由美军编写,由美军军官课堂讲授为主,辅以会话训练,内容都偏重于军事术语。由于我们过去从没接触过军事,感到十分陌生,只有靠死记硬背,特别是美国人喜欢把英语简单化,惯用俚语,尤其在军队中常用军队俚语作为口语,开始时不仅听不懂,也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但学习也就此匆匆结束了。
记得结业时蒋介石到场,发给我证书和赠送了中正佩剑。次日,就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集合,由美军飞机把我们分批送往昆明。当我们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时,早已有美军卡车在等候,将我们送往北校场译员管理处集中,听候分派。其实当我们在重庆结业时,早已根据我们的英语水平、工作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分派到战略服务部O.S.S.(Office Strategic Service)、中国作战指挥部C.C.C(Chinese Combat Command)、后勤部 S.O.S(Service Of Supply)等三个部门。我被派往C.C.C. 具体分配在14th Air Force Ist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Squadrom第十四航空队第一技术联络分队,担任杨中尉的随军翻译。
说来也巧,这位杨中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竟然是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可是他不会讲中文,也不识中文。据他说祖先是广东的移民,但对乡土一无所知,为人幽默,也很真诚。十四航空队的前身就是抗战初期陈纳德的美国飞虎志愿队,曾协助中国在华中、四川、西南战场的空战中打击日寇,屡立战功、久负盛名,美国参战后,就改为美军编制,正式成为美国空军。
从生疏到熟练的合作
十四航空队除了配合中国军队地面作战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空运任务,就是在滇缅公路尚未打通时,中国战场所需的物资、装备,特别是汽油运输全靠他们,他们从缅甸、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当时称为驼峰),是历史上有名的危险飞行,不少人员因此丧生,英语称为Over hump Flight(飞越驼峰)。我随杨中尉到后勤部的供应站(PX)领取装备,除了全套作战军服以外,还有五连发的步枪、弹药、通讯器材、钢盔、皮靴、野外露营的帐篷,甚至连受伤急救时为了识别血型,而挂在头颈上的血型牌以及防虫药水,还有不少干粮等,真是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分量重到拿不动,只好借助吉普车才能运走。我们在云南呈贡军营等待出发,住在军官宿舍,美国军官与士兵的待遇截然不同,划分得很清楚,我作为一名有军官衔的翻译官,享受军官的待遇。给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在军官食堂吃早餐的一幕,食堂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戴的白色钢盔上写着MP大字的宪兵,在他的身边居然贴着一张写有“不剃胡须者不得吃”的告示,并逐一检查进餐人员。起初我很不理解,吃饭和剃须有什么关系呢?果然有一位美国军官因误点匆匆赶来,来不及刮去满脸的胡子,一把被宪兵拦住,并向他行了个军礼,劝他剃了胡子再来吃饭。我好生奇怪地问杨中尉,答称这是军官的军容问题要求严格。从此我也养成每天一早剃须的习惯,直到现在几十年都从不间断。在食堂门口还放置多种维生素药丸和鱼肝油丸,每人必须吃了才能进食堂。伙食倒还不错,每天能吃到牛奶面包和大多数是肉类的罐头食品,在抗战期间物资短缺,能吃到这样的伙食真不错了。

1947年于上海中国银行工作之暇的作者
杨中尉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到中越边境配合中国炮兵作战,担任陆空的联络,我们在呈贡待命。一天清晨,杨中尉来到我住处告之,立即出发,目的地是中越边境靠近镇南关(即现在的友谊关)叫凭祥的地方。这里是十四航空队技术联络中队的总部所在地。到了那里,我们分成七八个小组,奉命行动,接到指令后我与杨中尉开吉普车拉着通讯器材和装备、野外露营的帐篷和干粮,按指令到离前线一定距离的规定到达的地方,测定方位,取得信号。原来此地已接近前线,人烟稀少十分荒凉,有时我们要经过崎岖的山路,有时要穿越森林,偶尔还听到远处的炮声,于是马上与中国炮兵接上关系。对方是新一军(青年军)即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孙立人部队,配有美式装备的火炮,通话者不是连长就是排长。经过数十分钟的商谈和布置,就立刻行动起来。我们的具体任务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用英语,将中国炮兵发射方位与要求,通知十四航空队,与美国飞行员通话联络,然后把美军飞机侦察到的情报,用步话机通知给中国的炮兵,校正炮兵所需要的目标和方位。只听到了远方的炮声,然后飞机检查命中的效果,修正炮击目标的位置,再开始新的攻击……我与杨中尉的工作从生疏到熟练,逐渐取得较好的效果。从通讯中,我感到几次合作都很顺利,听到对方的简单赞扬,“打中了!OK”,三方此时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我们连续走了几个地方,有时还露营在野外原始森林里。由于装备齐全,生活并不困难,吃干粮B(Breakfast早餐)D(Dinner午餐)S(Supper晚餐)三种,干粮内有香烟、饼干、咖啡和罐头食品等等,睡帐篷,还有蚊帐、羊毛毯,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后又奉命到中缅边境前线,如法炮制。由于配合默契,效果显著,受到表彰。
载歌载舞欢庆抗战胜利
当时美军掌握了制空权,日军闻风丧胆,中国军队没有空军,又没有懂英语的地面部队,我能在其中建立联系,为中国炮兵安上了“顺风耳”、“千里眼”,虽然每天都在炮火连天中度过,但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却觉得自己能用英语这个武器打击敌人,为抗战出一分力感到欣慰,现在回忆起来却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值得的最自豪的时光。

1946年作者(左一)与同在上海中国银行的弟弟陶盛(后调往香港,1951年赴美国,为美国RBN电脑工程师)合影
正当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着,我们又奉命调往柳州前线,在飞赴柳州途中,突然从飞机的无线电中听到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威力很大的叫Atomic Bomb炸弹的消息,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炸弹,更不知道这就是原子弹。当我们抵达柳州机场时,只见一群奇装打扮的美国兵向我们围拢来,有的剃光了头,有的连眉毛也剃掉,像只剥光鸡蛋,有的赤膊涂上色彩,载歌载舞兴奋异常。我们问他们为何高兴?回答说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了。这确实是美军官兵们的普遍心声,想不到漫长的八年抗战就此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不久我即从柳州取道昆明返回重庆,到外事局办理退伍服兵役复员的手续,脱下军装,复员到重庆中国银行,结束了这段难忘而又激动的从军生涯。
许多年后,我曾于1982年赴美国探亲时,找过杨中尉,但时隔多年遍寻不遇,真是遗憾。
退伍后,中国银行总行又指派我参加赴台湾开设分行的筹备工作,虽然后来因故没有建成,但这又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在这就不详述了。
由于在母校打下的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我在抗战期间有条件投笔从戎,加入译员行列在盟军工作,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英语也为生活工作所用,特别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又有了用武之地,能代表中国银行与外方(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等银行)合资筹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并任董事、副总经理,参与管理达二十年之久,并将多年的工作经验写成《商人银行运作实务》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深圳特区为改革开放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