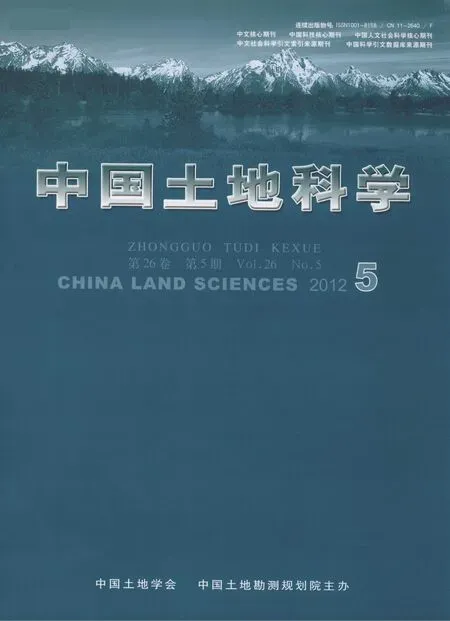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衍生路径及抑制
谭术魁,张孜仪,2
(1.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1 引言
土地的自然稀缺性僵化了其供给弹性,但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富有弹性,这就引发了对土地财产权的竞争和垄断。土地财产权的运作若缺乏必要的管控,就会产生诸如侵蚀财产权模糊的公共领域等有损社会公益的事件。经济高速发展所催生的城市盲目扩张、大量农地非农化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的行为失范等现象均建立在一定的土地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土地用途管制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公权调控私权的重要手段,是国家为减少外部性而对私人土地财产权益施以的强制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明确提出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资源供给引导需求,对农地非农化实行严格管制,从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然而,现行土地用途管制的模糊性和懈怠为寻租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本研究尝试以土地财产权为主线,探究土地用途管制领域寻租行为的衍生逻辑,为规范权力的正当行使提供政策建议,以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频度。
2 决定财产权结构的土地用途管制及其与寻租的勾连
2.1 土地用途管制及其对财产权的规制
土地用途管制指国家为严格土地利用而制定实施的一项具有财产权性质的法律制度[1]。土地用途管制在国外也称“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土地规划许可制”(英国)、“建设开发许可制”(法国、韩国等)等[2]。土地用途管制可以被定义为界定财产权范围的一种过程,即通过对财产使用范围进行界定,让财产权得以明确执行[3]。土地用途管制权就体现着一国政府的“最高权或统治权”及“最终所有权和处分权”,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可以订立土地用途管制规则,来限制私人合法使用其土地的权利范围,以避免或解决可能产生的外部性争端[4]。Fischel认为土地用途管制实质上是一种集体财产权,只不过土地用途管制将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权由私人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而居民则拥有了合法的授权,可以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去挑战土地用途管制的决定,以维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益[5]。
土地用途管制实质上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多以公共利益作为管制缘由)来调控土地财产权,主要通过对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他物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配置来规范土地利用秩序。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以土地用途管制主要规范土地他物权,即土地用益物权的行使。
2.2 土地用途管制与寻租的勾连
政府为了矫正社会活动外部性而实施的管制,往往会导致经济租的产生,这些因为政府管制而创造的经济租或利益,会让寻租者愿意花费资源及成本竞相追逐,而政府为防止寻租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紧缩管制,这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租[6]。Lambsdorff和Cornelius调查了26个非洲国家,发现一种简单的相关性:腐败与“政府管制的模糊性和懈怠”呈现正相关[7]。Mills以土地利用外部性为视角创设寻租模型,意在揭示土地用途管制是一种负和博弈,因它带来了不公平的租值分配[8]。与Mills相左的观点是,寻租亦可产生正和博弈结果,甚至可以将社会成本内部化,不一而足。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寻租活动是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这源于对寻租的定义。寻租思想的创始者Tullock认为,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代名词[9]。Buchanan等通过分析寻租的三个层次,揭示出利益集团(土地财产权人或投资开发者)与公权力主体青睐寻租与创租的动因[10]。国内学界对于土地用途管制少有将其与寻租行为衔接的翔实研究。
土地用途管制作为政府界定土地财产权的政策工具,限制了土地财产权人或者投资开发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使用土地资源的自由度。土地财产权人及利益相关人若想获取更大的开发利用权限,则须与政府协商,以改变土地用途管制模式,扩大自身的权利范围,寻租行为的产生便不可避免,这也是近些年来土地领域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3 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衍生逻辑
3.1 寻租行为个案实证
寻租行为类型多样,包括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本研究尝试以独占型寻租与竞争型寻租为模型,辅之以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领域的衍生逻辑。
3.1.1 独占型寻租行为之个案 土地用途管制中的独占型寻租指土地财产权人或者投资开发商等主体通过向政府机关游说,对某种土地用途进行特殊管制,以保有其独占或寡占利益的行为。独占型寻租虽然会极大地削弱政府公信力,但是一旦政府从中可获益良多,这种寻租行为仍会发生。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暂停新高尔夫球场建设,但近年来各地圈地建高尔夫球场、圈地建别墅等案件依然频频曝光,2010年山东高速绿城雪野湖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高速”)在山东省莱芜市雪野镇圈地2000多亩开发高尔夫球场以及别墅项目即为典型。山东省莱芜市政府之所以敢悖国家禁令而对高尔夫球场项目大开“绿灯”,主要在于这种项目对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来说都潜存巨大利益。高尔夫球项目可抬高周边别墅价格,满足“山东高速”的利益需求,而地方政府从中收益的不仅是城市形象的提升,更在于土地财政的“盆满钵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1]。该案最终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但目前土地的财产权结构已被重新界定。“山东高速”不动产开发项目固然可提升地区环境品质,但是地价却被抬高,土地利用成本大幅攀升,失去土地的村民只能靠外出务工养家糊口,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加。可见,此种独占型寻租引发的社会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3.1.2 竞争型寻租行为之个案 土地用途管制领域的竞争型寻租,是指土地财产权人或者投资开发者通过向政府机关游说,致使政府解除对土地使用某种形式的管制,以扩大其财产权范围。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严格、僵化与滞后性特征,往往无法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土地财产权人或者开发商会设法寻租,以最大化自己的土地权益。
典型个案为2009年深圳市“‘小产权房’开禁”事件。2009年5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其中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除未申报的外,符合确认条件的,适当照顾原村民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在区分违法建筑和当事人不同情况的基础上予以处罚和补收地价款后,按规定办理初始登记,依法核发房产证。”虽然该规定在当时还处于调查阶段,但深圳市人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庞大的“小产权房”数量严重影响了深圳房地产市场。土地法律的“软”约束力为乡镇政府、村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及投资开发商的寻租活动创造了空间。村民、村集体为最大化自身土地财产权益游说政府,投资开发商为谋取商机亦不惜重金加入寻租队伍,以获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商品住房的“许可”。如果说深圳“小产权房”建设领域的寻租是土地用途管制中寻租的第一个层面,那么谋求“小产权房”合法化则是第二个层面的寻租。经过民主协商,深圳市四届人大通过《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这是“小产权房”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影响政府决策的效应。反映在土地财产权上,就是政府对土地财产权管制的执行力不足,导致违法行为甚为普遍,当违法者的规模变得甚为庞大,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时候,集体寻租行为便产生。
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小产权房”转正事件,最终被国土资源部于2009年6月9日开专场会议予以止息[12]。因该项决定有违法律及中央有关规定,即使是一种试错,也可见其中诱发寻租行为的脉络。
3.2 寻租行为的生成路径
无论是独占型寻租还是竞争型寻租,都是相关主体以自身财产权益最大化为动因,试图改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行为。透过对上述个案的分析,结合现行土地领域腐败案件的高发不止,不难揭示出寻租行为在中国土地用途管制中衍生的逻辑(图1)[13]。

图1 寻租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发生路径Fig.1 The path of Rent-seeking in the land use control
在未受寻租行为左右的前提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制定和实施沿着A—B—C的路径输出,但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制度正常创新路径会被扭曲。诸如前文谈到的个案,“山东高速”圈地2000余亩开发高尔夫球场及别墅项目的过程是沿着A—B—D前进的,因最终结果未定,寻租者理想的结果A—B—D—A能否实现还有待观察。“小产权房”是寻租所引致的土地财产权重新分配的结果,A—B—D成为普遍生成路径。深圳市人大通过《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使得“小产权房”建设领域集体行动的结果影响到公权力机关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创新,于是出现A—B—D—A的循环,但因《决定》被止息,未能出现A—B—D—A—B—C的运行路径。之所以会出现A—B—D—A或者A—B—D—A—B—C的制度运行模式,一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待完备,不合理的财产权结构、不科学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并不能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二是因为制度执行力不足。制度实施的社会基础欠缺、执行主体执行能力不足、土地财产权人及开发商土地使用理念错位等都会影响制度执行效果。如果制度执行成本过高,政府会考虑重新配置土地财产权,以出现A—B—C—E—A理想的制度创新路径。
4 抑制寻租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4.1 合理化财产权结构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于清晰地界定财产权,而所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式,其实质都是资源分配的问题[14]。然而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双面利刃,国家既可以制定出促进财产权运作效率的政策,也可能导致财产权的无效率,这就是“国家—财产权悖论”[15]。中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存在诸多欠科学的地方,如集体土地财产权的界定、土地流转过程中财产权交易的公平性、城乡规划过程中集体参与的保障、土地征收程序的信息公开及补偿制度等都有待完善,以上缺陷均可从土地财产权体系中找到症结点。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可绘制中国土地权利(力)体系图(图2),建构合理的财产权体系,会大大压缩寻租产生的空间。
中国土地权利(力)体系中最易引发寻租行为的当属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导致集体土地他物权在面临侵害时,无法通过个人土地财产权来维护,往往以公权力介入作为纠纷解决的关键。在土地公有制背景下,合理化财产权结构的关键是土地他物权的有效配置。要强化土地他物权,为他物权人最优化利用土地设置保障,如通过构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建立健全集体土地在有限空间内自由流转机制、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措施来保障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土地财产权的强力保障,可激发财产权人更加有效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并能监督制约土地公用权对土地财产权的干预力度和方式,这就压缩了寻租行为发生的空间,威慑了公权力运行中的肆意。

图2 中国现行土地权利(力)体系Fig.2 Current land rights(power)system
4.2 强化制度执行力
圈地建高尔夫球场和“小产权房”问题的产生,就是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因制度自身不完备而发生难以执行之虞,寻租人会伺机侵入,易得逞的寻租行为会产生“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这也是土地领域腐败“大案”、“窝案”高发的原因。要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执行力,须从执行主体及执行环境上下工夫。
就执行主体而言,政府在管制土地用途过程中,须具备使制度得以实施的能力。中国土地用途管制领域权力集中[16],这不仅不利于执行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约,还不利于政府执行信息公开及民众参与监督。适当分散土地用途管制权是一种可取选择,比如土地征收权力的行使,所涉土地规划权、占用耕地补偿权、征收决定权、征收执行权、征收补偿权等公权力要配置合理。提高制度执行力还要求执行主体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保证执行过程不因个人主观原因而阻滞。就执行环境而言,政府要加大土地利用理念普及范围、提高普及效度,使可持续发展、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支持土地用途管制的良好氛围。行政执法部门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与互动的有效性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执行力的提升。
4.3 健全诉求机制
要建立健全诉求机制,为修复受损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关键在于制裁机制的有效性,即侵权人受到应有的惩处。法律之所以规定制裁,其目的在于保障法律命令得到遵守和执行,强迫“行为符合业已确立的秩序”[17]。可见,健全诉求机制同样可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执行力,威慑寻租行为。
健全诉求机制,还应确保利益相关人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只有知悉财产权被重新分配的过程及结果,才能为权利诉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还应保障受损方的辩护权,使其利益诉求获得充分的尊重和表达,因为在纠纷解决中,司法机关、仲裁机关等主体扮演中立者角色,最终裁决取决于优势证据。中国法律对土地纠纷解决设置了政府处理前置程序,而多数土地纠纷案系由政府行为引发,这种自己做自己“裁判官”的行为,削弱了案件处理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且多数案件因此被挡在司法裁判的门槛之外。一旦寻租者与执行主体相勾结,受损的土地财产权利秩序将更难修复。健全诉求机制的路径在于扩大可诉侵权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从程序和实体上保障土地财产权人诉权的实现。
4.4 建立制度创新平台
只有为土地财产权人和投资开发人创设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才能使制度创新沿着图1中A—B—C—E—A的正常路径发生发展,避免出现A—B—D—A扭曲的制度创新路径。建立制度创新平台要求立法为公权力机关、土地财产权人、投资开发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积极参与人(如专家学者等)提供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信息。通过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协商来综合判断、鉴别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所界定的土地财产权是否属于最优模式,并为创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重新界定财产权提供直接、有效的信息指导,保障图1中C—E信息反馈与收集渠道的畅通无阻。通过创建制度创新信息表达平台来实现制度创新,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更替模式,因新制度的孕育过程凝聚了公众的积极参与,事先已获充分认可,其后的执行难度和成本将减低。制度就是激励或者约束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制度创新同样须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共同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外在制度变革必须获取足够数量的民众和民间组织内心的认可,也只有当多数民众即使面对利益集团(寻租者)的抵制仍然愿意支持变革时,制度创新才会发生[18]。可通过举行纠纷解决听证会、开通网络征询意见平台、开展实地调研、定期不定期举办制度实施效果研讨会等方式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创新创设信息反馈平台。尽可能扩大民众直接参与的范围和强度,以避免信息失真,确保公民立法权得以实现。民众积极参与表达个人意志,还有利于政府及时把握舆情动态,对于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不无助益。
(
):
[1] 沈守愚,等.论土地用途管制的法权基础[A].土地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7.
[2] 程久苗.试论土地用途管制[J].中国农村经济,2000,(7):22.
[3] Lawrence Lai Wai Chung.The Economics of Land-use Zon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Work of Coase[J].Town Planning Review, 1994, 65(1): 77-79.
[4] Robert H.Nelson.Zoning Myth and Practice-from Euclid into the Future[A].Zoning and the American Dream:Promise Still to Keep[C].Chicago:Planners Press, 1989: 299-318.
[5] William A.Fischel.The Economics of Zoning Laws: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American Land Use Controls[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4-279.
[6] W.A.Evans.Externalities, Rent-Seekings and Town Plannning, Discussion Paper i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R].England:University of Reading, 1982, No.10.转引自张刚维、林森田.寻租行为与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财产权观点之分析[J].台湾土地研究,2008(2):142.
[7] J.Graf Lambsdorff and P.Cornelius, Corrupti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Growth[A].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0/2001,World Economic Forum[C].New York, Oxford: Harvad Un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0-78.
[8] D.E.Mills.Is Zoning a Positive-Sum Game?[J].Land Economics, 1989, 65(1): 1-12.
[9] 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
[10] Buchannan, James M, Robert D.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eds).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M].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 李继远.山东高速圈地千亩违规建高尔夫球场[N].华夏时报,2011-08-27.
[12]张晏.国土资源部听取深圳市有关情况汇报,明确———“深圳‘小产权房’转正”说法属媒体误解[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06-11.
[13]张刚维,林森田.寻租行为与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财产权观点之分析[J].台湾土地研究,2008,(2):142.
[14] L.W.C.Lai, C.Webster.Property Rights, Planning and Markets:Managing Spontaneous Cities[M].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3: 178-189.
[15] 刘伟,李风圣.产权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99.
[16] 人民日报.土地腐败案高发,因该领域权力过分集中[N].人民日报,2010-01-14.
[17]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0.
[18]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63-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