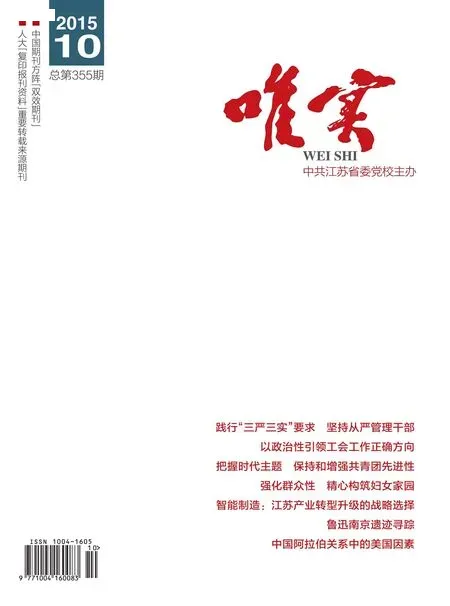孔子思想的“原教旨”初探
李 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孔子思想的“原教旨”初探
李 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原教旨”主要强调孔子本人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初衷,教授学问之宗旨。孔子“原教旨”的目的在于批判“无道”的“天下”,重构“有道”的天下,提出自己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其内容涉及四个层次,即“人的主体属性的提升”、“主体行为规范”、“学术研究”及“政治实践”;原教旨的品质显现出全面性、多元性和辩证性的特点。
儒学宗教化;原教旨;内圣外王;儒家文化
引 言
“儒家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多元性、概括性之特点,它并非孔孟以及孔孟以来任何一个儒士一家之言,而是中国古代有识之“儒士”阶层在研习和继承前辈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植根于中国古代生产、生活、政治制度理念之中的“文化体系”。如此,倘若以一家之言概括儒家文化,任意褒贬,在学术上则是“断章取义”,背离学术之精神要旨。然而,探求儒家文化,还得以“儒家之开创者”的圣人孔子及其第一代弟子之言论思想入手,因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原教旨”。“原教旨”主要强调孔子本人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初衷,教授学问之宗旨。探求孔子之原初“教旨”,既非“复古”,更非对孔子思想作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化性、政治性价值判断,而只是以“价值中立”原则“就事论事”,以彰显孔子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给予其后世和今世的启发。
严格意义上讲,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把握“历史经验”,即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还要把握作者自身的“主观体验”,即作者自身带有主观性质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两者不可偏其一。倘若失去“历史经验”,则无法客观全面理解作者的思想来源,陷入“形而上”的怪圈;倘若避开作者的“主观体验”,则无法实现研究者与作者之间在主观心智上的“统一”,极易得出带有研究者主观偏见或感情倾向的结论。把握孔子思想之“原教旨”,也是如此。
若以《论语》、《大学》、《中庸》为蓝本对孔子思想之“原教旨”进行整体性和宏观性考究的话,孔子之“原教旨”在内容上涉及四个层次,即“人的主体属性的提升”、“主体行为规范”、“学术研究”、“政治实践”。其目的在于回应春秋战国“天下无道”的现实,提出自己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
一、孔子“原教旨”的初衷:批判“无道”的
“天下”,重构“有道”的“天下”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孔子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时期。新兴贵族阶层纷纷各自分治,政权林立并且更替频繁,争霸战争不断,与此同时,周王朝时期的“井田制”经济基础逐渐趋于瓦解,百姓遭殃。
从自身的“主观体验”来看,“礼乐崩坏”、“天下无道”是孔子对时局的评价,《论语》中多次提到夫子这一论断。如一位隐士微生亩曾问孔子:“何为是栖栖者与?”孔子回答道:“疾固也。”(《论语·宪问》)“疾固也”这一句话道出孔子本人“栖栖”于周游列国的缘由。在他眼里,世人皆“固”,顽固不化,迫切需要智者的教化和指点,自己亲身探究“道”以及向弟子传道皆是为了了此心愿。还如,当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答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年代的从政者皆是见识和气量狭小的人,不值得一提,根本不能称为言而有信品德高尚的“士”。而最能体现孔子对现实不满的则是春秋时代的“越礼”行为,当他提到鲁国大夫季氏时,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照古代礼制,“八佾”属于天子之礼,大夫不可以使用。[1]孔子对李氏越礼的行为耿耿于怀,感慨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以孔子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审视当时的“历史环境”,诸如世人“固”、从政者皆“斗筲之人”、“大夫越礼”,等等,“天下无道”则是最为精辟的概括。
排除带有政治现实性的价值判断,只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思索夫子思想对“历史经验”的“主观体验”,可以看出,孔子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现实批判主义者和教育家。他站在一个智者的高度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作了一系列的批判,并且始终以“教化者”的身份“传道”与“授业”。如此看来,孔子思想的初衷就在于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实现“天下有道”。此后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皆为寻求“天下有道”的具体行为路径,为世人指点迷津。
二、孔子“原教旨”之内容:微观层次探究
如果将孔子定位于一个教育家的话,可以说,他施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后世的嫡传弟子或者自称为儒士之士一般都只是继承或者研习孔子所施教的一项“技艺”而已。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以他们的“一家之言”概括孔子思想,极易使后世误读。譬如,经汉朝大儒董仲舒创立而后世予以完善、宣扬、固化的核心价值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文化和政治领域“非议”孔子为“官本位”、“社会等级化”、“男尊女卑”的口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因此,应对孔子“原教旨”的具体内容作一理性、客观的“微观层次”之探究,以求更精致地把握孔学之“原教旨”。
孔子思想的四个层次
如前所述,孔子“原教旨”的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欲实现“天下有道”。倘若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句话中揣摩“道”的含义,“道”事实上就是发扬人类天生具有的“理性”之本性,如“善”、“仁”、“德”,等等。因此,为寻求“有道”,孔子自然期冀的是个人、群体以及社会自身的“全面性”发展。具体而言,孔子主要从四个层次具体阐述了自己寻求“有道”之“天下”的主张和观点。
第一,主体属性的提高:道德属性和社会实践性的统一。孔子十分强调“修身”。从哲学层面看,“修身”就是提高主体自身的社会属性,增强主体意识,实现主体精神层次的发展并且将此精神寓于实践活动之中。“修身”主要着眼于两方面:其一是自身道德的培养,即“性”、“德”、“仁”,暂且以“道德属性”概括;其二是自身在各种社会关系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中信守的“德”,即为“社会实践性”。
一是道德属性。孔子重视“德”的培养是为了弘扬人的“道德属性”,让人能够更好地在“天下无道”的现实中反省自己,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彰显“天性”,而后“推己及人”。
孔子谈“德”并非“坐而论道”,抑或“空谈义理”。从孔子“原教旨”的目的以及他谈德的内容和方式上看,此“德”必须要寓于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之中。换言之,它是一个“经验性”的产物,并为经验服务,而非带有超自然的因素。
探析其情况,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目前缺乏对此类工程进行相关估算,还有缺少一定的评估标准要求,大部分施工单位仍然沿袭传统的评估方式,即是以典型的工程项目为建设依据,这样就会在实际实施中因为建设项目的标准地点或者时间与规模等不同,而使得估算与投资表现出了很大差异,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控制与造价管理。不仅如此,施工单位还存在着整体控制不够重视的问题,仍然存在轻决策设计而重视施工等问题现象,也就导致很难从整体对施工的过程全面控制。
二是社会实践性。中国自清末至今所经历的百年“现代化运动”使得国人在思想上受“西学个体文化”的熏染进而对孔学时常抱有轻蔑、调侃之偏见,“愚忠”、“泯灭个性”、“固步自封”、“形而上”等词语频繁出现,孔子本人也被扣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者的帽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文化上的大加挞伐却无法消除孔学对公民生活、国家政治统治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日常生活之中,植根于国人意识的“熟人关系”、“对人品的重视”、“行为的集体性和社会性”等都在无形之中彰显着孔夫子的教诲。
孔子作为现实主义批判家,其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同时,也服务于实践,“服务社会”应该是孔子思想最终的归宿。若只从人的主体属性这一层面分析,孔子所强调的“德”不仅来自于人之“天性”,而且还必须要寓于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之中,为现实服务,促成“天下有道”的实现。换言之,他只是以一种常人的思维来思索人在“现实生活”中遵循的基本、重要的生存法则而已。这里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历史超越性,时至今日,这种“生存法则”对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民族国家的秩序都具有影响。
第二,主体行为的规范:“礼”的外在约束性。孔子一直强调“礼”,“礼”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约束主体行为的规范。孔子作为一个“智人”,明晓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要有“规范”保证“秩序”,万物各归其位,才会实现“天下有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此“礼”:
其一,这个“礼”与前述的“德”相辅相成。既贯穿在以“己”为核心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也自上而下地将天子直至庶人纳入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之中,使人们各得其位、各得其所,如此实现天下大同。而且这个“礼”也是实现“中庸”这个大德所必须的,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力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这些“德”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必定会造成不好的结果,这就是以“礼”来实现“中庸”之道。
其二,孔子的“礼”并非完全是仅靠内心约束的“道德”。事实上,中国古代的“道德”与今日引进的西方的“道德”在概念和本质上都有差异。后者认为,道德仅依靠“个人内心修养”来约束,不受其他任何外在力量的“限制”,因而无法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但是如果仔细体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就会明白,古代之“德”是受到个人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所有外在社会关系的约束的,这种约束绝不亚于国家“强制力”,强大的“株连性”绝对使得“德”必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如此,孔子的“礼”自然是“德”的外在表现,“德”与“礼”不可分开。
其三,我们在此并不是想要将“礼”与“法”相提并论。法史学家一直奉守的“法律儒家化”、“以礼入法”这一信条依然是以西方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期待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寻找到能够与“西方文化”衔接的东西,有此“先入为主”之见,便无法客观地审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思想。笔者尚未研习过中国古代“法家”之思想,但是至少可以断定:法家依然是从孔学中延伸出来的,而与西方所言的带有浓厚基督教情节的“法律”在本质上并不相通。中国现代的法律从西方“移植”而来,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都会有自己历史地形成的行为规范,只不过,在西方是“法律”,而在中国则是“礼”。即使在现代法治条件下,“礼”作为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其价值仍不可移动。
第三,学术研究之方法。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做学问”和“育人”有着自身特有的方法论系统,如“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等等。这些学习方法和态度古今通用,彰显着孔子倡导的“德”。在孔子看来,任何一种行为都应是“礼”和“德”的统一,“学”本身则是修己的一种方法,“德”脱离了“学”必然不会发挥作用。他在告诫弟子时强调“六言六弊”,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因此,只有“学”,才可以尽可能地发挥一切“德”的最佳功能。孔子之言往往着重讲述为人处世最为基本但是常人却不注意的道理,这就是后世将孔子视为“圣人”的缘由。
其一,倡导“仁”政,而“仁”要符合“礼”。具体而言,自然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一言以蔽之,孔子实行仁政,其核心在于“人”。仁者,人也,就要“爱人”。
其二,政治家要做到“德才兼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焉。”(《中庸》)君主自然要“贤”,具体而言,则是:“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六韬·文韬·盈虚第二》)选拔人才要“举直错诸枉”,否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在弟子仲弓向他讨教“如何行政事”时,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他的“选贤任能”的政治思想备受后人推崇。所谓“贤”,自然是要求政治家既要有“德”也要有“才”,这样才能治理天下。
其三,民本思想。孔子倡导“仁”政,“仁”者爱人,“人”即为天下人、天下百姓。孔子的“民本”思想在于:一是肯定“民”的智慧。孔子强调自己的知识来源于与民交流,如此而已矣。二是主张“保民”、“惠民”、“信民”,这是为政的根本。“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言,孔子认为这种行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在与子贡谈论政事的时候,将“民信”作为“足食、足兵、民信”此三个政治要素之首,而且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一思想被孟子发挥到极致,他认为,“保民”乃定天下之本,“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治理天下,就要做到,“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数口之家无饥”、“斑白者不负薪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因此,君主应“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选拔人才、赏罚方面,都要听从“民意”。“国人皆曰贤之,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至于后世,一直将“爱民”视为“国之大务”。“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弟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六韬·文韬·国务第三》)可见,古代政治制度也并非绝对专权,“爱民”、“有德”均是约束君王权力的标准。
三、孔子原教旨之品质:宏观层次探究
纵观《论语》、《大学》、《中庸》中记载的孔子之言行,认真参悟且进行宏观性和整体性思考,则孔子思想可以用“全面性、多元性、辩证性”来概括。
“全面性”意指孔子之思想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并不局限于“外王”抑或“政治”,而是兼容并包,从做人到做事,从修身养性到从事学术、政事等实践,孔子都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具有“元价值”的行为规范:德行一致、仁、礼,等等。“多元性”即为,自天子以至庶人都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可用之处”,士、农、工、商皆可以成为“君子”。“辩证性”则是对那种将“孔子”视为“唯心主义”代表的观点的反驳。孔子是最为杰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本质上十分“务实”。他倡导“先行后言”,先做事后说话,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主张政治家“德才兼备”也体现了“辩证性”,有德有才才有资格“王天下”,否则,必然招致灾难。《中庸》记载,孔子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即有德之人如果无法获得有权力的人的信任,就无法实现“治天下”的目的。这是一句非常现实的话,虽有才却无法获得权威或者治国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只不过,后世忽略了“德”,而只知道争“权力”。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德是其思想辩证性的精华,凡事要有“度”,否则,便会由“智人”变为“愚人”。
四、对几种观点的批驳
在此,笔者将对一些观点予以简单的反驳。
1.儒家文化宗教化。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完全将儒家文化视为“宗教”,[2]这是不妥的。宗教最本质的东西是“超经验因素”,儒家文化即使包含此种因素也是汉朝以后其他“异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影响所致。从本质上说,“儒家并没有被神秘主义所支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并不完全服从为超自然媒介所控制的天命观”[3]。比如,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在孔子时代,“鬼”是指逝去的“祖宗”,“神”则指“天”,并没有专指佛家所指的“鬼魂”等东西。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并批判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鬼神”这些非经验性的东西,孔子认为,只需“敬”,合乎“礼仪”,而且不要经常谈论。他要求人们学会面对现实存在的事物。尽管孔子“畏天”,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但是这个“天命”也并没有所谓的“宗教情结”,而是常人在遇到无法左右之事时寻找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而已。
2.“内圣外王”之观点。余英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中国宋朝的“古文运动”以及“新学”或者“理学”之兴起的目的就是“复兴”古代内圣外王之“道统”,以此重建人间秩序。[4]笔者认为,孔子之“内圣”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外王”。孔学是全面性的,政治实践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同时,孔子之志也并非为了“仕途”。他曾经对颜渊、子路说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从政也只是实现志向的一个手段和方法而已,如果将孔学仅定为“内圣外王”,有失偏颇。孟子是最为执着于“政治”的,但是他又少谈“内圣”,常谈“外王”。□
[1]张志钢.论语通译[M].北京:光明出版社,2007:15.
[2]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9.
[4]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责任编辑:戴群英
B222.2
A
1004-1605(2012)10-0034-04
李娟(1984-)女,山东茌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