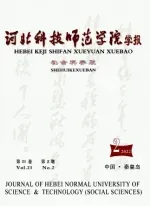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诗歌实验:以毛翰《天籁如斯》等多媒体诗歌为例
王钰哲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新世纪以来,网络技术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与变革。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正在蓬勃发展,传统文学的作者也纷纷同意把自己的纸质文学作品制作成电子版以尝试数码时代的营销,豆瓣阅读、唐茶阅读等应用程序也在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相比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诗歌作为文学的急先锋,在这一场变革的浪潮中同样表现得引人注目。不但知名诗人们纷纷开设博客发表新作,许多草根作者也通过诗歌网站、论坛或个人博客发布自己的作品。无论是民间诗刊还是正规期刊都一样凭借发布电子版本用以在网络上与读者沟通。此外,以毛翰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将诗歌文本与精美的图片、优美的音乐组合而成的新型诗歌可谓是网络时代的一次诗歌实践。网络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样也造成了一定的局限,这是应当正视并加以分析的。
一、诗歌与网络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民刊无疑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到80年代的《他们》、《非非》、《莽汉》,再到90年代末期至少上百种的诗歌民刊,诗歌的民间写作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变化中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无可争议。诗歌民刊固然有不受出版规定的约束,拥有民间写作的独特活力与较少受到外在影响等优势,但同时也受限于印刷成本与流通传播。如《今天》编辑部搬迁到海外后,国内读者想要再读到该杂志就相当困难,但在网络大规模普及的今日,从《今天》的网站上下载阅读该杂志的电子版已经相当方便。而网络诗歌的大规模涌现,也给诗歌民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且二者已经有相互“结盟”并挑战主流诗坛的趋向。曾任《诗刊》主编的叶延滨就认为从传播方式的角度看,诗歌民刊(或称“地下刊物”)正与网络诗歌一起构成对主流诗歌媒体的挑战,且三者已经形成三分天下之势。主流的传统诗歌刊物的数量正逐渐减少,而互联网络由于一方面如诗歌民刊一般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独有的开放性与互动性打破了主流媒体的话语垄断,成为了民间作者创作与表达的最佳平台[1]。文学评论家张清华甚至认为传统的诗歌刊物已经不再统领诗坛,已经由民间诗坛取而代之。这已经是一场“江湖”对“庙堂”的胜利。[2]在民间与网络的压力下,主流的诗歌媒体也开始不断吸收诗歌民刊的优秀作品,并将自己的刊物搬上网络以扩大影响。
与主流的诗歌刊物不同,网络诗歌凭借数目众多的诗歌网站与诗歌论坛已经大为繁荣。在近年来的开博热潮中,无论是已经成名的诗人、诗评家还是草根的民间作者都纷纷借这个新的交流平台发表新作。甚至在新近流行的微博中,也能找到民间诗歌作者自发组织的诗歌微博群以交流作品,如新浪微博“海外诗刊”与“紫竹沉香”微博群,当然所交流的都是140字以下的短诗。网络诗歌固然有相当数量的知名诗人与诗评家参与,如洪烛、罗振亚、傅天虹、吴思敬、蒋登科、芒克、翟永明、韩东、伊沙、徐敬亚、李亚伟等诗人、诗评家纷纷开设博客,但主要还是体现民间的声音和意愿。虽然网络上几乎没有节制的创作自由大幅度地释放了人们心中的诗歌能量,实现了许多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发表的民间作者的诗歌理想,但网络这一平台同样对诗歌艺术本身造成了不小的伤害。陈平原就曾指出:“目前网上的文字,优点是少伪饰,多灵气,随意挥洒,天马行空。可写作的自由与文章的美感,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3]网络诗歌的结构粗糙、词汇单一、创作平面化和模式化等弊病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固然有网络时代本身的“浅阅读”、“快阅读”等原因,但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就难以期待网络诗歌的进一步规范和升华。同样,由于在网络上匿名发言往往无所顾忌,也很容易形成集体性的网络暴力。这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获鲁迅文学奖时所引发的争议中表现得极其明显。当然,网络诗歌作为新兴事物,它所蕴含的新质与萌芽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虽然广义上一切通过网络传播的诗作都叫网络诗歌,但也有论者从制作方式着眼,认为可以把利用电脑的多媒体技术所创作的数字式文本视作是狭义的网络诗歌。我们所要讨论利用网络资源创作的新型诗歌便是此类可以视作是可期待的诗歌“新质”之一。
二、网络时代的新型诗歌
新型诗歌是借助于多媒体技术与开放的网络平台所创作的多媒体诗歌与超文本诗歌❶有论者(如吴思敬)称毛翰的多媒体诗歌实验也为“超文本新诗”,但超文本作品侧重于链接跳转、读者互动、接龙创作等性质,本文还是将其称为“多媒体诗歌”,以确保概念上不会混淆。。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多媒体技术与文学结合的范例有很多,例如语文课堂上制作的多媒体课件,网易、腾讯等电子邮箱服务商所提供的配几句短诗的FLASH电子贺卡,网友把原创歌词与影视片段剪辑组合而成的自制MV等。多媒体作品有许多特点,但主要在于审美感觉的立体性、作品的开放性以及文本生成的实时互动性[4]168。在多媒体作品中,作者往往要整合多种网络资源,在一部短剧中往往以文本、视频、FLASH动画、音乐等多种资源作为表现手段。而一部作品中的音乐、视频、图像固然由作者设计制作或筛选加工而成,但有时却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最终完成。例如米罗·卡索创作的《鱼鼓》,作为一首新型诗歌,与传统诗歌的不同之处是需要读者的互动才能“完成”。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必须用鼠标点击画面上的按钮才会逐渐出现诗句,而这些不完整的句子需要通过读者的敲击才能不断移动相互衔接,直到最后才形成一首完整的诗,读者在欣赏此类诗歌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参与创作的乐趣。与此类多媒体诗相似的还有超文本诗歌,这是更多依托于网络的“超文本”特点而创作的诗歌,欧阳有权称其为“以文字的巧妙排列或关键词闪烁变色而成的‘动态交互诗’”[4]186。这类新型诗歌在港台已有不少诗人尝试创作。在姚大钧创建的“妙缪庙”网站等站点上,已经展现了不少港台诗人超文本新诗的创作实绩。但无论是多媒体新诗还是超文本新诗,在大陆还相对较为沉寂,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网络与文学、网络与诗歌的相关论文专著发表或出版,但目前大陆诗坛唯有毛翰先生通过其多媒体诗歌实践来试图建构网络时代的诗歌美学,下文将结合毛翰先生的作品来分析此类多媒体诗歌的成就与局限。
三、毛翰的诗歌创作
毛翰先生的多媒体诗歌实验开展于数年前,迄今已完成包括电子版诗集《天籁如斯》在内的30种诗歌创作。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与朋友之间的电邮交流,获得了相当的好评与反响。毛翰先生的多媒体诗歌创作,大多使用的是微软公司的PowerPoint软件,将诗歌文本与配图、音乐结合到一起,制作成可在他人电脑上直接播放的PPS文件。作品完成后一般只有3~4Mb大小,在网络传播上相对于动辄十几Mb大小的电子杂志来说有一定的优势❶毛翰诗作《天籁如斯》的第二版由亿刊网公司重新制作,是可执行的EXE格式电子杂志(约25Mb),读者可手动翻页,也是将文本与音乐、图片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作品。。这一类多媒体诗歌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孕育而生的新鲜事物,客观评价其优劣得失是相当有必要的。
首先,作为一种新的形式,这类作品结合了图像、文本与音乐的多重特点,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文本。诗歌内蕴也通过图片与音乐的参与得到了复合与强化,文本本身的内涵与画面造成的视觉冲击力、音乐带来的听觉冲击力交织结合,能给受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欣赏体验。其次,这种PPS超文本诗歌还可以广泛运用到其他文娱活动(如配乐诗朗诵活动)中,届时如果配合这种PPS诗歌,能使原来单一的朗诵取得诗、画、乐的多重审美愉悦。作为节假日礼物,该超文本诗歌作品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络相互传递,成为亲朋之间沟通交流的一种新型媒介渠道。与传统的书信礼物相比,这种时效性、交流性更强的作品更符合数码时代的特点与要求,最后,对于青年读者而言,学习PowerPoint技术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毛翰等人的多媒体诗歌的创作实绩,将极大地拉近青年读者与诗歌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将日渐边缘化的诗歌再次拉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互联网时代的多媒体诗歌的“尝试集”已经诞生,已经使一些多年不读诗的人重新爱上了诗,使一些从来不读新诗(自由诗)的人对新诗(自由诗)刮目相看。虽然毛翰的多媒体诗歌创作依然有不少可以批评讨论之处,但其创作的努力是毫无疑问值得肯定的。
而当我们学习欣赏并进而创作此类多媒体诗歌时,首先,触及到的问题是对数码版权的侵权事宜。一般诗歌的创作版权属于作者本人,但此类多媒体诗歌,应当注意到除了诗歌文本之外,图片与音乐的原作者的权利也应当得到重视。当作者出于学习目的“自娱自乐”地制作这种多媒体诗歌时,不用顾虑到作品可能引发的纠纷,但如毛翰先生《天籁如斯》作为数码出版物公开发行的作品,就应该考虑到背景音乐与所插入的配图是否与原作者或公司取得了沟通或许可。其次,正如蒋登科所指出:“浅阅读是网络阅读的基本特点,对诗歌这种需要投入很多心力的文学样式,阅读者很难对作品进行细读,大多是一次性的平面阅读,忽略了对作品全面、深刻的美学感悟。”[5]同时,虽然现在的电脑显示屏技术已经相对进步,但长时间注视仍会引起读者的视觉疲劳。所以一般的多媒体诗歌制作,一方面结合了音乐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读者的需要,PPS作品中的诗歌文本都会分段出现,每隔若干秒自动切换到下一段,并与不同的图片相互搭配。但这样对于一些意蕴相对更为深刻的诗歌文本而言,很难让读者把握其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性,也容易使得多媒体诗歌的创作显得平面化和表面化。再次,对于此类新诗的读者而言,当音乐、诗歌、图像同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我们的“阅读”也已经有了改变,对于此类复合文本,诗、图、乐的三种渠道究竟谁是主导就形成了一种问题。一般会认为既然“超文本”诗依然是诗歌作品,那诗歌文本应该依然是主导,而音乐与插图应该是“配乐”与“配图”,是起辅助性的作用的。而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由于图片与音乐过强的冲击力,有可能使诗歌变成图片与音乐的“字幕讲解”或者“文字说明”。毛翰先生自己在创作《恋歌三章》的过程中就因为配乐配画的“挑剔”而不得不对诗歌文本几度修补。对于学习制作多媒体诗歌的初学者,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矛盾就变成了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最后,网络固然给诗歌传播带来了便利条件,也是毛翰诗歌能够出现的先决条件。但同样也应该注意到互联网络与电脑等终端设备并非在我国已经完全普及,一旦失去了电脑等数码设备,相互交流这类多媒体诗歌就有了不小的困难。可以说,这类多媒体诗歌凭借网络这股东风兴起,但同时也被局限在网络之上。随着互联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信这一问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今天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流行也给这一类诗歌带来了一定的转变契机,值得作者与研究者们注意。
结 语
毛翰先生的作品固然在面对上述问题时拿出了自己的创作实绩,他的《天籁如斯》等作品可以说很好地处理了诗歌文本、图片与音乐之间的矛盾,三者或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或在相互间的反差中形成一种张力,让人深思。陆正兰指出毛翰的创作综合了中西之长,既避开过分西化的故作姿态,又避免拘泥十九世纪前中国传统的强迫症状[6],虽然所选用的摄影作品和钢琴音乐都本自西洋,但也能通过精心的编排展现古典韵味。正如最早的《弹歌》、《大雅》、《九歌》等古诗是与音乐舞蹈浑然天成的那样,今天的多媒体诗歌也可以认为是诗歌从纯文本向多媒体的“回归”。当然在认可毛翰诗歌的同时,依然要认识到网络时代诗歌的发展重点依然是诗歌文体本身的重建,百年新诗经过了不断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作为一种永远充满活力的文学体裁,新诗的探索还依然远没有结束。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边缘化的诗歌能重新“生存”于这古老的诗国。毛翰先生与台湾诗人的创作则是几条探索诗歌在网络时代的“发展”的途径,也可以说是探索了吕进先生所谓“三大重建”中传播方式重建的新路。但不能把诗歌创作的道路仅仅局限在此类多媒体诗歌或超文本诗歌当中。诗歌的重建还包括诗体重建和诗歌精神重建,而传播方式的重建也应当有更多的渠道和走向,而在专注于通过音乐、图片等手段增强诗歌表现力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诗歌内部的话语蕴藉和审美内涵依然是决定一首诗歌能否被读者长时间阅读和关注的核心关键。这是在肯定和提倡多媒体诗歌的创作尝试时同样需要意识到的问题。
[1]周剑虹,佘林颖,冯康.网络诗歌勃兴 中国诗歌传播深刻变革[EB/OL].[2005-11-04].http://news.xinhuanet.com/it/2005-11/04/content_3728773.htm.
[2]张清华.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5.
[3]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M].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1.
[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发展史——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5]刘秀娟.重新发现诗歌的力量[N].文艺报,2010-08-02(1).
[6]陆正兰.超文本诗歌联合解码中的张力——论毛翰《天籁如斯》的形式创新[J].诗探索,2007(3):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