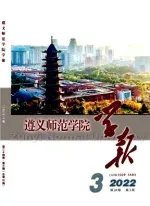仡佬族衣食住行风情
孙建芳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仡佬族,一个率先在崇山峻岭中“开荒辟草”的民族,一个世世代代被人呼作“蛮王仡佬”的民族,一个曾经辉煌灿烂却多灾多难的民族,一个历经大悲大喜却卓然于世的民族,落地生根,抽枝开叉;高山远水铸就了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春风秋雨雕塑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从此,他们在黔北大山里生生不息,发芽开花;从此,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云霞灿烂,绝代风华;从此,中华民族大家庭就盛开着这朵绚丽迷人的民族之花。
长期的社会实践使仡佬族人不但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磨炼出了各行各业心灵手巧的民间艺人。在他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能工巧匠层出不穷,衣食住行各领风骚,各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衣:恕和先贤制衣襟,青衫黑袍配桶裙
仡佬族区域广泛,不同支系所穿服装往往颜色不同,所以,人们干脆简单地依其服色称之为红仡佬、白仡佬、青仡佬、花仡佬。这个自称“仡佬”而意译为“竹”的民族,有穿云破石的豪迈气概,却摆脱不了世代的贫瘠与苦难,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的服装上。回溯历史,曾经的仡佬族,无论男女老幼,绝大部分青衫黑袍,默默地穿行在生养他们的群山之中,躬耕劳作、采摘编织……深黑的服饰一如生命中的沉重叹息,又如日子里的悲伤哭泣。贵州的诸多土著民族,如苗族、水族、彝族、侗族、布依族等,常常衣着华美、色泽艳丽,首饰精良、环佩叮铛,能歌善舞、舞美歌亮。他们用夸张的装扮、鲜艳的色彩、闪亮的银饰,激情的歌舞,将年头月尾、季末节梢渲染得五彩缤纷、灿烂夺目。
仡佬族却与众不同,曾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使他们深沉含蓄、沉默寡言,喜怒皆能不行之于色,平日里少见轻歌曼舞,即便是节日的祭祀庆典、民众狂欢,也少有劲歌热舞,更没有狂歌醉舞,他们用青衫黑袍、酽茶烈酒,就可以将寡淡如水的日子打点得千滋百味、丰满妖娆。他们的日常服装用色单调,裁剪简单,但色泽大胆,对比强烈,面料多来自民间手工制作、自织自染的棉麻细布,结实耐用,朴素大方。他们衣着的最大特点,是上衣前短后长,这是因为,生活在大山之中的仡佬族,每日面对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梯下坎,千折百回,躬身爬坡时,前短后长的衣襟、无需裁剪的桶裙最是相宜,这也算因地制“衣”的典范了。
“桶裙”在仡佬族服饰中最负盛名,具有“标志性”意义。古代仡佬族男女皆穿裙,区别在于男裙短女裙长。用一幅布横围腰间,无褶无叉,其状如桶,谓之“桶裙”;也有说裙腰无褶皱,穿时以裙自头贯通而下,故又名“通裙”。各地桶裙长短不一,颜色各异,质地有别,有土布做成,有羊毛织就,葛、麻、丝、棉,不一而足,但裙摆往往都镶有色彩艳丽、图案漂亮的各式花边。他们的歌谣唱道:“盘古老王分天地,九天天主制人烟。五濮始祖种五谷,恕和先贤制衣襟。”
这是他们的神话故事,也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是他们的历史书,也是他们的教科书。关于“衣”,他们真有一部“专著”《染匠传言大吉》,是道真仡佬族人韩铨顺于清光绪丙申年(1896年)编写的一部染匠知识大全。全书共五章90页,是作者传训弟子的一本“教材”。这部有关印染棉、麻、丝绸和毛料等布匹的古籍,详述了印染不同材质的方法和步骤,以及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为行业始祖生日大祭仪式等,是作者根据师传及长期劳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仡佬族在印染文化上不可多得的独到贡献。[1]
食:酸甜苦辣皆入味,迎来送往真性情
“食色性也”。生存是人的第一本能,也是社会的第一要务,因此,食物便成了生命中最可宝贵也最被关注的东西。民以食为天,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概莫如此。而每一个民族的美食,往往也都有别于其他民族,要么别出心裁,要么独树一帜,食材五花八门,做功千奇百怪,吃法更是标新立异,甚至匪夷所思。有的令人垂涎三尺,有的令人望而生畏,有的叫人食欲大振,有的让人退避三舍……而仡佬族的食谱,虽无派无系,却自成一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他们喜酸爱辣,酿酒制茶,生生把“食”创造到了极致,尤其是他们的茶、酒、酸、辣,那可既是“美味”更是“绝味”。
首先是“茶”。据史料记载,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被誉为“东方饮料的皇帝”。茶叶含有400多种成分,具有利尿消脂、明目益思、消炎解毒、提神醒脑等功效。
即便与汉民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相比,仡佬族的茶也堪称一绝:
“茶鲜鲜,茶鲜鲜,仡佬油茶几百年。
男人喝了更强壮,女人喝了更漂亮。”
这是仡佬族人人会唱的“敬茶歌”。热情好客的仡佬人,不管贫穷富贵,只要客人造访,无论远乡近邻、生人熟客,都要端出特制的“油茶”殷勤款待。主妇们炒茶制茶的手艺和热情,令人称奇:先用猪油爆炒青茶,拌以蛋、肉熬煮,再加入芝麻、黄豆、花生末,最后放入食盐、花椒等调料即可食用,同时佐以各色果蔬点心,如包谷花、米花、酥食、麻饼、花生、糯米粑等。客人食之既提神,又驱寒,还助消化,香甜可口,滋润养人,余韵悠长,唇齿留香。在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油茶干脆就叫“干劲汤”,顾名思义,就是喝了油茶后神清气爽,精神倍增,干起活来不知疲倦,劲头十足。
“地满云连树,山空洞出砂。春枝飞越鸟,落日煮僧茶。”这是一首古诗,生动地描写了仡佬族发源地务川百姓世外桃源般的诗意生活,其实也是仡佬儿女对田园牧歌生活的真情寄托,是他们精神心灵的真实写照。仡佬族女子在清明前后、丽日晴空下赛歌采茶的身影,更是春深似海时节一道令人心醉的美丽风景。
接着是“酒”。贵州盛产美酒,是名不虚传的“醉美”酒乡,流淌着一条著名的“美酒河”,这也是一条“英雄河”,那就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河。赤水河两岸除去名闻天下的国酒茅台,还有数十种各式各样名扬中外、闻之欲醉的名优白酒。高原山区“天无三日晴”,气候潮湿寒冷,需要白酒祛湿驱寒;温润的空气、甘冽的山泉、神秘的菌群也适合于酿酒。仡佬族很早就会酿酒,他们用糯米、包谷、高粱、红薯、甚至野生的青杠籽烤酒,传说最早的“枸酱”即茅台酒的前身,就是他们酿制出来的。
仡佬族酒俗繁多,酒礼复杂,终其一生,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离不开酒:出生有“月米酒”,生日有“生期酒”,结婚喝“花红酒”,盖房请“上梁酒”,乔迁新居吃“搬家酒”,老人去世办“丧葬酒”,逢年过节吃“祭祀酒”,总之,每个节日忌日都有名目各异、种类不同的“酒”。酒已经成为仡佬人的一种生命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交际手段,人们习惯把各种或简陋或奢华的筵席统统简称为“吃酒”,甚至走亲访友也不例外。而仡佬族酒俗酒礼最典型最别致的,当属名闻遐迩的“三幺台”。“幺台”是仡佬族民间的方言土语,意为“结束”;“台”则是量词“道”、“次”的意思。“三幺台”就是请贵客吃饭,一顿饭要吃三台才算完结。这“三台”分别是茶席、酒席、正席,各有一个寓意美好的称谓,即“接风洗尘”、“八仙醉酒”、“四方团圆”;一道吃罢,再上一道,一道俗称一台,故三道称为“三么台”。
然后是“酸”。仡佬族喜欢“辣”,更爱“酸”,酸菜、泡菜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菜肴。民间俗语有“三天不吃酸,人要打偏偏”;“三天不吃酸,人要打捞窜”的说法,说的是酸菜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功能。山区的仡佬人家,几乎家家户户必做酸菜,好“送饭”(下饭)又好存放;而作为常备菜的“罐罐菜”,也是以酸为主,还有水腌菜、寸寸菜、酸辣椒、酸豇豆、酸茄子、酸蕨菜、酸萝卜丝、酸大头菜……这些普普通通的农家菜式,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可谓当之无愧的“山珍”,充分展示了仡佬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智慧,也承载着仡佬人独辟蹊径的饮食习俗。单单一味“酸”,就被他们吃出了百转千回的无穷滋味,比较突出的如——
皮酸:这是仡佬族招待贵客的“佐酒菜”,用牛皮或猪皮加工泡制而成,尤以水牛皮为佳,如果再加入牛蹄,就更是上乘的美味佳品。“皮酸”以酸味为主,加以佐料,麻、辣、咸、香适度,风味独特,有肉皮味而无油腻感,软而不烂,清脆又略带韧感,酸香爽口,去油清心,使人食欲大振。
麻糖醋:务川特产的“麻糖醋”,可算仡佬族饮食文化的一绝。区别于其他醋的最大特点,是除了做调味品外,还可直接饮用,是盛夏时节清凉解暑的绝佳饮料。其味酸中回甜,同时还带有浓厚的蜂蜜味儿,清醇绵长,祛渴生津,使人一饮难忘。[2]
臭酸火锅:盛行于黔南仡佬族地区的“臭酸火锅”,很像风靡各地的“臭豆腐乳”,闻着臭吃着香,一家子吃满寨子“香”,当地人形象而又风趣地称之为“丑酸”。已有上千年历史的“臭酸”,酸中有辣,又酸又辣,麻辣不分家,真真让人胃口大开,爱不释“筷”。
最后是辣。辣椒是仡佬族须臾难离的美食。民谚曰: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辣椒本是外来物种,原产于中南美洲的亚热带地区,明末传入中国沿海,清初始在贵州种植。道光《遵义府志》曾有记载:“郡人通称海椒,亦称辣角,园蔬要品,每味不离。盐酒渍之,可食终岁。”虽是引进品种,但勤劳智慧、富于想象、勇于创造的仡佬族人,却把辣椒“种”出了诗意,“吃”出了风情,“变”成了文化。他们的歌谣唱到:
“白米饭来红辣椒,金碗盛来银筷挑。
龙肉下饭吃不饱,海椒下饭乐淘淘。”
辣椒吃法多多,创意无穷:可炒可炸、可蒸可煮、可煎可熬、可烧可烤,千变万化,推陈出新。喜食辛辣的仡佬人,年深日久渐渐养成“无辣不成菜”的生活习惯,这就把辣椒的做法和吃法都发挥到了极致。除应时应季的新鲜辣椒外,还有香喷喷的“胡辣椒”,油汪汪的“油辣椒”,酸辣适中的“糟辣椒”、酱辣椒,开胃下饭的“酢海椒”、“泡辣椒”,还有欲罢不能的“糍粑海椒”、“莽椒”、“海椒粑”,以及油制辣椒、辣椒酱、辣椒面、辣椒油、袋装辣椒干等辣椒制品,还有街头随处可见、立等可食的名优小吃“麻辣烫”,以及无论大酒店小饭馆或街边食摊,荤素皆必不可少的“海椒蘸水”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辣椒成了仡佬人的挚爱,大街小巷,华屋陋室,只要哪家在“制”辣椒,无论煎炸烧烤,空气里满满地弥漫着辣椒的香辣味儿令人口馋。
仡佬人喜食辣椒,有着阴冷潮湿的高原气候祛湿驱寒的实际需求。“仡乡辣椒满山坡,辣椒林里妹想哥。山歌唱了万十首,情哥在妹心窝窝。”此时,小小辣椒又成了仡佬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传情达意的桥梁和媒介。
住:“贫女梳头”手艺巧,家住“干栏”和“吊脚”
仡佬族房屋村寨往往依山顺势而建,因地制宜,省地节料,“干栏式”、“吊脚楼”,既是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民族智慧的体现。
远古时代,仡佬族地区山高谷深,树茂林密,更兼雨重雾浓,虫灾蛇祸,因此住房形式特殊。《魏书·僚传》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以此隔离瘴气潮湿,避免野兽祸害。后虽将房屋建于地面,但多系楼房,人居楼上,楼下圈养牲畜,仍沿以“干栏”之名。黔北一带至今还有不少“干栏”式建筑,多以木板为壁,上盖以瓦。清代以来,在汉文化影响下,仡佬族改楼房为平房,正房三间并列,中为堂屋,左右二间各隔为前、后两进,前进用作灶房、火塘,后进为卧室。房屋墙壁多用土板筑成,屋顶盖以茅草。
因地域分布广阔以及他民族的影响,各地仡佬族民居差异很大,呈现出不同的建筑格局,既独具风情又与当地环境浑然一体。如黔中一带多为石板房,以石块砌壁,原木作楼枕,编竹为楼,存放杂物,方形薄石板作瓦,人居楼下。这种石屋与附近的布依族和汉族“屯堡人”大同小异。“屯堡人”的石碉楼易守难攻,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对当地仡佬族民居影响很大。滇东南和桂西北仡佬族的住房,一般多是筑土墙,以木板搭制为楼。黔西北一带多为茅草房,草盖得厚实整齐,屋脊和屋檐相当讲究,特别是檐下收尾处精心编织造型各异的带状结,如同盖瓦屋面的“封檐板”,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被外界美誉为“贫女巧梳头”。黔北仡佬族,房前屋后竹木葱茏,屋面覆盖小青瓦,四周安装木板壁,若是篾条墙、篱笆墙,则粉刷白灰,清爽明快,赏心悦目。黔东北的仡佬族则酷爱修建干栏式“翘角楼”,竹木掩映下,栋栋小楼风姿绰约,娇俏迷人。正屋一侧,加建厢房,均为两层,多是吊脚,底屋关牲口、堆柴草、放农具,楼上环以“直棂栏杆”,檐下晾晒衣物,成为开放式仓库。飞檐翘角小巧玲珑,美观实用,既增加室内采光,又扩大室外使用空间。封檐板刷上白石灰分外醒目,逢年过节,门窗、立柱遍贴对联,气氛更为喜庆热烈。秋收时节,家家户户檐下挂满金灿灿的包谷,红艳艳的辣椒,丰年美景令人顿生满足之感、快乐之意。
对于仡佬族别具特色的民居,文人骚客常常不由自主放歌赞美,他们挥毫泼墨,赋诗填词:
“梦里修竹依农家,仡佬山乡景物华。
高廠瓦屋鳞栉比,低岚呈瑞舞飞霞。
房内楼居梯而上,角落火铺满星花。
别致水缸多彩艺,梨林深处更堪夸。”
现代都市时尚流行的“楼中楼”,原来却是仡佬先民的首创。仡佬族诗人、仡佬学会会长田金海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仡佬族极富创意的民居文化。
更令人叫绝的,是那“挂在悬崖上的街”:“转过山岗,还远远的,看见峡谷那边一溜房子斜在崖畔,心有一种紧;大多木房子,屁股上生一些桩,斜斜的坐在崖壁,成一溜吊脚楼;风吹草动的,那房那楼的仿佛也吱吱嘎嘎的响……”[3]远远望去,“吊脚楼”组成的街,整个就“挂”在悬崖上,要多险有多险,要多奇有多奇。著名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小说《挂在悬崖上的街》,描绘了仡佬山乡独一无二的小镇街景,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令人过目难忘。
旧时仡佬族住房因贫富不同差别较大。富者一般是木柱穿架的高房大屋,叫“穿斗房”,四壁、天楼、地楼全用厚木板装制,顶盖瓦片或石板,雕梁画柱,细钻阶檐,高大宽敞,干燥舒适。穷人则简陋得多,往往土墙茅屋,树皮盖顶,甚至住岩洞,或在树上搭棚巢居,或住屋檐直接触地的“四脚棚”,或用树枝、苞谷杆等编成“千根柱头落脚”,俗称“千脚棚”的“塌塌房”。新中国成立后,仡佬族住房状况日益改善,砖木结构住房广泛出现。如今,木结构住房居多,钢筋混凝土的多层楼房也逐步兴起。
行:开门见山弯又弯,七十二拐九连环
仡佬族聚居区大多为高原山区,山高坡陡,少有平地,古语“跬步皆山”,正所谓“开门见山”。仡佬族村寨往往坐落于云雾缭绕的半山腰上,抛开唯美的抒情和诗意的浪漫,其生产劳动、生活娱乐及人来客往、出门远行皆多有不便。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常有“三十六道拐”、“七十二道拐”、“九十九道拐”等形象贴切的称谓,民间总结为“隔山喊得应,见面走一天。”崇山峻岭,山水阻隔,在这盘旋往复的山路上下下,人们常常边走边唱:
“七十二弯下路边,等船不来口喊天。
凄惨岸脚歌一夜,肚皮饿来口又干。”
山多路险,这一方面练就了仡佬族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和生存智慧。
新中国成立前,既因贫穷也因环境所限,仡佬族男女老幼一年四季皆打赤脚,或穿自家编织的草鞋。为便于在遍布荆棘碎石的山道上行走,他们每天用烧得滚烫的桐油擦脚,以增厚脚底的硬皮。山高水深,坡陡路险,特别是在山路上负重远行,晃晃悠悠的担子多有不便,因此仡佬人很少挑担,多为“背篼”。如果所背之物过重,途中需要歇息,重物很难放下,放下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也很难再背上,因此,他们常随身携带一根形如钉耙的“拐耙子”,累了就随地用这根木拐作为支点站着休息,直到恢复体力可以继续前行。正是这些出卖劳力的“背夫”(背老二)、挑夫(挑子客)、抬夫(脚子),用他们的铁肩铁脚板,负着沉重的货物,下四川、去广西、出云南……走南闯北,肩挑背扛,何其悲壮苍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大量投资,百姓出工出力,开山凿洞,跨河架桥,一条条阳关大道使得“天堑变通途”,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工程,翻山越岭不再令人望而生畏。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仡佬族,迎来送往如履平地,走村串寨安车代步,肩背手提、牛驮马运的悲苦日子已是历史远景。遥想当年,黔北作家石定的小说《公路从门前过》,通车通路的惊喜犹历历在目,作者因此荣获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而今,面对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现代交通网络,仡佬人微笑莞尔,只能向孩子“忆苦思甜”,向孩子的孩子“话说当年”了。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了云贵高原独有的地形地貌,这块原生态的、“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锦绣大地,其山魂水魄、日精月华必将促使仡佬儿女用勤劳智慧为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勾勒浓墨重彩的“风俗画”,为日新月异的时代风云抒写行云流水的“华彩乐章”。仡佬族,这朵绚丽的民族之花,在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里,在争奇斗艳的百花园里,和55个兄弟民族一起,高歌猛进,尽情绽放。
[1]梅应魁.《染匠传言大吉》识读(上)[J].中国仡佬族2008创刊号,黔新出报刊(2008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52号).57.
[2]张永胜.仡佬族百年实录(下)[M].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8.1176.
[3]赵剑平.挂在悬崖上的街 [M].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199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