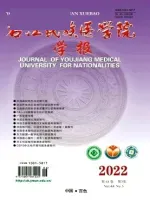儿童缺血性脑卒中研究进展
凌俊
(广西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广西 百色 533000 E-mail:847097471@qq.com)
儿童缺血性脑卒中(IS)是由多种病因导致颅内动脉管腔狭窄、闭塞,供血区域神经细胞发生缺血坏死,神经影像学检查显示病变区域有梗死存在,急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持续可超过24h,占儿童脑卒中的40%~45%[1],出生 1个月~18岁的儿童均可发病,是儿童期重要的致残性疾病之一。儿童IS发生率虽然很低,但因病因复杂多样,临床症状不典型,医师在诊治过程中容易导致儿童IS的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对儿童身心发育危害性大,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为此,笔者对国内外临床医学界进行的儿童IS的致病因、疗法及预后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流行病学
成年人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约为2501/10万,多见于年龄在50~60岁以上中老年人,大部分病人存在动脉硬化的慢性病变。而12岁以下儿童IS发病率较成年人低,在北美和欧洲,18岁以下儿童IS的发病率为每年2~13/10万[2,3],中国香港儿童发病率为2.1/10万[4]。一般情况下,儿童IS在婴儿期发病率最高,进入儿童期又显著下降,发生率约1/10万,这是由于儿童期特有的生理特征导致血浆凝血酶原浓度降低、凝血酶活性下降、血浆α2巨球蛋白浓度增高,机体内凝血酶显著抑制以及内皮抗栓能力增强,从而明显降低了儿童受到血栓疾病侵害危险,随着年龄增长,10岁以后发病率及病死率的危险性又逐步增加。文献报道儿童IS男童发病多于女童[5,6],发病率男女之比约为1.8∶1.0[7],提示儿童IS的发生存在性别差异。Fullerton等[6,8]研究发现,美国黑人较白人更易患儿童IS,且病死率高,结果提示儿童IS的发生及预后存在种族差异。
2 病因
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成年人特别是中老年人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因。而儿童IS的病因则与成人明显不同,常见儿童IS病因在北美地区以心脏病和心脏手术为儿童IS的主要危险因素[9],在欧洲地区则以凝血功能异常、黑人以镰状细胞病(SCD)为主要危险因素[10],亚洲地区报道,日本因烟雾病导致IS的比例较高[11],中国台湾地区儿童IS最常见的病因依次为血管病(包括烟雾病、夹层动脉瘤和先天性血管畸形)、感染、代谢性疾病[12],心脏病是中国香港儿童IS重要的病因[13],刘平等[7]学者研究报道,中国儿童IS的常见病因有烟雾病、头部外伤和感染。可见儿童IS为多病因疾病,因地域、种族、性别的不同,有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病因。
2.1 烟雾病 烟雾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闭塞性脑血管疾病,该病为神经影像学现象,也称自发性基底动脉环闭塞症或Moyamoya病,是儿童期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常见病因。有研究证据表明,烟雾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多基因病,且带有低外显率者遗传性强。该病常见于日本、中国、朝鲜,可以是家族性或散发性。目前随着现代神经影像学的快速发展,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烟雾病的检出率逐年增高,并已成为儿童IS常见的病因。患者在4岁左右和30~40岁出现两个发病高峰,半数烟雾病病人10岁前可出现临床症状,主要临床表现有头痛、癫痫、进行性认知功能减退及脑卒中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可发现患者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中动脉近端狭窄或闭塞、颅底可见烟雾状的异常血管网、且病变部位多为双侧性。DSA或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检查发现颅底异常血管网是烟雾病的典型改变[14],DSA检查是诊断烟雾病的金标准,但因具有一定创伤性及受儿童年龄的限制,DSA难以作为诊断儿童时期烟雾病的首选。而头颅MRI结合MRA检查因具有无创伤性、不受年龄限制、操作方便、不需要造影剂等优点,且多数烟雾病可据此明确诊断,故具有重要临床诊断应有价值。但是对临床上高度怀疑烟雾病,经MRA未能明确诊断或拟行手术治疗者,DSA检查仍是必须的[15]。
2.2 外伤 婴幼儿期因脑部血管纤细,自主神经功能发育不健全,当发生外伤时头部突然屈伸运动,牵拉颈部血管,外力结果导致动脉壁挫伤、内膜受损、反射性血管痉挛或闭塞而使供血减少,也可因外伤后组织因子大量进入血液循环,启动了体内外源性凝血系统,容易形成血栓,故儿童期外伤无论是否合并头部外伤,均可导致儿童IS发生。而婴幼儿位于基底核区的穿支动脉、豆纹动脉和前脉络膜动脉因距离脑部大动脉主干较远,动脉走向迂曲,故基底核区更易发生血管栓塞。有报道发现外伤后发生脑梗死的儿童有脑部豆状核钙化,提示可能存在某些内分泌代谢方面的紊乱,造成黏多糖胶体沉积在小血管内及其周围,小血管壁发育脆弱为导致供血区发生梗死的内在原因[16]。
2.3 感染 儿童缺血性脑血管病多为脑动脉炎引起,约占45.5%[17],病毒或细菌感染可直接引起脑血管炎,使脑动脉管腔变窄、闭塞或形成血栓,导致供血区域血流灌注不足,神经细胞发生变性、坏死,同时感染可能引起系统性炎性反应形成血栓、高凝状态或直接破坏内皮细胞导致IS的发生[18]。有研究报道[19]42例儿童IS病例中12例有感染因素,其中7例呼吸道感染,3例颅内感染,感染病原有EB病毒、结核、支原体。2例发病前3个月有水痘和麻疹病史。提示儿童时期各部位的感染,不论是病毒还是细菌感染,都可以导致儿童IS的发生。
2.4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是指心脏血管在胎儿时期因各种原因引起发育异常而导致的心血管畸形,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心脏病,出现血流动力学障碍,血液流动缓慢,容易形成附壁血栓,血栓脱落后造成血管栓塞,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可因感染、脱水引起血液黏稠度增加而更易形成脑血栓,1/5~3/5的缺血性卒中为附壁血栓引起。新生儿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为5/1000~10/1000,可见先天性心脏病是儿童IS的重要危险因素。先天性心脏病病因研究近年来有了重大进展,根据目前研究,由于染色体和单基因异常而导致的各种先天性心脏病约占总数的15%。但目前多数学者仍认为心血管畸形主要为遗传和环境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结果所致,导致心血管畸形的因素主要有:①妊娠早期胎儿宫内病毒感染,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和柯萨奇病毒感染等;②母亲妊娠期有大剂量放射线接触史和服用致畸药物史(甲糖宁、抗癌药、抗癫痫药物等);③母亲妊娠期营养和代谢紊乱性疾病(糖尿病、高钙血症等);④引起胎儿宫内缺氧的各种慢性疾病等;⑤母亲妊娠早期有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⑥环境因素,如大气、水质、毒物及放射性元素等。
2.5 SCD SCD是由于β链第6位谷氨酸被缬氨酸取代,形成Hbs,致使电荷改变,在脱氧情况下,Hbs可聚合成长棒状聚合物,导致红细胞镰变而引起血黏度增高,引起继发性血管梗阻症状发生。该病在欧美国家发生率为1/400,多见于黑色人种,对于SCD引起的儿童IS,TCD检查有较高诊断价值,颅内动脉血流速度达200cm/s或以上者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20]。对于经颅多普勒(TCD)异常的SCD儿童如能及时给予输液治疗可明显降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有研究证明,长期输液治疗可使儿童IS的再发率低于10%。
2.6 先天性或遗传性疾病 许多先天性或遗传性疾病由于影响了凝血因子的转化或使血液中促凝因子增多而致血栓形成[21],这也是儿童IS病因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疾病:①先天性蛋白C或S缺乏症:该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遗传病,蛋白C可通过蛋白分解抑制激活的凝血因子Ⅴ和凝血因子Ⅷ的活性,起到一定抗凝作用,是机体内主要的抗凝蛋白之一,如果蛋白C或S的基因出现突变,将导致蛋白C或S的含量降低或功能异常,血液呈高凝状态而形成血栓。②高胱氨酸尿症:高胱氨酸尿症是一种缺乏胱硫醚合成酶的常染色体遗传性代谢性疾病。可有骨骼异常、智力障碍、发育障碍、四肢强直、头发稀疏、水晶体位置异常及心血管系统异常等临床症状,患者因高胱氨酸堆积、胱氨酸缺乏,容易导致血小板凝集,形成血栓而死亡。有研究报道45例儿童IS中有18%病例(8例)存在高半胱氨酸水平增高[22]。③遗传性抗凝血酶Ⅲ缺乏症:该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1965年由Egeberg等首先报道,发病率有显著种族差异,性别之间无差异,父母患本病则子女发病可能性约59%。抗凝血酶Ⅲ对凝血酶Xa有抑制作用,同时还可抑制凝血酶Ⅸ、Ⅺ及Ⅻ的功能,抗凝血酶Ⅲ缺乏容易发生血栓形成。该病诊断需基于对患者全病史及家系谱的了解,阴性家族史者也不能完全除外自发变异的先天性缺乏症。
3 治疗及预后
有关儿童IS的治疗因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目前我国仍无统一的儿童IS诊治指南,造成临床研究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儿童期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低,研究例数少;二是儿童IS病因的复杂、重叠和差异形成不均一的发病群体;三是对儿童IS诊治多侧重于脑卒中发生后的治疗,而不像成人开展前瞻性群体性大规模研究,如病前体检筛查、急性期溶栓和血管内介入治疗以及远期预后观察。目前对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的儿童开展免费手术矫正是预防儿童IS的一项重要措施。在SCD儿童的一、二级预防脑卒中中,应用钙通道阻滞剂预防儿童IS发生有效,但是反复输液治疗仍是降低SCD儿童镰刀细胞浓度的重要措施。烟雾病在诊断明确后行手术治疗效果最好,但儿童IS的血管介入治疗因例数较少,且临床资料一般来源于对成人随机试验的推测,而应用于成人数据的安全有效性也没有在儿童应用中得到确认。也有报道提出,补充叶酸和维生素B12、降低胆固醇对某些脑卒中儿童可能更适合[23]。对于儿童IS急性期是否进行溶栓治疗(纤维蛋白溶酶原活化剂、尿激酶)、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或抗凝治疗(肝素钠、华法令),以及是否应用阿司匹林预防治疗、疗程多久,均有争议[24,25]。有关儿童IS的预后观察随访研究多为欧美国家开展,但存在研究例数少、随访时间短等问题,特别是儿童IS接近成人期的远期预后随访研究资料匮乏。我国学者研究后发现儿童IS远期预后较好,均可以达到生活自理。约50%患儿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功能障碍和心理问题,整体认知能力偏低。基底节、内囊和丘脑部位梗死和特发性IS者运动功能预后良好[26]。故明确儿童IS的常见危险因素,提前预防干预,做好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正确治疗,对患儿预后有着重要影响。
总之,儿童 IS因为发病率低,临床症状不典型,在临床诊疗中易被误诊、漏诊,而延误治疗,严重影响患儿预后恢复和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正确掌握和认识儿童IS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医师在诊疗中如发现患儿出现头痛、语言障碍、感觉障碍、意识障碍、惊厥或偏瘫等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时,应选择合适的神经影像学检查,以排除有儿童IS发生的可能,尽快明确诊断,争取早期治疗,降低并发症和后遗症发生。今后还应针对儿童IS积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统一制定我国儿童IS的预防、干预、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导临床科学预防和治疗,同时加大对儿童IS预后观察和随访,特别是远期预后跟踪随访研究,对患儿开展日常生活能力、运动功能、社会交往、语言、心理行为和认知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为儿童IS的研究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1] Mackay M T,Gordon A.Stroke in child ren[J].Aust Fam Physician,2007,36(11):896-902.
[2] Lynch JK,H irtz DG,DeVeber G,et al.Reporto 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orke Workshop on perinataland childhood stroke[J].Pediatrics,2002,109(1):116-123.
[3] Lynch JK,Han CJ.Pediatric stroke:w hat do we know and w hat do w e need to know?[J].Sem in Neurol,2005,25(4):410-423.
[4] Chung B,W ong V.Pediatric stroke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subjects[J].Pediatrics,2004,114(2):206-212.
[5] 石凯丽,邹丽萍,王建军,等.157例儿童动脉缺血性卒中住院病例回顾性分析[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7,22(11):830-833.
[6] Fullerton HJ,Wu YW,Zhao S,et al.Risk of stroke in child ren:ethnic and gender disparties[J].Neurology,2003,61(2):189-194.
[7] 刘平,张月华,马秀伟,等.儿童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特点及病因分析[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8,23(24):1891-1893.
[8] Fu llerton HJ,Chetkovich DM,YW,et al.Deaths from stroke in US child ren,1979 to 1998[J].Neurology,2002,59(1):34-39.
[9] deVeber G,Canadian Paediatric Ischem ic Stroke Study Group.Canadian Paediatric Ischem ic Stroke Registry: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arterial ischem ic stroke[J].Ann Neurol,2000,48:526.
[10] Lynch JK.The hospitalization of childhood stroke in the United State,1979-2000[J].Stroke,2003,34:287.
[11] Shi KL(石凯丽),Zou LP.儿童动脉缺血性卒中的研究进展[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07,2(5):388-394.
[12] Lee YY,Lin KL,Wang HS,et al.Risk factors and outcoms of childhood ischem ic stroke in Taiw an[J].Brain Dev,2008,30(1):14-19.
[13] Chung B,Wong V.Pediatric stroke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subjects[J].Pediatrics,2004,114(2):206-212.
[14] 马秀伟,陈军,张月华,等.儿童烟雾病临床及影像学特点[J].临床儿科杂志,2008,26(2):92-95.
[15] Yamada I,Nakagawa T,Matsushima Y,et al.Highresolution turbo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for diagnosis ofmoyamoya disease[J].Stroke,2001,32(8):1825-1831.
[16] 张培功,秦东京,庄悦新,等.小儿外伤性腔隙性脑梗塞(附28例临床及CT分析)[J].中华放射学杂志,1995,29(4):252-254.
[17] 齐献忠.儿童中风21例分析[J].河南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3,6(5):50-51.
[18] Lindsberg PJ,Grau AJ.Inflammation and infections as risk factors for ischemic stroke[J].Stroke,2003,34(10):2518-2532.
[19] 陈红梅,陈锐,刘炎洁,等.儿童缺血性脑卒中42例临床分析[J].内蒙古医学杂志,2010,42(12):1502-1503.
[20] Adams RJ.Stroke p 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sickle cell disease[J].A rch Neurol,2001,58(3):565-568.
[21] 岳炫烨,马存根.凝血酶与缺血性脑损害的炎症反应[J].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分册,2004,12(5):375-378.
[22] Roach ES.Etiology of stroke in children[J].Sem in Pediatr Neurol,2000,7(4):244-260.
[23] DeVeber G,Roach ES,Riela AR,et al.Stroke in child ren:recognition,treatment,and future directions[J].Sem Pediatr Neurology,2000,7(2):39.
[24] Simma B,Martin G,Muller T,et al.Risk factors for pediatric storke:Consequences for the rapy and quality of life[J].Pediatr Neurol,2007,37(2):121-126.
[25] Bemard TJ,Goldenberg NA,Amstrong-Wells J,et al.Treatment of childhood arterial ischem ic stroke[J].Ann Neurol,2008,63(6):679-696.
[26] 李久伟,丁昌红,赵若岩,等.儿童缺血性脑卒中远期预后追踪研究[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11,6(6):40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