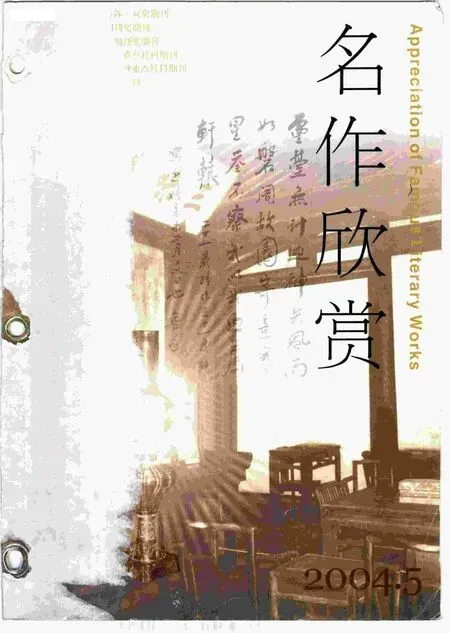渴求·苦难·迷失:新世纪文学底层民工书写论析
⊙丁智才[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南宁 530003]
新世纪以来,底层书写逐渐成了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虽然,书写底层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学史上描绘凡人百姓、关注贫弱群体、挖掘社会底层生活曾出现不少名作;但以前作品大多是表现贫困乡村的农民抑或繁华都市的贫民,而游移于二者之间的民工则不多。近年来,随着民工问题的日益突出,当前文学的底层书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
民工潮的出现是城乡二元体制对立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被一分为二:城市和乡村。与此相联系的是城市人和农村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工人和农民。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线,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制度和体制之中,工人和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存在着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不可转换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广泛引入的市场机制,打开了城市的大门,使原有的户籍制度受到冲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者在城市中的生存提供了大量新的工作机会,使那些因耕地少、农业生产力低下而离乡的未充分就业的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城市外来者、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的出现,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只不过近几年来,这一群体呈迅速地扩大的态势,现在更是达到1.2亿人的规模。这个相当于英法两国总人口的民工潮,汹涌而起,潮涌潮涨,成为我国在全世界独有的一大景观。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大,大中小城市纷纷向农村扩张。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种城乡融合的过程,其实不然。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有血腥味的掠夺:“城市和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①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和还没有逾越前现代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历史阶段的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有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阶段之中。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民工正是这个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的变化,是需要当前作家底层书写着力表现的领域。
底层民工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许多作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两难命题。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一些作家用文学表达了对底层民工命运的深切关注,不仅对其生活困境做了形象的表述,而且感同身受地展现了民工真实的生存处境,梳理和跟踪了他们在乡村、城市辗转过程中的心灵颠沛、精神困境、心理变异、价值失落等生命脉络。
二
城乡差别的巨大悬殊导致了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与渴求。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农民对城市的这种渴望。除了主人公宋家银的北京之行,小说几乎没写城市,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是陌生的,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城市。但城市又是熟悉的,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城市的一切曾经无数次地出现。所以宋家银们对城市充满了强烈渴望,对工人身份哪怕是临时工身份的取得,也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因为工人身份意味着身份的质变,意味着城市人资格的获得。所以宋家银像疯了似的希望丈夫能出去工作,哪怕再苦再累的工作,哪怕牺牲生活中其他任何的东西。如果没有对城市文明深刻的认同,是不会有这样渴望心理的。为了能进城,农村人挖空了心思,甚至不择手段,与城市人通婚是农村姑娘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通婚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城市户口的获得显然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李铁的中篇小说《城市里的一棵庄稼》描写了年轻的农村姑娘崔喜为了进城很是费了一番心机,争取嫁给了死了妻子、三十多岁的宝东,如愿地成为了一个城市人。身份的改变压抑了自己的委屈,后来在面临爱情与城市户口之间抉择的时候,她依然选择了后者。叶舟的小说《世面》通过进城农民的眼睛反映出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石太和王从容两个进城的民工,某一夜,他俩在他们所打工的城市过了一次夜生活。对于五彩缤纷的城市,他们太陌生了,他们不懂什么是卡拉,他们不懂恋人间的亲吻,他们不懂穿着衣服的模特竟然能跟真人一模一样,造成这差距的是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割裂,这种割裂使城市与乡村虽同处于一个社会,但却处在不同的文明层面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工对城市的向往不仅仅是对城市物质生活的渴望,而且也是对先进文明的向往,这也是民工进城大潮的推动力。
夏天敏的小说《接吻长安街》表现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别出心裁。文本以大量的心理描写直接表现这一主题,主人公“我”是一个一心想做城里人的民工:“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当我从报纸杂志上读到一些厌倦城市、厌倦城里的高楼大厦、厌倦水泥造就的建筑,想返璞归真,到农村去寻找牧歌似生活的文章时,我在心里就恨得牙痒痒的,真想有机会当面吐他一脸的唾沫。”后现代文化心态对于仍然生活在农耕文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来无疑很奢侈。因为,解脱贫困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渴望,让一个还没有尝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农耕者去享受后现代的精神面包是不现实的。所以,对城市文明的渴求成为农民工阶层的理想,融入城市便成为民工们的最高追求目标,他们不但要取得这个城市的肉体身份的确认,更重要的是还要取得城市的精神身份证。因此,“我”才别出心裁地用到长安街接吻来证明自我在这个城市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工对城市的渴望,不仅仅是城市富足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获得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城市外乡人起码的精神权利。
三
怀着对城市的极大渴望,来到城市、工矿的民工们生活和精神面貌到底怎样?许多作家以巨大悲悯与同情表现了这些挣扎在生死边缘、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的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遇。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就勾勒了一幅幅底层民工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图景。小说中主人公是都市里的“乡下人”,是游入都市里的“泥鳅”。他们找不到自己赖以生活的阳光、土壤与水分,匍匐在都市的各个角落,经历着为人所不齿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卑贱、无足轻重,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被“吃掉”,就是变成都市里的浮云、落叶和垃圾。国瑞及其兄弟姐妹们的“歌哭”与呻吟萦绕小说的始终,这种真实、鲜活的底层生命的体验与呈现,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源自小说深处的感动。
民工生活的严峻性使得一向以艺术形式探索而著名的先锋作家残雪在审视民工问题时,也不得不淡化怪异色彩而用颇具现实主义的笔调表现了底层民工的悲惨境遇,其《民工团》描绘了民工承受肉体煎熬的生活场景:工头三点五分就叫醒他们去扛二百多斤的水泥包,简直就是现代“周扒皮”的形象再生;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小说较客观地写出了当下农民的处境: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辛而无望的,而外出打工却又是饱受欺凌与侮辱。不仅如此,他们的生命与安全也毫无保障。李师东的小说《廊桥遗梦之民工版》在开头即写道:“工程队原来计划以牺牲五个民工的代价把这座桥搞定,但是断断续续修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死了六个人。一时之间好多民工都想打退堂鼓,工程队只能提高20%工资来挽留,并且鼓励加班。”这里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令人瞠目结舌。王祥夫的小说《找啊找》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询了当下农民工的这一命运。在石墨窑上打工的顾小波早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死去,与顾小波一起出去打工的乡亲,在金钱的驱动下掩埋了他的尸体,并向四处寻找丈夫的顾妻隐瞒了死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民工处境的危险,也看到了朴素的乡间伦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坍塌。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刘庆邦前两年的小说《神木》,也是通过两个打工农民的故事(矿井塌方后两人害死另一人以从中牟利),显示了民工的残酷处境。这些作品表达了对普遍的不公正的一种抗议:当民工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时,当他们在这世间除了侮辱与欺骗什么也无法得到时,当他们无论怎样辛苦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时,他们的精神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民工们的悲苦境地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肉体的折磨、生命的无保障,更有内心精神上的苦痛与煎熬。“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要重要得多。”②当这些苦难一并构成了对民工的价值、尊严否定的时候,敏感的作家总是不愿漠视他们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对人物心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探索,使得作家越过了艰难生活的表面现象,进入到了更广阔、更深层的对人性、历史、文化的反省和思考之上。陈继明的小说《粉刷工吉祥》让人深思:民工吉祥在邮局汇款时发生争执,遭侮辱后愤而反击,终被保安拿下,接下来是漫长的惩罚过程。被保安强行灌醉,扒掉裤衩扔在臭水沟,吉祥醒来后只能赤身裸体在楼里一家一户敲门寻找自己的衣服,这个读来让人心里颤栗的细节隐喻深刻,吉祥被剥去的不仅是遮羞的裤衩,更有乡下人的精神外衣。所以后来无论同乡如何追问,吉祥都不愿说出受暴真相。小说结尾出人意料——“接下来,吉祥继续干活。这座大楼很快要粉刷完了。”在若无其事的平淡中结束,但惟其平淡却愈显骇异。在小说开头,吉祥并不是一个内向而懦弱的人,遭受侮辱后的愤而还击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在经受了保安“非人”的惩罚后,他“似乎认为,自己有这么一张爱说大话的臭嘴,是有必要吃点亏的”,接着“告诫自己万不可嘴硬”,直至最后“没表现出一丝怨愤”,“笑似乎也不再是原初的了,含着原来所没有的浓浓的傻气和呆气”。风暴过后,吉祥的反应愈是平淡克制,其遭受的伤害便愈发显得惨痛酷烈;小说在叙事的从容冷静与结尾的戛然而止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和激越的人道主义诘问:是什么驯服了健康人性?是什么清除了吉祥们对人之为人的正当权利的记忆与秉持?
四
民工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束手无策时,往往容易走向非正常的生存道路。在城市文明的严重压迫下,民工们不再相信靠踏实劳动能征服城市,从而选择了与城市的对抗、报复,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最终迷失自我。由于社会的忽视和不公正,导致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无法生存或应得到的利益受损,从而使他们通过另外一些社会机制给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因素和消极影响,使得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犯罪是民工进行社会报复的最普遍也是最低级的形式。自古以来,思想家就认为贫穷并不会必然导致犯罪,但贫穷无疑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贫穷与不公正结合在一起时,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社会统治关系的一种形式。”③《泥鳅》中的蔡毅江便是一个例子,他承受不了城市给他留下终身残疾的厄运,开始以恶抗恶,人性丑陋开始显现出来,以致落入法网。胡学文的小说《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描写了不甘受穷的农民老六进城后的堕落。被城市生活彻底改变了价值观的老六在城市里注定会成为既不同于农民亦不同于城市人的存在,城市让这个外来者产生了失望继而报复的心理:向城市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老六不惜将“我”的妹妹送给一个大学教授做玩物,以致后来“我”杀了教授,城市就这样吞噬了四个农村青年的肉体与心灵。
对城市的报复心理还来自于城市人与乡村人之间深深的隔膜。从城市人角度讲,他们对乡下人有一种歧视的心理和强烈的优越感,一边享受着民工劳动带给自己日常生活的便利,一边又鄙视、提防甚至凌辱民工;对于民工来说,对城市的向往,就是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羡慕之中亦有嫉妒。不论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城市人与乡下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不同位的。但从最根本上说还是在精神上不能对话交流,这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城乡社会的隔膜。李锐的小说《颜色》触及了这一方面,它通过一个揽活民工眼中的行为艺术,突出地表现了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与错位。小说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角度:一对身裹紧身衣的青年男女,在火车站前表现互相在对方身上刷黑白两色的油漆这一行为艺术。三天中他们最虔诚的观众是一个胸前挂着“杂工”牌子的民工,他眼巴巴地守候着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累了以后花钱雇他表演。在这里,城乡两个世界的差别和对立、乡下佬与城市艺术家的逆向反差、精神上的反叛与物质上的追求奇异地纠结在一起,被并置在一起“看”与“被看”,而又相互错位,具有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既耐人寻味又引人深思,是一篇现实与现代结合较好的底层书写。
马克思说过农民的转化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农民工正以悲壮的方式为实现这种转化而抗争。李民骐将农民工称为“中国的新无产阶级”。在新世纪的中国,这些新的无产阶级大批地走出千年土地,来到了城市,开创自己的未来。如此亘古未有的现象,对文学创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文学底层书写如何表现民工,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①[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4页。
② 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选自陈思和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