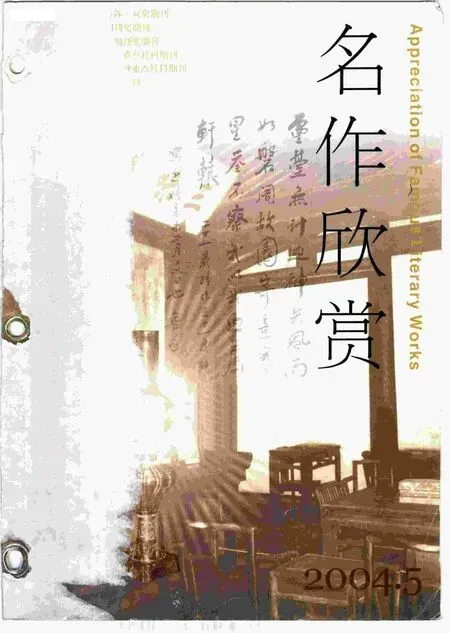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母题的生成及演变
⊙孙玉生 姜丽梅[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1870年,当日本人高山助幸发明第一辆人力车时,他可能没有料到,日后它竟然会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四”以降是人力车夫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大批的人力车夫形象开始被作家带入文学作品中来,遍及于诗歌、戏剧、小说等各方面,构建起清晰的文学基因图谱,形成了动态的文学创作母题。笔者试图从社会学、政治文化等角度来探究“人力车夫”文学母题的生成和流变。
一、从社会现象到文学现实:现代“人力车夫”文学母题的生成
毋庸置疑,20世纪初期,人力车夫已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这一现象走入作家的视域,最终定格为文学现实,在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渐渐地沉凝为一种文学母题,从而对文学艺术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母题的生成动因与人力车夫群体结构的规模化,“劳工神圣”的一声呐喊,以及“血”和“泪”的文学倡导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人力车夫群体结构的规模化。人力车,又名东洋车,北京称为洋车,天津称为胶皮,上海一带称为黄包车,它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都市里最常见的一种交通工具。在中国,人力车夫多是从破产的农村流落到城市的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完全沦为无产者,成为城市社会出卖苦力的劳工。“五四”时期,人力车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了社会底层的一大特定群体。从规模上看,据调查,20年代初期全国有50多万人力车夫。而1923年时北京就有公用人力车24000多辆,1924年时上海两租界加上华界的公用人力车总数15161辆(注:《申报》1924年8月6日)。从年龄构成上看,有幼童、青壮年、老叟(据统计,人力车夫最小的才十一岁,最大的有六十六岁);从形式上看,他们有拉半天的,有拉整天的,有拉包月的,有拉散车的等,规模之大、分工之细致可见一斑。到了20年代中后期,人力车夫的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随着人力车夫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进步文人开始关注人力车夫的命运。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注意到了人力车夫的悲惨人生:“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①可见,人力车夫工作强度大,收入微薄,却要承负着全家生活的重累。之后,人力车夫也渐渐成为了社会的关注焦点,人力车夫问题成为了社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②显然,人力车夫开始作为底层群体形象进入文人视野,人们已经把人力车夫的命运放到了人道主义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
(二)“劳工神圣”的启示。“五四”时期,人力车夫作为底层民众受到作家广泛的关注,这主要是与“劳工神圣”思想的传播有关。早在“五四”之初,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就注意到了“如工厂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③。嗣后的文学界,更多地关注平民的历史命运。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大声疾呼“劳工神圣”并坚定地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④同月,李大钊也做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且断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⑤很快,“劳工神圣”的口号在知识界风行,“劳工神圣”逐渐成为关注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平民主义思潮,并很快成为中心意识形态。正如有的刊物在描绘当时情况所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⑥随着“社会改造”、“劳工神圣”等口号的震颤和回荡,这种呼声渐渐形成作家内在的一种驱动力。一旦,这些呐喊凝结为进步作家的主体意识,触发他们创作灵感的神经,那么,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就会变成一种伟大而又神圣的“政治工作”。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车夫形象步入文学作品,“它们都是同一种驱动力所产生的表达。”⑦从此,人力车夫作品开始成为作家当时宣泄感情的传声筒,并从作家的笔尖上不断滴出人力车夫的血和泪,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长廊里,较浓重灿烂的一笔。
(三)“血”和“泪”的文学倡导。人力车夫文学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会对于“血”和“泪”文学的倡导也不无关系。1921年6月末,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6期的《杂谈》里发表了《血和泪的文学》一文,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认为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怎能吟诵风月?他号召文学创作内容的急需改良:“兄弟们啊!果真不动心么?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⑧郑振铎在介绍《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谈到“血和泪的文学”时,也强调它是从痛苦中发出的呼声,它能震撼全人类的心灵,因为这种呼声是被侮辱的,受难人们血和泪的哭泣。因此,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其要点偏重于真挚性、悲剧性。
1922年,茅盾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可以说是对郑振铎主倡的“血”和“泪”文学的间接声援。茅盾认为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文学的作用,“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中国文学里从来就很少有真情的流露,热烈的情绪颤动。“出于真情的文学才是有生气的文学,中国文人一向就缺少真挚的情感。”⑨尽管对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血”和“泪”文学主张,文学界的反响是不一的,例如郁达夫、郭沫若就持有不同的意见。郁达夫的小说《血泪》中平添的有关人力车夫的“血泪”情节,就是对这一口号的刻意讽刺与反拨。但某种意义说,这又起到了欲盖弥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促使了这一口号在部分作家神经中沉淀的加速和创作冲动意识的生成,而最终成为文学现实。
二、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现代人力车夫文学母题的演变
20世纪前半叶,“人力车夫”母题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洪流的奔泻,作家的思维方式、创作心态、审美趋向的急遽变革以及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呈现出清晰的螺旋上升式的演变轨迹。这恰好客观地反映了“人力车夫”母题作品发展的历史径路。
(一)乌托邦式的同情与赞美。“五四”时期到20年代末,“人力车夫”母题作品试图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表现了人力车夫生活的苦难及其优秀品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受着反复的历史阵痛,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虽然被废除,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反而使之处于常年纷乱的军阀混战之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也烙上了时代的痛苦印记,他们任人践踏、欺凌,生活困顿,精神疲惫,但又不乏质朴、善良、坚韧的美好操行。因此,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作品,存在一个普遍的倾向,作家在写出他们生活苦难的同时,也对其身上固有的优秀品德进行了歌颂。
胡适和沈尹默的同名诗歌《人力车夫》都慨叹了人间的不平,抒发了对弱者的同情。刘半农的《车毯》中的“北风吹来,冻得要死,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却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的抒写,则展示了其“舍身取毯”的矛盾以及被饥寒煎熬的痛苦心理,颇具震撼力。孙 工的短篇小说《隔绝的世界》以富人热闹筵宴的场面,来反衬穷人生离死别的凄惨:临近除夕,拉包月的车夫的儿子患了重病,富人恣乐打牌,却不准车夫回家探视,最后父子遥望两茫茫,隔绝在两个世界里。欧阳予倩的短剧《车夫之家》则展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车夫子死而又被迫搬家的悲惨命运。
同时期的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还侧重于对人力车夫美好品德的观照和歌颂。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则反映人力车夫的善良品行。“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我穿着嫌冷/他穿着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
“五四”时期极力展现车夫人性闪光的作家首推鲁迅,其《一件小事》通过车夫的行为与坐车者自私心理的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人力车夫的无私助人的精神境界,一种需要仰视的人性的巅峰。无独有偶,郁达夫的《薄奠》也展示了人力车夫心灵的纯美。文人出于对车夫的悲惨生活同情,悄悄地摘下银表来资助其家庭用度,但第二天清晨车夫却登门奉还。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小说将车夫的贫困生活与其优秀品质结合起来,使其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人力车夫的文学作品创作颇丰,主题具有一定的趋同性,或同情于苦难,或赞美于善行。人力车夫形象在特定时期里被不同的作家反复描写或重塑,使之承载着特殊的符号内涵,具有了叙事文学母题的功能。这类作品的现实意义:关心劣势群体,同情弱小者,强调了“人”的发现,带有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正像周作人所指出的:“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⑩但此类作品大量集中出现也显现了其局限性,即注重社会表层问题的感性展现,忽视了对主人公内在世界的揭示。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作品反倒成了“人道主义”的传声筒,流于问题的表面而缺乏深刻性。因为人道主义本来就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海市蜃楼,“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⑪
(二)人性的扭曲与毁灭。20世纪30年代,“人力车夫”母题的作品着重从人性的角度着力探讨人力车夫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即展示了人性的扭曲、毁灭与社会存在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国内政权的反复更迭,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潮头不再汹涌澎湃,而客观冷静地剖析社会则成为作家们新的创作原则。因此,作家们不再把车夫当成自己人道精神的传声筒,而把车夫放置在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来发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力图表现人力车夫的精神向度及其悲剧性。因此,这一时期作家在创作上已超越了“五四”时期对车夫生活的简单、直观的表现,主题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卞之琳的《酸梅汤》写于30年代初,借一位车夫和卖酸梅汤老人的调侃,展示了各自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今年这儿的柿子,一颗颗/想必还是那么红,那么肿,/花生就和去年的总相同/一样黄瘪,一样瘦。”“只有你头上倒是在变/一年比一年白了。”时值三秋,他们的生意一样的惨淡,酸梅汤无人问津,车夫也无人理会,其心境都像那酸梅汤似的酸味儿,而且冰凉。这是灰暗时代对人情绪的浸染。
臧克家的《洋车夫》写出了人力车夫雨中等客的情景,着重表现其灰色精神特征。风雨之夜,车夫明明知道这样的恶劣天气,不大可能会有客的,却全然不顾,像一只水淋的呆木鸡一样,仍然固执地等待着。无独有偶,茅盾的散文《上海大年夜》也这样写道:“刚刚走出弄堂门,三四辆人力车就包围来,每个车夫都像老主顾似的把车杠一放,拍车上的坐垫,乱嚷着‘这里来呀!’而且似乎每一个暗角里都有人力车夫埋伏着,都在急急出动了。”在举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车夫却像饥饿的狮子伏在暗中伺机俘获猎物一样地争抢顾客,他们是一群失去自主生命力、没有方向感的“肉身”,疲惫地挣扎在社会边缘的“机会主义者”。
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无疑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小说通过对祥子“三起三落”人生奋斗的展现,客观、动态地揭露了旧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暗腐朽的政治制度。当然,祥子人生悲剧的形成与他的个人主义奋斗不无关系,但其悲剧根源还是那个病态社会使然,即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所造成的恶果,正像夏志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他克服了小说里列举的一切困难,他一定也会碰到另外一些,一样地也会打垮他。要是没有健全的环境,祥子所做的那种个人的奋斗努力不但没有用,最后还会心力交瘁。”⑫因而,只要那不合理的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存在,祥子就无法摆脱这种人生宿命的纠缠。
总的来说,30年代的人力车夫的作品强化了车夫个体意识和社会环境之关系,凸显特定时代因素是造成底层个体悲剧命运的最关键所在,带有很强的社会批判色彩,现实主义成分也有所加强。但这类作品也暴露了一致的局限性:即作家在展示人力车夫悲剧命运的同时,并没有理性地给其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仍然没有跳出感性的窠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反抗。40年代,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交通工具的多元化出现,人力车夫不再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这类题材的作品数量也急剧下滑,但其思想内容却更上一层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力求从民族解放的视点来昭示人力车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主人公顽强意志的赞美,无畏牺牲精神的弘扬是这类作品的主旋律。
随着“全民族战争”的深入开展,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下开始复苏。由于抗战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人力车夫题材的创作主题也随之发生了位移与转型,即作家开始观照人力车夫与民族存在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意识地理性表现人力车夫的革命情操与思想境界。因此,人力车夫的形象不再是社会历史舞台上的看客,他们在时代洪流的激荡中也渐渐觉醒,积极地融入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之中,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郑敏诗歌《人力车夫》:“举起,永远的举起,他的腿/在这痛苦的世界上奔跑,好像不会停留的水/用那没有痛苦的姿态,痛苦早已昏睡/在时间里,仍能屹立的人/他是这古老土地的坚忍的化身。”诗人把人力车夫描摹成古老民族坚强精神的化身,他多灾多难,历经世间苦痛,但他并没有被现实吓倒,反而愈挫愈勇,坚实地屹立在古老的神奇土地上。诗人最后发出“反省吧,反省吧”的呼唤,希冀用我们全体的手、全体的足,“去拔除蔓生的野草,踏出一条坦途。”只有底层民众反抗意识的彻底觉醒,担当起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才能踏出一条通向光明的坦途。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也写出了在国破家难之际,人民爱国意识的萌生和视死如归的反抗。作品中车夫小崔的形象感人至深,他誓死不当汉奸,行刑时更是体现出民族不屈的精神。作品中的情调也跳出了以往所呈现的廉价的同情、失望和沉闷,而取代之的是催人奋进的悲壮、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人力车夫作品的创作更加强化了政治因素的渗入,体现了作家创作的理性回归,文学的社会功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表现顽强民族内在精神的弘扬和泣血的呐喊,或表现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作家把人力车夫的命运放置于民族解放与自身命运的契合点上,去完成其精神的伟大蜕变,客观地反映了作家在这一母题作品中的知性表达。这正是“人力车夫”母题作品最具魅力的质素所在。
“文变染乎世情”(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力车夫作品随着时间、政治主流和文学主潮的变迁而不断发生转型,三个不同时段中的“人力车夫”母题内涵都有其内在的文学符号密码,但都没有离开过对“人”的发现,即从对“人”的个体生存的苦痛、人性美好操行的抒写,到对正常人性异化和毁灭的揭示,以及人生意义、自我价值实现的探索,始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在艺术上也日臻成熟。而这恰好图示了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
① 李大钊:《可怜的人力车夫》,《甲寅》1917年2月10日。
②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0日。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④ 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⑤ 守常:《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⑥ 《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0年6月17日。
⑦[美]马克·罗斯科:《艺术家的真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⑧ 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载《文学旬刊》第6期,1921年6月30日。
⑨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1922年7月10日。
⑩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5页。
⑫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