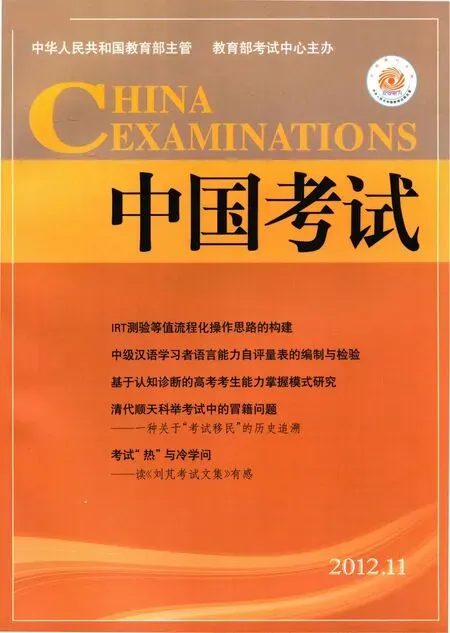清代顺天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一种关于“考试移民”的历史追溯
刘希伟
众所周知,科举冒籍现象自唐代便已出现,至宋明两代则相当普遍。清代,伴随着户籍制度的相对松动,人口流动现象越发普遍。在此背景下,由于科举录取率以及士子科场竞争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科举冒籍现象尤为普遍。而在1 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历代京师之地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普遍的冒籍应试问题。同样,终清一代顺天地区也一直是“冒籍渊薮”。不仅童试冒籍十分严重,且其乡试中也存在十分普遍的冒籍问题。关于清代顺天科举冒籍,之前有王洪兵的《清代顺天府科举冒籍问题研究》一文(载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以说已经作了较为专门、系统的探讨。不过,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仍可对其作进一步剖析。本文将在扼要阐释清代科举制原籍应试原则与寄籍应试之法的基础上,剖析其不同时期顺天科举考试中所存在的冒籍问题,尤其是拟对某些科年的冒籍案件进行尽可能深入、详细的挖掘与介绍,最后对于政府所采取的治理举措及其治理效果作一基本评估。
1 清代科举制的原籍应试原则与寄籍应试之法
在清代,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是科举制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中,原籍应试原则是要求考生在原籍所在地以本身所属户籍类别应试的原则。此一原则中包括两方面要义:其一为“原籍所在地”,即“原籍地”;其二为“本身所属户籍类别”,即“籍类”。在原籍应试原则中,考生同时必须遵行原籍地与籍类两个方面的规定,否则,违反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构成“冒籍”应试。就地域一维来看,原籍应试原则意味着考生必须在其原籍地参加科举考试。具体说来,府、县试一般在考生原籍所属之府、县境内进行。不过,考生在原籍所在地以本身所属户籍类别应试,仅是原籍应试原则的一般情形。在童试的各级考试中,包括府、县试以及院试,均存在原籍应试的特别情形。如府、县试中均存在“借考异地”的情形,而院试中也存在“调考”、“借考异地”的情形。由于在“借考异地”、“调考”中,考生一般仍是以原籍地所属户籍类别应考,且多数情况下是在“原籍地”所配置的学额内录取,只是考试地点与通常意义上在“原籍地”应试不同,因此可以视为原籍应试原则的特别情形。
在原籍应试原则之外,清代科举制最为主要一种的变通为寄籍应试之法。寄籍应试之法是专门针对流迁人口应考科举的一种政策规定。所谓寄籍,一般是指离开原籍所在地加入另外一个地区的户籍系统。清人吴荣光在《吾学录初编》中称,“他省人于寄居地方置有坟庐已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是为寄籍。”[1]“寄籍”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某一人寄居于原籍之外的其他地区,而是已经达到了某些条件之后正式入籍到了这一地区。寄籍应试,有时又称“入籍应试”。同时,寄籍应试并非仅指跨省应试,只要合法地跨州县应试便属于寄籍应试。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由于寄籍应试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入籍某一地区,因此寄籍应试的规定与入籍要求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清代入籍某一地区需要以置有田产、房产等不动产为必要条件,故寄籍应试首先也必须满足这些入籍凭证方面的要求。从年限上看,通常需要入籍达二十年以上,并且原籍实不可归,才可以在取具族邻担保等基础上向流入地政府申请寄籍应试。同样,在整个清代、全国各地这样一个宏大的时空范围内,由于各地具体经济社会状况、入籍条件不同,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寄籍应试条件的差异或者说变通之处。但就总体而言,清代寄籍考试多数情况下是按照这些规定进行,而与寄籍、冒籍有关的考试事件,也主要是按照这种“定例”要求进行裁决。
2 康熙时期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
在清代科举制下,由于考试竞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加之人口流动越发普遍而寄籍应试条件又相对较为严苛,于是出现了士子既不在原籍应试也不以合法的寄籍方式应试,而是通过非法冒充户籍至相对更容易录取的地区参加考试的现象,即科举冒籍问题;抑或是在真正人口流动背景下由于尚未完全达到寄籍应试条件便在流入地参加了考试从而被判定为冒籍应试的现象。顺天地区,尤其是作为其附郭县的大兴与宛平,由于属于“额多人少”、录取率相对较高的一类地区,加之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因此科举冒籍现象相当普遍。
顺治初时,全国不少省份或者尚处于战乱状态,或者战乱甫平,此时清政府对于南方士子在顺天寄籍应考的管制曾一度比较宽松。例如,顺治元年(1644)顺天地区曾设有“寓学”,规定外来游学者只要取具相关的凭证便可竞争“寓学”名额。顺治二年(1645)又规定从监生乡试中额内分拨三名给寓学生员。不过,同年便又停止了“寓学”。清政府深知设置“寓学”学额与中额的做法等于是为冒籍开禁,缺乏起码的可行性,因此而将其关闭。关于顺治时期的科举冒籍现象,所能见到的资料比较有限,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顺天地区不存在冒籍应试问题。考虑到冒籍应试是科举考试史上的一大顽症,而历代京师之地尤为严重,加之清王朝定鼎初期户籍管理还不甚规范等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在顺治时顺天地区便存在诸多的科举冒籍问题。
康熙时期,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相当普遍,相关的史料记载也远比顺治朝丰富。在此我们以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科与三十五年(1696)丙子科顺天乡试为例探讨这一地区的冒籍应试问题。
2.1 康熙十六年丁巳科顺天乡试中的冒籍应试问题
康熙十六年(1667)丁巳科顺天乡试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系缘于各地捐纳而开,因此只为贡监生而设,且无会试。顺天地区由于捐纳人数较多而单独开科。由于顺天地区为京师所在,各地士子多有寄籍、游学者往来其中,基于这一考虑,礼部认为“辟门宜广”,因此准许各省在京士子附试于此。同时,考虑到南北士子在科场竞争力上存在明显差异,为防止南北中式多寡过于悬殊采行了南北分卷制。榜发之后,因场中弊窦而议论四起,冒籍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御史范承勋所题关于惩治顺天乡试冒籍者一折,可以窥其一斑。“如今岁顺天乡试榜发之后,议论纷纷,臣因无确据,未敢轻渎天听。惟冒籍中式者,历历有人。”[2]据其所奏可知,此次顺天乡试中式者共计有36人,而籍属直隶者与非直隶者分别为11人与25人,二者所占比例分别约为31%与69%。非直隶籍的25人虽然并非全部属于冒籍,但多人属于冒籍中式。“及细询之,北卷中多系冒籍,有臣访问最真者顾用霖、宋宓、申珂、张登第系苏州人,陶熙、沈龙骧系浙江人。此数人中,有系现任京官之子弟者,亦有不系现任者。”[3]这里需要注意之处至少有三:一是在范承勋看来此6人仅为“访问最真者”,恐怕可能还有其他尚未完全确定、甚至是完全未被觉察的冒籍者;二是这里所举仅为已经中式者,其他与考但未中式者无疑更多;三是6人均为江南或浙江人。“至于未中监生中,尚有以南冒北者,亦当严察,勒令归籍。”范承勋认为,“父兄既在本籍,子弟舍近而就远,是诚何心也?”“盖准其入京闱,非准其冒京籍也”。其在援引魏裔介检举庚戌科进士宫梦仁冒籍之例的基础上,认为主考彭定求、胡会恩当负其责。尤其是考虑到范承勋所检举的6名冒籍者中,4名为江南籍,2名为浙江籍,而彭定求、胡会恩分别为江南常州人、浙江德清人,故认为属于考官明知故隐的情形。“及揭晓之后,顾用霖等俱系同乡之人,尚可推诿不知乎?明知而故隐之,其存心亦不可问矣!”[4]
该科顺天乡试尽管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然而借之亦可管窥这一地区的冒籍应试问题。
2.2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顺天乡试中的冒籍应试问题
康熙三十五年(1696),御史张泰交揭发了丙子科顺天乡试中的冒籍问题。“乃竟有非生非俊之徒,明系白丁,混行入场。其中有租赁空白,实收填为俊秀,假冒箱贯者;有实收亦真,张冠李戴顶替姓名者。中则补捐偿值,不中则租费无几。终南捷径,群相效尤。该部以京官印结为凭,京官以本人实收为据,遂至莫可究诘。”[5]榜发之后,一时满城风雨,物议沸腾。北皿字号中式举人,真姓名真籍贯者不过数人,其余皆属假冒。这还未计其他字号,而只是冒考北皿者便已如此严重。在张泰交最初的题奏中,所列冒籍“察访的确者”有12人。在后来康熙、吏部、礼部以及张泰交之间的往来文书中,确认属于冒籍中式者的有10人。具体情形如下:
冒籍者的供词很值得关注,虽多属假捏但却可以更加丰富、饱满地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形。其中部分冒籍者的供词如下:
吴廷桢、邵之政、杨国维、邵元龙、丁珍、卢轩、蒋玑供:我们并无改换姓名,租赁空白,实收填为俊秀,冒名顶替之处。我们因族人与母舅俱在北方居住,将我们过继为子,有十余年的,有八九年的,且北方现有田地、房产,俱在北方纳监。但系微贱之人,不知定例于北皿应考。

表1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顺天乡试冒籍北皿字号中式者统计
苏亮礼供:我是直隶故城县人,祖父产业现在故城县城南徐家庄,坟在郑家口御河边。我不是南方人,因从江南师传读书,所以我的声音像江南人的声音。[6]
礼部认为,吴廷桢、邵之政、杨国维、邵元龙、丁珍、卢轩、蒋玑均自认不讳,“南方人是实,有何辩处?”根据科场条例“籍贯假借者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的规定,应将吴廷桢、邵之政、杨国维、丁珍、卢轩、蒋玑照例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至于苏亮礼,礼部认为一是根据御史张泰交参本,苏亮礼实为江南人,本姓陈;二是“听其声音是江南人的声音,揆此故城县人是虚”,因此,亦应将其照冒籍例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7]另外的两名中式举人“王曰嘉”、“张英俊”,则早已闻风而逃,“顺天府及五城各呈称遍查无踪”。对于此二人,礼部称应先革去举人,至查获到日再将其脱逃之罪交与刑部。
以上处理意见均得到了康熙的同意。至于主考官曹鉴伦、张希良,均被降一级留任,为诸生出结的兵马司指挥俞允捷、蔺仙种则被革职。
同样需要注意,一是这10人仅是所被揭发并察访确切者;二是这还只是冒考北皿字号中的中式者,未中式者以及冒籍应考其他字号者尚未计入。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想见当时的冒籍问题实在是严重。
不过,其中的吴廷桢后来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时,吴廷桢等“迎驾于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吴中才子也”。康熙当场御试,并以“圣驾巡幸”为题,限江韵。吴廷桢应声曰:龙舟彩鹢动旗幢,圣主巡方至越邦。当时,康熙问侍臣“舟至何处”。对曰:已至吴江。吴廷桢乃续曰: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钦赐举人。[8]而据《国朝诗人征略》则有另一版本,即吴廷桢所赋诗为“绿波潋滟照船窗,天子归来自越邦。忽听钟声传刻漏,计程今已到吴江。”且在其说出前两句时,曾“思不能属,窘甚。”忽然听到钟鸣之声,遂而生情,并完成后两句。有人戏称鸣钟为“救命钟”。[9]两个不同的版本比较而言,似第一版本更易博得康熙的欢喜。吴廷桢尽管曾有冒籍前科,但终因其才华而被康熙钦此举人。后来其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登进癸未进士,殿试列二甲第五名。《茶香室三钞》又言“合一甲,则适符所梦名数”。[10]
之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科顺天乡试中,又有南方士子冒籍中式。“己卯京闱榜放,台臣言南人冒北籍应试,内有中式举人唐执玉、王昌等八名,牒公察治,公以士子获举甚难,且率土王臣何斤斤于此,访有入籍田土、户口、坟墓即不问。”[11]其中之“公”指直隶霸昌道按察司副使郎廷栋。这里的问题是,置有田土、坟墓等不见得就一定完全满足了寄籍应试的要求。据此可以说,对于冒籍问题,当时郎廷栋实际上并不那么关切。
3 乾隆时期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
从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乾隆时期有关禁止冒籍应试的条文相当密集,禁令一申再申,其中不少都是直接针对顺天地区的冒籍应试问题而出台的。
乾隆四年(1739)覆准,“从前冒籍顺天生员,除康熙六十年、雍正十三年勒令改归后,或仍有实系南人,认宗冒考,或本系南生重考入学者,统以一年为限,令该教官逐一详报学政暨顺天府丞,并许该生自首,均改归原籍。”[12]这一规定显然是针对当时以及之前冒籍顺天入学者的改归问题而出台的。从中可以看到,顺天地区的部分冒籍入学者属于已经在原籍入学的士子。亦即,某些南方士子已在其本籍地入学,之后或者出于增加乡试中式率的考虑,抑或者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再冒籍顺天入学,如此便造成了“两地入学,两地食廪”的问题。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来要求冒籍入学者改归原籍往往并不顺利,二来又不断有新的冒籍顺天入学、中式者。
乾隆六年(1741),顺天府府丞郑其储在一份奏折中道出了大兴、宛平两县冒籍丛生的部分原因。“臣查大兴、宛平两县,向来冒籍丛集,本地绅衿人户获其厚利,认为子侄冒籍,藉其门户以应考,虽易名改姓,而不以为嫌。又有贪污廪生需索多金,公然认保,钻营最密,牢不可破。”[13]由此可知,大兴、宛平的某些“绅衿之户”为获厚利而将外来冒籍者认为子侄,此是两县冒籍者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所在。绅衿之户,或者为退居在乡之官员,或者为生员,往往在地方社会有着较强的操控力,从而即使当地的某些士子明知其与外来冒籍者存在不法交易,却可能不敢告发。其次,某些廪生的非法承保是外来冒籍者能够成功冒籍与考的又一成因所在。郑其储十分注意冒籍问题的治理,从两县内查出了80余名冒籍者,均不收录。同时,其又称“但臣耳目有限,尚有不能周知者。”的确,此80余名冒籍者充其量只能说是已经被察觉者,很有可能还有部分漏网者。果然,后又有大兴县廪生于暿向郑其储控告其因受蒙蔽而为冒籍者“王习祥”出具保结的问题。“今据大兴县廪生于暿呈称,暿续保大兴县童生王习祥,原凭顺天府副榜贡生王启闻并原保廪生王芝共称,习祥系监生王贻蕙亲子,副榜贡生王启闻之嫡堂弟,暿允其保结,已蒙录取第四拾玖名。今访得王贻蕙并无妻室,焉得有子?查王习祥本系韩姓,江南长洲县人,王贻蕙认为子,明系假冒,大干法纪。暿访闻的确,不敢隐匿等情。”[14]此又为一起江苏籍士子通过冒入他人户下并改姓易名从而冒籍应试的案例。监生王贻蕙并无妻室却将冒籍者认作其子,副榜贡生王启闻将之认为嫡堂弟,而原廪保也一同为之隐匿,如此于暿便误信为真从而出结应保。
乾隆二十一年(1756),顺天举行了丙子科乡试,榜后发现其中的冒籍问题十分严重。“乾隆二十一年,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等题覆:冒籍例禁甚严,乃士子怀幸进之心,希图诡遇,而地方官日久视为具文,并不实力奉行,以致本科冒籍顺天者,转多于前。若非彻底清厘,弊不能绝。……”[15]同年,御史范棫士奏准,“顺天乡试立南北皿字号,分额取中,向有南人冒捐北监入试者,而本年乡试为最甚。查直隶一省,由顺天学政录科,士子冒捐北监者,州县官听从胥役蒙混出结,而学臣但凭结送录送。伏恳敕下部议,严行禁止,嗣后直隶州县不得蒙混出结,学臣不得滥行录送,违者严加议处。”[16]
从中我们可以获知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冒捐北监”从而得以应考顺天乡试是某些南方士子所采取的重要冒籍方式之一。二是,在这种“冒捐北监”中,州县胥役参与了舞弊行为。衙门胥役在州县行政的实际运作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州县官的某些看法与行为比较容易受其影响。如此,在胥役参与冒籍舞弊案件时,如果未出现土著考生“攻冒籍”的问题,则州县官十分容易被蒙蔽其中从而为冒籍诸生出结。学政则往往只根据州县所呈交的各种册结进行录送,对于其中的冒籍问题不易察觉。
同年,御史陈庆升又揭发南方士子冒入北贝字号应试中式的问题。试看以下内容:
(乾隆二十一年)又,御史陈庆升奏准,顺天乡试,南人冒北皿中式者固不乏人,冒北贝中式者,更不可数计。其中变更姓名,或托依本地门户捏称子侄,或冒认他人姓名,改填三代,甚至不肖廪生,于府县考时倩人豫考空名,临期以重利贿卖。至有原系本籍廪生,来此冒名现任职官子弟就近冒考者,迨乡、会中式后始赴吏、礼两部,具呈托言寄养外族,改归本宗。亦有竟仍榜姓久不归宗者,如现在翰林薛田玉之榜名田玉,丁田澍之榜名田澍,司员杜玉林之榜名王林,周际清之榜姓孙。又如华云□①原字左边一个“成”,右边一个“鸟”。、张孝泉,历科解元马锦昌、毛师灏、冯秉忠,马国本之本姓陶,余继绅之本姓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未有今科冒名冒籍之多者。窃思朝廷取士,欲得真才,先端士志,借此进身之始,诡计潜踪,隐姓冒名,冒认他人三代,恬不为耻,干犯科条,行险徼幸。且以国家抡才大典,为廪生网利之具,亦非所以正学校而重科场也。[17]
根据这一内容可以发现,南方士子冒考北贝字号是其另外一条比较普遍的冒籍途径。陈庆升认为,该科顺天乡试南方士子冒考北贝字号中式的人数明显多于冒考北皿字号者。这些冒籍者,“或托依本地门户捏称子侄,或冒认他人姓名,改填三代”。实际上,这也是冒籍应试者所采取的惯常方式。在冒籍顺天应试者中,还有另外一类特别方式值得关注,亦即外地廪生冒充现任职官子弟。此类冒籍者往往在乡、会试中式后再赴吏、礼二部呈请改归本宗。当然,也有中式后并不改归的现象。
此外,在顺天乡试中还有不少属于官员子弟冒籍中式的情况。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顺天乡试应试者中,龙承祖系云南师宗州知州龙廷栋之子,吴钟侨系广东灵山县知县吴至慎之子,张□②原字不清,特以“□”代替。系原任大兴县知县唐继祖之孙,三人均系冒籍中式。这仅仅是已经确查清楚者,实际上极有可能尚有官员子弟冒籍而未被察觉。“至本科冒籍举人,其父兄现任职官者,必不止此数人,应俟顺天府查明之日,俱照此议处。[18]前揭史料中所称翰林薛田玉、丁田澍,司员杜玉林、周际清,以及华云□、张孝泉、历科解元马锦昌、毛师灏、冯秉忠,马国本之本姓陶、余继绅等等,虽然并非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顺天乡试中式,也不能排除确有“寄养外族”中式者,但在陈庆升看来多数人属于冒籍。其中的籍贯不清而又未改归者均被施以了相应的处罚。“内除薛田玉、冯秉忠、马国果,业经改归江南原籍,毛师灏缘事斥革外,其现为职官者,应照违令笞五十私罪律,将翰林院丁忧编修丁田澍,户部丁忧主事张孝泉,于补官日各罚俸一年。刑部主事杜玉林、周际清,工部主事华云□,各罚俸一年。原任知县缘事降调马锦昌,举人余继绅,均于得官日罚俸一年,仍各令其照例改归。”[19]
区内外高校对“学校管理层不重视数据利用;未形成制度,决算数据利用率不高”等5个方面高校部门决算报表利用存在的问题认知数据对比分析如表8所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学士九卿议覆顺天府尹刘纶条奏贡监报捐一折时称,“此等捐纳贡监,其因应试投捐者,乃图力取科名,冒占试额,自当从严办理。然例由国子监分堂肄业,或由学政录科,其为数不过数百人,年貌语音不难立办,嗣后应专其责成,务令于肄业录科时,严加察验,以杜冒滥。倘仍前滥行收考,一经发觉,必将录送各官,严加议处。”[20]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捐纳贡监人数不多但冒籍应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亦即地方官稽察不力。
钱维城在“请改归冒籍生员疏”中认为,学政“惟有凭文录取”是大兴、宛平冒籍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提到了两县冒籍的某些缘由与背景,“但大兴宛平二县地居辇毂之下,为贤才聚集之所,是以大兴宛平入学率多外省入籍之人,缘本童之祖、父,或因经商而寄籍,或系仕宦而卜居,因而子侄得以援例考试。”[21]当然如果完全满足了寄籍应试条件,则不应视之为冒籍。若“系仕宦而卜居”则不合相关规定,因为清代禁止官员子弟随任冒籍。“官员在现任地方,令子弟等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22]钱维城认为,如果这些入学者果系童生,尚可毋庸置疑。但是其中不乏本系贡监生员或因实在不能回籍,或系希图获得两地乡试资格而重考入学者,如此则一人占两处学额,实属冒滥。如果原系食饩之生重考入学而再补廪,则又是以一人而顶食两处廪饩,更是大干功令。对于冒籍入学者,钱氏建议应照雍正八年三月兵部议覆顺天府府丞王□条奏顺天府京卫武生改归原籍之例,限文到两个月内许令各生具呈自首,准其存留一处衣顶。如以顺天府学生员考试,则将原籍贡监生员之处移咨除名;如以原籍贡监生员考试,则将顺天府学生员之处行学除名。倘若容隐过期不首,一经发觉则两处衣顶皆应斥革。[23]
4 嘉道时期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
从相关记载来看,嘉道时期的科举冒籍问题依然是相当严重。嘉庆十二年(1807)谕:“周廷栋奏大、宛两县童试冒籍较多,据实奏请查办一折。考试为抡才大典,而府县试尤为士子始进之阶,文风各省不同,学额亦定数不一,自应严禁冒籍,以遴实学而息纷争。京师大、宛两县,为四方文人萃聚之区,向来多有南省士子希图幸进冒籍应试者,历经科道条奏清查,而此弊相沿已久,仍未肃清。总由不肖廪保扶同徇隐,而特经派出之审音御史等又视为积习相沿,惧干嫌怨,仍不实力稽查所致。”[24]从中可以看到,大兴、宛平两县冒籍之弊长期禁而不绝的原因至少二,即一是在于不肖廪保扶同隐匿,二是在于审音御史惧干嫌怨,稽查不力。对此,上谕要求审音御史必须严行审音机制。
在某些年份,清查冒籍的确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如嘉庆十九年(1814),大兴、宛平两县一下子便清除了一百余名冒籍应试者。“据称本年大兴、宛平两县考试童生,冒籍甚多,经该县斥逐一百余名,尚未净尽,甚至廪保等于出结识认时有争执殴詈情事,现届府考之期,请旨查办,并将未经斥逐之冒考童生十八名,开单呈览等语。顺天大宛两县童试,向来冒籍者多,历经查办饬禁,近年弊混未除,致有廪保等互相争竞之事,自应详加厘剔,以端士习,著该府丞会同此次审音御史,将单开冒籍各童生,并此外有无蒙混应试者,逐一查明区别,照例核办。”[25]不过,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当时的清理究竟是否彻底。顺天地区的冒籍应试问题如同久治不愈的顽症,虽然可能在某一特殊时点清除了大批的冒籍者,但很快又会有大量的冒籍问题出现。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科顺天乡试中又存在大批的冒籍者,且有多人中式。可谓是“冒籍除不尽,科名吹又生”。“嘉庆二十三年谕,御史王允辉奏严禁顺天乡试冒籍一折,冒籍跨考,例禁綦严,但恐日久玩生,又复混淆滋弊,兹据该御史奏,本年顺天乡试,冒捐北监、冒入北贝中式者颇多,著顺天学政及顺天府尹严行查察,顺天寄籍生监,如有未满年限,及未经呈明冒考者,无论已未中式,一经查出,立即严参,以清户籍。”[26]
《异辞录》卷一之“潘鼎新会试不第”条又载:“道光末年,时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后,好为大言,訾北人之无学。某君得高第,辄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辈冒籍者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约中式之后,不为出结会试。”[27]晚清安徽籍的刘秉璋与潘鼎新,二人皆曾冒籍顺天应试,而刘秉璋最终还中式进士并成为清末名臣。[28]
再看以下史料:
这一史料明确提及了顺天乡试所存在的冒籍问题。其中所言“甚至本人尚在上海潜游,而姓名忽登中录者”,有可能是被冒名应试,也有可能是其本人雇倩枪手至顺天冒籍应试。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则其不只是单纯的冒籍跨考,同时还与雇倩或者说枪替交织在一起。在邓承修看来,如果各地能够严行复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考官滥行录取以及冒籍等各类舞弊问题。而在当时科场弊端积重难返、时局日益艰迫的社会气氛下,“可挽颓风”一语似乎已经发出了曾如日月星辰之周而复始的科举制行将走向覆亡的叹息。
道光三十年(1850)赵东昕条陈严禁冒籍跨考一折,主要就是由于顺天地区尤其是大兴、宛平两县的冒籍问题而引发。其所奏的部分内容为,“乡、会试中式后,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方准覆试。其无结不能覆试者,大约皆冒籍之徒,同乡不肯出结。是以未经覆试之举人、贡士,礼部从未准其改籍。第此辈巧于舞文弄法,既无结覆试,又无结改籍,势必向地方官营求详情,一经准改,必致纷纷跨考,愈无忌惮。”“大兴、宛平之廪生,半系冒籍,所保童生,非本籍者,十有八九。童生之冒考,皆廪保之利薮。”“大、宛两县之生员,半系他省之廪、附,往往借改籍名目,将功名卖与他人,给其弟侄,……”[30]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是贯穿于整个清代的科举考试中的。
鉴于同光时期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与之前的科举冒籍具有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故不再对之展开探讨。
5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的治理:在有效与无效之间
清代科举冒籍,不仅破坏了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以及寄籍应试之法的规则与秩序,而且滋生了诸多的社会腐败,同时还经常引发土客冲突与法律争讼问题。对于这一科场顽症,清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设置了诸如从童生互保到廪生保结,从族邻出结到教官出结,从州县出结到知府出结,从初试到复试等多层次的防治网络。这些规定是普遍性的,亦即全国各个地区的科举考试都必须贯彻,如此自然也适用于顺天地区的科举考试。
此外,针对顺天地区科举冒籍问题的防治,又存在一种特别的审音机制。所谓审音机制是指对应试的童生在经过了互保、派保之后,再进行核对口音,以判断是否为本州县人或是否已入籍达二十年。从制度层面看,顺天地区童试中的审音机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知县负责到府尹、府丞监督,再到专门审音御史的添派、回避与问责的过程,一个从相对简单不断走向细致、完善的过程。审音机制的这一发展过程,前后经历了至少七十余年的时间,大约到乾隆中后期时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31]这一过程既折射出了大兴、宛平两县冒籍应试问题的顽固性,也折射出了制度演化过程中的人为建构性。
那么,如何评价清代防治科举冒籍的政策与举措?其一方面可以说是有效的,因为如果缺失了童生互保、廪生担保、官员担保等相关防范机制,则冒籍问题必将更为普遍、高发。但另一方面,这种防治效果又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仅就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便可以认为,冒籍应试,尤其是跨区域性的冒籍应试,无疑可以说是清代相当普遍的一种科场舞弊现象。同样,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的治理,一方面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效果又十分有限。
清代顺天科举考试中之所以一直存在如此普遍的冒籍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廪保机制走向了异化。“廪生为胶庠领袖”[32],在各类生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童试中,廪保责任甚重,可以说冒籍治理中最被倚重的一项内容。同时,廪生不但权重,而且往往在地方社会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与操纵力。从清代科举史可以看到,只要有廪生作保,即使某一考生身价不清抑或存在冒籍情形,也同样可以与考。从以上关于顺天科举冒籍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为冒籍者作保反而成了廪保获利的一条途径,如此,廪保机制便大打折扣。而只要廪保机制出现问题,则其余的童生互保、教官出结、官员出结以及审音机制等等便经常无法奏效。既然童试冒籍相当普遍、严重,则冒籍者入学之后便比较容易获得参加乡试的机会,从而又造成了乡试冒籍问题。其次,清代对于冒籍应试者的处罚力度较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清代对于冒籍者的处罚一般说来仅是革去已获科名、发回原籍,而在乡会试中有时还进行罚科处理。这样的处罚力度不可谓不轻,且若只是因为冒籍而被除名,有时又可捐考或捐复举人头衔。至道光三十年,才开始规定扶同徇隐外来考生至大兴、宛平冒籍应试者的廪保在被斥革之后永远不准捐复。[33]再次,顺天科举冒籍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还与考生多冒考北皿字号以及多有官员子弟牵涉其中有关。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使得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复杂、棘手。
在清代顺天地区的科举冒籍问题中,多数情形属于民籍考生跨区域冒占民籍应试,但也有非民籍考生进行既跨籍类又跨区域冒占民籍应试问题。例如,彭鹏在出任顺天府三河县知县时曾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颁有“严饬儒童冒籍示”,其中便提到了“若旗户冒民,他处冒籍,夤缘勾引,为逋逃薮保无孤寒灰心改业之虑,特示于众曰,查投旗人混入民户应试,现奉部行处分最严”的内容。[34]不过,此类情形相对比较少见。此外,顺天府其他地区例如三河、良乡等县也都存在科举冒籍问题,只是不如大兴、宛平两县那么普遍而已。
总之,直隶虽然位居科举大省之列,但其土著士子文风较之江南、浙江等省士子相对落后,在科举竞争力上难以与之相抗衡。因此,不少南方士子尤其是江南、浙江等科举大省的士子,纷纷冒籍顺天应试,其中尤以冒籍大兴、宛平两地者居多。在顺天乡试中,冒籍者所冒字号主要是北皿字号与北贝字号。此外,冒籍者中又有不少属于官员子弟。清政府每次对于科举考试在户籍方面包括寄籍、冒籍等进行的规定,通常都是针对当时所实际存在的冒籍舞弊问题而出台的,抑或是针对某些两歧问题地方不能擅自做出决断而出台。这些规定在《钦定科场条例》、《钦定学政全书》以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官方文献中都有着较多、较为集中的反映,有时看似片言只语的简单规定,其背后所折射的往往都是数量普遍、情节复杂的冒籍问题。清代针对顺天尤其是大兴、宛平地区的冒籍问题采取了诸多的应对措施,禁令一申再申。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不少冒籍者为官员子弟,因此,这一地区尤其是大兴、宛平两县始终是外来士子尤其是江浙士子冒籍应试的首选地之一。清代顺天地区科举冒籍的治理效果,充其量只能说在有效与无效之间。
[1] (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二,《政术门·户籍》.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
[2] [2][3][4]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144、144、145.
[5] [6][7](清)张泰交《.受祜堂集》,卷之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542、544、544-545.
[8]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338-339.
[9] (清)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十九《,吴廷桢》,清道光十年刻本.
[10] (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三《,屡试第一不入学》,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11] (清)李绂《.穆堂类稿》,初稿,卷二十五《,湖南按察使郎公曁元配金夫人合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4.
[12] (清)昆冈,刘启端,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一,《礼部·学校·生童户籍》.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46-247.
[13] [14]《顺天府府丞纪录十四次臣郑其储谨奏为参奏事》.张伟仁.《明清档案》第10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A103-58(2-2),B58268.
[15] [16][18][19](清)杜受田,英汇,等《.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附载旧例》.文清阁编《历代科举文献集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704、2705、2704-2705、2704.
[17] [20][30][33](清)杜受田,英汇,等《.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冒占民籍例案》.文清阁编《历代科举文献集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675-2676、2676、2688-2689、2690.
[21] [23](清)钱维城《.钱文敏公全集》文集卷三,奏疏二《,请改归冒籍生员疏》.
[22] (清)杜受田,英汇,等《.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现行事例》.文清阁编《历代科举文献集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672.
[24] [25][26](清)昆冈,刘启端,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一,《礼部·学校·生童户籍》.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54、255、256.
[27] [28](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23-24、2-3、23-24.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〇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686-687.
[31]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17-18.
[32] (清)索尔讷等.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童试事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78.
[34] (清)彭鹏《.古愚心言》,卷八《,严饬儒童冒籍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23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