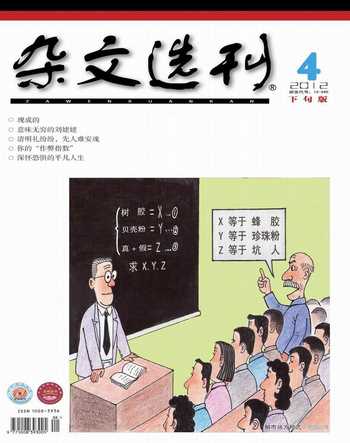造城与毁城
羽戈
我住的地方,离宁波天一阁并不远。黄昏漫步,大约十分钟可至。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只去过两次,还是陪远来的友人附庸风雅;大多时候,宁可过其门而不入。相比经数百年风雨摧折的天一阁,我更喜欢环绕它的陈旧、残破却错落有致的民居,与那些闲话说范家太公(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的白头老人脸上的淡然。
然而有一天,当我路过那里,稍一侧眼,却发现曾经像蔓草一样包围天一阁的民居不见了,那些用足以穿云裂石的宁波方言指手画脚的老人不见了,只剩一地残垣断壁,在冬天的阳光之下,如悲剧的冷寂布景。百米外,被庞大的阴影笼罩的天一阁愈加突兀,像一面孤独的旗帜。
此地即将上演的戏码,虽然冠以“历史文化”之名,其所谓“历史文化”却不过用来搭台,主角还是唱白脸的GDP。秦砖汉瓦重新堆砌出来的古典主义,只是彩绘的幕布;财神爷面前的袅袅香烟,构成了剧情的主流。
我从未想过,我与新闻的距离曾如此之近。
据《中国周刊》2012年1月30日报道,2011年12月18日晚,就在那块曾经的居民区,如今的废墟、无人区,未来的高堂广厦之上,在篝火、投影仪和广告灯的惨白光亮之下,这块土地的原住民们,自发演出了一场“废墟音乐会”。
“有那么一刻,我停止拍摄,静静谛听,”一位全程拍摄了这场废墟音乐会的摄影师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街坊音乐会,而是月湖西岸老街区的一场葬礼,一曲挽歌。”
谁的葬礼,谁的挽歌?新闻借摄影师之口追问:“同城之中,我们一直在相遇,一直牵手,可谁让我们城殇?”——“城殇”二字,触目惊心,哪怕我对这座城市并无火热的认同感,它终究裹住了我的肉身,犹如一袭暖衣,若它死了,寒意就来了。
八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
八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遽然消失,我甚至来不及追寻它们的背影;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迅速崛起,十里繁华,仿佛一夜长成,犹如变脸。只是它变幻太快了,以至丢掉了灵魂。
何止是宁波,今日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不是如此呢?一边毁城,一边造城,或者一边造城,一边毁城。城市改造的速度,超过了贪官落马的速度。有时你一低头,一转身,就沦为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更别提那些老灵魂了,往事成风雨,故园化废墟,他们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新闻的说法,那场废墟音乐会所奏鸣的只能是挽歌,原住民对历史的捍卫只能止于精神,深沉的爱只能止于怀念。
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从闭关锁国向国际化的过渡,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如钱塘潮起,不可阻挡。然而,由城市化所激起的社会内战同样不可阻挡。
也许,那一夜的挽歌,将随那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与那些瓦砾,那些掌故,消逝于城市化的潮汐。也许,旧地的老灵魂,将迷失于现代性的兴盛与危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日光之下,天一阁和范钦先生的石像,将更加孤独。
【原载2012年2月6日《中国经营报·时评》】